英語翻譯風格研究論文
時間:2022-03-05 05:08:00
導語:英語翻譯風格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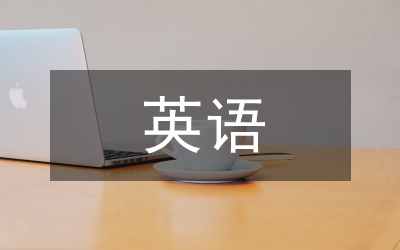
一、什么是風格
當代關于“風格”的定義,很多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劉重德先生把風格概括為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宏觀上而言,風格即文學觀點,譯者要盡量使譯作符合原文的思想,和原文一樣感人;微觀上而言,風格是語言學的觀點,是通過章、句、字的巧妙配合而成的。張今先生把它劃分為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劉柄善先生則把兩個方面合為一句話“風格是作家的個性經過一定思想文化陶冶后通過一定語言手段的自然表現”。徐有志在楊自儉主編的《語言多學科研究》(上冊)一書中將眾說紛紜的風格定義從文本角度上分歸四大類:一是指個人運用語言的特征,即個人的語言習慣。所謂“莎士比亞的風格”、“魯迅的風格”即指此。它常常強調個人表現出的特有的或首創的語言特點,所以廣而言之,它可以指一個作家對常規用法的“變異”。二是指集體運用語言的特征,即眾人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場合等情景下表現出的類似的語言習慣,諸如“建安風骨”、“美國式幽默”、“公眾講演風格”、“民謠風格”等。這個定義的重心不在于發話人的個人特點,而在于他們在特定場合表現出的類似特征。三是指有效的表達方式,即所謂“以最有效的方式講適切的話”,如大部分寫作教程中所提倡的那種“明白的”或“優雅的”風格。四是單指“好的”文學作品的一種特點,文學批評家們廣泛運用的諸如“莊嚴”、“華美”、“清麗”、“平淡”等風格。
二、風格的可譯性
盡管很多人贊同風格不可譯的觀點,更多的學者還是認為風格不但可以翻譯,而且非譯不可。早在1954年,茅盾就說過:“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這是一種很困難的工作。但是文學翻譯的主要任務,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實的復制出來,那么這種創造性的翻譯就完全是必要的。世界文學翻譯中的許多卓越的范例,就證明了這是可能的;在我國,像魯迅譯果戈里的《死魂靈》,瞿秋白譯普希金的《茨閃》和高爾基的一些短篇,也證明了藝術創造性的翻譯,是完全可能的。”英國詩人兼文學批評家MatthewArnold(阿諾德)也提出類似的見解,即要創造性地傳達原作的風格,雖然困難,但并不是不可能。他認為不能把傳達原作的風格排斥在“信實”概念之外,并且翻譯必須保持語言的自然性。
風格之可譯,在于它不是什么虛無飄渺的東西,它是可以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的。高健先生認為:“風格具有可譯性,可以譯出;不但可以譯出,而且能夠譯好,作到情詞相稱,不失原旨。”劉宓慶先生把它見諸形,稱為“風格的符號體系”——“風格的符號體系就是在原文的語言形式上可讓我們認識的風格標志。”“大多數風格標志是可以轉換的,其中包括形式標志和非形式標志。例如,語域標志、詞語標志以及為數不少的文法標志、章法標志及絕大部分修辭標志在雙語轉換中都可以做到比較理想的契合。”風格最終是要通過語言符號來表現的。所以再現原作風格時,不可忽視字、句、章的運用與配合。
不可譯論者常持有兩個觀點:一是譯者有自己的風格,因而不可能忠實地再現作者的風格;二是文字里有雙關、諧音、押韻等特殊結構決不可譯。下面本文將用一些實例來證明不可譯論者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一)幽默故事的翻譯
二戰后,一艘裝備精良的美國軍艦趾高氣揚地開進英國港口,船身上寫著“SecondtoNone”。當它停靠在碼頭時,卻發現旁邊停泊著一艘殘破的英國小炮艇,船身上寫著“None”。會英語的人一看一定會忍俊不禁。最先進的軍艦叫“SecondtoNone”(舉世無雙)而破舊的小炮船卻叫“None”(無名小輩)。有人把“SecondtoNone”譯為“天下無敵”,把“None”譯為“天下”,雖然沒有把“None”的字面意義譯出來,但譯文在整體上天然成趣,幽默的啟示義已揭示出來了。
(二)詩歌、對聯的翻譯
中國的古詩、對聯,由于大量地運用雙關、諧音與韻腳,并且要求每行字數相等,平仄相對。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要完全明白詩文的意思也不容易,要翻譯,且要譯出風格,那就難上加難了,然而也不是不可能。
錢歌川先生認為:“拆字為漢字特有的玩意,決不可能譯。”并舉了下面一個例子:
人曾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為婢,女又何妨成奴。
在這副對聯里,每句都有兩組可以拆分的字,可謂十分難譯。許淵沖先生將其譯為:
ABuddhistcannotbudintoaBuddha,
Amaidenmaybemadeahousemaid.
許先生巧妙地運用英語的押頭韻和相應的字形變化等手法,在視覺上、乃至聲音上再現了原詩的拆字妙處。
再看一個英文詩歌漢譯的例子:
Thedaysareintheyellowleaf,
Theflowersandfruitsoflovearegone,
Theworm,thecanker,andthegrief
Areminealone.
這是拜倫《這一天我滿三十六歲》一詩的第二節,楊德豫先生將其譯為:
我的歲月似深秋的黃葉,
愛情的香花甜果已凋殘;
只有蛀蟲、病毒和災孽,
是我的財產。
譯文基本按照原詩的用詞和形式。第一句以明喻替代原詩的暗喻,第二句根據語意添加“香”、“甜”二字,第四句則用一個暗喻譯原詩的直陳句;譯詩與原詩句式長短相當,形式相似,用韻也與原詩一致,因為abab式。原詩中的一切形象,如黃葉、香花、甜果、蛀蟲、病毒、災孽,一件不漏,可謂較好地保存了原詩的音、形、意三美,讀來確有拜倫的韻味和風格。
(三)小說的翻譯
小說的創作講究整體性,每一個細節的設計都可能影響到整篇小說的風格和布局,因此在小說的翻譯中,對每一處微小的翻譯都值得譯者注意。
《飄》是描寫美國內戰時期的一部暢銷小說,其中有大量美國南方黑人英語的實例,下面是黑人姆媽的一段話:
‘Soyouneedsaspangnewprettydressterborrymoneywid.Datdoanlissenjes''''rightterme.An''''youain''''sayin''''whardemoneytercomefrum.''''
作為一種英語變體,黑人英語擁有屈折變化的特征,但漢語并非屈折變化的語言,翻譯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另外從語言層次講,黑人英語通常有省略音素的現象,如/r/,/b/音等。還有音的輕化,如“de”實際是“the”這使黑人英語聽起來十分短促有力。
我們來對比這段文字的幾種譯文:
“那么你要新衣服是為了借錢用的了,這種事情俺倒不大聽見過,而且你又不肯說出向誰去借錢。”(傅東華譯)
“這么說你為了借錢需要一件新的漂亮衣服,這道理我覺得不太對勁。再說,你又不肯說出向誰去借錢”(陳良廷等譯)
“原來你需要穿一件簇新的漂亮衣裳去借錢。可這種事俺覺得并不怎么對頭。你又不直說錢究竟從哪兒來的。”(戴侃等譯)
陳譯中用“嶄新”、戴譯中用“簇新”來譯原文中的“pretty”似乎用詞過于正式了,因為一個黑人姆媽是不會說出這樣書面語味道較濃的話。從行為的口氣來講,黑人姆媽說話非常短促有力,這是因為黑人英語的固有特征以及她的特殊“歷史地位”。——她曾服侍了愛倫和斯佳麗母女兩代人。盡管如此,讀者還是可以聽得出她仆人的口氣。在上面三個譯文中,陳譯與戴譯聽上去像是平等人之間的對話,傅譯最為簡潔,比較貼近原文的語氣,也比較能譯出原文的風格。
上文作者從幽默故事的翻譯、詩歌與對聯的翻譯和小說的翻譯等幾個方面著手,選取了一些優秀的翻譯的例子,盡管不夠全面,但也充分說明了風格是可譯的。翻譯是一項極為艱辛的勞動,優秀的譯作要求存在于文字修養本身以外的修養,只有通過大量的實踐,才可能有所突破。
- 上一篇:翻譯能力分析與測試研究論文
- 下一篇:中英文化翻譯策略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