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藝研究中“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批判性考察
時間:2022-08-25 05:17:00
導語:對于文藝研究中“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批判性考察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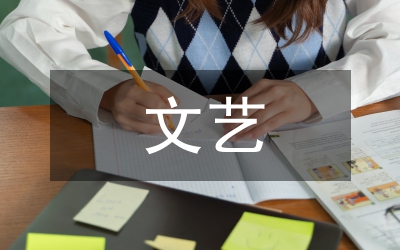
[內容提要]“主客二分”是隨西方近代認識論哲學發展起來的一種思維模式,它在當今我國不僅受到哲學界、同時也受到文藝理論界的質疑。本文一方面肯定了這種質疑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指出這種批評由于沒有看到它在現代、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發展,因而難免陷于片面。文章對這一理論在哲學分析、鑒別的基礎上,最后從哲學層面與心理學層面統一的觀點出發,聯系文藝活動實際,對它作了較為細致、具體的闡釋。
[關鍵詞]“主客二分”思維模式批判性
一
近幾年來,文藝理論界對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愈來愈持批評和否定的態度。這既有受當代西方哲學和文藝理論思潮影響的因素,也與主客二分思維模式本身存在的問題密切相關。這種思維模式本身到底存在著哪些問題?它何以會在當今西方哲學和文藝理論中引起人們那么強烈的不滿?在我看來,可能主要有這樣兩個方面:
首先,主客二分這種思維模式是由實體性思維的方式而萌生出來,在西方哲學史上,它的確立大概始于柏拉圖。在柏拉圖以前,古希臘哲人一般都把存在看作是一個過程,柏拉圖也承認具體事物是永遠不停地運動的,是一個生成的過程;但他認為“生成的事物是從某個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是不屬于生成的”1(P285),它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永恒不變的。亞里斯多德繼承了這一思想,還進而認定這種生成的基礎是某種實體,認為“其他一切都因實體而有意義”2(P420),從而把這種給定的實體看作是“第一哲學”所研究的對象。這樣,就形成了西方傳統哲學中的本體論形而上學。它的基本特點就是把世界本體看作是一種獨立于人而存在的、預成的、永恒不變的東西,哲學的任務就是致力于去探討世界的這種本原和始基。這就是一種萌芽狀態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這種觀點到了古希臘晚期被懷疑主義稱之為“獨斷論”,認為這種世界本體是不可知的。所以到了近代,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西方哲學家就開始轉換思維方式,把哲學關注的對象從世界本體轉向認識主體,即世界是什么轉換為我怎么認識世界。但這個認識主體在他們眼中同樣是一種孤立的、預成的實體,如西方近代認識論哲學創始人笛卡爾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時候,對這個口號作了這樣的解釋:“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點以便存在,也不依賴任何物質性的東西;因此,這個‘我’,亦即我賴以成為我的心靈,是與身體完全不等同的,甚至比身體更容易認識,縱然身體并不存在,心靈也仍然不失其為心靈”3(P369)。既然實體是不依賴于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那么這也就等于把“我”看作為一個脫離現實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認識主體,從而導致心與物,人與世界處于外在對立、機械分割的狀態,這決定了在他的認識論中,主體與客體完全是獨立二分的。所以,與古希臘的本體論形而上學相對,人們把笛卡爾的哲學稱之為主體論形而上學。這種傾向不僅影響到了整個近代認識論哲學,而且也波及到了西方近代的文藝理論。在許多作家和理論家看來,文藝只不過是作家對于外在世界的一種反映。在這里,世界是獨立于作家而存在的,而作家只不過是這個獨立于他而存在的外在世界的觀察者和摹仿者,看待一個作家才能的重要標志之一,莫過于他是否善于觀察。所以福樓拜教導莫泊桑:“對你所要表現的東西,要長時間很注意去觀察它,以便能發現別人沒有發現過和沒有寫過的特點”4(P237),巴爾扎克也認為:“只有根據事實,根據觀察,根據親眼看到過的生活中的圖畫,根據生活中得來的結論寫的書,才享有永恒的光榮”5(P145)。這種心物、主客對立的二元論的哲學觀和文藝觀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不僅受到意志哲學、生命哲學、現象學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如量子力學創始之一海森伯在《物理學與哲學》中認為“自然科學是自然和我們自身相互作用的一部分”,“這使得把世界與我嚴格區分開是不可能的”,“這或許是笛卡爾未能想到的一種可能性”)的質疑,而且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批判。如狄爾泰對于他所創立的“精神科學”(亦稱“生命哲學”,因為他所說的“生命”主要指“精神生命”)的對象作了這樣的界定:“在各種精神科學之中,研究主題都是真實存在的單元,都是作為處于內在經驗之中的事實而被給定的”,所以“都不可能把人當作處于其與社會進行的各種互動過程之外的東西來發現——可以說,都不可能把人當作先于社會而存在的東西來發現的”6(P53、55)。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也從“在世界中存在”這個基本主題出發,認為“在之中”不是一種空間性的外在關系,而是一種時間性的內在的“依寓”關系。“主體和客體因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實在的東西本質上只有作為世內存在者才是可以通達的”。從這一認識出發,他把傳統的主客二分看作是“一個不祥的前提”7(P74、244、73)來加以否定。這些批評對于西方近代認識論哲學的主客二分說而言,應該說還是比較準確的。
其次,由于古希臘本體論哲學把本體看作是世界的終極本原,一切科學的最終依據,是一種知識的對象,認為它只有通過認識、通過理智活動才能把握;因而都貶低其他心理活動來提高和崇揚理智。如柏拉圖認為理智在人的靈魂中“應占統治的地位”8(P297),亞里斯多德也主張“理智為了處于支配地位,為了認識,它一定不混雜的,必然地思維著一切,雜入了任何異質的東西,就會阻礙理智”9(P491)。這思想后來也為笛卡爾所繼承和發展,他在把“我”看作“一個在思維的東西”、認為只有在思維的我才能作為主體而存在的同時,還把數學的方法引入哲學研究,要求思維必須像數學推算一樣嚴格清晰,強調只有“我們十分明、十分清楚地設想到的東西,才是真的”3(P.369),因而就把哲學的方法確定為邏輯的推演。盡管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和排斥情感和想象;但認為那些由理智所得來的,“比起我自己那個落入想象范圍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部分來,我知道得要清楚得多”10(P370)。這樣,也就把心與物、人與世界的關系看作主要是一種科學認識的關系,就像海德格爾所批評的“通達這種存在者的唯一真實道路是認識,而且是數學、物理學意義上的認識”7(P119)。這種思想首先影響到了當時正在法國興起的新古典主義文藝理論,它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他的《詩的藝術》中就曾這樣告誡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獲得成功,“首先必須愛理性”,“理性之向前進行常只有一條正路”,“一切文章永遠只有憑理性才能獲得價值和光芒”11(P290)。這就不僅把主客體的關系,而且把主客體本身也給分割了,使它們都成了抽象的而不再是實際存在的人與世界。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意志哲學、生命哲學等哲學派別的興起,這種哲學觀和文藝觀也同樣受到猛烈的沖擊和否定。因為這些哲學都反對把世界的本體看作是一種凝固、抽象、不變的、永恒的實體,而看作是一種人的意志活動或生命活動,一種生成的過程,認為世界就是人的意志和生命活動的一種顯現,世界就是“意志的客體性,是意志的顯出,意志的鏡子”。因而,人就不僅是主體,同時也就成了客體和對象。對于這樣一個意志的直觀世界,意志的表象世界的反映,也就成了意志的一種“自我意識”12(P236)。由于這個意志的表象世界是個別的、鮮活的、變動不居的,相應地它也就是不可能以理智而只能通過“直觀”去進行把握。這樣,直觀也就成了“一切證據的最高源泉,只有直接間接以直觀為依據才有絕對的真理,并且確信是最近的,也是最可靠的途徑。因為一旦概念介于其間,就難免不為迷誤所乘”12(P114)。這種觀點后來也為尼采、狄爾泰、柏格森、胡塞爾、海德格爾等人所繼承和發展。如狄爾泰把“體驗”看作是把握和占有生命的方式,就是因為在于他眼中,生命是一個無法通過觀察去把握的一個鮮活的有機整體,所以他既反對理性主義離開人的具體存在,把人看作僅僅是一個“在思想的東西”,也不贊同經驗主義“從那些感覺和表象出發來構想人”,認為這樣的理解“都完全是抽象的”,“就像從各種原子出發所構想的人一樣”6(P202)。這思想得到了海德格爾的積極肯定,說“他從這種生命本身的整體出發,試圖依照生命體驗的結構網絡與發展網絡來領會這種‘生命’的‘體驗’。他的‘精神科學的心理學不愿再依循心理元素與心理原子制定方向,不愿再拼揍起靈魂生命;這種心理學毋寧以‘生命整體’與諸‘形態’為表象的’”7(P58)。這些言論都向我們表明了,人作為一個知、意、情統一的有機整體,是無法被抽象為僅僅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的,他與世界所發生的除了理智的、認識的關系之外,還有意志的、情感的關系,包括直覺和體驗在內;片面地強調理智,無視甚至排除直覺和體驗,就等于這個生命整體給分解、割裂了,這是不可能說明人與世界以及主體與客體關系的整體特性,特別是文藝活動中的主客體關系的。
從上述初步分析來看,我認為自意志哲學、生命哲學以來,西方許多哲學流派對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的分析和批判,有不少具體意見都是正確的、是深中肯綮的。但是,是否因此說明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就一無是處,就應該全盤予以否定和拋棄了呢?這結論恐怕還為時過早。因為我覺得當海德格爾等人把主客二分看作是哲學的“一個不祥的前提”的時候,他們似乎不應有地忽視了、或沒有看到這樣兩點:一、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出現,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歷史進步的積極成果。在早期希臘哲學中,哲學與日常意識和神話意識是未曾分離的,而在“日常意識和神話的水平上,是沒有認識論上的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的”,“世界、宇宙是作為完整的、與人統一的東西而出現的”;直到希臘哲學的古典時期,特別是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世界劃分感性和理性兩個世界之后,才開始萌生了主客體的意識13(P9—14)。這種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產生表明人與世界開始從原先混亂的狀態中分離出來,把世界當作自己認識和意志的對象,由此使得人的活動開始從自然的狀態進入文化的領域,從而使得社會得以發展、人類得以進步。所以,沒有主客二分,也就沒有現代的科技文明。盡管主客二分的理論本身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科技文明由于資本主義的片面利用,也產生了許多負面的社會效應,使原本作為人類文明的成果反過來變成了奴役人的異已力量。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此把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不加分析地全盤加以否定,而應該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之進行改造。否則就等于否定了人類文明的成果,把人重新引向愚昧、原始、自然的狀態。二、主客二分理論本身也是在發展的,自19世紀中葉以來,就已逐步開始從笛卡爾的思維模式中擺脫出來,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哲學著作中,對于主客二分的研究更有了長足的進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引論》中在談到西方近代科學的思維方式時曾經指出:它“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具體的聯系去進行考察,……這種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移入到哲學中來之后,就造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看不到任何事物之間,包括主客體的關系“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14(P60—62)。這就說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于主客體關系的認識已不同于笛卡爾等人,把它們看作既二分對立,又能互相滲透的,這是對主客體理論研究的一大推進。這種對立統一、相互聯系的主客體理論,后來在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具體化。但由于海德格爾等人自身視野和思維方式的局限,使得他們對主客體理論的批判還只是停留在以笛卡爾等人的思想為對立面的認識水平,而無視它在現當代的發展。這就不僅使得他們的理論不可能真正達到時代的高度,而且還不可避免地帶有許多明顯的片面性和偏狹性。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主客體理論的時候,我覺得就不僅存在著一個超越笛卡爾,而且還存在著一個超越海德格爾的問題。
二
要實現這一目標,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明的方向是值得我們遵循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主客體理論研究方面到底作出了哪些貢獻、取得了哪些進展。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人的活動時曾經指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這是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15(P53),使人的活動有了自己的對象,從而開始形成了主客體的二分對立,并確立了人自身在活動中的主體的地位。這表明馬克思創始人是接受并堅持以主客體的理論來分析和考察人的活動的。
但是與笛卡爾等近代哲學家不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是把主客體看作是兩個預設的、彼此孤立而存在的實體。他們把實踐的思想引入哲學,認為不論主體還是客體,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和分化出來,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豐富起來的。從客體方面來看,與直觀唯物主義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它作為人的對象世界,不是外在于人而獨立存在的、與人不發生關系的甚至處于對立狀態的自然,“不是某種開天闊地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始終為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6(P48)。這表明“只要有人存在”,亦即在人的活動世界里,“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互相制約”16(P21)。因此,在活動過程中,人們所面對的都不是本然的自然,外部自然只有通過人的實踐與人發生關系與聯系之后,才有可能成為人的對象,同時也決定了“人的思維最本質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是單獨的自然本身”17(P551)。人只能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他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中。從主體方面來看,人作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的發動者和承擔者,也不同于舊唯物主義哲學家眼中的那種自然狀態的人,同樣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是因為一方面,當人“通過這種活動(按:即指實踐)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18(P201—2)。所以“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對象而存在,由人化的自然是才產生出來的”15(P83)。而另一方面,在實踐過程中所結成的人的交往活動,又將歷史和人類的文化成果轉移到個人的身上,使得人的活動過程同時也成了人自身社會化的過程,成了對于人類文化的實際的掌握過程,從而使“單個人的歷史”同時也成了“他以前或同時代其他人的歷史”的一個縮影19(P515)。因此對于人來說,只有當他掌握了人類社會實踐過程所積累起來和積淀下來的思想、智慧和能力之后,他在活動中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主體。這都說明,在馬克思主義那里,主體與客體已不像在笛卡爾等人的眼中那樣,是孤立的、預成的、一成不變的、外在對立、機械分割的;而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和分化出來的,是互相關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的,“主體是在認識和改造客體的過程中,在對客體的關系中獲取自己的規定的,活動的客體怎樣,它的主體也是怎樣,反之變然”13(P73)。正是主客體之間這種互滲互動的關系,推動著主客體的關系隨著人類的實踐而不斷地發展。所以它們的關系不是抽象的、一成不變的,而總是歷史的、具體的。這樣,就從根本上與直觀唯物主義和思辨形而上學劃清了界線,為我們對主客體關系的正確解釋提供了存在論的前提。
基于從上述存在論意義上對主客體理論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在認識論的主客體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也提出了與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完全不同的原則,這些原則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近代認識論哲學一般都把認識看作是一種單向的活動;經驗主義視認識為主體對外界刺激的消極的接納,認為:“一切知識都只是從感覺獲得的”20(P395)。“我們所具有的大部分觀念的這個巨大的源泉是完完全全依靠我們的感官,并且通過感官而流到理智的,我把這個源泉稱為感覺,”21(P450)。而理性主義則認為認識源于人的一種理性觀念,認為“我的本性具有一種先天所賦予的完滿性”3(P375),所以“心靈的一切觀念都必須從那個能夠表示自然全體的本原和源泉的觀念中推導出來,這樣,這個觀念本身也就可以作為其他觀念的源泉”22(P413)。可見這些思想都是以主客體分裂為特征的。與之不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則把認識看作是主客體交互作用的產物。他首先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把一切意識看作都是對存在的一種反映;但又認為這種反映不是直觀的、消極的,認為“從前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就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23(P.16)而這種從“主觀方面去理解”的思維方式,正是理性主義的一大特征。它們反對把認識看作只是個人感覺經驗的成果,而認為是“由于一個比我更完滿的本性把這個觀念放進我心里頭來。”3(P375)因而認識“必須首先有一個真觀念存在于我們心中,作為天賦的工具”,認識的“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我們如何指導心靈,使它依照一定真觀念的規范去進行認識”22(P412)。這樣,就對經驗主義、直觀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從根本上來了一個顛倒,認為認識不是主觀符合客觀,而是客觀符合主觀,即它總是由主體在某種現有觀念指導下對于客觀事物進行選擇、整合、同化、建構的結果。這實際上是以唯心主義的語言說出了認識對于由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主體現有經驗和思想模式的依賴性,這思想顯然要比直觀唯物主義包含著更多深刻的真理成分。這我想就是馬克思批評直觀唯物主義“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的主要原因。但是馬克思同樣不贊同理性主義,認為它“抽象地發展了”這種認識的“能動的方面”23(P.16)。而所謂“抽象地發展了”,以我之見,就是指理性主義在正確地指出了認識必須要以主體自身的現有觀念作為工具的時候,卻認識不到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和根源,認識不到它本身就是由經驗整合、提升而來,是人類實踐的產物和社會歷史的成果,并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而錯誤地把它看作是一種先天的、天賦的東西。這樣不僅使本末顛倒,而且也把問題抽象化了。這就鮮明不過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是一種既不同于直觀唯物主義又不同于思辨形而上學的、主客體既二分又統一、既對立又互滲的認識原則。
其次,與近代認識論哲學不同還在于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現實的歷史的人”16(P50、30、48),而非近代哲學家(包括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內)所理解的那種與社會歷史分離的抽象的人。所以,對于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就不應該僅僅歸結為認識的關系,甚至即使是認識的關系,也不等于完全是一種抽象的理智關系;而認為人是“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因此,正像人的本質規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實的關系也是多種多樣的”15(P80、81)。正是從這種整體性的思想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反對傳統的德國思辨哲學把人看作是一種“絕對的理念”,一種“無人身的理性”,認為“思辨哲學家在一切場合談到人的時候,指的都不是具體的東西,而是抽象的東西,即理念、精神等等”24(P7)。這些人都是“從天上降到地上的”16(P30)。而且對于英國近代唯物主義日趨理性化的傾向也曾作過尖銳的批判,如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認為英國唯物主義“在它的第一個創始人培根那里,還在樸素的形式下包含著全面發展的前芽,物質帶著詩意的感性光輝對人的全身心發出微笑”,但“在以后發展中變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鮮明的色彩,變成了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類了。為了在自己的領域內克服敵視人類的,毫無血肉的精神,唯物主義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當一個禁欲主義者。它變成理智的東西,同時以無情的徹底性來發展理智的一切結論”24(P163—164)。由此可見,在認識論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雖然不像狄爾泰等人那樣從心理學的角度,從體驗的心理關聯的角度來論證生命的整體性,而始終堅持從哲學的層面上來探討認識活動中的主客體的關系問題。但又始終認為主體作為現實的、歷史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不是一種“無人身的理性”,而總是在一定的需要、動機、目的、愿望參與下從事活動的。這就使得在這種活動中所形成的主客體關系的內容不可能是純思辨、純邏輯的,它必然還包含有感覺和體驗、意志和情感的成分;所以在反對形而上學、反對科學主義、反對工具理性,在維護人的存在的整體上方面,卻有著共同的致思方向,這也是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反“異化”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對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存在論和認識論方面所開展的這些關于主客體關系的內容豐富的論述,迄今為止在文藝理論界似乎很少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至于前蘇聯哲學、心理學中對之所作的一些有價值的研究和闡發,那就更遠在人們的視野之外。這就使得我們今天在主客體問題的認識上仍然沒有擺脫海德格爾的批判視域,還僅僅停留在以笛卡爾思想作為自己理論的對立面的水平,這就限制了我們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深入開展和準確把握。
按照馬克思主義這種對立統一的主客體理論來審視文藝,那么,在我們看來,文藝的對象就不應該看作是一種獨立于作家而存在的外在世界,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實踐的產物,帶有作家思想人格、人生經歷的鮮明的印記。而文藝創作也不只是作家對于現實生活的簡單記錄,他總是以自己的全身心,亦即以知、意、情統一的人投入對世界的把握和加工之中。這就決定了文藝所反映的不僅只是發生在作家周圍與他自己的人生經歷須臾不分離的活生生社會現實,而且作家也不可能僅僅依靠認識活動,以思想、概念的形式去進行把握,而只能以情感體驗的方式去與之建立聯系。情感總是帶有很大的直覺性與無意識性的,它不僅未經概念的分解,而且往往將主體自身融入對象,并按照自己個人的方式,根據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感受來對世界作出反映。所以它所把握并向我們所展示的總是一種整體的、鮮活的、原初形態的東西。但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情感體驗是直感的,一般是未經理性的分析和認知的,所以往往又免不了帶有某種淺表性和朦朧性,因而還需要尋求與理性的結合,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這樣一種主客二分與互滲統一的結晶。這種統一往往以兩種方式實現:一是過程性的。狄德羅、華滋華斯、黑格爾等都談到這個問題,流傳最廣的就是華滋華斯所說的:“詩起源于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25(P22),它表明在激情狀態下人的意識水平是很低的;只有等到激情過后,再對自己當初的情感進行一番回味,經過比較理智的態度去分析、評判和整理之后,才能被之納入一定的藝術形式,并得到比較完美的藝術表現。二是同步性的。如一些即興之作,雖然就一時的感受揮毫成篇,但有許多之所以能成為千古名篇、廣為流傳,實際上是以作家自身長期的情感的陶冶、人格的磨煉為前提的。我國古代詩論十分強調作家作詩要以自己的“胸襟”或“襟袍”為根基,如葉燮說:“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辯以出,隨遇而生,隨生而盛”26。沈德潛也說:“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步真詩”27。所以,在文學創作中,作家的情感與理智的關系不論以哪一種形式出現,本質上都是主客二分和合一的辯證統一。當然,在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中,也有主張排斥理智的介入,完全憑直覺、體驗、非理性、無意識來進行創作的,如意識流小說,超現實主義詩歌等等,但這種作品到底能得到多少人的欣賞和認同,它的發展前景又將會怎樣,都是一個有待歷史檢驗和證明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此為依據來否定文藝創作中創作主客對立而又互滲的這一普遍原則。
三
以上,我們主要還只是從哲學的層面上來說明文藝創作中主客對立與互滲的辯證關系。但是人與世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有各種形式,在不同的形式中,它們的表現方式和形態都各不相同,在理智關系中,主導的形式是二分的;反之,在情感關系中,主導的形式則是合一的。由于在文藝創作中,作家主要是以審美情感為中介與世界建立的關系的,以致人們常常抓住這種特殊的現象來否定文藝活動中的主客二分的原則。這在某種意義上就犯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批評的:以“經驗的事實”來解釋“深奧的哲學問題的”錯誤16(P.49)。但反過來,我們也不能無視這些經驗事實的存在,以及它在文藝理論研究中的價值,因為文藝活動總是在現象的、經驗的層面上進行的。所以,只有當我們把哲學層面上的研究貫徹到經驗層面上去,把文藝活動中的這些經驗現象說透了,我們的哲學探討才有意義,我們的文藝理論也才不致于滿足于演繹哲學而獲得具體而充實的內容。這就要求我們在探討主客二分思維模式時,不能把目光僅僅停留在哲學的層面,還應該與心理學層面的研究結合起來。在主客體關系的問題上,哲學層面研究與心理學層面的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哲學研究的是社會主體、類主體,而心理學研究則是個人主體,如同狄爾泰所說“心理學的對象始終不過是某種個體而已”6(P55)。而在這兩個層面之間,心理學層面的研究無疑應該以哲學層面的研究為基礎和前提,如同對于個體的人的認識必須以對類的人的認識為基礎和前提那樣。因為一切個體的、心理活動的形式,都只有按照人是社會、歷史、文化的人的觀點,才有可能對它作出正確的解釋。所以對于兩個層面的關系,我們必須要以一種辯證的觀點來進行理解和把握。
下面,我想就通過對情感活動與理智活動的比較分析,來看看在心理學層面上,這兩者的主客體關系到底有哪些具體的特點和區別:
首先,理智活動(亦即思維活動)的目的是在感覺和表象的基礎上,通過概念、判斷、推理,來認識事物的客觀屬性。盡管理智活動的客體和主體都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由實踐活動分離出來的,從哲學層面上看,兩者都既是對立又是互滲的;科學研究同樣也證明了認識總是在一定的“范式”和儀器為中介而達到的,它不可能做到對事物作純粹的客觀的描述,而不可避免地總是要帶有某種主觀的印記。但若是把它們看作一種心理活動,從心理形式的方面來看,那總是處于二分對立的狀態的,是一種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研究者和被研究對象的關系;否則就無法得到對于事物科學的認識結論。而情感狀態卻與之不同,因為情感是具有彌散性的,所以在情感關系中,一旦當主體為某一對象所打動而產生某種情感之后,反過來他又會把自己情感移入到對象,就像叔本華所說的“自失于對象之中”12(P.250),并在與對象進行交流過程中使自己的情感不斷地得到強化,以致有些作家在情感狀態中由于自己“自失于”對象而分不清他想象的世界與現實的世界的區別,把自己虛構的人物不僅當作生活在他周圍世界的實有的人物那樣,為他們的命運、遭際傾注著自己全部的同情,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小說《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中所說的:“我同我的想象、同我親手塑造的人物共同生活著,他們好像是我的親人,是實際活著的人;我熱愛他們的,與他們同歡樂,共悲愁,有時甚至為我的心地單純的主人公灑下最真誠的眼淚”。甚至有時還由于“自居心理”的作用,把自己喜愛的人物當作自己本人,去經歷他們的苦難、分享他們的喜悅,如同福樓拜在描寫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殺時那樣,自己也感到“一嘴的砒霜味,就像自己中毒一樣”,把吃下去的晚飯也“全嘔出來”28(P137),以致描寫死亡,也像愛侖堡所說的,就“意味著試著自己去死”29(P245)。盡管這種主客融合的狀態一般說來都是經由作家理性加工之后所重新返回到的情感無意識狀態,與原發性的情感不同,其中已經滲透著理性的成分,帶有作家態度和評價的印記;但就心理形式上來說,卻不能不說是主客合一的。
其次,理智活動的目的既然是為了認識事物的客觀屬性,所以在理智活動中,作為認識主體的人也就被分化、析離成為一種思想的工具,一個像笛卡爾所說的“在思維的東西”。盡管從哲學層面上看,我們認為這種認識主體不是抽象的,既非理性主義所理解的抽象的類主體,也非經驗主義所理解的抽象的個人主體,而是歷史地形成的,有著具體社會歷史的內容的人。因為人的思維活動是“離不開人類所積累的知識與他們所形成的思維活動方式的”,“每個單獨的人只有在掌握概括地反映社會實踐經驗的語言、概念、邏輯時,他才能成為思維的主體”30(P16—17)。這說明思維活動包括它的主客體在內,都是帶有社會歷史的性質的,它不僅在實踐的基礎上產生,而且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就心理形式而言,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總是以普遍的、類主體的身份而出現的。不管在具體的認識活動過程中,作為認識活動的發動者和承擔者的個人懷有怎樣強烈的個人欲望和情感去投入這一活動,但這種欲望和情感無論如何是不能具體地介入到對客體的認識和評價的,否則就不可能獲得客觀的、科學的結論;這同時也決定了認識活動的成果一般不是以意識的個人形式,而只能是以意識的社會形式而呈示,通常是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方式來加以表述的。與之相反,在情感狀態中,主體既不是以抽象的類主體,也不是以抽象的個人主體的身分,而是以具體的社會歷史生活中的個人主體和身份而出現的。這是由于情感作為一種主體對客體的某種態度和體驗,它的產生總是以客體能滿足主體某種需要為前提條件的,而人的需要總是現實的,是受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的。這就決定了人的情感不同于動物的情欲,都有著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但就它的出現形式來說,卻總是當下的、即時的,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產生的,并受著在這一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各種心理關聯所支配和調節。這就使得它不像在理智活動中那樣,通過把對象進行分解來提取概念,而總是在多種關系和聯系中反映著客體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決定了情感的內容總挾帶著意識的原始狀態的全部豐富性而呈現在人們心目之中,它不僅是整體的、鮮活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復的,不是為概念所能窮盡的,而只求助于感性形象來加以表現,就像黑格爾所說,“藝術之所以抓住這個形式,既不是由于它碰巧在那里,也不是由于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形式可用,而是由于具體的內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實在的,也就感性的表現作為它的一個因素。”31(P89)也就是說,它只有通這種感性的方式,才能使情感狀態中的這種復雜而獨特的心理關聯,獲得完整而真切生動的再現。
再次,理智活動所要達到的認識成果由于凝結在概念、判斷、推理之中,所以一旦形成概念、判斷、推理,認識活動也就相對地告一段落;雖然認識的目的是為了實踐,它的真理性也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得到確證。但實踐作為一種意志活動,它的特點就是按照主體一定的需要和目的,采取和利用一定的手段,通過改造對象世界,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它同樣是一種主客二分的活動。這決定了理智活動始終是在主客二分的狀態中進行的。而在情感活動中,由于主體情感的移入客體,不僅使得客體從外在于作家的客觀存在轉化為作家自己情感的載體,使情感的對象同時成了顯示在對象中的作家的自身,如同費爾巴哈所說的:“對象是人的顯示出來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客觀的‘我’。”32(P470)這樣,就使得在理智狀態下的主客體的二分趨向于合一,這才會出現我們前面所說的作家有時往往分不清現實世界與他的虛構世界的區別的情況。而且還由于“情感只是向情感說話”,“情感只能為情感所了解”,“情感的對象本身只能是情感本身”32(P472)。因而它的活動也就不像在理智關系中那樣,無視客體獨立存在和自主性質,即把客體只是作為一個被認識的對象,使它不僅是被動地存在著,而且還必然要對之進行知性的分解。這種分解對于鮮活的生命個體來說實際上是一種宰殺,以致尼采認為“理性是摧殘生命最危險的力量。”33(P344)這樣,客體當然就不可能作為獨立自主的生命個體而自由地存在了。而在情感關系中由于客體是作為生命現象而存在的,它是自主的、獨立的、不是為人所能隨意支配和控制的,就像許多作家在談到自己筆下人物的命運和生活道路時所說,都是隨著情節的發展,人物自己所作的一種選擇,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巴金談到:“我開始寫《秋》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淑貞會投井自殺,我倒想讓她在15歲就嫁出去,這倒是更可能辦到的事。但我越往下寫,淑貞的路越窄,寫到第三十九章(新版第四十二章),淑貞向花園跑去,我才想到了那口井,才想到淑貞要投井自殺,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34(P.242)。這樣,就使得情感關系不像在理智活動中那樣,直接以主客體的方式建立關系,而只能是以一個情感主體與另一個情感主體之間所開展的交流為中介。這決定了作家創作不可能完全是獨白式的,它不僅時時刻刻的在與自己筆下的人物開展交往,同時還是與作家心中潛隱的讀者所進行的一場對話。就像黑格爾所說的“藝術作品不是獨立自足地存在著的,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一句向起反應的心靈所說的話,一種向情感和思想所發生出的呼吁。”31(P89)。他總是要向讀者發出召喚,通過讀者的閱讀把這種交往擴大到與整個社會之間。現代解釋學和接受美學在這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進展,它們把閱讀看作是以作品為中介所開展的作家與讀者的一場對話,并通過對話來達到“從你中發現我”的目的。35(P110)這就需要我們把主客體的理論從縱向的主客體的互動關系進一步擴展到橫向主體間交往關系的研究,這些內容是傳統的主客體關系理論所無法涵蓋的。
以上事實都說明在文藝活動過程中,主客體的關系是很復雜的,因而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就不能只滿足于哲學的演繹,還應該從心理學的角度,借鑒心理學研究的成果來對之作出具體分析。當然,若是以此來否定哲學的一般原理的普遍指導意義,也會失之偏頗。所以,我認為要對文藝活動中的主客體關系作出有說服力的闡釋,關鍵問題就在于我們在研究中如何有效地把哲學與心理學這兩個層面辯證而有機地結合起來。
1柏拉圖:《斐德羅篇》,《古希臘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古希臘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3笛卡爾:《談方法》,《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4莫泊桑:《論小說》,《歐美古典作家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5巴爾扎克:《〈古物陳列室〉初版序言》,《巴爾扎克論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6狄爾泰:《精神科學引導》,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7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三聯書店1981年版。
8柏拉圖:《國家篇》,《古希臘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9亞里士多德:《論靈魂》,《古希臘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0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古希臘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1布瓦洛:《詩的藝術》,《西方文論選》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12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現的世界》,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3帕爾紐克主編:《作為哲學問題的主體和客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14恩格斯:《反杜林論·引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5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0霍布斯:《論物體》,《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21洛克:《人類理智論》,《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22斯賓諾莎:《理智改正論》,《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23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5華滋華斯:《〈抒情歌謠集〉序言》,《19世紀英國詩人論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26葉燮:《原詩》。
27沈德潛:《說詩睟語》。
28福樓拜:《致喬治·桑》,《譯文》1957年第4期。
29斯托洛維奇:《審美價值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30列昂節夫:《活動·意識·個性》,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31黑格爾:《美學》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32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下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3尼采:《看哪,這人》,《悲劇的誕生》,三聯書店1986年版。
34巴金:《談〈秋〉》,《巴金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35伽達默爾:《美學和解釋學》,《哲學解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