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美本質觀研究論文
時間:2022-03-15 04:15:00
導語:美學美本質觀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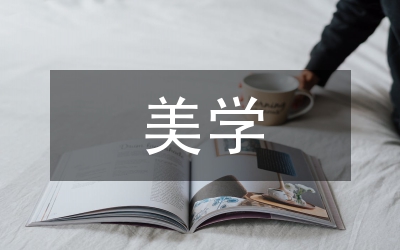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摘要:自從本世紀五十年代美學大討論中形成了四大美學流派之后,美學界迄今沒有出現人所公認的新學派。
(1)今天的美學界通行的美本質觀,仍然是五十年代李澤厚的美在社會實踐說。大學里通用的美學教材,南方高校以劉叔成、夏之放等編著的為主,北方高校以楊辛、甘霖編著的為主,這些八十年代編寫、出版的美學原理教材,不過是李澤厚學說的改造和豐富,作為其理論支點的美本質觀,仍是“美在實踐”、“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平心而論,這個觀點在言必稱馬克思的當時環境中出現,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具有理論深化的意義,是運用馬克思言論能夠較為圓通地解釋較多審美現象的美學定義。然而,作為作者、編者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美本質觀”,它是名不副實、似是而非的,從審美實踐來看,它更是牽強附會的、漏洞百出的。時至今日,如果對它的理論失誤毫無所知,不加分辨地傳播授受,不僅對不起今天這個學術問題可以自由探討的時代,而且會誤人子弟、貽害后學。因此,對這個美學定義的理論疏漏進行一次公開的徹底的檢討,實在已是刻不容緩。
說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關鍵必須搞清楚“人的本質”是什么。應當指出,“人的本質”與“美的本質”一樣,是個既簡單又復雜、幾千年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問題。以“人的本質”這樣一個涵義不確定的概念來界定美本質,只能使美本質的定義更加撲朔迷離。
認識一事物的本質,應當把它放在與它事物的聯系中。聯系就是既對立又統一。認識“人性”、“人的本質”,應當把它置于與其它動物的對立和統一中加以考察。人與動物的統一是人的基本屬性,人與動物的對立即人的特殊屬性。“人性”、“人的本質”應當是人的基本屬性與人的特性、人的生物屬性與人的非生物屬性的統一,二者缺一不可。而馬克思則是在人的特性、人的非動物屬性的意義上使用“人性”、“人的本質”概念的。如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廢除私有制就是徹底解放人的全部感官和特性。不過要達到這種解放,就要靠這些感官和特性在主體和對象兩方面都已變成人性的。”他先舉眼睛為例說明對象必須具有人性:“眼睛已變成人性的眼睛,正因為它的對象已變成一種社會性的人性的對象,一種由人造成和為人服務的對象。”接著舉耳朵為例說明它必須具有人性:“正如只有音樂才喚醒人的音樂感覺,對于不懂音樂的耳朵,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就不是它的對象。”在1845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人類才具有,動物界是不存在“社會關系”的。恩格斯也是這樣。在《反杜林論》中,他說:“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等等。正如朱光潛先生所分析指出的那樣:“所謂‘人性的’,……也就是非動物性的。”
(2)建國以后,理論界無論從“社會性”、還是從“意識性”、抑或是從“勞動”、“實踐”方面解釋“人性”或“人的本質”,都是把“人性”、“人的本質”當作人的特性、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屬性來對待的。應當說,這是對“人性”、“人的本質”理解的一個嚴重失誤。其嚴重的后果,是造成了建國幾十年來對人的起碼的生存欲求(即生物欲求)的粗暴踐踏(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這種欲求是非人性的)。而以“人的特性”界定“人的本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就成了“人的特性的對象化”,由此來解釋一切美學現象,其荒謬性不言而喻。
那么,馬克思理解的“人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馬克思講過人的特性是“自覺自由的活動”、是“勞動”、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國理論界也分別從“意識性”、“勞動實踐性”、“社會性”三方面使用“人性”或“人的本質”一語,這三者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很有必要作一番澄清。
以“意識”、“理性”作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西方古典哲學的一個傳統觀念。受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影響,馬克思早期也曾將人的特性理解為“理性”和“自由”。
(3)大約從1844年開始,他的這一思想逐步發生轉變。這一轉變的標志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1845年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1845—1846年與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時期,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開始形成。用唯物史觀來看人的特性,他發覺原來的觀點太膚淺了。從“意識”的內容、本質來看,“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
(4)從意識的發生史乃至人類的發生史來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并不是在于他們有思想,而是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必備的生活資料”。
(5)可見,人的“意識”是由人類的特殊謀生活動——“勞動”或者說“實踐”決定的,“勞動”或者說“實踐”是比“意識”更為根本的人與動物的區別。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還有一些言論可作參考。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6)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中的作用》中指出:“人類社會區別于猿群的特征……是勞動。”
(7)以“勞動”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之后,“意識”還是不是人與動物的區別呢?仍然是的,雖然不是根本區別。《手稿》指出:“勞動”的特征就是“有意識”:“一個物種的全部特性就在于物種生活活動方式,而人的物種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活動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恩格斯在《自然辨證法》中也曾說過:“歷史和自然史的不同,僅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識的機體的發展過程。”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他指出:勞動使猿的腦髓變成人的腦髓,產生了具有意識機能的人腦。
(8)可見,意識是由勞動派生的人與動物的另一區別,但不是根本區別。那么,“社會性”呢?它也是由勞動派生的人與動物區別的另一表現形態。馬克思指出,人類的勞動有一個特點,即必須在一定的群體協作關系中才能進行。人類的這種群體協作關系,就是“社會關系”,人因而具有了“社會性”,成了“社會動物”:“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夠作到——就象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
(9)“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
(10)由于人必須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才能從事勞動生產,所以,“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11)可見,社會關系實即勞動關系,是由勞動決定的人與動物的另一區別。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照馬克思的本意,勞動、意識、社會關系雖然都是人與動物的區別,但三者的關系并不是并立的,勞動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意識、社會關系則是在這一根本區別之上產生的分枝性區別。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常常在并立的意義上使用勞動、意識、社會關系來說明人的特性,這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誤解。實踐派美學將人的本質(即人的特性)理解為勞動、實踐,這是符合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實踐派美學在這里面臨兩個致命的問題,第一,它所信奉的馬克思的這一人的特性觀能否成立?是否正確?第二,以勞動、實踐作為美的本質,是否符合馬克思的本意?是否符合審美實踐?
關于第一個問題,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勞動”是什么?馬克思給它的定義是,它是人的特殊的謀生活動方式,即“有意識的”、“自覺自由的”“生活活動”方式。同時馬克思又說,“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并不是在于他們有思想,而是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必備的生活資料”,是“勞動”把人從動物界分離出來,并創造了人腦的“意識”機能(恩格斯),產生了以社會勞動生活為反映內容的“意識”形態。于是,同意循環的邏輯矛盾產生了:一方面說“勞動”決定、創造了“意識”,另一方面又說“勞動”是“有意識的”謀生活動,請問,在具有“意識”機能的人腦產生以前,哪來“有意識的”謀生活動——“勞動”?如果保持“勞動”的現有語義不變,那么,正確的邏輯推斷應是先有“意識”后有“有意識的”物質謀生活動“勞動”;不是“勞動”創造了人,面是類人猿的長期的無意識的物質謀生活動產生了具有“意識”機能的“人腦”,其后再產生了人類特有的“有意識的”謀生活動——“勞動”:于是,“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恰恰在于“他們有思想”,而不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必備的生活資料”——“勞動”。馬克思以“意識”為起點走到了決定“意識”的“勞動”,他自以為前進了一大步,殊不知他所界說的“勞動”又是以“有意識”為前提、由“意識”決定的,他實際上仍在原地踏步。就是說,按照正常的邏輯去理解馬克思的人的特性論,我們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意識”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勞動”僅僅是由“意識”決定的人與動物的另一區別。
(12)馬克思說的“社會關系”也存在同樣的漏洞。人們通常把“社會關系”理解為群體合作關系,這與馬克思的意思不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社會關系”只相對于人才存在,“社會關系的含義是指許多個人的合作”,動物的群體合作關系叫“畜群”關系,只有人的群體合作關系才叫“社會關系”。一方面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一方面又說“社會關系”是“人的合作關系”,這就陷入了同義反復,人是什么實際上沒說清楚。事實上,馬克思說的“社會關系”從另一角度看又是勞動關系,勞動關系即“有意識的”謀生活動的主體相互結成的合作關系,他仍是以活動主體是否具有“意識”作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屬性。
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這樣的邏輯錯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將人腦機能的“意識”與作為意識形態的“意識”混為一體了。其實,作為“意識形態”的“意識”,必須有反映內容,可能“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社會)存在”(其實也不盡然,如意識對內在本能欲望的反映),是由勞動生活構成、決定的,而作為人腦機能的“意識”,則無須反映內容,只是指人腦具有的生理心理功能,它決不是由勞動構成的。作為人與動物根本區別的“意識”,只能是意識機能,而不是意識形態。嬰幼兒剛出生時沒有意識形態,但有意識機能,你不能否認他是人。把意識形態與意識機能混淆起來,從意識形態由勞動構成其本質、內容,斷定勞動比意識是更為根本、深沉的人與動物的區別,是導致勞動——人的本質論的思想誤區之一。
關于第二個問題,早就有學者指出,將勞動、實踐這一“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當作美的本質,是不符合馬克思本意的。比如黃海澄在1986年出版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美學原理》一書中指出:“人的本質或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及類似的說法,的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出現過,然而他不是在給美下定義時使用這些語言的。如果我們機械地照搬過來給美下定義,就顯得不夠全面、不夠準確,看起來似乎是尊重馬克思,而實際上是歪曲了馬克思的意思。”
(13)實踐論美學號稱“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八十年代以來,這部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的經濟學手稿似乎變成了美學手稿,各派美學家紛紛據此去重新說明美本質,他們或以此修正自己原來的觀點,如朱光潛、蔣孔陽(14),或以此充實自己原有觀點的論據,如蔡儀、李澤厚。
(15)現行實踐美學觀的美學教科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連篇累牘地形成的。盡管解釋各異,他們的思路幾乎不外是:《手稿》說過“勞動創造美”,所以美的本質是勞動;《手稿》指出“勞動”即“有意識的生活活動”——“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所以美的本質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顯然,這里在裝糊涂,它置換了原來命題中的概念,“勞動”和“美”這兩個不周延的概念搖身一變成了周延的概念,原來主詞和賓詞不可逆的判斷變成了可逆判斷。好象拔高了馬克思,其實歪曲了馬克思;好象理直氣壯,其實強詞奪理。眾所周知,《手稿》是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所造成的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嚴重脫節的不平等現象時論及“勞動創造美”的。馬克思指出:“勞動固然為富人生產出奇妙的作品,卻替勞動者生產出窮困。勞動生產出宮殿,替勞動者生產出茅棚。勞動生產出(劉丕坤譯本作”創造了“)美,替勞動者卻生產出丑陋。勞動者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卻把一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方式的勞動,把剩下的一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出聰明才智,替勞動者卻生產出愚蠢和白癡。”
(16)顯而易見,在“勞動創造了美”這個命題中,賓詞“美”指為富人生產的財富之美,屬不周延概念,并非指所有勞動產品都是美的,更不是指大千世界一切的美。同樣,主詞“勞動”也只是指部分的勞動——“異化勞動”,而不是指所有的勞動:并且,在“異化勞動”中,只有為“富人”生產“宮殿”之類“奇妙作品”的那部分“異化勞動”才創造“美”,而為“勞動者”自身生產“茅棚”之類的那部分勞動就只能產生遮風避雨、安身立命的使用價值。就是說,“勞動”也屬于不周延概念。因此,由此得出“美的本質”是“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的推論,與馬克思的原意相去甚遠。
用審美實踐去衡量“美的本質”在“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在“勞動實踐”這一觀點,其缺陷就更加明顯。如上所述,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勞動”,因此“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即“勞動的對象化”。姑且不說“勞動”作為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物質活動,本身巳包含物化、對象化的意思,說“勞動的對象化”等于說“對象化”的“對象化”,邏輯上經不住推敲。即便假定這個命題邏輯上沒問題,則“勞動對象化”即勞動的物化、產品化,我們能說勞動產品都是美的嗎?當然不能。作為勞動產品,它必須具備的本質、特征和使命是效用(或者說使用價值)而非美,勞動可以在創造了效用的同時創造美,但美并不構成勞動必須承擔的使命和必須具備的特征。這本來是個常識。如果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意識”、“社會關系”,以這種“人的本質”的“對象化”來界定美則更顯得以偏概全。眾所周知,不只“意識”、“社會關系”的“對象化”可能是美,本能、情感的對象化、人與自然關系的對象化也可能是美:同時,并非所有“意識”、“社會關系”的“對象化”都是美的,只有善的道德意識、善的社會關系的對象化才是美的,正如“美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有待說明什么樣的“人的本質”是美的一樣。對此,早有學人指出:“‘對象化’的說法沒有規定究竟是人的什么樣的本質或本質力量對象化了才是美的。事實上,并不是一切人的、也不是人的一切本質或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都是美的,因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是復雜多樣的,人的本質也就不可能是統一的。岳飛與秦檜……之流在本質上怎能相提并論?”
(17)正因為不能相提并論,所以出現了這樣的十分牽強附會的解釋:“人的本質力量……是促進人類進步、推動歷史前進的求真、向善的積極力量……一切反動分子的腐朽、沒落的行為,都是與歷史發展的潮流相違背的,不能算是人的本質力量,而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反動。”
(18)所以,岳飛之類的道德上的好人是具有“人的本質力量”的;秦檜之類道德上的壞人是不具有“人的本質力量”的,于是,現實成了理論的奴婢,為使理論能自圓其說,人成了非人。這實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自說自話。
也許實踐美學論者意識到說美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存在著明顯的以偏概全,于是他們從馬克思《手稿》中挑出“人的本質力量”一語,以此涵蓋“人的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全部本質力量和功能”
(19)再以“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解釋一切審美現象。這種做法,可謂用心良苦,然而經不住推敲。首先,毋庸置疑,“人的本質力量”的涵義應是“人的本質”內涵的邏輯延伸,二者可能外延有所不同,但主要意義當是統一的,不可能“人的本質”指“勞動”、“意識”、“社會關系”等人的非生物屬性,“人的本質力量”則指“人的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全部本質力量和功能”,即人的生物屬性和非生物屬性的總和。其次,《手稿》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剛開始形成過程中的產物,唯物史觀占主導地位,但費爾巴哈的抽象人性論還有殘存,“人的本質力量”用語就是一個顯證。在《手稿》中,“人的本質力量”用語意義模糊不定,有時確指“人的肉體與精神”兩方面的力量,但這恰恰是馬克思后來所揚棄的思想,不代表馬克思成熟以后的看法。再者,如上所述,并非所有“人的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力量”的“對象化”都是美的。
在實踐派美學的美本質定義中,“對象化”概念也存在問題。馬克思使用的“對象化”一語本來自黑格爾,主指精神外化為物質的物化活動。黑格爾是在“理念”的“異化”運動中考察“理念”形態的。黑格爾認為,在自然界產生以前,“理念”就存在了。這時,“理念”尚處在純抽象階段,是片面、不真實的。由于“理念”內在的矛盾作用,抽象的“理念”通過自我否定“異化”為“自然”,“自然”是“理念”發展的純物質階段,也是片面、不真實的。于是又通過內在矛盾作用,“自然”“異化”為“絕對理念”。到了這一階段,精神與物質、主觀與客觀達到辯證統一,“理念”也就不再發展了。抽象理念異化為自然即精神變物質的過程,黑格爾有時又叫做“外化”、“對象化”。可見,“對象化”是理念“異化”運動的特種形式。在《手稿》中,馬克思講“對象化”,主要就指這層意思。表面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就是“人的物種生活(即有意識的生活活動、勞動)的對象化”,事實上,由于“人的物種生活”是以具有“意識”機能的大腦為存在前提的,所以,馬克思說的“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實指“人的意識的對象化”。毫無疑問,物質性活動,是對象化活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特點。即便按照字面意義,“對象化”也具有“物化”的意思。如果保持這個意義不變,那么符合“人的本質對象化”的美只能是一部分具有審美價值的勞動產品:如果要用“人的本質的對象化”來解釋一切的美,包括移情、直覺外射、人格象征的美(主要指自然美),就必須作出說明:這種可以局限在主體直覺、情感、想象范圍內的“對象化”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對象化”,而是自己對這個詞的重新活用。
綜上所述,馬克思說的“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就其自覺的一面而言,是指“勞動的對象化”,就其不自覺的事實一面而言,是指“意識活動的物化——勞動”:它揭示的是人類的特殊謀生——經濟活動——勞動的本質,而不是美的本質。若把美定義為人的本質或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不可能不漏洞百出的。
(20)實踐美學及其理論核心的漏洞實際上一點即破,然而讀者可以看出,本文在論述這引些漏洞時則顯得相當沉重和吃力。原因不在別的,而在謬誤(請允許我用這個詞)重復一千遍,就容易被人當作真理。如果說這種學說在言必稱馬克思的若干年前出現尚情有可原,那么在學術問題可以實事求是自由探討的今天,在本世紀即將過去、新世紀即將到來的世紀之交,再重復這樣的學說就顯得愚蠢可笑了。徹底清除這種似是而非的學說,我們的美學工作者就沒有了退路,沒有了得過且過、可以將就的倚靠,這對于我們探討新的美本質定義,建構新的美學體系極有推動作用。探討新的美本質定義,建構新的美學體系,只要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審美實踐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即便從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現成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而且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反之,不是從審美實踐出發而是從馬克思等人關于美的片言只語出發,對審美現實進行削足適履式的肢解,這樣的學說不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且是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對美本質的新的探討、對美學體系的新的建構,就應當遵循實事求是的方法論。我們相信,由此產生的思維成果必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 上一篇:學生美術課想象力培養論文
- 下一篇:當代電影美術色彩設計芻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