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散文藝術
時間:2022-06-27 10:33:31
導語:董仲舒散文藝術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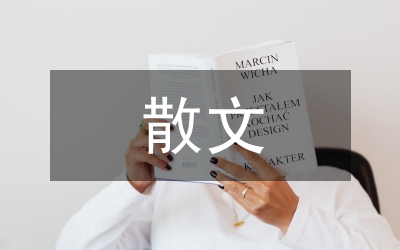
據史料記載,董仲舒著述豐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余萬言,皆傳于后世[1]2525-2526。”董仲舒是當時就負有盛名的經學大師和文章家,但董仲舒的作品,后世散佚甚多,現在僅存《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一些書疏文。劉熙載在其《藝概•文概》中說:“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礡、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于其原委窮之[2]10。”的確,董仲舒著述豐富,即使從現存作品來看,數量仍然較大,足以代表西漢散文眾多體式中的一體。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董仲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經學和思想成就方面,而很少有人從文學的角度對他的作品進行全面的總結和研究,即使有文學史偶爾提及,也僅僅是說到他的“天人三策”,至于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及針對時事的議論文,則被認為缺乏文采而置而不論。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雖然在西漢散文中給董仲舒留了一席之地,但論述相當簡短概括,且主要集中在“天人三策”上,如說:“其(天人三策)論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歷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曉暢,理致細密,全無艱澀滯重之筆;其語言樸素無華,其風格則儒雅雍容。這使它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則缺乏文學性,除散見于《漢書》中的幾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3]179。”這可以說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客觀地說,與西漢其他著名散文家相比,董仲舒的散文在藝術上確是略為遜色。韓愈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4]359。”董仲舒對后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方面是事實,但他的散文不僅完整地表達了他的思想體系,在思想觀念方面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在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的時候,還使用了多樣化的表現手法,有些篇章,語言很有文采,表達很有氣勢,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在行文過程中,能夠體現出作者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貌。因此可以說,董仲舒的散文,可以代表西漢散文多種風格中的一格。以下將以《春秋繁露》為中心,探討董仲舒散文的藝術特色。
“比物聯類”“推類而及”是我們先人的一種重要的認識世界、掌握知識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儒家的治學實踐中得到了自覺的遵守。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周易》,就是用八經卦、六十四別卦來統類宇宙萬物,依據“推類而及”的原則預測吉兇。從《論語》的記載來看,“比物聯類”也是孔子教育學生認識事物、掌握知識的最重要的方法。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5]68。”他贊揚子夏學《詩》能類推聯想,他最喜愛的學生便是能“聞一以知十”的顏淵。根據章太炎的解釋,作為夫子之道的“忠恕”,其含義之一,就是它是一種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學習方法,他說:“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6]426。”這種“一以貫之,觸類而長”的治學方法,為儒家后學所繼承和發揚,如戰國后期的大儒荀子就多次闡說和強調這種“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治學方法,在《非相》篇中他說:圣人何以不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7]52在荀子看來,宇宙萬物,古今之事,皆可“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關鍵是能夠“通倫類”,他說:“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漢初的學者,特別是儒家學者,仍然秉持這種方法以治學,無論是《詩》學還是《春秋》學都是如此,因此他們的解經方式通達、開放、靈活,與此后五經博士系統的章句之學有很大的不同。董仲舒深悉這種治學方法的精髓,他說:“《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8]95。”他就是遵循這種治學法則,以《春秋》為依托,運用通倫比類的方法,構筑了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的思想體系。他說:“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8]33。”又說:“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8]97。”在董仲舒看來,天、地、人就是一個相類相通的整體,人不僅與天相類,簡直就是具體而微的天,“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8]341。因此,由天可以推及人,因為人與天相符,“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8]357。反過來,也可以由人事以求天道,“求天數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8]218。因為天人異體同類,所以他們相通相感,此起彼應,“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8]360。天、地、人,宇宙萬物,以類相從,同類相感相應,構成一個彼此相關的整體,因此,圣人要治國安民,就必須法天而行,否則就會引起宇宙運行的故障,出現災變。“圣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8]35。董仲舒就是這樣通過闡說《春秋》,運用“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方法,將自然、社會、政治倫理、人性等思想觀念融合到他的天人思想體系中。與用“以類相推”的方法構筑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個特點相適應,董仲舒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也多用類比和類推的方法。《天地之行》篇說: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于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圣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于淵也;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為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8]460在這里,作者將身體與國家、治身與治國進行類比,雙線并進,步步深入,由治身之理推及治國之道,得出國家治平在任賢的結論。在《五行相生》篇中,董仲舒首先說:“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為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8]362。”然后由五行之行不同類推出與五行相類的五官:司農、司馬、司營、司徒、司寇,應該各司其職,不得相亂。在《五行相勝》篇中,董仲舒用五行相勝的原理,類推出各官府應該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結論。作者有時用通俗的類比將深奧的道理闡述出來,如他論人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為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后能為絲,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謂善。[8]312類比與類推的說理方法,在董仲舒的散文中使用得非常普遍,這里不再多說。
從董仲舒現有的作品來看,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說,構成了他著作的主題部分,因為他正是借助于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發來建構他的理論體系的,闡發的過程也同時便是他建構理論體系的過程。但也應該看到,他解讀《春秋》、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所運用的“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物聯類”“觀物比德”是一種比較原始、比較低級的認知方式,它是靠直覺,通過聯想而形成的一種認識事物、掌握知識的方法,因而它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模糊性和非科學性。董仲舒的許多推論就有很大的隨意性,如《人副天數》篇說:“天德施,地德化,人徳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于天也[8]354-355。”這純粹是一種主觀想象。有些議論甚至顯得十分荒謬可笑,如他的求雨、止雨之法。但是,如果只是這樣,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專精覃思,在廣覽百家,貫通五經的同時,對《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進行創造性闡發而產生的著作,絕對不會產生那樣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春秋繁露》不僅有許多精義,而且在經常的情況下析理精微,富有思辯色彩。如在《竹林》篇中,他通過考察《春秋》的用辭特點來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文中假設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他首先以畝有數莖苗即可以稱為無苗為比,說明春秋幾百年之間即使有一二義戰,亦可稱為無義戰,然后說:故《春秋》之于偏戰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8]50孟子曾經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但那僅僅是出于仁義之心,反對殘害百姓的一種籠統的說法。董仲舒在這里針對人們對此問題的疑問,闡說了《春秋》對于戰爭的態度,分析精譬,思辯色彩很濃。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就是這樣來辨名析理,解說嫌疑,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的。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說的:“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8]55。”他對于祭仲、逢丑夫行權問題的辨析,對趙盾、許止弒君之事的解說,都明辨嫌疑,是非分明,細致精微。董仲舒對世事人情也有深微的體察和精妙的分析,如他論南宮長萬弒宋閔公之事: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于陰,大夫立于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8]125-12宋閔公被殺的根本原因是君臣無別,但直接原因則是“俱而矜婦人”,這對男人心理的把握十分準確。在儒家的經典中,對漢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倫理觀念、民風民俗等影響最大的是《公羊春秋》,而《公羊春秋》之所以能發生這樣大的影響,固然是通過董仲舒對它的富有創造性的解讀,但也與他的說理方式有關。由于董仲舒運用“比物聯類”這種比較原始的、比較大眾化的思維方式,去闡說有關天、地、人的系統知識,這就使他的理論體系擁有廣泛的受眾。他的有關天道自然、政治制度、倫理道德等理論,為國君、官僚和各類學者所接受,對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以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由于他的思維方式的大眾化而造成的許多觀念意識的低俗性,又使他的許多思想意識為底層民眾所廣泛接受,對俗文化、大眾社會心理以及民風民俗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
董仲舒既不是柔懦無所守的儒生,也不是設法媚悅皇帝的弄臣,而是有明確政治理想、有堅定人生信念、有高尚道德操守的儒學大師。《史記•儒林列傳》載:“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9]3128。”如同西漢大多數儒生那樣,他是以帝王師的心態來面對皇帝,發表議論的。在他的著作中,對漢朝的各種社會政治弊端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特別是指出了漢王朝在制度方面的缺陷,認為漢朝的現行政治制度與暴秦的制度并無多大不同,應該按照儒家理想的社會政治制度進行改造。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通過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發,比較詳細完備地描述了這種理想的政治藍圖。如同孟軻那樣,他既有明確的政治信念和堅定的道德操守,加以他的時代去戰國未遠,所以他的散文,在行文中蘊含著一股郁勃雄霸之氣,即使是那些表面看上去“雍容儒雅”的對策文也是如此,因為他的治學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學的話語霸權。如他在《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中說:“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1]2504-2505。”徹底否定了漢朝的現行制度,要求漢王朝改弦更張,否則將難以企求天下治平的局面。語氣堅定,不容置疑。《春秋繁露》則靈活運用多種句式,特別是經常使用排比句式,不僅使內容得到完美地表達,而且增強了文章的氣勢,如《天地之行》篇中說: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8]458-459使用句式整齊的長排,使意義表達完滿,富有氣勢。又如他論述臣子的地位和功能說:“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于上,所以致義也[8]459-460。”整齊而充滿力度。這樣的長排,在《春秋繁露》中時可見到,表明董仲舒的散文并非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缺乏文采。有時在表達過程中,作者能變換句式,使行文跌落起伏,搖曳多姿。《必仁且智》篇中說: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诐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8]258根據表達內容的不同變換句式,時長時短,靈活多變,讀來令人產生一種蕩氣回腸的感覺。在《立元神》篇,董仲舒用雙線并行、層層遞進、回環闡說的方法,闡說事理。如其中的一段說:體國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于任賢,欲為神者在于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8]170雙線齊進,隔句蟬聯,使文章在表達上有氣勢,有文采。
《春秋》用字謹嚴,是人們所公認的,后儒所說的“《春秋》一字以褒貶”,雖不無夸大,卻能反映出《春秋》用辭的慎重。對此,董仲舒也多次申說。在《實性》篇中,他說:“《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霣石則后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圣人于言無所茍而已矣[8]312-313。”在《精華》篇中,他又說:“《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于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8]85。”董仲舒體認并完全繼承了這種精神,他在《春秋繁露》中特設《深察名號》一篇,強調慎于名號的重要。他說:“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8]284-285。”極力強調慎于名號的重要。在《仁義法》中,他通過辨析字義闡發了《春秋》的功能和精義:“《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于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8]249。”董仲舒在解讀《春秋》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辨析事理以確立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繼承了《春秋》的藝術傳統。首先是用詞準確。這個特點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有全面的表現,不必多說。其次是詞匯豐富。董仲舒的著作視野闊大,內容豐富,貫通天、地、人。他將宇宙萬物分類辨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疇,這些概念和范疇對后世中國哲學、政治、道德、思想等領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在分析具體問題的時候,往往運用排比句,變換語詞,從不同側面對問題的性質和特點進行闡發、論述,用詞豐富、準確而嚴謹,析理精微,是非分明。
后人稱《春秋繁露》為斷獄之書,實不為過。再次是用詞靈活。如《楚莊王》篇中說: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參考文獻: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用詞如此靈活,后世大概只有韓愈能夠繼其足武。董仲舒是漢代“經義”之文的開創者,但他的散文與漢武帝以后的儒生,如貢禹、劉向等人的“經義”之文有很大不同,他的散文仍存留著戰國士人的雄豪之氣以及漢初學術自由的靈動之氣,因此“雍容儒雅”不能概括董仲舒散文的全貌,因為如同其他大家一樣,董仲舒的散文風格也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
- 上一篇:詞體文學演化中對吳聲西曲容受
- 下一篇:畜牧局信息公開工作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