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論文:“先天性”與“必然性”1
時間:2022-08-27 10:34:00
導語:邏輯學論文:“先天性”與“必然性”1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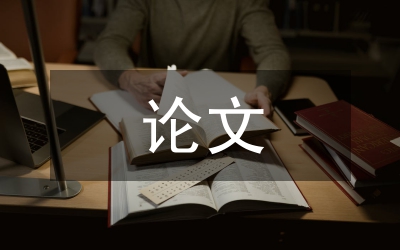
導言
“先天的(apriori)”是康德首先在哲學上予以精心刻畫的重要概念,自那以后,“先天的就是必然的”幾乎已經成為哲學中的定論。康德認為,雖然我們的一切知識都始于經驗,但是卻不能說一切知識都來自經驗。存在有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這就是先天的知識1,這是康德對“先天的”這一概念的最初說明。康德區分“來自”經驗的知識與“先天的”知識,乃是因為在他看來,經驗不能提供真正的普遍性知識,而只能提供偶然的、由歸納而來的相對的普遍性知識。對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比如數學知識等等,用“來自經驗”解釋是不通的,說明不了其普遍必然性的來源。為了說明經驗知識與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的根本不同,康德才把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稱為“先天的知識”。從這個說明即可推知,所謂先天的知識,肯定就是“普遍必然的”知識,內在地隱含著這些知識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不可能受到任何經驗的反駁。故而對于康德來說,“先天的知識就是必然的知識”可以說是個分析命題。康德研究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是以肯定這個命題為前提的。
20世紀以來哲學發生了語言學的轉向,成就之一就是分析哲學。分析哲學無論在研究的方法還是在所研究的問題上,都與傳統哲學與很大的差別。不過,對于先天性、必然性,在分析哲學中也有研究。在這種討論中出現了康德的名字,出現了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這一命題,似乎表明所研究的是與康德同樣的問題,看起來只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與過去不同了。美國哲學家克里普克(S.Kripke)在他發表于70年代的《命題與必然性》(NamingandNecessity)中,提出了與康德“先天的就是必然的”矛盾的“先天偶然命題”和“后天必然命題”,在分析哲學界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被認為是運用新的哲學方法所取得的一項偉大成就。只要翻看一下介紹分析哲學的文獻我們就會發現,克里普克的思想一般總是被單獨列為一章或至少若干節。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繆勒在其頗有影響的《當代哲學主流》一書中,對克里普克的這一新貢獻大加贊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克里普克對包括康德在內的許多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而在此之后又拋棄了他們的觀點。尤其是,克里普克對康德關于先天與后天、必然與偶然的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必然性”是形而上學概念,而“先天的”則是認識論概念,康德以及其后的哲學家們常常把二者等同看待,實際上是混淆了概念的不同2。1999年出版的CONCISEENCYCLOPIDIAOFPHILOSOPHYOFLANGUAGE,在“先天”條目中比較清楚地闡述了先天這個概念(apriori)的特性,澄清了一些謬見,也把克里普克的一個結論當作普遍原則的特例提了出來3。
然而,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在《命名與必然性》中,克里普克沒有對康德進行文本研究,也未提出什么理論;他基本上只是輕巧地舉出了幾個“先天偶然命題”和“后天必然命題”的例子。有了這些反例,康德的觀點顯得不攻自破。克里普克的做法就像是四兩撥千斤,用纖細的木棍把沉重的大廈撥翻了。詫異之余,我們也許百思不得其解:從康德對“先天的”這一概念的闡釋來看,“先天的就是必然的”是顯然的,怎么可能有反例呢?
這種疑慮即使在克里普克的書中都提出了4,然而卻沒有得到他本人以及其他哲學家的認真對待。
本文認真對待這一疑問----從標題即可看出,本文對克里普克的結論持否定態度,認為克里普克是“錯誤地發展”了康德。不過,這種說法需要作些說明。
說一個人錯誤地發展了某種思想,一般是說通過對此思想的某種形式的歪曲而引出了錯誤的結論。本文說克里普克錯誤地發展了康德思想,似乎斷言了這個意思。不過,嚴格地說,克里普克對康德思想的關系很難說是“發展”。因為克里普克并沒有真正領會和把握康德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他的很多論述和和結論雖然在表面上是在康德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但是其實不然,是常識和哲學概念雜交的產物。康德哲學的確存在問題和矛盾,但是矛盾恰恰不可能在克里普克所批判的地方----經過對“先天”、“必然”、“經驗”等概念的澄清,這將會一目了然。
為證明這些論斷,我們需要:一、提出康德和克里普克對“先天”和“必然”的定義或理解;二、根據他們的論述和總體思想,分析、確定各自理解的確切含義;三、比較兩人概念的異同,并據此剖析克里普克對康德的“發展”的實質。在這一過程當中,我們對克里普克的論述采取最寬容的態度,在他的論述不清晰、不確定,或里面的矛盾和漏洞不屬于原則性的時候,我們就對這些論述采取最有一致性的理解。把問題的關鍵確定下來后,我們著手做這件事:一般地判斷康德和克里普克各自觀點的正確性,本文不提出任何理論、也不利用康德理論,而僅僅嚴格地堅守概念意義的前提下,把“經驗”與“先天”、“必然”的關系從原則上確定出來,證明即使在對克里普克最為寬容的態度下,“先天偶然命題”和“后天必然命題”也必定是不可能的,“先天”與“必然”完全是一致的。因而在二者的關系上,對康德思想的發展只可能在于其他方面,本文最后將會對此進行探討。克里普克與康德的不同沒有構成對康德的進步,而是由于方法論的系統性錯誤:把只能處于本質主義系統中才有意義的概念,在非本質主義的系統中去理解。這破壞了那些概念所依賴的架構,破壞了概念本身的意義。因而錯誤雖是必然的,然而卻有整體性和深刻性,在常識的層面顯不出來,難以被發現。
克里普克:對“先天”概念的“正確”理解和例證
克里普克的結論出現很久而未遇真正的反駁這件事表明,做這些事情很不容易。我們看看克里普克是怎樣發展康德思想的。
克里普克指出,“先天”是一個認識論概念,而不是像康德認為的那樣是本體論概念。克里普克認為,自從康德以來,人們總是這樣理解“先天”:
①一個先天的真理(aprioritruth)就是可以獨立于任何經驗而被認識的真理,也就是說,先天地認識這個真理是可能的。5
緊接著,克里普克對①提出了一個看上去自然而然的問題:所謂的“可能”究竟是對誰而言的呢?對上帝、火星人、還是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都沒有說及6。克里普克想以此指出,人們對先天的看法至少存在不明確之處,沒有指明到底對誰而言先天真理是能被先天地認識的(這是顯然合理的要求)。為了補上這個“誰”,克里普克建議我們“最好”(Itmightbebest)7這樣理解“先天”:我們不說什么“先天真理”而只是問這樣一個問題:
②一個特殊的人(aparticularperson)是否可以先天地知道(knowapriori)或者在先天證據的基礎上(onbasisofapriorievidence)相信某事(something)?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就是先天地認識了這個真理8。這就是克里普克對“先天”的理解,跟①相比在語言形式上有兩處明顯的改變:“先天真理”(aprioritruth)不見了,出現了“先天地知道”(knowapriori)。
“必然性”在克里普克看來則是個本體論概念,是指在任何可能世界中都為真的事情:
③某事是真的,如果它不可能不是真的、在這一方面世界不可能是別的樣子的,它就是一個必然真理;否則就是偶然真理。如此,它就與某一個人是否有任何事的任何知識脫離開關系了。9
不管這個說明是否足夠清晰,對于克里普克來說,在這樣的區分之后,“必然性”就成了一個本體論概念,因為它只關涉到世界是否會是另外一個樣子,而無關乎某個真理是怎樣被認識的。10克里普克認為,一個真理往往既可以先天地被認識,也可以后天地被認識,所以在原則上,“必然性”是一個既可以與“先天”、也可以與“后天”搭配的概念。換言之,“后天必然真理”與“先天偶然真理”都是可能的11,康德的“先天的就是必然的”是錯誤的。
光有這些簡單的分析顯然是駁不倒康德的,重頭戲是克里普克給出的“后天必然真理”與“先天偶然真理”的例子:前者有“巴黎米尺是一米長”,后者有“理論同一命題”和“專名的同一”兩種。是這些例子而不是克里普克的簡單說明,才更有震撼力和說服力。
先天偶然真理
我們都知道“巴黎米尺”曾經是米的標準單位,在某個時刻t0,它的長度被定義為一米這種長度單位。由于這是“一米”的定義,克里普克認為,我們無需任何經驗就可以知道12巴黎米尺是一米長。然而,如果把巴黎米尺加熱,由于熱脹冷縮(這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物理學定律)的緣故,它就會變長而不再是一米長了。因而,巴黎米尺在被定義為一米的單位的那一時刻是一米長就是偶然的──它恰巧沒有再長一點或再短一點,它恰巧沒有處于一個更熱的環境等等──這些情況當然都是可能發生的。綜合這二個結果,“巴黎米尺是一米長”就被克里普克認為是個“先天偶然命題”了:對巴黎米尺是一米長的認識是先天的,無需任何經驗;而巴黎米尺當時只是偶然那么長,它本也可以不是那么長。因此,存在這樣的真理:既是可以先天地被認識的,同時也是偶然成立的,“先天”與“必然性”在康德那里的固有聯系就被打破,我們就有了一個“先天偶然真理”的例子。
后天必然真理
克里普克也給出了這種命題的例子,而且不止一類而是兩類。
(一)其一為“專名同一”,或者說是“對象的同一性”,如“晨星等于暮星”這個例子。
“晨星”和“暮星”其實是同一顆星,人們在早晨觀察到了一顆星體,命名為“晨星”;在晚上也觀察到一顆星,命名為“暮星”,而二者的同一性尚未被認識到,人們尚未發現“晨星”和“暮星”不過就是我們今天稱為“金星”的星體。這個例子因為弗雷格在“意義與指稱”這個被認為開分析哲學先河的文章中使用過,至少在分析哲學界人人皆知。弗雷格(Frege)的思想確實顯得非常明顯和直觀:晨星與暮星包含的認識價值不一樣,然而它們指同一顆星卻也是毫無疑義的,這就給出了著名的“意義”與“指稱”的區分13。
弗雷格沒有考慮必然性問題,克里普克把這個例子與必然性聯系起來,是饒有興味的一件事。克里普克描述了美國哲學家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爭論。蒯因(Quine)認為,建立“晨星”與“暮星”的同一,知道我們只是給同一個星貼了兩次“標簽”,乃是經驗發現的結果14。克里普克同意蒯因關于這是“經驗發現”的說法,但是又認為對象的同一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一個對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不是它自己----這是另外一位美國哲學家馬庫斯(Marcus)的看法。結合這兩條,克里普克認為我們“經驗地發現了必然真理”,“晨星就是暮星”因而是“后天必然真理”。15
(二)另外一類這種命題就是科學理論名詞的同一性。
水的分子結構是H2O,可以說是一個科學發現。但是在一開始識別水的時候,人們依靠的則是水的外部特征,如它是無色無味的。(這也是無疑的,在化學未出現的時候,到哪里講H2O呢?O水的分子結構是H2O,是必然的,水不可能不是H2O,如果它有另外的結構,那就是另外的物質而不是水。然而,單靠水是無色無味的,分析不出水是H2O結構,必須有經驗的參與才行。總之,“水是H2O”以及大量類似情況的理論名詞的同一性(如“光是光子流”,“黃金是原子序數為79的元素”等等)也是“后天必然命題”:既是必然的,然而又是后天地認識到的。16
對克里普克的質疑
克里普克的觀點顯得僅靠事實就能證明,我們也確實不能說,在克里普克的例子當中有一眼即可看穿的錯誤,比如,我們顯然不能直接了當地說,水不是H2O,或水是H2O不是經驗的發現,科學理論中的理論名詞的同一性不是必然的,晨星即是暮星不是經驗發現的等等。
克里普克思想的提出已近三十年,分析哲學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后也有很多,但是卻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哲學中學院式研究的原則在這里似乎被遺忘了----在“先天的”、“必然的”這些問題上,密切結合康德思想的思考還沒有過,無論在克里普克那兒還是在后來的研究者那兒都是如此。如果說,這對于創新者克里普克是允許的,對于試圖論證或反駁克里普克觀點的后來者卻不應該。這個本來很奇怪、但是長時間以來可能反而讓人們見怪不怪的事實,表明康德與克里普克思想的聯系還遠遠沒有被揭示清楚。
其實,就連“先天”、“必然”等概念,克里普克也不是從康德哲學出發加以闡釋的。克里普克自己在“附錄”中說,他確實尋找不到證據表明康德就是如①那樣理解“先天真理”的,但當代哲學界確乎是那樣理解“先天真理”的,他的錯誤在于不謹慎地把康德也歸入這種理解了17。克里普克的重點不在于發現康德是否會這樣想,而在于批判現代人們對先天真理的那種理解。在“附錄”中克里普克還說BarryT.Stroud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引起他注意這一“事實”:康德自己犯了一個緊密相關的錯誤(thefactthatKanthimselfmakesacloselyrelatedmistake),認為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先天知識的可靠標準18。從克里普克的此類論述來看,他好像只是從“先天”及“必然”等概念的“正宗”定義發現所有被指認出的錯誤的。
克里普克對康德的反駁,形式上利用的是一個命題與其逆否命題的等價性:
如果康德的理論正確,“先天的就是必然的”;然而“巴黎米尺是一米長”是“先天偶然命題”,“晨星等于暮星”是“后天必然命題,是反例;所以康德是錯的。
這個推理的唯一要求是:
克里普克所涉及的“先天”與“必然”等等概念,與康德的是同樣的概念。
如果克里普克的概念就是康德的概念,而且其反例確實堅持了這些概念,他的論斷就是正確的。要知道這一點,歸根結底又必須考察克里普克對那些概念的敘述,對自己結論的論證。這從字面上是看不出的。克里普克對康德以來人們對“先天”的理解的表述是如此簡單,并且通過簡短的推理“證明”康德是不正確的,我們很難知道這是一種簡單之美還是一種深刻的迷誤。我們需要從克里普克與康德在字面上差不多的表述中,尋找是否有被忽視了的本質差別。如果有,必定很難找到;但是一旦找到,收獲也必定不菲。
如果克里普克與康德的“先天”、“必然”是同樣的概念,由于二人結論相反,他們的論證應該對對方的結論構成反駁。但是,雙方的論證并不構成對對方的反駁,二人的論證與對方的觀點甚至都難以聯系起來。康德的論證過于復雜,牽扯到很多克里普克沒有提及的概念、理論構造;而克里普克幾乎沒有什么論證能與康德關聯上,他只是舉反例“證明”康德是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需要探討這種可能性:克里普克的概念與康德的可能并不相同。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就克里普克的本意來說,他不是想提出新的“先天”(和“必然”)概念。他不是真正建議我們“最好”在他所提出的意義上使用“先天”這個詞、像康德那樣用則是“不太好”。“好”與“不好”與觀點的正確性無關,考慮的是達到目的時的功效,這顯然不是克里普克的意思。在他指出“先天”是一個認識論概念而非本體論概念、“先天”被用作本體論概念而非認識論概念屬于不當或錯誤的時19,他的意思是,就其本來的意義來說,“先天”應是他所謂的“認識論”概念,而不能夠是形而上學概念。既然如此,克里普克當然需要認為:他的概念與康德的概念在最初的意義上是一致的;但只有他的理解才符合這種最初的意義,康德的則不然。
必須找到關于“先天”和“必然”的這種最初的意義并建構論證,以在康德思想和克里普克思想之間建立聯系。即使克里普克沒有誤解康德、他的概念與康德的概念是內在地一致的,亦非直接可見。我們既需要知道康德的核心觀點,也需要知道克里普克的核心觀點。
對“先天”的概念分析:從克里普克到康德
康德對“先天”的原始說法才有資格充當上面所說的“頭”,克里普克對康德的批判或者需要承認這個原初的定義,只是認為康德進一步的理解出錯了;或者需要認為,康德的原始定義一開始就不正確。
如果康德只是提出個“先天”的定義,那么除非這個定義本身存在矛盾,我們不能說像康德那樣提出一個定義有什么不對----提出任何定義都屬于思想自由。其實,克里普克也是承認這個定義的,他在敘述康德以來人們對“先天”的理解時說“一個先天的真理(aprioritruth)就是可以獨立于任何經驗而被認識的真理”,使用了“先天真理”(aprioritruth)這個概念而未作任何交代,表明他繼承了這個概念。克里普克還說:“IguessthetraditionalcharacterizationfromKantgoessomethinglike:aprioritrutharethosewhichcanbeknownindependentlyofanyexperience”20,“thetraditionalcharacterization”顯然是對“先天真理”的性質的刻劃,是對“先天真理”下了個判斷,下判斷的前提當然是已經有了“先天真理”這個概念。當然,不僅如此,克里普克在這兒還使用了“被先天地認識”(knownapriori)這個概念,對這個概念也未作任何交代,表明“先天地認識”也是已有概念。所以,
“先天地認識”與“先天真理”不是處于定義關系之中,“先天地認識”也應當是已有的概念。
正是由于“先天真理”與“先天地認識”均是已有概念,對于二者的關系判斷得對不對,是可以根據其各自的定義加以決定的。在克里普克看來,康德把二者的關系判斷錯了:把先天真理“能被先天地認識”判斷成先天真理“只能被先天地認識”了。而基于同樣的前提,我們也可以判斷克里普克對康德理解的判斷是否正確。
克里普克最為明白地承認“先天真理”這個既有概念,是在第63頁的注26中:先天真理是已知其真是獨立于一切經驗的21。此外,他還在若干處,如在“附錄”中,使用了“先天真理”(或“先天知識”)這個概念。
克里普克建議我們不說“先天真理”而只談對于一個特殊個人來說,某個真理是先天地還是后天地被認識的,似乎克里普克在質疑“先天真理”這個概念本身是不恰當的。其實不然,克里普克是認為,人們使用“先天”這個概念如果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應該像他那樣22。所以,克里普克只是認為,只有他對“先天”的理解是沒有矛盾的。
1.康德的“先天”基本上是這樣引出的:
④存在有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這就是先天的知識23。
康德是借助于“知識”來定義“先天”的,如果轉化成明顯的定義形式,那就是:
④′先天的知識就是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
這個定義如果單獨地看并不清楚,因為“獨立于一切經驗”是十分含混的。對這一概念及相關問題的分析,將在本文較后的地方進行。不管怎么說,我們已經知道,克里普克也是承認這個定義的。
按照克里普克所認為的傳統對“先天”的理解,那就是:
①一個先天的真理就是可以獨立于任何經驗而被認識的真理,也就是說,先天地認識這個真理是可能的。24
克里普克的說法里出現了動詞“認識”,因而“對誰而言能被先天地認識”成了問題。克里普克認為,這個“誰”是指特殊個人:
②一個特殊個人(aparticularperson)是否可以先天地知道(knowapriori)或者在先天證據的基礎上(onbasisofapriorievidence)相信某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就是先天地認識了這個真理。25
在此之后,克里普克就不再談先天真理了,而只談先天地認識。
②是從前面的設問引出來的,是對前面設問的回答,所以從道理上講,論斷②應該是可以從①中推論出來的,②應該只是把①中未明顯地說出的“誰”說了出來。所以
克里普克應該認為,①中的沒露面的主語應該是②里面所說的“特殊個人”。
在對“先天”作了這樣的發揮之后,克里普克關于特殊個人可以后天地認識一個本也可被先天地認識的真理的例子才算是證明了康德是錯誤的。----當然,這還要求了下面這個前提:即克里普克除認為①與②是等價的而外,還認為④或④′等價于①。因為克里普克認為,先天真理應該是①所表述的那樣,康德的錯誤只是把其中的“能”換成“只能”或“必須”了,可見,①應該能從④或④′中推出。反過來,“能被先天地認識的真理”一定是先天真理(因為它不可能是后天真理),從①又可以推出④或④′。
①中的“真理”其實是知識,與康德沒有實質差別,且“獨立于一切經驗”與“獨立于任何經驗”可視為相等的表達,于是對于克里普克,
獨立于一切經驗的知識與獨立于任何經驗而能被認識的真理(或知識),應該是等價的。
但是,要求①與④或④′等價,不等于它們就是等價的,或者其等價性是明顯的。我們需要注意這些轉換與②的關系,①與④或④′中沒有明顯的認識者,雖然它們暗中是應該包含認識者的。
如果認識者是②所說的“特殊個人”,則這應該是隱含在①與④、④′中的。
因而,克里普克對“先天”的理解完整地說來應該是:
⑤先天真理就是能獨立于任何經驗、但不必非得如此被特殊個人認識的“真理”。
這一結論在克里普克論述的語境中幾乎無法懷疑,懷疑它似乎就是主張這里的“能”是對上帝而言的,或者是對火星人而言的,或者不是對任何個人而言的,當然很荒謬。但是,只要閱讀康德就可以知道,康德所說的認識者十分清楚,就是人類或人類的認識能力。克里普克說康德以來人們對“先天”的理解沒有提到認識者,沒有提到先天真理是對“誰”而言能被先天地認識的,并以“上帝、火星人、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設問,實際上隱藏了一個問題:康德的認識者指人類認識能力,而他則主張是“特殊個人”,二者對于“先天”與“必然”這些概念來說,到底有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如果沒有,那么克里普克說自康德以來人們對“先天”的理解沒有提認識者、應該像他那樣提出,當然就是不確切的;如果有差別,由于克里普克必須承接康德的“先天”定義、而康德的定義又是對人類認識能力而言的,完整地看,克里普克也需要承接康德原初的“先天真理”所內在地包含的這個前提。可是克里普克的“特殊個人”與人類認識能力在“先天”這個概念上又是有差別的,克里普克的“先天”概念與康德的就不可能是一回事了。
這當然不是克里普克的想法,他并不認為自己是自作主張,要對不同于①中內在地包含著的認識者(人類認識能力)的特殊個人講認識方式----那是新提出了一個“先天地認識”的概念,即對于“特殊個人”而言的“先天地認識”。盡管它可以與康德的對應概念(對于“人類認識能力”而言的“先天地認識”)有密切的關系,但畢竟與原來的概念不同了。若是這樣,克里普克就無權批判康德錯了。所以克里普克還需要認為,
在①中就已經內在地隱含著:“認識者”指特殊個人與指人類認識能力,是等價的。當然,是否如此尚難預料。
克里普克在設問“對誰而言能”時,似乎暗中假定了只可能有三種選擇:“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上帝和火星人。其實不然,提出“上帝、火星人”不過是作秀式的引子,克里普克想用對“上帝”而言、對“火星人”而言的荒謬性,表明只能對“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言如何認識。即便如此,對于“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也并不是只有確定的一種理解,是否不同理解之下“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與康德的人類認識能力都是相同的,還不明顯。
3.克里普克對“先天”的定義還進行了闡釋或發揮,但使用了一些模棱兩可的話語,可能會節外生枝,需要事先處理。在他對“先天”的解釋即②中,有一個說法是“在先天證據的基礎上(onbasisofpurelyapriorievidence)相信(believe)某事”26。什么是純粹的先天證據呢?“證據”一般總有經驗性,“先天證據”會是什么樣的呢?此外,什么是“相信”?它與“認識”相隔太遠了。
首先,我們不能對“相信”(believe)摳字眼,把“相信”與“知道”(know)視為不同。克里普克在用了“相信”一詞后,舉了利用計算機知道一個數是否素數的例子,認為這屬于后天認識數學真理:
然而,這也許能被一個做了精妙運算的人先天地知道。27
在這里,“知道”顯然同前面的“相信”是在等同地使用的,正是這種聯系才使得克里普克能把“先天地認識”而非僅僅“先天地相信”,與“后天地認識”進行對比。如果與“先天”相連的只是“相信”而不是“知道”,而“相信”又是日常意義上的,那么由于“相信”有隨意性,相信妖魔鬼怪存在也并無不可,無論是先天地相信還是后天地相信都沒有什么意義了。同時,克里普克也就等于是沒有論證“先天地認識”,只論證了“先天地相信”。可見,應當這樣理解克里普克:他只是隨意地使用了兩個不同的詞“相信”和“知道”(即“認識”),它們是等義的。有了這樣一個理解,我們就可以拋開這些枝節問題。
其次,從克里普克關于利用計算機知道一個數是否素數的例子中我們知道:克里普克所謂先天地知道,在這個例子當中不過是指用通過數學運算、數學證明的方式知道。這就算是“在純粹先天地基礎上”認識的,否則就不是。據此,縱然我們還沒有在一般意義上涉及“先天”與“后天”的關系,從而徹底搞清楚“先天的證據”指什么,這個特殊例子總可以算作一個可靠事實,使我們可以對照克里普克的論述展開一些討論了。在考慮“獨立于一切經驗”的意思的時候,這個例子的價值充分顯現出來了。
從康德到克里普克的轉換中的問題
1.上面論證了,如果克里普克不是對特殊個人新引入一個“先天”概念,那么⑤就應該是①的推論。如果第一,這一點沒問題;第二,“能先天地認識”與“只能先天地認識”有差別,那么克里普克的思想對康德就會構成進步,為知識的分類提供了更深入的依據,根據①以認識方式(“先天地認識”和“后天地認識”)可以對知識(先天的、后天的)分類:
第1類知識:只能先天地被認識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先天知識。
第2類知識:只能后天地被認識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后天知識。
第3類知識:既能先天地也能后天地被認識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先天知識,但它如何被認識,可以因人而異,甚至對同一個人也可以依每次認識時的具體情況而異。在克里普克看來,康德沒有認識到這種可能性。
這樣的分類是完備的且絕無交叉,因為“先天地認識”與“后天地認識”是對立的概念。先天地認識的必定是先天真理,而后天地認識的則既可能是先天真理,也可能是后天真理。第1、3類知識是先天知識,第2類是后天知識。第3類知識不需要比第1類知識的外延小,也可以是相同的----這只有兩種可能:每一個先天知識都可以被后天地認識;或者,并不存在可以被后天地認識的先天知識。對于克里普克來說,問題的關鍵當然不在于第3類知識與第1類知識的外延大小,而在于第3類知識是非空的,這只需要舉出一個例子就可以了,即舉出一個原本被認為只能先天地被認識的真理(康德觀點)事實上也可以被后天地認識。
從這個分類可以看到,無論先天真理事實上是怎樣被認識的,克里普克都會承認先天真理和后天真理之間的本質差別是:
后天真理只能被后天地認識,不可能被先天地認識;而先天真理必須能被先天地認識,不管事實上它是怎樣被認識的。
雖說在克里普克的觀點中,先天真理的根牢牢地留在了“能被先天地認識”那里,不可能出現先天真理不能被先天地認識、而只能被后天地認識的情況,但與康德以來的傳統理解不同的是,先天真理似乎稍許侵占了原來所理解的后天真理的地盤:
先天真理,至少某些先天真理,既可能被先天地認識,也可能被后天地認識。
2.關于①、②和④中涉及的“誰”或認識者,“特殊個人”與“人類認識能力”是沒有區別的嗎?
特殊個人當然是“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可是這并不能使“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的意思明白無誤。如果把“特殊個人”理解成“任一特殊個人”----這是對“特殊個人”的第一種理解,那么第3類知識就是對“任一特殊個人都能被先天地也能被后天地認識”的知識。這時,只有每一個特殊個人都“能先天地認識”的知識才算是“能被先天地認識”的知識;而對“特殊個人”的第二種理解是:第3類知識的定義中所說的“能被先天地認識”和知識,是指“存在特殊個人”“能先天地認識”這個知識。只要存在特殊個人能先天地認識某真理,它就是可先天地被認識的。相對于“上帝”和“火星人”的,應該是后一種意義的“特殊個人”,不過第一種理解也不是不可能。我們分別研究這兩種理解。
(1)第一種理解下的“特殊個人”與“能……”的矛盾
我們常說“你一輩子都懂不了……”,雖然是貶低他人的,可是有時也說出了真實情況,讓某個特殊個人認識某個真理有時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復雜的數學真理。完全可能,某個特殊個人一輩子都不能先天地認識它。復雜的數學猜想可以是靠熟悉的定理證明的,可是總有人在數學證明擺到眼前的時候也不能理解。特殊個人對“素數”的認識可能只限于知道其定義,即知道某個數n若是素數,它就不可能被1之外任何比n小的數整除盡,以及給定的數是不是素數----他能靠逐一地用從1到這個數之內的所有數做除數去試驗的方法知道特定的數是否素數。如果有人提出一個普遍的判定方法,通過復雜的數學推理證明了這個方法,他可能怎么也理解不了。此外,對于有智力缺陷的特殊個人來說,一輩子都不能(不拘是先天還是后天地)認識平常的真理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不是每一個“特殊個人”都是“具有我們那樣心靈的人”。對于任何一個特殊個人,我們總可以找到一個他一輩子都沒認識、也不可能認識的科學知識,對于這個知識,我們問他是先天地認識了還是后天地認識了,就猶如問一個伽利略時代的人,他是先天地知道還是后天地知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樣荒謬。顯然,問題不是先天知道或者后天知道,而是根本沒有知道這回事。所以,如果對于任一特殊個人考慮事實上一個真理是怎樣被認識的,那么,必須考慮特殊個人并不認識或不能認識某個真理之情形。
所以,對“特殊個人”取第一種理解,用“能被任一特殊個人獨立于一切經驗地認識的真理”來理解“先天真理”,有內在矛盾。克里普克講特殊個人認識先天真理的方式,前提自然是所講的特殊個人認識了或能認識那個真理,對“特殊個人”的這種理解因此必須放棄。28
(2)第二種理解下的“特殊個人”與“能……”的一致性
第二種理解下的“特殊個人”貌似特殊,實則代表一般的認識者或代表人類的認識能力,“特殊個人”無特殊性。人類認識能力與特殊個人的關系是:特殊個體只能作為這種能力的一個代表或一般可能性出現,沒有任何特殊性。某一個“特殊個人”以某種方式認識了某個真理,那表明人類能夠那樣認識該真理;某“特殊個人”能認識某個真理,也就表明人類是可以那樣認識該真理的。
對于先天真理來說,存在一個尚不知其份量的問題:
如果只是后天地認識了它,而沒有先天地認識它,這個先天真理怎么與只能、因而在事實上也只是被后天地認識的后天真理區別開?
事實上被后天地認識了的先天真理,必須在原則上也能被先天地認識,這一點才有本質的重要性。“能……”與“事實上……”不在同一個層面,后天地認識了一個先天真理時,怎么也認識到了這個真理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呢?這對克里普克是否構成了嚴峻的挑戰,我們還得拭目以待。
表面上,有可能一個先天真理在事實上是被后天地認識的,從未被先天地認識。可是,若僅僅是那樣,它是先天真理、“能被先天地認識”這一點就無論如何也顯示不出來,它與任何一個后天真理還怎么區分呢?所以,
一個真理若是先天真理,它必須是在事實上被某些特殊個人先天地認識了。
唯有如此才能表明它是先天真理,才可以與后天真理區別開。所以,對于人類一般意識來說,“事實上被先天地認識了”與“能被先天地認識”沒有什么區別,“能先天地被認識”與“事實上被先天地認識”完全是統一的29。然而,
這使得“能被先天地認識”與“事實上被先天地認識”根本沒有區別,不是克里普克直接需要的結論。
(3)克里普克的“特殊個人”
克里普克的“特殊個人”雖然表面上不是上面的第二種理解,但卻必須以它為基礎,必須與之一致。
當克里普克講先天地認識、后天地認識某個先天真理的時候,不管他心目中的“認識者”即“特殊個人”是不是康德的人類認識能力,“特殊個人”都必須能夠認識該真理,否則何談“特殊個人”如何認識、是先天還是后天地認識了該真理呢?所以,
克里普克所說的“特殊個人”能認識或認識了所說的真理,是他講認識方式的前提或要求。
但是,如果根本沒有任何特殊個人能夠認識或已認識某個真理,克里普克的前提或要求就落空了,他根本無法再有意義地講認識方式了。克里普克需要有人能夠認識或已經認識了該真理,在此之后才有可能細談是先天地還是后天地認識此真理等。顯然,這要求的恰好是“存在特殊個人”能認識或已認識那個真理。可見,
克里普克如果要保持概念的一致性,就必須在人類認識能力的意義上理解“特殊個人”,理解“特殊個人”后天地認識先天真理的可能性30。
同時,根據前面的結論,也必定存在“特殊個人”事實上先天地認識了任何先天真理,否則先天真理是真理、而且是先天地真理就無法肯定下來。這樣,克里普克要想談論后天地認識先天真理,只能一種可能:
存在特殊個人能夠或在事實上后天地認識某先天真理。
當然,克里普克不必證明對于任何先天真理都存在著后天地認識它的可能性。克里普克沒有作這么強的結論,他只要證明對一個先天真理存在后天地認識它的可能性,就證明了自己是正確的。克里普克的“特殊個人”依賴于上面的結論,他如果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就應該是發展了康德思想。
在“附錄”中,克里普克還講到了認識者的問題,他說先天知識這一概念是對“standardhumansort”而言的,所以他所說的“特殊個人”應該就是人類認識能力。
從任一個人對某個真理的關系:或者(能)認識、或者不(能)認識該真理這一平凡的事實,通過引入克里普克的兩種認識方式(“(能)先天地認識”和“(能)后天地認識”),可以推出任何一個特殊個人與某一先天真理都存在三種關系:(能)先天地認識、(能)后天地認識及不(能)認識。
對任一先天真理都必定“存在特殊個人”已經先天地認識了它,這是可以從“先天真理”這個概念推出的結論;但是對于是否“存在特殊個人”能夠后天地認識它,則是推論不出來的。康德根本沒有把這當作可能性,而克里普克認為是可能的,他認為特殊個人可以用后天的方式----比如通過計算機運算----知道一個數是否素數。如果他的例子是成功的,他當然就證明了可以后天地認識先天真理。至于后續的研究,是否所有先天真理都可以后天地認識,或者如果不是所有的先天真理都能夠,哪些能夠等等,都不需要由他去做。31
關于通過計算機運算知道一個數是否素數是“后天地認識”的方式,克里普克是從這不是“在純粹先天證據的基礎上”(onbasisofpureapriorievidence)認識而推論出的。由此可知,克里普克認為在這里“特殊個人”“不在純粹先天的證據的基礎上”認識了該真理,而“不在純粹先天的證據的基礎上”認識,就是后天地認識(而不是不認識以及偽裝了的先天地認識)。克里普克對于“先天地認識”、“后天地認識”所述甚少,仔細分析起來,其意義是很不明確的。克里普克結論的正誤也因此不是一目了然的。我們先分析克里普克的例子,獲得一些初步的認識,為更為深入的研究作準備克里普克后天認識先天真理的例子
克里普克批評人們把屬于“先天知識”范圍之內的東西,當成是不可能被經驗地認識的,實際上屬于這類陳述(即“先天知識”)范圍內的陳述可以被特殊個人在經驗的基礎上認識,他想舉一個常識意義上的例子予以說明,這就是通過計算機而認識一個數是否素數的例子32。但是,對于這個例子,有幾個與這樣進行認識相關的因素是值得考慮的,克里普克則似乎沒有考慮它們。
1.顯然,計算機運行一個數是否素數的程序是人設計出來的,而設計一個這樣的程序,當然要根據素數的定義,以及從這個定義而推出的某些“先天知識”──這在克里普克那兒屬于先天地認識的情形。
比如,根據素數的定義,我們可以設計出這么一個公式:如果一個數n(它肯定是一個大于1的奇數)不能夠被從3到(n+1)/2中的任何一個數整除,那它就是素數。根據這個公式,一個數是否素數,是可決定的,因為從2到(n+1)/2只有有限多的數。因此,對一個數是否素數的后天認識(只有在克里普克的例子是成功的時我們才可如此說)依賴于這些條件。這些條件的實質是什么呢?
就必要性而言,只有計算機正確地運行了這個計算程序,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這決不等于計算機屏幕顯示的結果正確----那不等于計算機是運行了計算程序,那也可能是碰巧得來的、誤操作得來的。要保證計算機確實提供了知識,正確地運行了計算程序就是必要條件。這一點,克里普克也不否認,他說了后天知道的條件,如知道關于計算機的物理法則等33,當然把它們視為保證這一點的前提條件了。
可是,在一種意義上,這種“知道”顯然無濟于事----就算知道了所有相關的法則,也不能保證某一臺特定的計算機一定會得到確定的結果。我們知道同一批產品的質量也不是完全一樣,出現不同計算結果的事情是可能的----如果另一臺計算機算出來的結果與這臺的不同,我們知道哪個結果是對的?這不可能從關于計算機的物理法則中推導出來,因為物理法則對于每臺計算機都是同樣的。所以,克里普克所說的后天知道的條件,實際上不過是理論上的情況,不是實際情況。
“理論上的情況”的實質是什么呢?為什么第一,“理論上的情況”不是實際情況;第二,克里普克的例子則需要實際情況(某臺計算機這次計算正確),克里普克還要講什么“理論上的情況”呢?這個要求的實質在于:
計算機確實正常地運行了程序,即計算機里發生了一個數學證明。
這是保證計算機屏幕上顯示的結果是正確的之邏輯要求。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屏幕上的結果就不能說是知識,它與誤操作得來的東西就無法區分。
因而,計算機正常地運行了程序,等于是進行了數學推導----決不等于推導不存在。如果另外一個人進行數學推導而認識了一個數學真理----對我來說這和計算機運算沒有實質差別----而我只是知道了他的結論,把它抄在我的作業本上,這算是我后天地認識了這個數學真理嗎?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這也不正確。試想,對于某個數是否素數,即使兩個不具備正常智力的人連計算機都不用就能回答“那是素數”或“那不是素數”,誰是“對”的、誰認識了那個數學真理呢?----回答“正確”的那一個并不比另一個“知道”得更多,如果再問一遍,他們可能就交換答案了。最根本的是存在一個真正的數學推導,不論它是人做的還是計算機通過人設計的程序做的(這在邏輯上并不重要)。
看來,克里普克的例子如果說明了什么,那就是:
克里普克后天地認識先天真理或必然真理的例子,實質上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后天地認識,它可能或者是“不認識”,或者是變相的“先天地認識”。
2.這些說明還都是在克里普克的意義上----即以數學推導方式認識一個數學真理就是先天地認識了它----作出的。事實上由于我們涉及了數學真理是先天真、必然真理這件事,連“數學推導”都似乎不清楚了,因為這里推導出來的是先天真理需要有所體現,涉及先天真理與經驗的關系。通常理解的數學證明往往就是寫下證明的邏輯過程等,撇開這是不是純粹先天地認識的方式不論,寫下證明的邏輯步驟怎么就是數學證明嗎了?靠記憶而復制一個數學證明就不見得是真正地認識了那個數學真理,瞎打誤撞寫對了一個奧妙無窮的數學真理也不是認識了它。我們顯然需要追問怎樣才算是真正認識了一個先天真理(至少這里的數學真理)這一問題。
不管怎樣解釋認識,根據先天真理的定義,認識(不管是先天地還是后天地)一個先天真理,都是認識該先天真理是真理,其為真不依賴于任何經驗,是必然的。邏輯意義的數學推導滿足這種要求,然而常識所含混地理解的數學推導則不能必然地滿足此要求:我們判斷一個人真正進行了數學推導(而不是背下來的等等),判據都是經驗的,因而只能是有限的經驗,它們怎么與“一切經驗”相關,因而成了問題。
例如,教師用同樣的方法教學生,總是有的學生學得快、學得好,有的學生學得慢、學不會,有經驗的教師通過觀察他所熟悉的學生總結出一些經驗判據,斷定哪些學生掌握了他講的知識,即能夠應用它們、證明它們等等,哪些學生則沒有掌握它們,在哪些地方會卡殼。這是常識意義上判斷一個人“認識”了某個數學真理的判據,它們與所認識的先天真理沒有必然聯系----不是一個人做了這些事(這是他掌握了某個先天真理的判據),就一定認識了先天真理的必然性,認識了這個真理獨立于一切經驗。始終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一個人可以做那些事,但是他仍然沒有認識到該真理是“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其根由就在于先天真理是“獨立于一切經驗”而為真的,而“一切經驗”指“一切可能的經驗”,不是有限經驗。
根據這個結論,對于某個先天真理,如果想對某人講認識它與不認識它的區別----這必定是要靠經驗判據來區別,或者是毫無意義的,怎么也達不到“獨立于一切經驗”的地步;或者,如果認識有可能達到的話,就需要某種超出有限經驗、從而使該真理之為真脫離“一切經驗”的條件,這是邏輯上的要求。如果存在這樣的條件,那么它們應該是不依賴于一切經驗的,因而是先天的東西。經驗與先天真理的這樣的一種邏輯結構,康德肯定是考慮過的,而克里普克則肯定沒有意識到需要那樣去考慮。我們在后面研究經驗與認識的一般關系時,將會獨立于康德的理論而詳細考察這個結構。
為了解答上面積攢起來的越來越難的問題,必須深入研究“認識”、“經驗”、“真理”等概念之間的內在關聯。我們首先需要把“先天”、“必然”的精確意義研究清楚。
康德“獨立于一切經驗”:判斷、命題之為真性
康德明確地對知識下過定義:知識就是判斷34。他所說的“知識”不等于“真理”,只有具有客觀性的知識才是真理。康德有時說,真理就是知識與對象相一致,這里的“知識”就不是通常我們所理解的具有真理性的判斷──因為與對象一致與否還不知道,與對象一致才是真理35。康德實際上研究的是命題,他雖然研究肯定判斷,但認為這種研究對于否定判斷也適用。
知識是判斷,判斷必須用概念作出,是對主詞與賓詞的關系的判斷。36
康德依據判斷中主賓詞的關系把一切判斷分為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兩類。
分析判斷就是這樣的判斷,其中主詞包含賓詞,因此整個判斷只不過是對主詞的一個說明,并不包含新的知識,對于知識沒有擴展。分析判斷也可以這樣理解:判斷的真理性單靠判斷中概念的意義就可以確定,不需要用經驗來檢驗其真。
綜合判斷是主詞并不包含賓詞的判斷,或者是不能單靠判斷中的概念就可以判斷其真偽的判斷,必須要有經驗參與才能判斷其真。一切經驗判斷當然都是綜合判斷,因其是否為真不是分析概念即可知道的。
從先天判斷與分析判斷的定義,康德作出了分析判斷是先天的判斷的結論:“一切分析命題都是先天判斷,即使它們的概念是經驗的。”37“讓一個分析判斷以經驗為根據,那是不合情理的,因為我用不著超出我的概念去做這種判斷,也用不著從經驗去證明它。”38很明顯,一個判斷是否分析判斷的判據在于:
判斷中概念之間的關系是否需要經驗才能判斷其成立上面。
命題中概念的關系不需要經驗即知其成立,則命題為先天真理。至于命題里面的單個概念是否與經驗有關,完全不在考慮之列。一個命題里面可以有經驗概念,但是這些概念之間的關系只靠分析概念即可知道是真的,這就是分析判斷。有的分析命題中出現的概念是經驗的,但概念之間的關系是不依賴經驗的。康德的分析命題之一就是“黃金是黃色的金屬”,不管它現在是否被認為它是分析命題(克里普克認為這是個偶然真理39),顯然它包含著經驗內容----“黃金”顯然是經驗概念。“黃金是黃色的金屬”仍被康德認為是分析的,不需要與現實進行對比就可以知其真。分析判斷也是先天判斷,分析判斷中都可以有經驗概念,比它外延大的先天判斷更不用說了。所以,一個知識是否先天的,不在于里面是否出現經驗概念,以及隨之而來的經驗性因素,而只在于其中的概念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一切經驗”而成立。
精品范文
10邏輯推理能力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