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論文:論真理的本質
時間:2022-08-27 10:41:00
導語:邏輯學論文:論真理的本質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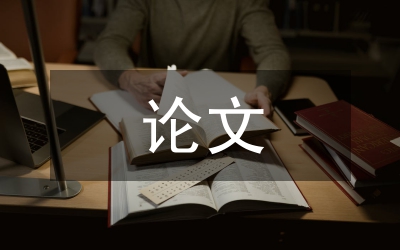
這里要講的是真理的本質。真理的本質問題并不關心真理是否向來是一種實際生活經驗的真理呢,還是一種經濟運算的真理,是一種技術考慮的真理呢,還是政治睿智的真理,特別地,是一種科學研究的真理呢,還是一種藝術造型的真理,甚或,是一種深入沉思的真理呢,還是一種宗教信仰的真理。這種本質之問撇開所有這一切,而觀入那唯一的東西,觀入那種標識出任何一般“真理”之為真理的東西。
然則憑著這個本質之問,我們難道沒有遁入那窒息一切思想的普遍性之空洞中去么?此種追問的浮夸性難道不是彰明了所有哲學的無根么?而一種有根的、轉向現實的思想,必須首先并且開門見山地堅決要求去建立那種在今天給予我們以尺度和標準的現實真理,以防止意見和評判的混淆。面對現實的需要,這個無視于一切現實的關于真理之本質的(“抽象的”)問題又有何用呢?這種本質之問難道不是我們所能問的最不著邊際、最干巴巴的問題么?
無人能逃避上述顧慮的明顯的確鑿性。無人能輕易忽視這一顧慮的逼人的嚴肅性。但誰在這一顧慮中說話呢?是“健全的”人類理智。它固執于顯而易見的利益需求而竭力反對關于存在者之本質的知識,即長期以來被稱為“哲學”的那種根本知識。
普通的人類理智自有其必然性;它以其特有的武器來維護它的權利。這就是訴諸于它的要求和思慮的“不言自明性”。而哲學從來就不能駁倒普通理智,因為后者對于哲學的語言置若罔聞。哲學甚至不能奢望去駁倒普通理智,因為后者對于那種被哲學置于本質洞察面前的東西熟視無睹。
再者,只消我們以為自己對那些生活經驗、行為、研究、造型和信仰的林林總總的“真理”感到確信,則我們本身就還持留在普通理智的明白可解性中。我們自己就助長了那種以“不言自明性”反對任何置疑要求的拒斥態度。
因此,即便我們必得追問真理,我們也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立身于何處?我們要知道我們今天的情形如何。我們要尋求那個應當在人的歷史中并且為這種歷史而為人設立起來的目標。我們要現實的“真理”。可見,還是真理!
但在尋求現實的“真理”之際,我們當也已經知道真理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者,我們只是“憑感受”并且“大體上”知道真理?不過,這種約莫含糊的“知道”和對之漠不關心的態度,難道不是比那種對真理之本質的純粹無知更加蒼白么?
一、流俗的真理概念
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呢?“真理”,這是一個崇高的、同時卻已經被用濫了的、幾近晦暗不明的字眼,它意指那個使真實成其為真實的東西。什么是真實(Wahres)呢?例如,我們說:“我們一起完成這項任務,是真實的快樂”。我們意思是說:這是一種純粹的、現實的快樂。真實就是現實(dasWirkliche)。據此,我們也談論不同于假金的真金。假金其實并非它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它只是一種“假象”(Schein),因而是非現實的。非現實被看作現實的反面。但假金其實也是某個現實的東西。因此,我們更明白地說:現實的金是真正的金。但兩者又都是“現實的”,真正的金并不亞于流通的非真正的金。可見,真金之真實并不能由它的現實性來保證。于是,我們又要重提這樣一個問題:這里何謂真正的和真實的?真正的金是那種現實的東西,其現實性符合于我們“本來”就事先并且總是以金所意指的東西。相反地,當我們以為是假金時,我們就說:“這是某種不相符的東西”。而對于“適得其所”的東西,我們就說:這是名符其實的。事情是相符的。
然而,我們不僅把現實的快樂、真正的金和所有此類存在者稱為真實的,而且首先也把我們關于存在者的陳述稱為真實的或者虛假的,而存在者本身按其方式可以是真正的或者非真正的,在其現實性中可以是這樣或者那樣。當一個陳述所指所說與它所陳述的事情相符合時,該陳述便是真實的。甚至在這里,我們也說:這是名符其實的。但現在相符的不是事情(Sache),而是命題(Satz)。
真實的東西,無論是真實的事情還是真實的命題,就是相符、一致的東西。在這里,真實和真理就意味著符合(Stimmen),而且是雙重意義上的符合:一方面是事情與關于事情的先行意謂的符合;另一方面則是陳述的意思與事情的符合。
傳統的真理定義表明了符合的這一雙重特性:veritasestadaequatioreietintellectus。這個定義的意思可以是:真理是物(事情)對知的適合。但它也可以表示:真理是知對物(事情)的適合。誠然,人們往往喜歡把上述本質界定僅僅表達為如下公式:veritasestadaequatiointellectusadrem[真理是知與物的符合]。不過,這樣被理解的真理,即命題真理,卻只有在事情真理(Sachwahrheit)的基礎上,亦即在adequatioreiadintellectum[物與知的符合]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真理的兩個本質概念始終就意指一種“以……為取向”,因此它們所思的就是作為正確性(Richtigkeit)的真理。
盡管如此,前者卻并非對后者的單純顛倒。而毋寧說,在兩種情況下,intellectus[知]與res[物]是被作了不同的思考。為了認清這一點,我們必須追溯通常的真理概念的流俗公式的最切近的(中世紀的)起源。作為adaequatioreiadintellectum[物與知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并不就是指后來的、唯基于人的主體性才有可能的康德的先驗思想,也即“對象符合于我們的知識”,而是指基督教神學的信仰,即認為:從物的所是和物是否存在看,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它們作為受造物(enscreatum)符合于在intellectusdivinus即上帝之精神中預先設定的理念,因而是適合理念的(idee-gerecht)(即正確的),并且在此意義上看來是“真實的”。就連intellectushumanus[人類理智]也是一種enscreatum[受造物]。作為上帝賦予人的一種能力,它必須滿足上帝的idea[理念]。但是,理智之所以是適合理念的,乃是由于它在其命題中實現所思與那個必然相應于idea[理念]的物的適合。如果一切存在者都是“受造的”,那么,人類知識之真理的可能性就基于這樣一回事情:物與命題同樣是適合理念的,因而根據上帝創世計劃的統一性而彼此吻合。作為adaequatiorei(creandae)adintellecctum(divinum)[物(受造物)與知(上帝)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保證了作為adaequatiointellectus(humani)adrem(creatam)[知(人類的)與物(創造的)的符合]的veritas[真理]。在本質上,真理無非是指convenientia[協同],也即作為受造物的存在者在自身中間與創造主的符合一致,一種根據創世秩序之規定的“符合”。
但是,在擺脫了創世觀念之后,這種秩序同樣也能一般地和不確定地作為世界秩序而被表象出來。神學上所構想的創世秩序為世界理性(Weltvernunft)對一切對象的可計劃性所取代。世界理性為自身立法,從而也要求其程序(這被看作是“合邏輯的”)具有直接的明白可解性。命題真理的本質在于陳述的正確性,這一點用不著特別的論證。即便是在人們以一種引人注目的徒勞努力去解釋這種正確性如何發生時,人們也是把這種正確性先行設定為真理的本質了。同樣,事情真理也總是意味著現成事物與其“合理性的”本質概念的符合。這就形成一種假象:仿佛這一對真理之本質的規定是無賴于對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質的闡釋的——這種闡釋總是包含著對作為intellectus[知識]的承擔者和實行者的人的本質的闡釋。于是,有關真理之本質的公式(veritasestadaequatiointellectusetrei[真理是知與物的符合])就獲得了它的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洞明的普遍有效性。這一真理概念的不言自明性的本質根據幾乎未曾得到過關注;而在這種自明性的支配下,人們也就承認下面這回事情是同樣不言自明的:真理有一個反面,并且有非真理(Unwahrheit)。命題的非真理(不正確性)就是陳述與事情的不一致。事情的非真理(非真正性)就是存在者與其本質的不符合。無論如何,非真理總是被把握為不符合。此種不符合落在真理之本質之外。因此,在把捉真理的純粹本質之際,就可以把作為真理的這樣一個反面的非真理撇在一邊了。
然而,歸根到底,我們還需要對真理之本質作一種特殊的揭示么?真理的純粹本質不是已經在那個不為任何理論所擾亂并且由其自明性所確保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中得到充分體現了嗎?再者,如果我們把那種將命題真理歸結為事情真理的做法看作它最初所顯示出來的東西,看作一種神學的解釋,如果我們此外還純粹地保持哲學上的本質界定,以防止神學的混雜,并且把真理概念局限于命題真理,那么,我們立即就遇到了一種古老的——盡管不是最古老的——思想傳統,依這個傳統來看,真理就是陳述(λογοζ)與事情(πραγμα)的符合一致(ομοιωσιζ)。假如我們知道陳述與事情的符合一致的意思,那么,在這里,有關陳述還有什么值得我們追問的呢?我們知道這種符合一致的意思嗎?
二、符合的內在可能性
我們在不同的意義上談論符合。例如,看到桌子上的兩個五分硬幣,我們便說:它們彼此是符合一致的。兩者由于外觀上的一致而相符合。因此,它們有著這種共同的外觀,而且就此而言,它們是相同的。進一步,譬如當我們就其中的一枚硬幣說:這枚硬幣是圓的,這時侯,我們也談到了符合。這里,是陳述與物相符合。其中的關系并不是物與物之間的,而是陳述與物之間的。但物與陳述又在何處符合一致呢?從外觀上看,這兩個相關的東西明顯是不同的嘛!硬幣是由金屬做成的,而陳述根本就不是質料性的。硬幣是圓形的,而陳述根本就沒有空間特性。人們可以用硬幣購買東西,而一個關于硬幣的陳述從來就不是貨幣。但盡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上述陳述作為一個真實的陳述卻與硬幣相符合。而且,根據流俗的真理概念,這種符合乃是一種適合。完全不同的陳述如何可能與硬幣適合呢?或許它必得成為硬幣并且以此完全取消自己。這是陳述決不可能做到的。一旦做到這一點,則陳述也就不可能成為與物相一致的陳述了。在適合中,陳述必須保持其所是,甚至首先要成其所是。那么,陳述的全然不同于任何一物的本質何在呢?陳述如何能夠通過守住其本質而與一個它者——物——適合呢?
這里,適合的意思不可能是不同物之間的一種物性上的同化。毋寧說,適合的本質取決于在陳述與物之間起著作用的那種關系的特性。只消這種“關系”還是不確定的,在其本質上還是未曾得到論究的,那么,所有關于此種適合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爭執,關于此種相稱的特性和程度的爭執,就都會淪于空洞。但是,關于硬幣的陳述把“自身”系于這一物,因為它把這一物表象(vor-stellen)出來,并且來言說這個被表象的東西,說它在其主要方面處于何種情況中。有所表象的陳述就像對一個如其所是的被表象之物那樣來說其所說。這個“像……那樣”(so-wie)涉及到表象及其所表象的東西。這里,在不考慮所有那些“心理學的”和“意識理論的”先入之見的情況下,表象(Vor-stellen)意味著讓物對立而為對象。作為如此這般被擺置者,對立者必須橫貫一個敞開的對立領域(offenesEntgegen),而同時自身又必須保持為一物并且自行顯示為一個持留的東西。橫貫對立領域的物的這一顯現實行于一個敞開域(Offenes)中,此敞開域的敞開狀態(Offenheit)首先并不是由表象創造出來的,而是一向只作為一個關聯領域而為后者所關涉和接受。表象性陳述與物的關系乃是那種關系(Verhaltnis)的實行,此種關系源始地并且向來作為一種行為(Verhalten)表現出來。但一切行為的特征在于,它持留于敞開域而總是系于一個可敞開者(Offenbares)之為可敞開者。如此這般的可敞開者,而且只有在這種嚴格意義上的可敞開者,在早先的西方思想中被經驗為“在場者”(dasAnwesende),并且長期以來就被稱為“存在者”。
行為向存在者保持開放。所有開放的關聯都是行為。依照存在者的種類和行為的方式,人的開放狀態各各不同。任何作業和動作,所有行動和籌謀,都處于一個敞開領域之中,在其中,存在者作為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才能夠適得其所并且成為可言說的(sagbar)。而只有當存在者本身向表象性陳述呈現自身,以至于后者服從于指令而如其所是地言說存在者之際,上述情形才會發生。由于陳述遵從這樣一個指令,它才指向存在者。如此這般指引著的言說便是正確的(即真實的)。如此這般被言說的東西便是正確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了。
行為的開放狀態(Offenstandigkeit)賦予陳述以正確性;因為只有通過行為的開放狀態,可敞開者才能成為表象性適合的標準。開放的行為本身必須讓自己來充當這種尺度。這意味著:它必須擔當起對一切表象之標準的先行確定。這歸于行為的開放狀態。但如果只有通過行為的這種開放狀態,陳述的正確性(真理)才是可能的,那么,首先使正確性得以成為可能的那個東西就必然具有更為源始的權利而被看作真理的本質了。
由此,習慣上獨一地把真理當作陳述的唯一本質位置而指派給它的做法,也就失效了。真理源始地并非寓居于命題之中。不過,與此同時也生發出一個問題,即開放的和先行確定標準的行為的內在可能性的根據問題,唯這種可能性才賦予命題之正確性以那種根本上實現了真理之本質的外觀。
三、正確性之可能性的根據
表象性陳述從哪里獲得指令,去指向對象并且依照正確性與對象符合一致?何以這種符合一致也一并決定著真理的本質?而先行確定一種定向,指示一種符合一致,諸如此類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呢?只有這樣來發生,即:這種先行確定已經自行開放而入于敞開域,已經為一個由敞開域而來運作著的結合當下各種表象的可敞開者自行開放出來了。這種為結合著的定向的自行開放,只有作為向敞開域的可敞開者的自由存在(Freisein)才是可能的。此種自由存在指示著迄今未曾得到把捉的自由之本質。作為正確性之內在可能性,行為的開放狀態植根于自由。真理的本質乃是自由(DasWesenderWahrheitistdieFreiheit)。
然而,這個關于正確性之本質的命題不是以一種不言自明替換了另一種不言自明么?為了能夠完成一個行為,由此也能夠完成表象性陳述的行為,乃至與“真理”符合或不符合的行為,行為者當然必須是自由的。不過,前面那個命題實際上并不意味著,作出陳述,通報和接受陳述,是一種無拘無束的行為;相反,這個命題倒是說:自由乃是真理之本質本身。在此,“本質”(Wesen)被理解為那種首先并且一般地被當作已知的東西的內在可能性的根據。但在自由這個概念中,我們所思的卻并不是真理,更不是真理的本質。所以,“真理(陳述之正確性)的本質是自由”這個命題就必然是令人詫異的。
把真理之本質設定在自由中——這難道不就是把真理委諸于人的隨心所欲嗎?人們把真理交付給人這個“搖擺不定的蘆葦”的任意性——難道還能有比這更為徹底的對真理的葬送嗎?在前面的探討中總是一再硬充健全判斷的東西,現在只是更清晰了些:真理在此被壓制到人類主體的主體性那里。盡管這個主體也能獲得一種客觀性,但這種客觀性也還與主體性一起,是人性的并且受人的支配。
錯誤和偽裝,謊言和欺騙,幻覺和假象,簡言之,形形色色的非真理,人們當然把它們歸咎于人。而非真理確實也是真理的反面,因此,非真理作為真理的非本質,便理所當然地被排除在真理的純粹本質的問題范圍之外了。非真理的這種人性起源,確實只是根據對立去證明那種“超出”人而起支配作用的“自在的”真理之本質。形而上學把這種真理看作不朽的和永恒的,是決不能建立在人之本質的易逝性和脆弱性之上的。那么,真理之本質如何還能在人的自由中找到其持存和根據呢?
對上面這個“真理的本質是自由”的命題的拒斥態度依靠的是一些先入之見,其中最為頑冥不化的是:自由是人的一個特性。自由的本質毋需進一步的置疑,也不容進一步的置疑。人是什么,盡人皆知的嘛!
四、自由的本質
然而,對作為正確性的真理與自由的本質聯系的說明卻動搖著上面所說的先入之見;當然,前提是我們準備好作一種思想的轉變。關于真理與自由的本質聯系的思索趨使我們去探討人之本質的問題,著眼點是保證讓我們獲得對人(即此在)的被遮蔽的本質根據的經驗的那個方面,并且是這樣,即這種經驗事先把我們置于源始地本質現身著的真理領域之中。但由此而來也顯示出:自由之所以是正確性之內在可能性的根據,只是因為它是從獨一無二的根本性的真理之源始本質那里獲得其本己本質的。自由首先已經被規定為對于敞開域的可敞開者來說的自由了。應當如何來思自由的這一本質呢?一個正確的表象性陳述與之相稱的那個可敞開者,乃是始終在開放行為中敞開的存在者。向著敞開域的可敞開者的自由讓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為讓存在者存在(dasSeinlassenvonSeiendem)。
通常地,譬如當我們放棄一件已經安排好的事情時,我們就會說到這種讓存在(Seinlassen)。“我們聽其自然吧”,意思就是:我們不再碰它,不再干預它。在這里,讓某物存在含有放任、放棄、冷漠、乃至疏忽等消極意義。
但在此必不可少的“讓存在者存在”一詞卻并沒有疏忽和冷漠的意思,而倒是相反。讓存在乃是讓參與到存在者那里。當然,我們也不能僅僅把它理解為對當下照面的或者尋找到的存在者的單純推動、保管、照料和安排。讓存在——即讓存在者成其所是——意味著:參與到敞開域及其敞開狀態中,每個仿佛與之俱來的存在者就置身于這種敞開狀態中。西方思想開端時就把這一敞開域把握為τααληθεα,即無蔽者。如果我們把αληθεια譯成“無蔽”,而不是譯成“真理”,那么,這種翻譯不僅更加“合乎字面”,而且包含著一種指示,即要重新思考通常的正確性意義上的真理概念,并予以追思,深入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狀態和解蔽過程的那個尚未被把握的東西那里。參與到存在者之被解蔽狀態中,這并不是喪失于這一狀態中,而是自行展開而成為一種在存在者面前的引退,以便使這個存在者以其所是和如何是的方式公開自身,并且使表象性適合從中取得標準。作為這種讓存在,它向存在者本身展開自身,并把一切行為置入敞開域中。讓存在,亦即自由,本身就是展開著的(aus-setzend),是綻出的(ek-sistent)。著眼于真理的本質,自由的本質顯示自身為進入存在者之被解蔽狀態的展開。
自由并不是通常理智喜歡任其借此名義四處流傳的東西,即那種偶而出現的在選擇中或偏向于此或偏向于彼的任意。自由并不是對行為的可為和不可為不加約束。但自由也并不只是對某個必需之物和必然之物(以及如此這般無論何種存在者)的準備。先于這一切(“消極的”和“積極的”自由),自由乃是參與到存在者本身的解蔽過程中去。被解蔽狀態本身被保存于綻出的參與(dasek-sistenteSich-einlassen)之中,由于這種參與,敞開域的敞開狀態,即這個“此”(Da),才是其所是。
在此之在(Da-sein)中,人才具有他由之得以綻出地生存的本質根據,而這個本質根據長期以來未曾被探究過。在這里,“生存”(Existenz)并不意味著一個存在者的出現和“定在”(Dasein)(現成存在)意義上的existentia[實存]。但“生存”在此也不是“在生存狀態上”意指人在身-心機制的基礎上構造出來的為其自身的道德努力。綻出之生存(Ek-sistenz)植根于作為自由的真理,乃是那種進入存在者本身的被解蔽狀態之中的展開。歷史性的人的綻出之生存還沒有得到把握,甚至還需要一種本質建基;歷史性的人的綻出之生存唯開端于那樣一個時刻,那時侯,最初的思想家追問著,憑著“什么是存在者”這個問題而投身到存在者之無蔽狀態中。在這個問題中,無蔽狀態才首次得到了經驗。存在者整體自行揭示為φυσιζ,即“自然”;但“自然”在此還不是意指存在者的一個特殊領域,而是指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整體,而且是在涌現著的在場(dasaufgehendeAnwesen)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唯當存在者本身被合乎本己地推入其無蔽狀態并且被保存于其中,唯當人們從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追問出發把握了這種保存,這時侯,歷史才得開始。對存在者整體的原初解蔽,對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追問,和西方歷史的發端,這三者乃是一回事;它們同時在一個“時代”里出現,這個“時代”本身才無可度量地為一切尺度開啟了敞開域。
然而,如果綻出的此之在——作為讓存在者存在——解放了人而讓人獲得其“自由”,因為它才為人提供出選擇的可能性(存在者),向人托出必然之物(存在者),那么,人的任性愿望就并不占有自由。人并不把自由“占有”為特性,情形恰恰相反:是自由,即綻出的、解蔽著的此之在占有人,如此源始地占有著人,以至于唯有自由才允諾給人類那種與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整體的關聯,而這種關聯才首先創建并標志著一切歷史。唯有綻出的人才是歷史性的人。“自然”是無歷史的。
如此這般來理解的作為讓存在者存在的自由,是存在者之解蔽意義上的真理之本質的實現和實行。“真理”并不是正確命題的標志,并不是由某個人類“主體”對一個“客體”所說出的、并且在某個地方——我們不知道在哪個領域中——“有效”的命題的標志;不如說,“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過這種解蔽,一種敞開狀態才成其本質。一切人類行為和姿態都在它的敞開域中展開。因此,人乃以綻出之生存的方式存在。
由于每一種人類行為各各以其方式保持開放,并且與它所對待的東西相協調,所以,讓存在之行為狀態,即自由,必然已經賦予它以一種內在指引的稟賦,即指引表象去符合于當下存在者。于是,所謂人綻出地生存(ek-sistieren)就意味著:一個歷史性人類的本質可能性的歷史對人來說被保存于存在者整體之解蔽中了。歷史的罕見而質樸的決斷就源出于真理之源始本質的現身方式中。
但另一方面,由于真理在本質上乃是自由,所以歷史性的人在讓存在者存在中也可能讓存在者不成其為它所是和如何是的存在者。這樣,存在者便被遮蓋和偽裝了。假象(Schein)占了上風。于此,真理的非本質(Unwesen)突現出來了。不過,因為綻出的自由作為真理的本質并不是人固有的特性,倒是人只有作為這種自由的所有物才綻出地生存出來,并因而才能有歷史,所以,即便真理的非本質也并不是事后來源于人的純然無能和疏忽。而毋寧說,非真理必然源出于真理的本質。只是因為真理和非真理在本質上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共屬一體的,一個真實的命題才能夠成為一個相應地非真實的命題的對立面。于是乎,真理之本質的問題才達到了問之所問的源始領域之中,其時,基于對真理的全部本質的先行洞識,這個問題也已經把對于非真理之沉思攝入本質揭示中了。對真理之非本質的探討并非事后補遺,而是充分地發動對真理之本質的追問的關鍵一步。但我們應如何來把捉真理之本質中的非本質呢?如果說陳述的正確性并沒有囊括真理的本質,那么,非真理也是不能與判斷的不正確性相等同的五、真理的本質
真理的本質揭示自身為自由。自由乃是綻出的、解蔽著的讓存在者存在。任何一種開放行為皆游弋于“讓存在者存在”之中,并且每每對此一或彼一存在者有所作為。作為參與到存在者整體本身的解蔽中去這樣一回事情,自由乃已經使一切行為協調于存在者整體。然而,我們卻不能把這種協調狀態(即調諧)把捉為“體驗”和“情感”,因為這樣做,我們只不過是使之喪失了本質,并且從那種東西(“生命”和“靈魂”)出發對之作出解釋而已——這種東西確實只能維持自己的本質權利的假象,只要它本身包含著對協調狀態的偽裝和誤解。協調狀態,也即一種入于存在者整體的綻出的展開狀態(Ausgesetztheit),之所以是能夠被“體驗”和“感受”的,只是因為“體驗的人”一向已經被嵌入一種揭示著存在者整體的協調狀態中了,而并沒有去猜測調諧之本質為何。歷史性的人的每一種行為,無論它是否被強調,無論它是否被理解,都是被調諧了的,并且通過這種調諧而被推入存在者整體之中了。存在者整體的敞開狀態并不就是我們恰好熟悉的存在者之總和。情形倒是相反:存在者不為人所熟悉的地方,存在者沒有或者還只是粗略地被科學所認識的地方,存在者整體的敞開狀態能夠更為本質地運作;而比較而言,在熟知的和隨時可知的東西成為大量的,并且由于技術無限度地推進對物的統治地位而使存在者不再能夠抵抗人們的賣力的認識活動的地方,存在者整體的敞開狀態倒是少見運作的。正是在這種無所不知和唯知獨尊的平庸無奇中,存在者之敞開狀態被敉平為表面的虛無,那種甚至不止于無關緊要而只還被遺忘的東西的虛無。
調諧著的讓存在者存在貫通一切于存在者中游弋的開放行為,并且先行于存在者。人的行為乃是完全由存在者整體之可敞開狀態來調諧的。但在日常計算和動作的視野里來看,這一“整體”似乎是不可計算、不可把捉的。從當下可敞開的存在者那里——無論這種存在者是自然中的存在者還是歷史中的存在者——我們是把捉不到這個“整體”的。盡管不斷地調諧一切,但它卻依然是未曾確定的東西、不可確定的東西,從而,它大抵也是最流行的東西、最不假思索的東西。不過,這個調諧者并非一無所有,而是一種對存在者整體的遮蔽。讓存在總是在個別行為中讓存在者存在,對存在者有所動作,并因之解蔽著存在者;正是因為這樣,讓存在才遮蔽著存在者整體。讓存在自身本也是一種遮蔽。在此之在的綻出的自由中,發生著對存在者整體的遮蔽,存在著(ist)遮蔽狀態。
六、作為遮蔽的非真理
遮蔽狀態拒絕給αληθεια[無蔽]以解蔽,并且還不允許無蔽成為δτερησιζ(剝奪),而是為無蔽保持著它的固有的最本己的東西。于是,從作為解蔽狀態的真理方面來看,遮蔽狀態就是非解蔽狀態(Un-entborgenheit),從而就是對真理之本質來說最本己的和根本性的非真理(Un-wahrheit)。存在者整體的遮蔽狀態決不是事后才出現的,并不是由于我們對存在者始終只有零碎的知識的緣故。存在者整體之遮蔽狀態,即根本性的非真理,比此一存在者或彼一存在者的任何一種可敞開狀態更為古老。它也比“讓存在”本身更為古老,這種“讓存在”在解蔽之際已然保持遮蔽了,并且向遮蔽過程有所動作了。是什么把讓存在保存于這種與遮蔽過程的關聯中的呢?無非是對被遮蔽者整體的遮蔽,對存在者本身的遮蔽而已——也就是神秘(dasGeheimnis)罷。并不是關于這個或那個東西的個別的神秘,而只是這一個,即歸根到底統攝著人的此之在的這種神秘本身(被遮蔽者之遮蔽)。
“讓存在”——即讓存在者整體存在——是解蔽著又遮蔽著的,其中發生著這樣一回事情:遮蔽顯現為首先被遮蔽者。綻出的此之在保存著最初的和最廣大的非解蔽狀態,即根本性的非真理。真理的根本性的非本質乃是神秘。這里,非本質還并不意味著是低于在一般之物(κοινον[共性]、γενοζ[種])及其可能性和根據這種意義上的本質的。這里所說的非本質乃是先行成其本質的本質。但“非本質”首先大抵是指那種已經脫落了的本質的畸變。不過,在上述任何一種意義上,非本質一向以其方式保持為本質性的,從來不會成為毫不相干意義上的非本質性的東西。而如此這般來談論非本質和非真理,已經遠遠違背了常識之見,看起來好像是在搬弄煞費苦心地構想出來的“佯謬”(Paradoxa)。這種印象是難以消除的,所以,我們似乎應當放棄這種矛盾的談論;不過,它只是對于通常的意見(Doxa)來說是矛盾的。而對有識之士來說,真理的原初的非本質(即非真理)中的“非”(Un-),卻指示著那尚未被經驗的存在之真理(而不只是存在者之真理)的領域。
作為“讓存在者存在”,自由在自身中就是斷然下了決心的姿態,即沒有自行鎖閉起來的姿態。一切行為都植根于此種姿態中,并且從中獲得指引而去向存在者及其解蔽。但這一對于遮蔽的姿態卻同時自行遮蔽,因為它一任神秘之被遺忘狀態占了上風,并且消隱于這種被遺忘狀態中了。盡管人不斷地在其行為中對存在者有所作為,但他也往往總是對待了此一或彼一存在者及其當下可敞開狀態而已。就是在最極端的情形中,他也還是固執于方便可達的和可控制的東西。而且,當他著手拓寬、改變、重新獲得和確保在其所作所為的各各不同領域中的存在者之可敞開狀態時,他也還是從方便可達的意圖和需要范圍內取得其行為的指令的。
然而,滯留于方便可達的東西,這本身就是不讓那種對被遮蔽者的遮蔽運作起來。誠然,在通行的東西中也有令人困惑的、未曾解釋的、未曾確定的、大可置疑的東西。但這些自身確實的問題只不過是通行之物的通行的過渡和中轉站,因而不是本質性的。當存在者整體的遮蔽狀態僅僅被附帶地看作一個偶爾呈報出來的界限時,作為基本事件的遮蔽便淪于被遺忘狀態中了。
不過,此在的被遺忘了的神秘并沒有為被遺忘狀態所消除;而毋寧說,這種被遺忘狀態倒是賦予被遺忘者的表面上的消隱以一種本己的現身當前。神秘在被遺忘狀態中并且為這種被遺忘狀態而自行拒絕,由此,它便讓在其通行之物中的歷史性的人寓于他所作成的東西。這樣一來,人類就得以根據總是最新的需要和意圖來充實他的“世界”,以他的打算和計劃來充滿他的“世界”。于是,在遺忘存在者整體之際,人便從上述他的打算和計劃中取得其尺度。他固守著這種尺度,并且不斷地為自己配備以新的尺度,卻還沒有考慮尺度之采納(Maβ-nahme)的根據和尺度之給出(Maβgabe)的本質。盡管向一些全新的尺度和目標前進了,但在其尺度的本質之真正性(Wesens-Echtheit)這回事情上,人卻茫然出了差錯。他愈是獨一地把自己當作主體,當作一切存在者的尺度,他就愈加弄錯了。人類猖獗的忘性固執于用那種對他而言總是方便可得的通行之物來確保他自己。這種固執在那種姿態中有它所不得而知的依靠;作為這種姿態,此在不僅綻出地生存(ek-sistiert),而且也固執地持存(in-sistiert),即頑固地守住那仿佛從自身而來自在地敞開的存在者所提供出來的東西。
綻出的此在是固執的。即便在固執的生存中,也有神秘在運作;只不過,此時神秘是作為被遺忘的、從而成為“非本質性的”真理的本質來運作的。
七、作為迷誤的非真理
人固執地孜孜于一向最切近可達的存在者。但另一方面,只有作為已經綻出的人,人才能固執,因為他確實把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當作標準了。而在他采納標準時,人類卻背離了神秘。固執地朝向(insistenteZuwendung)方便可達之物,與綻出地背離(ek-sistenteWegwendung)神秘,這兩者是共屬一體的。它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而這種朝向和背離卻又與此在中的來回往復的固有轉向亦步亦趨。人離開神秘而奔向方便可達的東西,匆匆地離開一個通行之物,趕向最切近的通行之物而與神秘失之交臂——這一番折騰就是誤入歧途(dasIrren)。
人彷徨歧途。人并不是才剛剛誤入歧途。人總是在迷誤中彷徨歧途,因為他在綻出之際也固執,從而已經在迷誤中了。人誤入其中的迷誤決不是仿佛只在人身邊伸展的東西,猶如一條人偶爾失足于其中的小溝;毋寧說,迷誤屬于歷史性的人被納入其中的此之在的內在機制。迷誤乃是那種轉向的運作領域,在這種轉向中,固執的綻出之生存(diein-sistenteEk-sistenz)總是隨機應變地重新遺忘自己,重新出了差錯。對被遮蔽的存在者整體的遮蔽支配著當下存在者的解蔽過程,此種解蔽過程作為遮蔽之遺忘狀態而成為迷誤。
迷誤是原初的真理之本質的本質性的反本質(Gegenwesen)。迷誤公開自身為本質性真理的每一個對立面的敞開域。迷誤(Irre)乃是錯誤(Irrtum)的敞開之所和根據。所謂錯誤,并非一個個別的差錯,而是那種其中錯綜交織了所有迷誤方式的歷史的領地(即統治地位)。
按其開放狀態以及它與存在者整體的關聯,每一種行為都各各是迷誤的方式。錯誤的范圍很廣,從日常的做錯、看錯、算錯,到本質性態度和決斷中的迷失和迷路,都是錯誤。但通常地,甚至依照哲學的學說,人們所認為的錯誤,乃是判斷的不正確性和知識的虛假性,它只不過是迷誤的一種,而且是最為膚淺的一種迷誤而已。一個歷史性的人類必然誤入迷誤之中,從而其行程是有迷誤的;這種迷誤本質上是與此在的敞開狀態相適合的。迷誤通過使人迷失道路而徹底支配著人。但使人迷失道路的迷誤同時也一道提供出一種可能性,這是一種人能夠從綻出之生存中獲得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通過經驗迷誤本身,并且在此之在的神秘那里不出差錯,人就可能不讓自己誤入歧途。
由于人的固執的綻出之生存行于迷誤之中,由于引人誤入歧途的迷誤總是以某種方式咄咄逼人并且由于這種逼迫控制了神秘——而且是一種被遺忘的神秘,所以,人在其此在的綻出之生存中就尤其屈服于神秘的支配和迷誤的逼迫了。他便處在受統一者和它者的強制的困境中了。完整的、包含著其最本己的非本質的真理之本質,憑這種不斷的來回往復的轉向,就把此在保持在困境之中了。此在就是入于困境的轉向。從人的此之在而來,并且唯從人的此之在而來,才出現了對必然性的解蔽,相應地也就出現了那種入于不可回避之物中的可能的移置(Versetzung)。
對存在者之為這樣一個存在者的解蔽同時也就是對存在者整體的遮蔽。在這種解蔽與遮蔽的同時中,就有迷誤在運作。對被遮蔽者之遮蔽與迷誤一道歸屬于真理的原初本質。從此在的固執的綻出之生存來理解,自由乃是(在表象之正確性意義上的)真理的本質,而這僅僅是因為自由本身源起于真理的源始本質,源起于在迷誤中的神秘之運作。“讓存在者存在”實行于保持開放的行為。但讓作為如此這般的整體的存在者存在,這回事情卻只有當它在其原初的本質中偶而被接納時才會合乎本質地發生。于是,朝向神秘的有決心的展開(Ent-schlossenheitzumGeheimnis)便在進入迷誤本身之途中了。于是,真理之本質的問題便得到了更為源始的追問。于是,真理之本質與本質之真理的交織關系的根據便顯露出來了。觀入那從迷誤而來的神秘,這乃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追問,即追問存在者之為存在者整體是什么。這種追問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問題——該問題根本上是令人誤入歧途的,因而在其多義性方面是尚未得到掌握的。源起于這樣一種追問的存在之思,自柏拉圖以來就被理解為“哲學”,后又被冠以“形而上學”之名。
八、真理問題與哲學
把人向著綻出之生存解放出來,這對于歷史具有奠基作用。這種解放在存在之思中達乎詞語;不過,詞語并不只是意見的“表達”,不如說,它一向已經是存在者整體之真理的得到完好保存的構造。至于有多少人能聽到這詞語,乃是無關緊要的事情。而正是那些能聽者決定了人在歷史中的位置。但在哲學發端的同一個世界瞬間里,也就開始了普通理智的鮮明突出的統治地位(智者學派)。
普通理智要求可敞開的存在者的無可置疑性,并且把任何一種運思的追問說成是對健全的人類理智的攻擊,是健全的人類理智的不幸迷惑。
然而,健全的、在它自身的區域內十分正當的理智對于哲學的評判卻并沒有切中哲學的本質,后者唯有根據與作為存在者整體的存在者的源始真理的關聯才能得到規定。但由于真理的完全本質包含著非本質,并且是首先作為遮蔽而運作的,所以,探究這種真理的哲學本身就是分裂性的。哲學之思想乃是柔和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derMilde),它并不拒絕存在者整體的遮蔽狀態。哲學之思想尤其是嚴格性的展開狀態(EntschlossenheitderStrenge),它并不沖破遮蔽,而是把它的完好無損的本質逼入把握活動的敞開域中,從而把它逼入其本己的真理之中。
在其“讓存在”——讓存在者作為如此這般的存在者整體而存在——的柔和的嚴格性和嚴格的柔和性中,哲學遂成為一種追問;這種追問并不唯一地持守于存在者,但也不允許任何外部強加的命令。這種最內在的思想困境已經為康德所猜度;因為康德在談到哲學時說:“這里,我們看到哲學實際上被置于一個糟糕的立足點上了,它應該是牢固的,雖然無論是天上還是地上都沒有它賴以立足的地方。在此,哲學應當證明它的純正性,作為它的法則的自我維持者,而不是作為那個向哲學訴說某種移植過來的意義或者誰也不知道的監護本性的人的代言人……”(《道德形而上學的基礎》,《康德文集》,學院版,第四卷,第425頁)。
康德的著作引發了西方形而上學的最后一次轉向。在他上述對哲學之本質的解說中,康德洞察到一個領域,按照他的形而上學立場,他是在主體性中,而且唯有從這個主體性而來,才能把握這個領域,并且必定要把它理解為它自身的法則的自我維護者。盡管如此,這一對哲學之規定性的本質洞見已經足以推翻任何對哲學之思想的貶損,其中最無助的一種貶損是聲稱:作為一種“文化”的“表達”(斯賓格勒)和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人類的裝飾品,哲學也還是有其價值的。
然而,哲學是否實現了它原初的決定性的本質而成為“其法則的自我維護者”,或者,哲學是否由其法則一向所屬的那個東西的真理來維護本身并獲得支撐,這取決于那種開端性,在這種開端性中,真理的源始本質對運思之追問來說成為本質性的。
我們眼下所闡述的嘗試使真理之本質的問題超越了流俗的本質概念中習慣界定的范囿,并且有助于我們去思索,真理之本質(dasWesenderWahrheit)的問題是否同時而且首先必定是本質之真理(dieWahrheitdesWesens)的問題。但在“本質”這個概念中,哲學思考的是存在。我們把陳述之正確性的內在可能性追溯到作為其“根據”的“讓存在”的綻出的自由,同時我們先行指出這個根據的本質開端就在于遮蔽和迷誤之中。這一番工作意在表明,真理之本質并非某種“抽象”普遍性的空洞的“一般之物”,而是那種獨一無二的歷史所具有的自行遮蔽著的唯一東西;這種獨一無二的歷史乃是我們所謂的存在的“意義”的解蔽的歷史——而長期以來,我們已習慣于僅僅把所謂存在當作存在者整體來思考。
九、注解
真理之本質的問題起于本質之真理的問題。在前一個問題中,我們首先是在“所是”(quidditas)或實在(realitas)的意義上來理解本質的,又把真理理解為知識的一個特性。而在本質之真理的問題中,“本質”一詞作動詞解;在這個還停留在形而上學之表象范圍內的詞語中,我們思的是存有(Seyn)——作為存在與存在者之間運作著的差異的那個存有。真理意味著作為存有之基本特征的有所澄明的庇護(lichtendesBergen)。真理之本質問題的答案在于下面這個命題:真理的本質是本質的真理。依照我們的解釋,人們不難看出,這個命題不只是顛倒了一下詞序而已,并不是要喚起某種背謬的假象。本質之真理是這個命題的主語——倘若我們畢竟還可以使用一下主語這個糟糕的語法范疇的話。有所澄明的庇護乃是知識與存在者的符合,其中的這個“是”(ist)也就是“讓……成其本質”(laβtwesen)。這個命題并不是辨證的。它根本就不是陳述意義上的命題。對真理之本質問題的回答是對存有之歷史范圍內的一個轉向的道說(dieSageeinerKehre)。因為存有包含著有所澄明的庇護,所以存有原初地顯現于遮蔽著的隱匿之光亮中。這種澄明的名稱就是希臘的αληθεια[無蔽]。
按照原先的計劃,“真理的本質”這個演講還要續以第二個演講,就是“本質的真理”。后面這個演講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做成;眼下,我在“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一文中已經把個中原因挑明了。
意義的問題(參看拙著《存在與時間》,1927年),亦即籌劃領域的問題(《存在與時間》,第151頁),亦即敞開狀態的問題,亦即存在之真理(而不止于存在者之真理)的問題——這乃是一個關鍵問題,而我們蓄意地未予展開。表面看來,我們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學的軌道上;但在其關鍵的步驟上,也就是從作為正確性的真理到綻出的自由,從綻出的自由到作為遮蔽和迷誤的真理,思想在這些步驟上卻實行了一個追問的轉變,這個轉變乃屬于對形而上學的克服。我在演講中所嘗試的思想實現在那種本質性的經驗中,它經驗到,唯從人能夠進入其中的那個此之在而來,歷史性的人才得以鄰近于存在之真理。于是,一切人類學和作為主體的人的主體性都被遺棄了——《存在與時間》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存在之真理被當作一種已經轉變了的歷史性的基本立場的根據來尋求了;不止于此,上面這個演講的進程就是要從這另一個根據(此之在)出發來運思。追問的過程本就是思想之道路。這種思想并不提供出觀念和概念,而是作為與存在之關聯的轉變來經驗和檢驗自身。
精品范文
10邏輯推理能力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