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xué)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jīng)驗(yàn)
時(shí)間:2022-08-27 10:54:00
導(dǎo)語(yǔ):哲學(xué)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jīng)驗(yàn)一文來(lái)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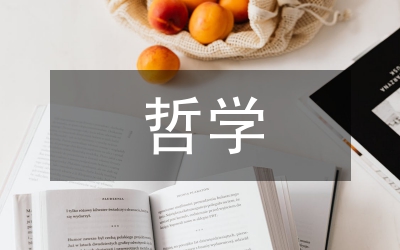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關(guān)于學(xué)術(shù)與政治,韋伯在1919年的講演中斷定:“這是兩個(gè)完全異質(zhì)的問(wèn)題”,“一名科學(xué)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jià)值判斷之時(shí),也就是對(duì)事實(shí)有充分理解的終結(jié)之時(shí)。”(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三聯(lián)書(shū)店,1998年,第38頁(yè))學(xué)術(shù)獨(dú)立于政治不但是韋伯的結(jié)論也是普世性的現(xiàn)代訴求,五四以來(lái)的中國(guó)學(xué)術(shù)之具有現(xiàn)代性,正基于其內(nèi)在的自由品格。但千方百計(jì)爭(zhēng)取獨(dú)立的中國(guó)學(xué)術(shù),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quán)力拘束為所有學(xué)者難以擺脫,其關(guān)系之復(fù)雜、過(guò)程之曲折,即使細(xì)讀韋伯也無(wú)法透徹理解。
1986年,著名哲學(xué)史家賀麟先生將1947年完成的《當(dāng)代中國(guó)哲學(xué)》一書(shū)修改后以《五十年來(lái)的中國(guó)哲學(xué)》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書(shū)在不影響原書(shū)的體系及主要論點(diǎn)的前提下,作了適當(dāng)?shù)男薷暮脱a(bǔ)充。”(《新版序》)揭呈此一修改所關(guān)涉的諸多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學(xué)術(shù)與政治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關(guān)系形式。
一哲學(xué)的政治化
經(jīng)過(guò)50年代政治學(xué)習(xí)、思想改造和學(xué)術(shù)思想批判等“洗腦”、“交心”的運(yùn)動(dòng)之后,賀麟一代的學(xué)者紛紛修改舊作以適應(yīng)新的環(huán)境。馮友蘭修改《中國(guó)哲學(xué)史》,劉大杰修改《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等都是著例。賀的《中國(guó)當(dāng)代哲學(xué)》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為《文化與人生》的新版寫(xiě)序時(shí)說(shuō)的:“我記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當(dāng)代中國(guó)哲學(xué)》一書(shū),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對(duì)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shuō)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duì)此說(shuō)的論點(diǎn),及發(fā)揮知行合一說(shuō)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不過(guò)嚴(yán)重的錯(cuò)誤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所謂‘力行哲學(xué)’。”(《文化與人生》,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此書(shū)還包含對(duì)辯證唯物論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強(qiáng)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連修改的基礎(chǔ)也不具備。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種新的政治標(biāo)準(zhǔn)代替舊的政治標(biāo)準(zhǔn),新舊兩版實(shí)際上都具有政治化寫(xiě)作的性質(zhì)。
賀在新版序中交代說(shuō):“只有第三章時(shí)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yàn)樯婕罢螁?wèn)題,且系基于學(xué)生的筆記寫(xiě)成,由于我當(dāng)時(shí)對(duì)于辯證唯物主義毫無(wú)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就“物質(zhì)在于意識(shí)之先”而言,舊版認(rèn)為這是科學(xué)常識(shí)而非哲學(xué),“哲學(xué)要問(wèn)在理論上邏輯上什么東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東西是核心,是命脈?”新版在“物質(zhì)在于意識(shí)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誤以為”數(shù)語(yǔ)以為限制;在指出哲學(xué)與科學(xué)的不同之后,加上“這并不能說(shuō)是辯證唯物論”一句,表明所批評(píng)的并非真正的辯證唯物論,但辯證唯物論究竟是什么,新版卻沒(méi)有交代。
就辯證法來(lái)說(shuō),舊版首先強(qiáng)調(diào),辯證法產(chǎn)生于哲學(xué)家研究人類(lèi)情感生活后發(fā)現(xiàn)的通理,“只有應(yīng)用到精神生活內(nèi)心生活上去,才見(jiàn)其生動(dòng)活潑”。賀本以此批評(píng)唯物辯證法,新版卻加上“各國(guó)新黑格爾派大都認(rèn)為”一句,表明這不是自己的觀點(diǎn)。其次,辯證法不能顛倒:“馬克思并沒(méi)有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guò)來(lái)。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dāng)讀黑格爾柏拉圖的著作。讀馬克思的著作對(duì)于辯證法的學(xué)習(xí),并無(wú)多大幫助。”新版刪去了最后一句,減輕批評(píng)的力度。第三,關(guān)于辯證法的三大規(guī)律,舊版認(rèn)為對(duì)“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原則,“辯證唯物論者從不曾好好發(fā)揮”,新版式改為“辯證唯物論者不見(jiàn)得有更多更好的發(fā)揮”,語(yǔ)氣稍緩;有關(guān)“否定之否定”的規(guī)律,新版沒(méi)有改動(dòng);關(guān)于質(zhì)量互轉(zhuǎn)規(guī)律,舊版認(rèn)為質(zhì)量關(guān)系“既無(wú)所謂互轉(zhuǎn),其本身和辯證法也不相干”,新版改為“它們的對(duì)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轉(zhuǎn)化,自身辯證發(fā)展的過(guò)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對(duì)辯證法的評(píng)論前后矛盾。
就唯物史觀而言,舊版以“以上種種說(shuō)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xué)思想的貧乏,不過(guò)辯證法唯物論主要觀點(diǎn)還是它的歷史哲學(xué)”開(kāi)頭,新版把這一句話改為“以上種種說(shuō)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xué)的方法論,許多都是承黑格爾而來(lái)的。”語(yǔ)氣由批判改為介紹。舊版對(duì)唯物史觀的批評(píng)有三點(diǎn):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會(huì)背景的歷史觀,屬于“客觀的或外觀的研究”,雖不能說(shuō)錯(cuò),卻不如“從思想本身來(lái)看思想”的內(nèi)觀法的深刻;二是不同意下層決定上層:“在我們看來(lái),經(jīng)濟(jì)始終是工具,上層的生活才是目的,我們固然不否認(rèn)工具的重要,但是我們更注意目的的重要。”“歸根結(jié)底不是經(jīng)濟(jì)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經(jīng)濟(jì),我們表面上受經(jīng)濟(jì)支配,實(shí)際上受經(jīng)濟(jì)背后的主人公支配。”三是認(rèn)為階級(jí)斗爭(zhēng)理論不足以解釋歷史:“這種只是政治斗爭(zhēng)的一個(gè)口號(hào)。但是歷史上的斗爭(zhēng)并不限于階級(jí),我們也可以說(shuō)歷史是觀念的斗爭(zhēng),民族的斗爭(zhēng)”。新版對(duì)這三個(gè)觀點(diǎn)基本沒(méi)有修改,我們無(wú)法從中看出賀對(duì)唯物史觀有什么新的認(rèn)識(shí)。(以上修改情況,參看舊版第61—67頁(yè),新版67—74)
舊版一以貫之地以“批判”為基調(diào),首尾一貫;新版易“批判”為“剖析”,有所肯定卻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實(shí)際上并未改變舊版對(duì)辯證唯物論的批判。從棄舊迎新的角度看,這一部分的修改是不成功的。為賀設(shè)想,最好的辦法應(yīng)當(dāng)是全部改寫(xiě)。
其實(shí),新版的改動(dòng)決不限于第三章。這一章的內(nèi)容是批判實(shí)驗(yàn)主義和辯證唯物論,以過(guò)渡到“正統(tǒng)哲學(xué)與三民主義哲學(xué)的展望”。所謂“正統(tǒng)哲學(xué)”,主要是西方源自古希臘羅馬的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和中國(guó)程朱陸王的新儒學(xué),它的當(dāng)代版即是三民主義哲學(xué)。三民主義哲學(xué)既如此重要,故舊版第四章全部討論“知行問(wèn)題的討論與發(fā)揮”,前4節(jié)討論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第5節(jié)討論的力行哲學(xué),以為“當(dāng)代哲學(xué)”的總結(jié)。孫中山既仍被奉為革命偉人,自無(wú)需大的改動(dòng),第五節(jié)則須全部刪去并換上。賀在新版序中對(duì)第四章的修改情況不著一辭,何以如此,我們不得而知。
舊版對(duì)蔣的評(píng)論,首先是在中外哲學(xué)的比較中發(fā)現(xiàn)其政治意義。“深切著明地見(jiàn)到一個(gè)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zhēng),須建筑在一個(gè)偉大的民族哲學(xué)與民族精神復(fù)興的運(yùn)動(dòng)上面,恐怕要首推為德意志復(fù)興建立精神基礎(chǔ)的大哲學(xué)家費(fèi)希特了。而蔣先生謀國(guó)規(guī)模的遠(yuǎn)大,識(shí)見(jiàn)的超卓,卻處處與費(fèi)希特所見(jiàn),幾若合符節(jié)。”(舊版第107頁(yè))如批評(píng)本民族之墮落,復(fù)興民族首在復(fù)興民族的道德、發(fā)展民族性等,蔣都堪與費(fèi)希特媲美。其次是從融會(huì)王陽(yáng)明與孫中山的角度表彰其哲學(xué)價(jià)值。賀認(rèn)為,王陽(yáng)明致知之教,其歸宿即在一個(gè)“行”字,蔣的“力行”就是重新提出陽(yáng)明的致良知之教。鑒于孫中山認(rèn)為王陽(yáng)明的知行合一“與真理相背馳,而無(wú)補(bǔ)于世道人心”,蔣特別提出“致知難行易的良知”來(lái)融會(huì)陽(yáng)明與中山。所謂“致知難行易之良知”,就是“本著我們自己的良知,照著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xué)說(shuō)去做。”“我們大家皆知道知難行易的哲學(xué),是今日救人心救民族最好的學(xué)說(shuō)。這個(gè)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我們能夠努力實(shí)行這個(gè)知難行易的學(xué)說(shuō)。這就是致知難行易的良知。”(舊版第111頁(yè))一個(gè)融會(huì)了從王陽(yáng)明到孫中山的哲學(xué),當(dāng)然就是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上知行問(wèn)題研究的最高成果:“蔣先生的力行哲學(xué)實(shí)在是發(fā)揮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shuō)的偉大成果,也就是為知難行易謀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證明。”(舊版第117頁(yè))其三是把“行”與古儒“仁”、“誠(chéng)”聯(lián)系起來(lái)分析其文化貢獻(xiàn)。舊版把蔣的前后言論聯(lián)貫起來(lái),認(rèn)為“蔣先生不惟承認(rèn)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這種看法不惟對(duì)人性有新認(rèn)識(shí),且于孔孟性善說(shuō)也有新的證明與發(fā)揮。”(舊版第113頁(yè))蔣的人生觀“實(shí)亦代表中國(guó)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觀”。
蔣之于中國(guó)哲學(xué)是如此重要,一旦刪去,豈不殘缺不全?賀應(yīng)當(dāng)感到高興的是,蔣之后有。《實(shí)踐論》所論也屬于哲學(xué)史上的知行問(wèn)題,而且他同樣重視實(shí)踐。所以以毛易蔣,內(nèi)容上仍然和諧一致。新版以“知行合一問(wèn)題——由朱熹、王陽(yáng)明、王船山、孫中山到《實(shí)踐論》”為結(jié)束。“從辯證法唯物論的認(rèn)識(shí)論來(lái)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論沒(méi)有看到知識(shí)的感性和實(shí)踐的基礎(chǔ);王陽(yáng)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觀上內(nèi)心體驗(yàn),王船山見(jiàn)解正確卻沒(méi)有把知行問(wèn)題作為哲學(xué)的重點(diǎn);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缺點(diǎn)最少,但把知行劃分為二截,認(rèn)為難易懸殊,理論實(shí)踐上都有困難。“不像朱熹那樣把知行分為二截,也不像王陽(yáng)明那樣在當(dāng)下的直覺(jué)里或內(nèi)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階級(jí)斗爭(zhēng)和社會(huì)實(shí)踐、生產(chǎn)實(shí)踐里去求理論與實(shí)踐的辯證統(tǒng)一,他不像孫中山那樣去作知行孰難孰易的比較,他不像朱熹、王陽(yáng)明兩人那樣皆同隱于內(nèi)心生活體驗(yàn)、知先行后的說(shuō)法,而是提出知識(shí)出于實(shí)踐而又為實(shí)踐所證明的實(shí)踐論。站在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立場(chǎng),掌握住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并靈活地運(yùn)用它來(lái)處理知識(shí)與實(shí)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知行統(tǒng)一論。所以他在立場(chǎng)上,唯物觀點(diǎn)上,辯證方法上以及問(wèn)題的提法上超過(guò)了孫中山,揚(yáng)棄了、發(fā)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觀點(diǎn)。他文中雖未提到他們,然而他又沒(méi)有把他們的貢獻(xiàn)完全拋開(kāi)”。(新版第209頁(yè))所以,不是孫中山,更不是,而是,才是中國(guó)哲學(xué)的最后總結(jié)。
49年以后的舊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馮友蘭對(duì)此體會(huì)甚深:“在解放以后,我也寫(xiě)了一些東西,其內(nèi)容是主要是懺悔,首先是對(duì)我在40年代所寫(xiě)的那幾本書(shū)的懺悔。并在懺悔中重新研究中國(guó)哲學(xué)史,開(kāi)始寫(xiě)《中國(guó)哲學(xué)史新編》。”但“這個(gè)修訂本只出了頭兩冊(cè)之后,我又感到修訂得連我自己也不滿意。我又著手修訂修訂本,但是在它即將付印之際,我發(fā)現(xiàn)這個(gè)修訂修訂本也必須重新再寫(xiě)。這一次,我完全從頭開(kāi)始重寫(xiě)。三十年已經(jīng)過(guò)去了,就這樣修訂、重寫(xiě),還沒(méi)有出版定本。”(《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309頁(yè))賀對(duì)第三章的修改是不成功的,但第四章以毛易蔣后,讀起來(lái)并無(wú)突兀湊合之感,因?yàn)樾掳媾f版都是政治化寫(xiě)作,其上下關(guān)系、歷史位置乃至一些觀點(diǎn)大同小異,兩版各成一史,均較完整。可見(jiàn),如果政治的力量強(qiáng)大并內(nèi)化為學(xué)者的自覺(jué)認(rèn)同,則政治與學(xué)術(shù)就沒(méi)有矛盾。40年揮,80年代闡釋?zhuān)溟g的過(guò)渡當(dāng)然充滿緊張和苦惱,在兩頭卻似乎圓融無(wú)礙,水到渠成。
二政治家的哲學(xué)化
哲學(xué)家認(rèn)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學(xué),哲學(xué)與政治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有相互接近的趨勢(shì),這是政治家進(jìn)入哲學(xué)史的基礎(chǔ)。
古中國(guó)有君師合一、政教合一的傳統(tǒng),在此傳統(tǒng)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蔣、毛都有“老師”情結(jié),蔣愛(ài)以“校長(zhǎng)”自居,毛在給個(gè)人崇拜降溫時(shí)仍愿保留“偉大導(dǎo)師”。自然,對(duì)于始終以“革命者”自期的政治家來(lái)說(shuō),傳統(tǒng)觀念的存續(xù)并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中國(guó)全能政治的需要。領(lǐng)袖不只是擁有至上權(quán)力,更應(yīng)當(dāng)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權(quán)威,以其道易天下。所以在繁重的軍政事務(wù)之際,他們都一度成為哲學(xué)著作家。認(rèn)為:“有了哲學(xué)基礎(chǔ),然后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確定。一切榮辱,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一個(gè)人沒(méi)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xiǎn)的時(shí)候,就難免變節(jié),臨到富貴貧賤轉(zhuǎn)變的時(shí)候,也難免變節(jié)。”(舊版第108頁(yè))也認(rèn)為:“一切大的政治錯(cuò)誤沒(méi)有不是離開(kāi)辯證唯物論的。”(陳晉主編:《讀書(shū)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31頁(yè))他們都認(rèn)識(shí)到,為著實(shí)現(xiàn)治國(guó)平天下的大業(yè),哲學(xué)不但可以用而且必須用。
哲學(xué)如此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從晚清開(kāi)始,注重自我意識(shí)、反抗權(quán)威、重心貴力的陸王心學(xué)及大乘佛學(xué)獨(dú)得盛大發(fā)揚(yáng),在不同時(shí)期擔(dān)當(dāng)了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之責(zé)的蔣、毛兩人,均對(duì)陸王心學(xué)深有體會(huì),都認(rèn)識(shí)到革命需要的個(gè)體的堅(jiān)強(qiáng)意志和犧牲精神。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duì)立,但他們的哲學(xué)卻有兩個(gè)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有言:“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復(fù)興中國(guó),完成革命,并沒(méi)有什么困難,只是在我們一念。……只要個(gè)個(gè)人照著自己良心上所認(rèn)為應(yīng)該做的事去做,則一切不好的動(dòng)念,如個(gè)人的意見(jiàn)和私仇可以消除凈盡,這是致良知。”(舊版第110—111頁(yè))在《矛盾論》也使精神突破物質(zhì)的限制:“我們承認(rèn)總的歷史發(fā)展中物質(zhì)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但是同時(shí)又承認(rèn)而且必須承認(rèn)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huì)意識(shí)對(duì)于社會(huì)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duì)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反作用。”后來(lái)更是越來(lái)越強(qiáng)調(diào)人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動(dòng)性,提高中國(guó)人民的能動(dòng)性、熱情,鼓吹變革現(xiàn)實(shí)的中國(guó)是可能的。”(《讀書(shū)筆記》第828頁(yè))二是強(qiáng)調(diào)行動(dòng)。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cuò)誤觀念,就是要實(shí)實(shí)在在地去做。”(舊版第110—111頁(yè))不但早期即有“與天奮斗其樂(lè)無(wú)窮,與地奮斗其樂(lè)無(wú)窮,與人奮斗其樂(lè)無(wú)窮”的名言,后來(lái)也認(rèn)為“先行后知,知難行易”(《讀書(shū)筆記》第863頁(yè))哲學(xué)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礪主體意志,鼓舞行動(dòng)勇氣,這里的意志是有明確的目標(biāo)和統(tǒng)一的紀(jì)律的意志;行動(dòng)是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性政治軍事斗爭(zhēng),他們的哲學(xué)是掌握群眾的理論,是變?yōu)槲镔|(zhì)的精神。蔣、毛都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哲學(xué)王”——按照英國(guó)學(xué)者巴克的解釋?zhuān)袄硐雵?guó)”的“哲學(xué)家不能對(duì)國(guó)家進(jìn)行任意的動(dòng)搖和變化,他應(yīng)當(dāng)讓它在對(duì)其基本原則的忠實(shí)尊奉中保持穩(wěn)定,靜物一樣的穩(wěn)定。”(厄內(nèi)斯特?巴克:《希臘政治理論》,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頁(yè))
蔣、毛是否有入史的資格,要由史家來(lái)審查。確實(shí),我們沒(méi)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學(xué)史把拿破侖、俾斯麥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寫(xiě)進(jìn)去。羅馬皇帝奧勒留之入史,不是因?yàn)樗腔实郏谄洹冻了间洝肥撬苟喔鹬髁x的經(jīng)典,而且奴隸出生的愛(ài)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樣的哲學(xué)地位。但是,蔣、毛的哲學(xué)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獨(dú)語(yǔ),而是現(xiàn)代中國(guó)牢籠百態(tài)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一度為無(wú)數(shù)人所信仰。抗戰(zhàn)前周佛海說(shuō)過(guò):“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lǐng)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引自艾思奇《<中國(guó)之命運(yùn)>——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xué)》,《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頁(yè))1958年,柯慶施等人也說(shuō)過(guò):“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引自李銳《的晚年悲劇》,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頁(yè))這種個(gè)人崇拜的言論,反映的是一種“主義”言說(shuō)是如何成為一種真實(shí)的動(dòng)員力量,并深刻地導(dǎo)引、規(guī)范著所屬時(shí)代的文化思想,這就是毛的名言“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義。所以“主義”云云不一定是哲學(xué),卻常常支配著哲學(xué)。比如賀麟的唯心認(rèn),一方面固然有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的資源,另一方面也與“主義”取同一主張:“新的中國(guó)哲學(xué),主張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礎(chǔ)上,精神的基礎(chǔ)上。沒(méi)有精神,什么都沒(méi)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礎(chǔ)才是最鞏固的基礎(chǔ)。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貴相知心,甚至戰(zhàn)爭(zhēng)也以攻心為上。”(舊版第68頁(yè))49年以前的哲學(xué)史要寫(xiě),49年以后的哲學(xué)史要寫(xiě),迄今為止,海峽兩岸關(guān)于毛、蔣的哲學(xué)研究已是汗牛充棟,其中不都是宣傳。
三哲學(xué)家的政治關(guān)懷
在現(xiàn)代哲學(xué)家中,賀是政治關(guān)懷較深的學(xué)者。49年以前,對(duì)他也禮遇有加,數(shù)次召見(jiàn),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學(xué)校講課,而且其侍從室在戰(zhàn)爭(zhēng)期間直接支持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xué)名著編譯委員會(huì)”,如賀所說(shuō):“自從民國(guó)三十年中國(guó)哲學(xué)會(huì)西洋名著編譯委員會(huì)成立后,我們對(duì)于西洋哲學(xué),才有嚴(yán)格認(rèn)真,有系統(tǒng)的有計(jì)劃的經(jīng)過(guò)專(zhuān)家校閱夠得上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的譯述和介紹。”(舊版第26頁(yè))以“抗戰(zhàn)領(lǐng)袖”而關(guān)心純粹哲學(xué),賀有知遇之感。馮友蘭也是官方學(xué)者,其《新原道》從孔子開(kāi)始一直寫(xiě)到自己的“新統(tǒng)”,卻沒(méi)有孫中山、的位置,甚至還批評(píng)過(guò)孫中山的學(xué)說(shuō)。賀不但在政治上維護(hù)蔣,還通過(guò)重心強(qiáng)調(diào)、歷史聯(lián)系、補(bǔ)充發(fā)揮等方式努力使蔣的哲學(xué)精致化、學(xué)理化。49年以后,賀麟的政治熱情沒(méi)有降溫,且很快與時(shí)俱進(jìn)。“當(dāng)他第一次讀完《新民主義論》以后,就產(chǎn)生了,當(dāng)年第一次讀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講演集時(shí)的類(lèi)似感受。”(楊子熙:《賀麟的生活與哲學(xué)》,《會(huì)通集》,三聯(lián)書(shū)店,1983年,第17頁(yè))1951年,賀表示“參加改變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適時(shí),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讓他參加寫(xiě)作班子,賀主動(dòng)寫(xiě)了《兩點(diǎn)感想,一點(diǎn)反省》一文發(fā)表。1957年4月,召見(jiàn)周谷城,賀奉命作陪。周谷城回憶:“大家受到領(lǐng)導(dǎo)同志的鼓舞,學(xué)習(xí)理論的熱情都是很高的。賀麟同志則更積極,大有盡棄所學(xué),專(zhuān)讀馬、列、毛書(shū)之概。記得大約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參加政協(xié)組織的參觀學(xué)習(xí)團(tuán),路過(guò)上海,順便到我家談天,看到我書(shū)架上亂七八糟的書(shū),幾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質(zhì)與記憶》;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時(shí)間與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則是詹姆斯的《極端的經(jīng)驗(yàn)主義》,他不抽了,笑著對(duì)我說(shuō):‘盡看這些!’”(賀麟:《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講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賀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
新的政治認(rèn)同改變了他對(duì)現(xiàn)代哲學(xué)的認(rèn)識(shí)。他對(duì)胡適的實(shí)驗(yàn)長(zhǎng)期持批評(píng)態(tài)度,但對(duì)胡適其人甚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適:“先生近年為國(guó)宣勞,功績(jī)至偉,而對(duì)學(xué)問(wèn)如此努力,寫(xiě)作收獲如此之多,使國(guó)內(nèi)朋友聞之莫不欣佩奮勵(lì)。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國(guó)思想史》早日寫(xiě)成出版。麟近應(yīng)《五十年來(lái)的中國(guó)》編者潘公展先生的約,寫(xiě)有《五十年來(lái)的哲學(xué)》一文,文中有兩三處提及先生,雖覺(jué)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見(jiàn)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閱,尚祈指正。”(《胡適來(lái)往書(shū)信選》下冊(cè),中華書(shū)局,1980年,第40頁(yè))但數(shù)年后,賀卻開(kāi)始批判胡適“反動(dòng)的資產(chǎn)階級(jí)唯心論思想”,至有“胡適成為美帝國(guó)主義的走狗,成為頭等戰(zhàn)爭(zhēng)罪犯,與人民公敵一文一武,異曲同工,決不是偶然的”等語(yǔ)。對(duì)于舊版中高度評(píng)價(jià)的哲學(xué)家們,1961年卻認(rèn)為“他們把西方哲學(xué)某一流派與他們喜愛(ài)的中國(guó)哲學(xué)某一流派相聯(lián)系,來(lái)一個(gè)‘中西合璧’,這樣就使得自己的哲學(xué)思想有一點(diǎn)‘創(chuàng)造性’,自創(chuàng)體系,自己搞一套雜湊的哲學(xué),更可以欺騙和影響較多的讀者、青年。……這種所謂‘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東西,既不是客觀科學(xué)地介紹西方哲學(xué)思想,也不是實(shí)事求是地整理中國(guó)的古典哲學(xué)著作,沒(méi)有推動(dòng)學(xué)術(shù)文化的向前發(fā)展,反而拖著向后退。”(賀麟:《加強(qiáng)對(duì)西方現(xiàn)代哲學(xué)的研究》,《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講演集》第176頁(yè))當(dāng)然,在1986年的氣氛中,胡適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學(xué)家們已開(kāi)始卷土重來(lái),賀已無(wú)須按五、六十年代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修改了。他應(yīng)該慶幸自己沒(méi)有五、六十年代修改舊作,那意味著馮友蘭的遭遇在等著他。
賀的政治關(guān)懷不是被動(dòng)的。他早就認(rèn)為:“凡是一個(gè)哲學(xué)家,與政治家總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哲學(xué)思想與政治思想亦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兩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應(yīng),終必殊途而同歸。”(舊版第69—70頁(yè))他是對(duì)政治敞開(kāi)大門(mén)的哲學(xué)家。1941年《學(xué)術(shù)與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說(shuō)明“獨(dú)立自由”和“脫節(jié)”根本是兩回事。“一個(gè)學(xué)者求學(xué)術(shù)的獨(dú)立與自由,有時(shí)誠(chéng)應(yīng)潔身自好,避免與政治發(fā)生關(guān)系。……但須知獨(dú)立自由與‘脫節(jié)’是兩回事,求學(xué)術(shù)的獨(dú)立自由可,求學(xué)術(shù)與政治的根本脫節(jié)就不可,學(xué)術(shù)與政治不但須彼此獨(dú)立自由,還須延緩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許多獨(dú)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個(gè)健全的近代社會(huì)。”此論完全正確,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軌道、政府專(zhuān)制獨(dú)裁的現(xiàn)代中國(guó),學(xué)者的“潔身自好”,學(xué)術(shù)的超然脫節(jié),很可能助長(zhǎng)政府的胡作非為,最后仍不免要傷害學(xué)者和學(xué)術(shù)。所以賀特別批評(píng)學(xué)術(shù)界逃避政治、視政治為畏途的現(xiàn)象:
在初期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代,學(xué)術(shù)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學(xué)術(shù)自由獨(dú)立的立場(chǎng),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污濁的政治,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賣(mài)國(guó)政府,不與舊官僚合作,不與舊軍閥妥協(xié)。……學(xué)術(shù)界這種獨(dú)立自由的態(tài)度,可以說(shuō)是為腐朽殘暴的北洋軍閥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們不能羅致有力的新進(jìn)分子,去支持陳舊腐敗的局面;間接有助于國(guó)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雖有不少紛亂,學(xué)術(shù)上的自由獨(dú)立,仍然保持相當(dāng)?shù)乃疁?zhǔn),但是學(xué)術(shù)界的人士,對(duì)于統(tǒng)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國(guó)民政府,態(tài)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脫,不理會(huì)是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界的普遍現(xiàn)象。到了七七事變,學(xué)術(shù)界的人士,也就進(jìn)而對(duì)政府取盡量輔助貢獻(xiàn)的態(tài)度,政府對(duì)于學(xué)術(shù)界也取咨詢尊重的態(tài)度,我們希望我們中國(guó)漸漸有自由獨(dú)立的政府,來(lái)尊重自由獨(dú)立的學(xué)術(shù),同時(shí)也漸漸有自由獨(dú)立的學(xué)術(shù),來(lái)貢獻(xiàn)于自由獨(dú)立的政府了。(《學(xué)術(shù)與政治》,《文化與人生》,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第246-247頁(yè))
賀此論基本上是站在國(guó)民政府的立場(chǎng)講話。學(xué)術(shù)脫離政治在北洋軍閥時(shí)代之所以是對(duì)的,因?yàn)樗陀^上支持國(guó)民革命。賀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民政府基本上是滿意的,1945年給胡適的信中就說(shuō):“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敗狹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義中,國(guó)民黨貢獻(xiàn)最少者亦惟民生。共產(chǎn)黨人黨見(jiàn)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較少民主精神也。”(《胡適來(lái)往書(shū)信選》第40—41頁(yè))
1956年,賀把政治上的忠誠(chéng)奉獻(xiàn)給此前曾批評(píng)過(guò)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黨,再度批評(píng)學(xué)術(shù)脫離政治的現(xiàn)象∶
但是共產(chǎn)黨和領(lǐng)導(dǎo)的人民政府做了數(shù)不清的驚天動(dòng)的偉大事業(yè),有著無(wú)限的威信,為全國(guó)人民所衷心愛(ài)戴,所有知識(shí)分子、專(zhuān)家、學(xué)者們大都興奮感激,擁護(hù)歌頌之不暇,更沒(méi)有人愿意脫離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會(huì)主義的革命建設(shè)。所以現(xiàn)在的問(wèn)題已不是脫離政治的問(wèn)題,而是知識(shí)分子在他的專(zhuān)業(yè)基礎(chǔ)如何依靠黨,得到黨的幫助和指導(dǎo)的問(wèn)題。(《知識(shí)分子怎樣循著自己專(zhuān)業(yè)的途徑走向社會(huì)主義?》《哲學(xué)和哲學(xué)史論文集》,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0年,第449頁(yè))
舊版擁蔣,新版頌毛,賀的哲學(xué)觀一貫通。他沒(méi)有指出甚或沒(méi)有注意的是,學(xué)者主動(dòng)以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于政治是一回事,在號(hào)令下把學(xué)術(shù)政治化或以政治取代學(xué)術(shù)是另一回事。其間的關(guān)鍵是政治家是否承認(rèn)并尊重學(xué)術(shù)獨(dú)立,政治本身又是否“獨(dú)立自由”?無(wú)視這個(gè)差別而要求學(xué)術(shù)與政治的聯(lián)系,即使理論上說(shuō)得通,實(shí)踐上也只會(huì)導(dǎo)致學(xué)術(shù)的取消。以賀本人為例,曾經(jīng)寫(xiě)出過(guò)《時(shí)空與超時(shí)空》、《知行合一新論》、《宋儒的思想方法》、《辯證法與辯證觀》這樣文章的人,后來(lái)除了批判和翻譯,基本上沒(méi)有真正的哲學(xué)論文,以至于在遲暮的1988年,只能抒發(fā)對(duì)舊作一往深情:“《文化與人生》一書(shū)雖然在編排方面有不少缺點(diǎn)和錯(cuò)誤,初次在報(bào)刊上發(fā)表時(shí),讀者尚有較好的反響。我自己也感到相當(dāng)滿意。”(《文化與人生》,商務(wù)印書(shū)館,1988年,新版序言)
四政治家的哲學(xué)地位
賀是哲學(xué)中人,并沒(méi)有在政治學(xué)說(shuō)與哲學(xué)之間劃等號(hào)。他的標(biāo)準(zhǔn)是:“至于哲學(xué)的職責(zé),則一方面要超出常識(shí),成立一貫的理論系統(tǒng),另一方面又要解釋何以常識(shí)表面上最易接受,而理論上欠貫徹的地方。如果要成立一種學(xué)說(shuō),就事實(shí)言,必能解釋問(wèn)題范圍內(nèi)所涉及的一切事實(shí),不能有一個(gè)例外。只消有一個(gè)例外,則此項(xiàng)學(xué)說(shuō)便發(fā)生動(dòng)搖,須得修正;就理論言,則該項(xiàng)問(wèn)題中的主要概念必須加以嚴(yán)密的分析,而下一謹(jǐn)嚴(yán)的界說(shuō)。對(duì)于概念和概念間的關(guān)系,必須建立有基本的原則,以作立論的根據(jù)。簡(jiǎn)言之,‘據(jù)界說(shuō)以思想,依原則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論所必須遵循的方法。必須這樣,才可得到普遍必然貫通的而不矛盾的真理或理論系統(tǒng)。”(舊版第71頁(yè))據(jù)此,孫中山、對(duì)知行學(xué)說(shuō)有貢獻(xiàn),所以可以入史,而馬克思主義“壓根兒就沒(méi)有哲學(xué)興趣,他們只徒摭拾黑格爾幾句口頭禪,牽強(qiáng)附會(huì)以為他們的信仰作辯護(hù),以為他們的主義作宣傳,他們的興趣本既不在哲學(xué),更不在了解黑格爾的哲學(xué)。”(賀麟:《黑格爾》,譯序,商務(wù)印書(shū)館,1936年)之所以提到辯證唯物論,只是因?yàn)樗恰熬乓话恕鼻昂笫觊g的思潮之一,要專(zhuān)辟一節(jié)予以“批判”。
然而,“為信仰作辯護(hù)、為主義作宣傳”是政治家的天職,馬克思主義如此,孫中山、又何嘗不是如此?舊版其他哲學(xué)家均有批評(píng),獨(dú)對(duì)孫、蔣只有聯(lián)貫、闡釋、發(fā)揮而無(wú)任何批評(píng)。從賀對(duì)孫、蔣的細(xì)密鋪陳來(lái)看,他并非在做應(yīng)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壓力下的政治表態(tài),而是基于學(xué)理的評(píng)論。但我們注意到,在賀頗為自得的《知行合一新論》一文中,卻沒(méi)有孫、蔣的位置,這表明對(duì)知行問(wèn)題提出“新論”,并不需要以孫、蔣為出發(fā)點(diǎn)。他們之進(jìn)入哲學(xué)史,借助的是賀麟的力量。賦予一種政治論說(shuō)以哲學(xué)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xué)地位的一種方式,它主要通過(guò)哲學(xué)家來(lái)完成。
還是共產(chǎn)黨人干脆。1941年,艾思奇發(fā)表《抗戰(zhàn)以來(lái)幾種重要哲學(xué)思想述評(píng)》一文,給哲學(xué)下的定義是:“哲學(xué)是各階級(jí)黨派的世界觀,是他們認(rèn)識(shí)事物的理論基礎(chǔ)和方法指南。”(《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549頁(yè))所以,不但辯證唯物論,陳立夫的唯生哲學(xué)、閻錫山“中的哲學(xué)”、國(guó)家社會(huì)黨的哲學(xué)、中國(guó)青年黨的哲學(xué)、張申府的哲學(xué),都是當(dāng)時(shí)“重要的哲學(xué)思想”。后來(lái)也說(shuō):“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nèi)绻梦ㄎ镛q證法,那就還需要補(bǔ)學(xué)一點(diǎn)它的對(duì)立面和形而上學(xué),康德和黑格爾,孔子和,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讀書(shū)筆記》第691頁(yè))黨派世界觀就是哲學(xué),哲學(xué)研究就是政治斗爭(zhēng)的一環(huán)。在比較陳立夫與閻錫山時(shí),艾思奇竟然能發(fā)現(xiàn)他們?cè)跈?quán)力系統(tǒng)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權(quán)時(shí)間:“‘中’的哲學(xué)不同于唯生論,在社會(huì)基礎(chǔ)上說(shuō),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來(lái)才當(dāng)權(quán)的國(guó)民黨當(dāng)局者的世界觀,而‘中’的哲學(xué)卻是民國(guó)以來(lái)就統(tǒng)治自成一個(gè)局面的地方政權(quán)當(dāng)局者的哲學(xué)。”(同上,第571頁(yè))賦予哲學(xué)以政治意義,這是政治家取得哲學(xué)地位的另一種方式,它主要由政治家自己來(lái)完成。
然而,不是任何政治家都可以進(jìn)入哲學(xué)史的。政治家與哲學(xué)家不同,他不是在哲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作具體的研究和學(xué)術(shù)的推進(jìn),其在哲學(xué)上的地位,主要不是其具體的論述和學(xué)術(shù)上的創(chuàng)造,而在于以其地位和影響力,或無(wú)意識(shí)中轉(zhuǎn)移一時(shí)風(fēng)氣、引領(lǐng)時(shí)代潮流,或有意識(shí)地借助權(quán)力推行自己的觀點(diǎn),給一時(shí)代的哲學(xué)打上烙印。政治人物有大有小,有顯有隱,能夠發(fā)揮這種影響且又為學(xué)者目力所及的,只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通常就是最高統(tǒng)治者,哲學(xué)史有其勢(shì)利的一面。支持國(guó)民黨的賀麟40年以前不會(huì)想到把陳立夫和閻錫山請(qǐng)進(jìn)哲學(xué)史,49年以后的大陸哲學(xué)史,除了以為批判對(duì)象外,一般也不再提及陳、閻等人。當(dāng)然,大、小,顯、隱是不斷變化的,40年代的哲學(xué)固屬統(tǒng)治思想,亦非書(shū)齋學(xué)者,不但其《實(shí)踐論》發(fā)表后不久就成為共產(chǎn)黨控制區(qū)域的哲學(xué)經(jīng)典,而且在毛的倡議下,艾思奇、何思敬等于1938年9月發(fā)起成立“延安新哲學(xué)學(xué)會(huì)”,許多機(jī)關(guān)、學(xué)校也成立了哲學(xué)小組。后來(lái)說(shuō):“過(guò)去在前線聽(tīng)到延安新哲學(xué)學(xué)會(huì)成立,前線同志聽(tīng)了都很高興,引起了研究新哲學(xué)的興趣。因此,兩年來(lái),辯證法大大地發(fā)展了,在華北及全國(guó)的一切進(jìn)步地區(qū),都研究著新哲學(xué)。”(許全興:《與中國(guó)20世紀(jì)哲學(xué)革命》,當(dāng)代中國(guó)出版社,1998年,第357頁(yè))確實(shí)在局部地區(qū)影響了中國(guó)哲學(xué),作為一個(gè)掌握政黨、擁有軍隊(duì)、治理數(shù)千萬(wàn)公民的領(lǐng)袖,毛至少遠(yuǎn)遠(yuǎn)比一些學(xué)院哲學(xué)家更重要。賀麟可能看不到《實(shí)踐論》及毛的哲學(xué)影響,但即使看到了,他也不會(huì)把寫(xiě)進(jìn)舊版。政治成見(jiàn)而外,在49年以前的論著不具有那樣的全國(guó)性,他作為中國(guó)哲學(xué)家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取得的,與此同時(shí)則下降為臺(tái)灣地區(qū)的哲學(xué)家。所以,即使在1986年寫(xiě)“五十年來(lái)的中國(guó)哲學(xué)”,毛似乎也不能取代蔣的位置。以毛易蔣的理由只能是哲學(xué)的:的哲學(xué)比的哲學(xué)更有創(chuàng)造性,更能代表中國(guó)哲學(xué)的進(jìn)步。
但賀沒(méi)有把理由講出來(lái)。其哲學(xué)史寫(xiě)作、修改的實(shí)踐表明,一旦涉及到政治家,賀的哲學(xué)判斷就不太清明。1988年在檢討其“吹捧”的錯(cuò)誤時(shí)說(shuō):“殊不知的目的、方針、政策均與孫中山相反,因而使得這書(shū)很早就在臺(tái)灣出版。”(《文化與人生》新版序言)吹捧自非哲學(xué)家所宜,類(lèi)似“這是他自己偉大人格的寫(xiě)照,自己實(shí)行主義矢死不二,忠貞精誠(chéng)的態(tài)度的自白。這也充分表現(xiàn)他之所以能領(lǐng)導(dǎo)革命偉業(yè),領(lǐng)導(dǎo)抗戰(zhàn)建的大業(yè)的精神基礎(chǔ)”之類(lèi)也很肉麻,(舊版第115頁(yè))但蔣之能否入史與其是否背叛孫中山無(wú)關(guān),孫不是哲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其他任何政治都不是哲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孔子有云:“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賀麟的變化只是時(shí)空環(huán)境變化的產(chǎn)物,而不是哲學(xué)思想的變化,正是孟子所謂“望道而未之見(jiàn)”。
熱門(mén)標(biāo)簽
哲學(xué)論文 哲學(xué)理論論文 哲學(xué)科技論文 哲學(xué)思想論文 哲學(xué)研究論文 哲學(xué)畢業(yè)論文 哲學(xué)知識(shí)論文 哲學(xué)史論文 哲學(xué)觀論文 哲學(xué)創(chuàng)新論文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