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文教育管理論文
時間:2022-06-02 10:36:00
導語:哲學人文教育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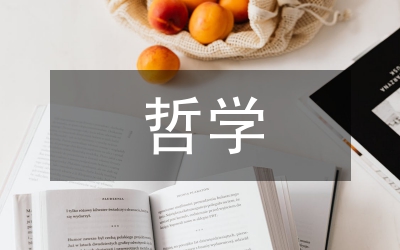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這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上面說的是文學部和它主要承擔的本科教育,再來看東大的大學院即研究生院。1992年東大的大學院由12個研究科構成,即:人文科學研究科、教育學研究科、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社會學研究科、經濟學研究科、綜合文化研究科、理學系研究科、工學系研究科、農學研究科、醫學系研究科、藥學系研究科、數理科學研究科。這些研究科也可以看成為研究生院的系。在研究科下設專攻(專業),1992年時人文科學研究科下有20個專業提供研究生課程,如西洋史學、東洋史學、考古學、倫理學、心理學、美術史學、哲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德國文學、中國哲學、印度哲學等。當然,并不是每個研究學科下都有這么多專業,除了工學系下有25個、理學系下有14個專業外,其他系科的專業較少,如法學政治學有4個、經濟學有3個、社會學有2個、數理系只有1個專業。人文學科的碩士課程和博士課程構規定有必修的學分,碩士課程標準修習年限為二年,博士(第一種)課程標準修習年限為三年。中國哲學專業的碩士課程必修學分為16,選修學分為14,課程修了者即獲得學位;博士課程必修學分12,選修學分8,共20個學分。
在以培養本科學生為主的觀念下,應當這樣說,大學院的研究生課程是由學部的教員來兼任的。每一專業在每一年都有事先制訂的教學課程。以1992年為例,東大大學院的中國哲學專業設14門課程,其中10門為特殊研究,4門為演習。特殊研究相當于我們的專題課,演習相當于我們所謂資料課。1992年的特殊研究課程,從殷周青銅器到清代思想與文學,幾乎各個斷代都有安排,并且這些課程大多是跨兩個學期的。這也就意味著,一個從外面來到東大的人,在任何時候都會有這么多課程可供選擇。我也才明白,為什么來北大的進修學者常常抱怨我們開的課程少。1992年擔任中國哲學專業課程的有14位教官,教授8人,副教授4人,非常勤講師2人。所謂非常勤講師,是指外聘的兼課教師,不在本校編制之內,但其本人的職稱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14人中12人為本校教師:4人來自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3人來自教養學部,4人來自東洋文化研究所,1人來自社會科學研究所。用我們的話來說,4人是系里面教研室的教師,8人則來自校內的基礎課和研究所。該年度與哲學相關的任課者共60人,其中教養學部6人、研究所10人,非常勤13人,這意味著有將近50%的任課人員來自文學部之外,即使只計算不在編的外校兼課者,也達22%。而按1995年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課程來看,9位教師擔任的16門課程,5人是自外校聘請的非常勤講師。在教育資源共享的方面,東大的經驗應該是可以借鑒的。
1995年東京大學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將大學院的人文科學研究科和社會科學研究科合并為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并提出把大學院重點化、部門化。就是說,大學院將取代文學部成為大學的重點,成為部門的名稱,大學將轉變為以培養研究生為主。這也就是池田教授文章那句開門見山的話的來由。而此后文學部的教學就應當說來由大學院的教師兼任了。這一年大學院的專業設置更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調整,不僅研究科和專業大加改變,專攻下又設研究方向,研究方向又可分為若干專門分野(專門領域)。如整個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改編為五個大專業:基礎文化研究專業、日本文化研究專業、亞洲文化研究專業、歐美文化研究專業、社會文化研究專業。五個專業下共有18個研究方向,這18個研究方向又共包括27個專門領域。在基礎文化研究專業的四個研究方向中有“思想文化”,其下又分為哲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四個專門領域。而在亞洲文化專業的三個研究方向中第一個是“東亞研究”,其下有三個專門領域:中國語中國文學、東亞歷史社會、東亞思想文化。這個“東亞思想文化”專門領域便是我們以前顯赫的“中國哲學”在今天的棲身之所了。換言之,從前所謂“中國哲學”的研究,在今天的東大大學院,不僅不屬于“哲學”學科,也不屬于“思想文化”研究方向,而變成“東亞研究”方向下的一部分了。事實上,中國文學、中國史和中國思想一樣,在這個新的格局中也都業已變為“東亞研究”方向的某一方面了。
日本大學的人文教育中向來只有“論文博士”的制度,即博士課程研究生畢業后,經過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的積累,在50歲左右時再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為博士學位的申請論文,通過一定的答辯程序(不一定在母校),獲得文學博士的學位。因此,博士研究生在“課程修了”之后,不必作博士論文,當然也不得博士學位,隨即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工作。90年代日本大學教育改革的一個動因是在“國際化”的潮流中建立“課程博士”制度的需要。在課程博士的制度下,博士研究生修得所有必需學分后,撰寫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通過即獲得博士學位,一般稱為課程博士,以與傳統制度的論文博士相區別。這無疑是對近十年大量外國學生在日本留學而要求獲得學位相適應的。據池田教授的文章說,東大94、95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為研究生在五年中提供建立在廣闊視野之上的跨學科教育,為社會輸送兼有專深知識和廣闊視野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同時,經過這些改革,“文學部在擁有與本科一一對應的研究者的基礎上,完成了向以培養研究者為任務的大學院大學的轉變”。說明近來的體制及學科改革都與課程博士制度的建立及大學基點的轉型背景有關。
透過東大近年在教育目標(大學院大學、課程博士)、教育體制(專業設置、講座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我們更注意的是其中所體現的學科調整和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變化。集中起來說,就是:擴大文化研究,發展地域研究,注重跨學科交流。特別是尋求一種整合的“亞洲研究”的意識非常強烈。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地域研究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亞洲研究”上面。從前東亞各國的各個方面的具體研究,現在都被納入一種“亞洲研究”的框架和視野中來重新審視和研究。在一般的意義上來看,日本80年代后期以來對文化研究和地域研究的強調,包括晚近對社會史研究的強調,顯然都是受到美國的人文社會研究的流行模式和趨勢的影響。特殊地說,在東亞的整合性研究方面,東大的人文學改革是與日本學術界80年代后期以來“亞洲研究轉向”是一致的,是受到此種研究發展的影響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3年開始出版至1995年全部出齊的七卷本的“從亞洲出發思考”(參看孫歌在《讀書》上的介紹)的宏篇巨制,不僅被許多學校立即作為參考書,東大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1995年即在“多分野交流”課程中設“‘從亞洲出發思考’的思考”系列討論班課程,由該書撰寫者輪流主持相關討論,引起了相當多的注意。1996年度開設的“歷史與地域—亞洲史中的日本殖民地”、“亞洲文化與民族主義”課程,都是在該書的研究框架引申出來的多學科交流的亞洲學研究專題。
東京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當然不能代表日本人文社會教育的全部,在有關哲學的教育方面,早稻田大學便與東大不同,其他學校也往往各有其特色。但以東大的地位和影響來說,該校近兩年的改革及其所反映的日本人文學研究的變化動向應當是值得注意的。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有著自己的傳統和理解,有在中國現代化過程遭遇的特殊課題,但在中國的人文學及人文學教育處在轉型和摸索的今天,注意了解外部世界的變化,及其對我們所具有的意義,更是必不可少的。
我個人的專業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研究在日本和東大曾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國哲學”也是東大的一個老專業,文學部一直有“中國哲學研究室”。甚至于80年代以前,東大有關中國的研究學會就稱為“中國哲學研究會”。但從80年代后期開始,東大中國哲學會改為“中國社會文化學會”,并主辦了水平很高的《中國—社會與文化》集刊(雖然學會的事務所仍設在東大老的中國哲學研究室),突出顯示了以東京地區中年學者代表的、要求日本的中國學從傳統的“漢學”模式(以及戰后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中國研究模式)向歐美“中國研究”模式的轉變的新潮流。現已擁有會員近1200人,其中與中國思想研究相關的學者約280人。1994年起,大學院的中國哲學專業和文學部的中國哲學研究室,皆將“中國哲學”改名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在這個改變中,“中國”雖然得到保留,而中國的“哲學”被消融在文化研究之中。與東大雙峰并峙的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研究室”也隨之改為“中國古典文獻學”。1995年后,東京大學大學院改革的結果是,大學院里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又被“亞洲文化研究”專業的“東亞思想文化”專業方向所取代;就是說,“中國”亦復消融在亞洲研究之中。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特質,日本民族重視經驗研究的傳統,日本國家當代的戰略選擇,這些因素各在此種變化中發生了何種作用,很難簡單地揭示出來。但無論如何,這種變化將會對今后幾十年的日本學術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面對并注意這種變化,尤其是“中國哲學”的變化,作為以研究中國哲學自命的學者,我的心情自然是很復雜的。在這篇文章里,盡管我給自己的任務是描述這一變化而不是評價它,可我仍然想說一句,那就是,在當代世界學術交互影響的今天,亞洲人文學領域發展和擴大文化研究、社會研究、地域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理所當然的;而另一方面,日本漢學的傳統及其成績,歷來為世界學術界所公認,如何在發展新的研究模式的同時,又能繼續發揚日本漢學的傳統特長,恐怕仍然是日本新一代學者面臨的重要課題。
- 上一篇:教育局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工作會講話(縣)
- 下一篇:哲學原創性敘事研究管理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