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08 10:57:00
導語:義和團運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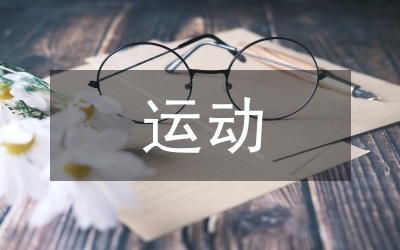
九十年前,當歷史開始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在中國的心臟地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西方侵略的群眾運動。事變肇端於山東地區零星發生的民教沖突,從一八九九年起事態像脫僵的野馬一樣迅速發展,演變為一股席捲整個北中國的排外浪潮。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沒有明確的宗旨,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仇恨——是仇恨將來自不同地域,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們組織為一支隊伍;是仇恨引導他們拆除鐵路,割斷電線,焚毀教堂并包圍使館區;又是仇恨使得他們忘卻恐懼,拿起冷兵器時代的武器抗擊馬克沁機槍和克虜伯缐膛炮裝備的八國聯軍。在一八九九——一九○○年運動高潮期間大量表現出來的癲狂行為是人類在飽受外部刺激、累積的敵對情緒超出心理抑制閥限(注一)情況下的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應。引發這種反應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純粹的利害沖突,而是屈辱,一種深入人心靈的屈辱。祗有當尊嚴遭到最粗暴地踐踏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會迸發出這樣野蠻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將義和團運動置於世界歷史的背景前面,我們就會看到這樣一幅圖景: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產業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經濟、軍事、技術的優勢瘋狂地掠奪殖民地,瓜分「勢力范圍」,在人類的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國家關系體系(注二)¾¾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統治世界的國際秩序——原來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國家關系的規范被規定為國際關系準則,作為這些規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學則提升為普遍的國家行為的道德基礎。隨著十九世紀中后期西方的勢力和影響空前膨脹,基督教民族對其文化和哲學的信心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傳教士將他們的神奉為「唯一真神」,以一種不可抑制的熱情反對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實業家和商人則是世俗的傳教士,他們將西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奉為人類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帶著同樣的宗教狂熱強迫其它民族接受他們的哲學和價值觀。當所有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國家政策的層面上反映出來的時候,人格化的國家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注三)也就扮演了熱衷於使和它們文化背景不同的國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師]的角色。迅速發展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軍事優勢為西方國家將其意志強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國際關系體系則替這種國家行為簽發了一份「通行證」。對「文明國家」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一個使它們的權力欲不斷得到滿足的機制,而對非西方民族來說,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則是一個使其每時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機制;越是熱愛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就對這種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強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熱情幫助基督教民族擴張勢力和影響,在世界的范圍確立了西方的統治;而當這種自信和熱情發展到利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肆無忌憚地觸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傷害這些民族歷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時候,事物的發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滲透激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首先作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發展起來的近代民族主義成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幟;被壓迫民族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不斷沖擊著以基督教民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國際關系體系。
作為世界范圍民族主義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和團運動為我們提供了一樁在國際關系中由文化和哲學的對立引發國際沖突的典型個案。本文將分四個部分探討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和義和團運動之間的聯系,以及義和團運動對我們建立一個健康的國際秩序有什么啟示。
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源於三十年戰爭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十五世紀末之后,歐洲各主要國家開始進入絕對主義時代。絕對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級君主制(注五),權力從分散的貴族那里集中到專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國家逐步演變為中央集權的近代民族國家。各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動給國際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內容:曾經盛極一時的封建領主的私人外交隨著封建主的沒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國家開始作為新型的外交主體登上了權力斗爭的舞臺。倫敦、巴黎、華沙、馬德里、維也納、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取代了中世紀星羅棋布的采邑成為歐洲的權力中心。圍繞著領土和權力,新興的民族國家展開了縱橫捭闔的外交活動和軍事斗爭,力圖最大限度地攫取國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將幾乎所有的歐洲強國都裹挾進去。戰爭的殘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國的君主普遍意識到只有確立一個包括共同利益、規則和單一價值觀的國家關系體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續受到損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亞條約》(TheTreatyofWestphalia)重新劃分各國領土和德國各諸侯的領地,將武力作出的裁決以多邊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三十年戰爭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的催生婆,在戰爭的瓦礫?焉希桓鋈碌墓手刃蚩汲魷幀8菝攔收窩д吒ダ椎呂錕恕な媛難芯浚鞣焦夜叵堤逑抵饕ǎ?/P>
1.相互承認擁有國家主權的國家。
2.以國際法的原則處理相互關系。
3.根據[勢力均衡]的政策謀求本國生存的國際社會是通過基督教結合起來的。(注六)
這一關系體的內容是由中世紀末期以來歐洲的政治現實——幾個勢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長期對峙;共同利益要求一個包容所有國家的集體安全體制以避免永無止盡的國際沖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們在尋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時可以找到共同的語言——所決定的。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時也正是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蓬勃興起,科學技術和工商業的結合使得生產力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業增長和科技進步賦予西方國家關系體系以無限擴張的可能性。可以說,這一體系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擴張,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不是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這一調整各平權主體關系的道德規范體系在世界范圍的簡單的復制,而是一個維護西方國家對世界統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這一秩序里,西方國家集團是立法者和審判者,源於西方哲學和價值觀的國際法和國際習慣是法律條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保證法律實施的強制力。[眾神之王]用[閃電霹靂]確立了奧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則用[堅船巨炮]確立了近代國際關系體系。這一進程始於西方國家關系體系開始向外擴張之時,在十九世紀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狂潮中最后完成。這樣,歷史的際會就將宰治世界的權力第一次交給少數幾個國家;這些國家是人類歷史上最幼稚的國家,剛剛經過一場反對神權的人文主義運動的洗禮。在這浪潮的沖擊下,宗教的節制精神被擯棄;古代社會的禁忌傳統遭到徹底的破壞;禁錮千年的人欲從「所羅門銅瓶」(注七)中釋放出來,像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熱烈的歡呼。沒有節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種子。隨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向全世界擴張,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充滿對立、沖突和動蕩的時代。
早在西方國家關系體系形成之前,舊大陸另一端的中國就出現了在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導下的邦國部族關系體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合體制。相傳「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遠近貢入賦棐」(注八)。「貢賦」這一象征著政治上臣屬關系的經濟義務的規定,標志著廣大地域內的部落已經聯結為圍繞著一個權力中心的政治共同體。紀元前十七——十一世紀的商代是信史時代的開端。留存下來的文獻資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個文明的曙光剛剛照亮天際的時代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比較成熟的邦國關系體系──「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屬國的領土,由封君管轄;「內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職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辭」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東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記錄,可與文獻相佐證。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注一三),在邦國關系體系內部和商展開了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紀的武王革命結束商朝六百年的統治,實現了王朝嬗代。對時人來說,殷周交替不僅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政治變故,而且也是一場觀念形態和社會心理的大震蕩——曾經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飛煙滅;古帝的血胤淪為下賤的奴隸(注一四);偉大的邦國滅亡了,就像一片枯葉在瑟瑟秋風中隕落——歷史運動的「勢」無情地嘲弄了人間的力量和人類視為永恒的價值。親身經歷鼎革巨變的人們無不為命運的無常所震怖。他們相信一個國家的運祚是由人格化的「天」決定的;「天高聽卑」(注一五),根據世人的所作所為降下吉兇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終謹慎地行使權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運。繼承商朝政治遺產的周人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態建設一個以「禮」為核心的邦國關系體系。周代(紀元前十一世紀至紀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級諸侯受封建國,拱衛王室,就像滿天的星斗圍繞著北極星作有規律的運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狀熊下的國家關系體系完全不同的原理運作的。在這里,國家行為的動因不是無魘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測的主宰的畏懼;國際政治不是對國家權力進行精密運算的高等數學,而是尋求宇宙和諧的藝術。當追逐土地、財富、權力的欲念澄靜下來,對萬物主宰的敬畏籠罩人心的時候,天地間便呈現出和諧、肅穆、莊嚴的美。這種美源于人類對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時間的魅力。在人欲橫流的時代,它就像一盞明亮的燈,引導著在蠻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鄉。
十四世紀后期明帝國(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隨著理學運動和政治權力的結合,中國開始進入古代哲學全面復興的時期。體現這一哲學的畿服制也在亞洲大陸東部的廣大范圍內重新建立起來。明清時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個層次:
1.朝廷直接管轄的行省。
2.臣屬于中央政府的少數族自治政權。
3.和中國保持「朝貢」關系的附屬國。
作為東亞的主導國家,中國放棄了蒙古人的擴張主義政策,它把建設一個合乎古代圣賢政治理想的和諧的宇宙秩序視為最大的利益。困擾民生的普遍義務兵役制被廢除,火器制造技術在它的故鄉原地踏步——如果說人類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黃金時代」,那么,它就是從「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時候開始的。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擴張到東亞大陸之前,中國領導下的國際社會維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礎不是「勢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熱衷于使用力量的人們的手中;唯其如此,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紀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圖上,畿服制的疆域隨著清帝國國力的衰退逐漸萎縮;而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正挾工業文明釋放出來的巨大的能量緩緩西來,前鋒直逼亞洲大陸東部。根植于人類對天人關系截然相反的認識的兩個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時空的原野上發生激烈的碰撞。
二
一八四○年六月出現在澳門海面的懿律艦隊中斷了一個古老的民族連續的歷史發展,以此為起點開始了近代中國坎坷多舛的歷程。義和團運動不是發生在草原民族像蝗蟲一樣蹂躪中原的時候,也不是發生在海上的倭寇像狂飆一樣襲擾沿海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一起典型的「近代事件」。
「近代」在這里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它還表示發端于中世紀末期的亞平寧半島的一股勢力在其緩慢的但確定不移的擴張過程中、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打下的烙印。這股勢力就是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逐步統治世界的「近代文明」。作為一個對古代世界崇拜外在力量的宗教反動的宗教體系,它信奉這樣的教義:人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人類的欲望是神圣的「最高存在」,只有不斷地滿足欲望,靈魂才能得到拯救;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或充棄存在的權利。」(注一七)正如對上帝的崇拜開創了中世紀,對人的自身的崇拜也開創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嶄新的時代——「近代」。「近代」是和謙卑、儉藥、誠篤、虔敬這些美好的德行格格不入的時代。在「理性」這面旗幟的指引下,人類不僅向養育自己幾百萬年的大自然發動了一場十字軍遠征,而且還將討伐的鋒芒指向它的同群。
當維護中世紀歐洲國家關系的基督教信念在懷疑主義思潮的沖擊下逐漸幻滅的時候,舊世界也就無可挽回地走向分崩離析。從「卡諾落晉見」(注一八)到「阿維農之囚」(注一九),梵蒂岡在失去精神世界的權力的同時也喪失了它在塵世的權力;曾幾何時,那些匍匐在教皇的權杖下的國家已經成為歐洲的真正的主宰。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圍繞著權力運轉的機制。納入這一體系的國家就像見到了紅布的斗牛一樣瘋狂地追逐著「國家權力」。不信「業報」,也不信「末日審判」,新世界完全泯滅了良知和道義感。對它來說,權力就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財富,就意味著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意志強加他人以獲得邪惡的滿足。這是一個由恐懼心、羞恥心、艷羨心、競爭心等情感叢集而成的強磁場,一個民族的靈魂一旦「吸附」其中,它就永遠喪失了選擇自己命運的自由。和歷史上游牧民族簡單粗糙的「野蠻」相比,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所體現的「文明」代表了我們這顆藍色的星球上自有生命以來出現過的最復雜最高級的「野蠻形態」。「文明世界」將自然界這所巨大的角斗場的競賽規則發揮到了可以稱為完美的極致;而在這些規則背后的,又是一個將所有宗教的魔鬼在萬神殿的神龕里面供奉起來的宗教。
在十七世紀后半期以及整個十八世紀,當黑暗隨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擴張的腳步吞噬著新舊大陸廣袤的土地的時候,偉大的「天朝」在世界的東方正煥發出人類文明的燦燦的光芒。中國周邊的民族懷著仰慕之心將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擬為「天朝」,不僅因為中國的力量,而且還因為它的以「禮」為核心的優雅的文化傳統。「禮」是一種代價,可以理解為人為了主宰自己的命運作出的必要的犧牲。在「禮」的背后隱藏著人類對「必然」的恐懼和對「自由」的熱望。從邈古洪荒不可窮詰的歲月以來,人類就在自然界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和其它的物種一起旋生旋滅,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冥冥的上蒼,直到這么一天,當它意識到需要約束其自然屬性,并且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時候,人才真正脫離了動物界,作為完全意義上的人在大地上站起來。古代的中國人將「禮」視為文明和野蠻的分野。「諸夏」之所以為「諸夏」,不是因為種族和血統的高貴,而是因為它經過「禮」的熏陶;而「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注二○)「夷狄」不論擁有多么強大的力量,在本質上和禽獸并沒有什么區別。自從前十一世紀周公制訂了包括畿服制在內的「周禮」之后,中國人就將「禮」的文化作為自己永久的精神家園。當腐朽沒落的人本主義思潮和「黑死病」一起在歐洲肆虐的時候,以人類的自身完善為宗旨的偉大的理學運動正風靡整個東亞大陸。這是一次由儒家學派的矩子和明清兩代賢明的政治家同領導的人類靈魂的革命,就像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在幾代人的時間內締造了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社會。前近代中國將重新發明的古典哲學看作滋養生命的五谷;儒家學派經典的研究蔚然成風;綰黃紆紫的「圣人之徙」是整個社會的良師,他們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民區分善惡。
中土不聞「天演」之說久矣,「為國以禮」的思想已經作為全社會的共識而深入人心。在清代有關歷史上的民族沖突的大量的通俗小說、戲曲、彈詞(注二一)、子弟書(注二二)中,中國是和詭詐暴戾的蠻族相對立的「禮義」的化身,它的勝利通常被公式化地表現為接受蠻夷君長逞遞的「降書順表」的道義上的勝利。信念可以造成人類想像力的障凝:就像二十世紀的公眾不能設想離開欲念我們這顆星球還能照常運轉一樣,中古時代末葉的中國人也很難想像一個沒有「禮義」的世界。
一七九三年九月,由馬戛爾尼爵士率領的龐大的英國使團經過將近一年的旅行前來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天顏」。他們不僅帶來了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鐘表、車輛、軍器、船式等「英國文明的成果」,而且還帶來了由中國自己體面地向日益迫近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打開大門的一個機會。萬樹園的主人非常禮貌地招待了來自遠方的賓客。但卻帶著滲透到每一個毛孔的驕傲將這個機會像塵埃一樣輕輕地抹去。當一個人知道自己正看護著從周公孔子那里薪傳不絕的文明的火種、而這火種燎原之后會為廣漠的宇宙帶來光明和溫暖的時候,他的驕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復也就是一個有著四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民族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作出的答覆。當這個度盡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紀后期終於找到自己的歸宿的時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貴的價值,而什么祗不過是歷史的長河中漂浮著的泡沫。
文明常與孱弱結伴,就像野蠻往往與力量搭擋,這是人類的一個宿命的悲哀。鴉片戰爭之后,被不列顛的炮艦強行納入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中國,突然發現它面對著自兩晉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來又一輪「胡化運動」的沖擊。如果說「文明世界」在處理人類的種群內部關系方面與其「前驅」相比取得了什么顯著的「進步」的話,那就是野蠻民族「恢復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沖動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一個無限地催發欲望的信念體系。新時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經不再滿足於僅僅征服遼闊的土地,他們還要征服無論是阿提拉大帝還是成吉思汗都無力染指的世界——人類的心靈。在近代歷史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進程中,近五百年來沐浴著人類文明的中國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令人窒息的「動物文明」。「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樣離奇的悲劇題材」(注二五)。
三
從邁入「近代」門檻的時候起,中國就為接踵而來的內變外患困頓不堪;但從一個歷史的長期看來,真正的危機直到十九世紀六○年代反洋教運動漸起波瀾之時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國的基督教勢力從一開始就和搭載炮艦而來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結下了不解之緣。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自后有傳教者來中國,一體保護。」(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廈條約》規定:「除傳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還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倘有中國人將佛西闌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注二八)一個宗教如果墮落到了需要憑籍與暴力的聯姻來維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為信仰體系已經棟折榱崩。倚仗著「文明世界」的軍事力量和不平等條約給予的特權在中國「布道」的基督教是一個和拿撒勒人耶穌在巴勒斯坦宣傳的貌合神離的基督教。以自律、寬容、博愛、謙遜著稱的基督教過「近代文明」這個醬缸幾個世紀的浸染已經面目全非,當此之時在基督的頂上仍然熠熠放光的只能是體現著時代精神的「國家利益」的光圈了。十九世紀中后期遣派來華的樊國梁安治泰們尊奉的「神」是民族國家征服異民族的卑鄙齷齪的情態;傳布的「福音」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深入到脊髓的敵視情緒;而他們孜孜矻矻經營的「上帝的事業」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列強稱霸世界的宏圖大計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為了「使上帝的榮光在中國顯現」。(注二九),教會不僅肆意祗毀「中國所守孔孟之道」(注三○),而且還「縱教民干預公事,挾侮官長,甚至地方匪類假冒招搖而各教士輒出護持,使各州縣不得行其法。」(注三一)基督教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等級森嚴的世界秩序構成致命的威脅。
當兩個世界秩序的沖突以儒教和基督教相互訐格的形式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展開的時候,它就比斬將搴旗的戰爭更加驚心動魄。對于一個嚴謹的儒教社會來說,傳教士無異霉菌和酵母;只要他們來到一個地方,那里的空氣就要發酵,水源就要污濁,人的道德就要腐敗,和諧寧靜的生活就要遭到破壞。中國的民眾可能目不識丁,也可能不知道周公孔子,但他們都從融入血液的道德信條受到褻瀆的事實感受到和中國社會內部的壓迫完全不同的壓迫,它使每一個曾經涵濡教澤的中國人血脈賁張怒發如狂。「凡一種文化值衰弱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所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注三一)生於「禮崩樂壞」的衰世,近代中國的紳士階段品味到了迎風待月詩酒弦歌的前輩們沒有體驗過的文明變遷的「黍離之悲」。濫觴於基督教世界的野蠻化浪潮就像上古時代的洪水一樣洶涌滔天,注定要吞沒他們心目中圣潔的宇宙圖景。「披髮左衽」的夢魘將中國的紳士階級推到了反洋教運動的潮頭。他們用流言、傳單、揭帖、書刊戰斗,教一個不知道仇恨的民族什么是種族仇恨。「強盜入室,埋寶穢土」;只有筑起一道壁壘森嚴的「夷夏之防」,中國的性靈才不至于在這場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澌滅淪喪。就這樣,引發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火山大噴火」的地應力一點一點地在近代中國歷史的深厚的巖層下面蘊蓄起來。
一個偉大的國家往往會遇到被迫在生存和信念之間作出痛苦的抉擇的時刻,這樣的場合在它的領導人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如果將曾經開創「康乾盛世」的清帝國在外部勢力的侵襲和國內政治變動的交替打擊之下終於在本世紀初走到盡頭的歷史看作一幕巨大的悲劇,那么秉國將近半個世紀的慈禧太后(一八六一——一九〇八年)就是這幕悲劇的中心人物。太后是一個靈魂屬於古代世界的統治者,自始至終都沒有沾染近代民族國家領導人不可救藥的「商人氣質」。在她看來,中國不是廣袤的土地和繁庶的人口的簡單的復合體,它的本質是一團在黑暗的宇宙中熊熊燃燒的火焰;如果這火熄滅了,那么即使她的國家有著強健的肌體,也不過為弱肉強食的世界貢獻一具行尸走肉。對於「生存競爭」奉為圭臬的十九世紀國際社會,太后只有生理上的厭憎和靈魂深處的鄙夷。伴隨著權力的高度責任感使她對「用夷變夏」的任何企圖切齒腐心。
初,戊戌上聽康有為言變法,擢用新黨。……於是太后復出聽政,立誅新黨數人,捕有為及其徒啟超。有為走英,啟超走日本,皆庇焉。遂與諸大臣等謀廢立,以上有疾頒視天下,微醫,三日一視臣工醫案,病益篤。而八國公使合詞以法國名醫某為薦,太后拒不納,又固請,不可已,遂入診。審辯良精,奏言某經當有患,然決於圣壽無慮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為至日本,與啟超為《清議報》,則譏宮闈無所諱。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已亥冬李鴻章為粵督,謀誅有為等。鴻章至粵不報,久之,乃奏言有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注三三)
傳教士還要用「上帝的靈光」掩飾其不可告人的動機,而「文明國家」甚至連最后這點遮羞布也覺得蕪累;只要能滿足膨脹的權力欲,這些嫻於馬基雅弗利主義的國家就可以毫不猶豫地用最卑鄙最無恥的方式公然踐踏國際關系領域的公共道德。一面以正式的外交關系承認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另一面又通過支持的方式對這種合法性提出異議,還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來傷害一個自有歷史以來就一直發揮著主體作用的國家的自尊嗎?「…戊戌之變政,已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實一貫以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論十年之朝局。」(注三四)
義和團運動不是一兩個階級的運動,而是整個民族的運動。上自太后以及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野老稚童,只要還有人類正常的情感和良知,就無不在祛除西方的勢力和影響方面發生強烈的共鳴。這個愛惜羽毛的民族在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之下蒙受了六十年的屈辱,現在再也無法忍受下去,累積了整整六十年的仇恨就像地層深處的溶巖一樣噴薄而出。義和團運動為我們展示了一幅人類在絕望的心理支配下進行自殺性報復的圖畫:
大劫當頭,血水橫流,就在今秋;但看鐵馬東西走,誰是誰非兩罷休。(注三五)
人們渴血,不是流仇敵的血,就是流自己頸上的血;只有遍地的鮮血,纔能使狂躁的心平靜下來,纔能讓銹跡才斑斑的時間齒輪重新啟動。
一九○○年六月召集的幾次御前會議是義和團運動的轉折點。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的爭執與其說是主戰派主和派之爭,倒不如說是人類的情感和理性之間的論爭。論爭的結果其實早在論爭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安排好了――當仇恨像烈火一樣熊熊燃燒的時候,任何形式的理性都是瀆神的。在六月二十一日的儀鸞殿會議上,太后椎心戟指誓約:「今日之事,諸大臣均聞之矣,我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戰。故事未可知,有如戰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諸公今日皆在此,當知我苦心,勿歸咎予一人,謂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注三六)當日頒布的宣戰上論聲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茍且圖存,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雄雌。」(注三七)這樣,一個主權國家,而不是松散的群眾團體,就作為行為主體向高踞在近代國際關系頂端的西方國家集團實施了不計后果的極端的報復行為。復仇的國家不受任何國際法和國際習慣的約束,甚至不顧及自身的利益,國家行為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渲不可遏制的仇恨。
四
從近代國際關系體系開始統治世界的那一刻起,「公正」就在國際政治領域悄然匿跡;因為這一體系的運轉正是以每時每刻戕殺「公正」為前提的。債發生在民族國家固執地相信實力已經為它們在道義的銀行開設了無限透支的帳戶的時候,并隨著權力的運作不斷地增值。「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而「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注三八)。「公正」注定要在塵世落實;如果不能由一個社會機制的運轉實現,就只有通過對這一機制的毀壞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報復是神圣的――欠下一磅肉就要還一磅肉,一滴血也不差(注三九),錙銖不爽的宇宙平衡器借助人類的報復實現了社會公正。義和團運動是一則暗示著近代國際關系體系將在人類復仇的火焰燒灼下走向毀滅的寓言――奔突不息的地火從歷史的斷裂處噴涌而出,將覆罩著世界的虛假的外殼燃為灰燼;偉大的歷史運動以最率直最粗魯的語言傾訴著蘊藏在宇宙深處的精神本質:
沿河一帶建樓房,扯旗放炮逞剛強;有朝西北真主來,一炬火光化無常。(注四○)
八千十萬神兵起,掃滅洋人世界新。(注四一)
在家好,在外好,在數難逃。(注四二)
你們不是迷信人間的力量嗎?但在永恒的時間看來,這種力量簡直不足齒數,它不能庇佑你們逃脫懲罰;「紅陽末劫」(注四三)到來的時候,你們的行為將會得到應有的報償。
二四加一五,這苦不算苦;遍地紅燈照,那苦才算苦。(注四四)
義和團運動還不是「末日審判」,它只不過是歷史老人的一次相當溫和的告誡。
由義和團運動引發的國際社會的震顫并沒有持續多久,脫離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沖動很快就被維護這一體系的暴力鎮壓下去。物質戰勝了精神,「文明國家」制服了桀傲不馴的「野蠻人群」,基督教民族的赫赫武功也不知道第幾百次證明了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就像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合乎永恒的自然法則。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是培育近視和淺見的最好的溫床;正是在目光如豆的現實主義觀念的引領下,二十世紀的世界在「國家意志」這一魔性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人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注四五)近代國際關系體系這位一切歷史時期最偉大的魔術師終于在公元一九四五年開始表演它的壓軸節目――核時代。這是怎樣一個概念呢?一觸即發的核武器的當量已經超過廣島原子彈的一百萬倍;「人類將被消滅多次這一從邏輯上說來不可能的事在技術上已是可能。」(注四六)核力量是人類追逐權力的貪欲主使下從自然那里盜來的贓物。「屬于凱撒的還給凱撒,屬于上帝的還給上帝」,人類可以輕易地引爆核武器,但卻永遠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操縱這本質上不屬于自己的力量。當本世紀驅近尾聲的時候,核武器迅速擴散的陰云正在與日俱增;《防止核擴散條約》(注四七)所起的作用僅限于將可能在明天發生的危機推遲到后天發生。與核擴散的危險日益加劇同時,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正以流水線作業的規模永不間斷地制造著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共戴天的仇恨――人類共同體的生存環境已經毒化到了沒有明天的地步。對于「第三世界」的人民來說,「文明世界」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啟蒙先生;它不僅盡心竭力地栽培手執左券而又喪失心智的「拳匪」,而且還教他們如何使用「引魂幡、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混天大旗、火牌、飛劍……」(注四八)。「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注四九)。如果這門課程繼續講授下去,還要做什么呢?等著贊美造物主的偉大吧。
一部歷史貫穿著永不停息的天人之爭――當人類懷著敬畏之心有條不紊地規劃前景,天地鬼神也奈何不得的時候,人是強大的;而當它放縱天性,將自己的明天拱手交給「上帝之手」的時候,人是虛弱的。近代世界在征服外宇宙的戰爭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利品,失去的只有一樣,但卻是最最寶貴的一樣――對自己命運的把握。從天人之爭揭開序幕的時候起,人類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卑屈猥瑣地拜倒在「自然」的腳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幻想小說作家儒略·凡爾納(注五○)的作品今天讀來已經像是在講述本世紀初發生的故事了――應當感到毛骨悚然啊,人類搭上了駛向未來的列車,而它不知道這趟車會將自己帶到哪一個站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連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也無法遏制人類進行精神探險的勃勃雄心的時候,我們時代面臨的災難就是一個定數。古羅馬作家奧維德在其大作《變形記》中記敘了這樣一個故事(注五一):
日神的兒子法厄同糾纏他的父親,要求駕著日神的飛馬在空中馳聘一天。慈愛的父親諄諄告誡他的兒子:你的要求太過份了,你的力氣和年紀都辦不到,它的名字叫作「災難」。但是法厄同不聽他的話,還是提出原來的要求。無奈的父親只好引他到烏爾岡所造的高大的車輦前面。
年輕的法厄登上了輕車,興高采烈地握住韁繩。日神的四匹快馬感到車輦的載重和往常不同,就亂奔起來,離開了原來的軌道。發愁的法厄同從天頂往下看,臉色發白,兩膝發軟,后悔不該駕他父親的馬。太陽車一直向前沖去,就像風中的船,船上的舵手把不住舵,索性放了手,讓神去擺布。
最后軸脫輻散,破車的殘軀斷片散落一地。法厄同,火焰燒著了他的赤金色的頭髮,頭朝下栽下去,拖著一條長尾巴在空中隕落。遠離故鄉,在天的另一邊的厄里達諾斯河收容了他,洗凈了他余煙未息的臉。
法厄同慘遭殺之禍,不是因為他只是一個孩子,而是因為他不相信自己只是一個孩子,和法厄同一樣驕傲的固執的人類也在公元十四世紀「興高采烈地握住」了「近代文明」這根疆繩,開始了征服宇宙的漫漫長征。法力無邊的「理性」將引領著人類在「此岸世界」建成「千年王國」這一新時代的迷信就像癌細胞一樣從意大利半島擴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是天性啊,人永遠想辦到「自己的力氣和年紀都辦不到」的事。早在童年時代,人類就已經「洞悉」了包括宇宙的起源在內的所有的奧秘;也只有當它確信自己全知全能的時候,人才能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平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能力遠不能匹配膨脹的欲望,這支統治地球二、三百萬年的有生世界「黃金貴族」也像可憐的法厄同一樣正在一步一步地臨近它的「厄里達諾斯河」。
即將來臨的二十世紀將是人類在生存和信念之間作出最后抉擇的世紀。不是人類的文明克服了文藝復興運動以來逐漸統治世界的人本主義哲學,并將它丟進歷史的垃圾堆;就是這一從頭到腳都在流膿的哲學克服了人類文明,將文明連同它的載體一起送進墳墓。柔弱是生命的徵象,而僵硬則是死亡的朕兆――最可畏懼的就是在應當畏懼的時候根本不知道畏懼為何物。對于向下一個世紀邁進的人類來說,沒有比徹底變革已經病入膏肓的近代國際關系體系更為急迫的任務了。持續將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的結束為我們帶來了締造持久和平的一個機會,精疲力竭的世界在呼喚者和平。作為這一回合權力斗爭的最大贏家,「文明世界」也像鴿子一樣不時地咕咕著它的「和平新倡儀」,似乎比所有的民族都更關心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就像磨刀霍霍的屠夫念誦「南無」,從和平的劊子手那里發出的「和平」的呼吁褻瀆了「和平」這個最圣潔的詞匯。「文明世界」要的是什么樣的「和平」?它的「和平」的只能是在權力的天平上增減砝碼平衡出來的「和平」,只能是肆無忌憚地傷害鄰人而不遭報復的「和平」。這樣的「和平」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再過一萬年都不會有的。「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律條,比塵世的律條更高的律條。「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注五二),負債累累的國家要想躲過二十世紀的「義和團運動」,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一些。
已經讓冷酷刻薄的達爾文主義腐蝕了靈魂的世界永遠也不會明白,以實現邪惡的意志為旨歸的「國家權力」是毫無憑依的空中樓閣,因為主宰的奴婢沒有任何權力可言;建筑在人類的饕餮之性之上的「國家利益」不過是制造廉價的欣快感的可卡因和安非他命,正是在這欣快感的牽引下,國際社會正步履蹣跚地走向「地獄之門」。和寥廓的宇宙相比,人類的認知能力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永遠都是微不足道的。對人來說,真實的善不是成為宇宙的主宰,而是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天降災殃殺不仁,不仁人殺不仁人;不仁人殺何時了,自有仁人殺不仁。(注五三)
游身于震怖人心的「死亡游戲」之外,永遠把握著命運航船的方向舵,這纔是最根本的權力。
善者善惡者惡,善惡分明七月半;安者安亂者亂,安亂之時自然見。(注五四)
在道義帳薄上努力減少一些赤字,增加一些黑字,真正的利益就寫在這帳簿上面。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注五五)和平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贈賜――當它成為藍天白云底下的真實狀態之前,就首先作為一種靜謐肅穆的氛圍存在于人類的精神世界,就像微風拂過水面泛起一層漣漪,「求仁得仁」,作為對人類敬畏之心的酬答,上天也就將「和平」這最珍貴的禮品慷慨地賜予蕓蕓眾生。只有當「憂德之不建而不患力之不足」(注五六)成為全人類的共識的時候,我們纔能架構一個公正的以和平為旨歸的國家關系體系;也只有架構一個公正的以和平為旨歸的國家關系體系,我們的子孫后代和我們偉大的文明纔能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繼續繁衍下去。
注釋:
注一:指引起動物有機體反應的最低刺激強度。
注二:各種政治行為體(主要指國家)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的統一體。
注三:指能夠獨立地參與國際事務并在其中發揮影響的政治實體。
注四:君主獨裁的政權形式。專制君主擁有無限的權力,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器維持其統治。
注五:又名:「等級代表君主制」。中世紀歐洲王權借助等級代表機構實行統治的一種政權形式。
注六:見T.L舒曼《國際政治》,第四版,馬克勞·希爾書店一九四八年,第七四頁。
注七:見《一千零一夜》:〈漁夫和魔鬼的故事〉。
注八:《尚書·禹貢》。
注九:《尚書·酒誥》。
注一○: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八·一○·三。
注一一:胡厚宣《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錄》五三0。
注十二:郭沫若《卜辭通纂》四五三。
注一三:《左傳·襄公四年》。
注一四:《史記·宋微子世家》
注一五:《詩·小雅·大明》。
注一六:《國語·周語》,〈祭公諫征犬戎〉。
注一七:恩格斯《反杜林論》引論,《馬恩選集》第三卷。
注一八:十一世紀末葉,法蘭克里亞王朝皇帝亨利四世公開對抗教皇。一○七六年二月教皇宣布開除亨利教籍。亨利被迫于一○七七年一月至教皇駐地卡諾落表示懺悔。史稱「卡諾莎晉見」。
注一九:一三○九年,法王腓力四世將教廷從羅馬遷至法國南部的阿維農,開始了所謂教皇成為「阿維農之囚」時代(一三○九――一三七八)。
注二○:《禮記·曲禮上》。
注二一:一種流傳于中國南方的曲藝。有說有唱。以三弦伴奏。此指唱彈詞的底本。
注二二:盛行于清代的一種曲藝。由鼓詞派生。滿族八旗子弟所創。此指子弟書的底本。
注二三:吠陀(Veda)描述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情形:天帝Indra毀壞了敵人的城堡,解放牲畜,他們釋放河流(指破壞堤壩、引水渠等工程)。而其傳統的說法則是釋放宇宙本性的自由。
注二四:指大擴張時期的蒙古人。見(伊)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
注二五: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恩選集》第二卷。
注二六: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
注二七:同注二六。
注二八:同注二六。
注二九:傳教士郭實臘言:「上帝的榮光必在中國顯現」。《中國叢報》一八三二年八月,第一四○頁。
注三○: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三,第六二頁。
注三一:同注三十。
注三二:陳寅恪《王國維挽詞》。
注三三:李超瓊《庚子傳信錄》,見《義和團史料》上冊第二○七――二○八頁。
注三四: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注三五:「某仙師乩語」,見黃曾源《義和團事實》詩注。
注三七: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
注三八:《老子》七十七章作「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注三九:見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
注四○:「云游道人詩」,見孫敬:《義和團揭貼》,《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一六頁。
注四一:「津城土地尊乩語」,見王火選輯《義和團雜記》,《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注四二:「乩語」,寄生編《庚子荓峰錄》下卷。
注四三:白蓮教以為世界分為青陽、紅陽、白陽三期。紅陽期末將出現最后一次大劫。無生老母派彌勒佛下凡,大開普渡,遍殺惡孽。
注四四:「朱紅燈乩語」,見李杕《拳匪禍教記》,第三四六頁。
注四五:《老子》七十二章。
注四六:米·謝·戈爾巴喬夫《改革與新思維》第一七三頁。
注四七:NuclearNon-proliferationTreaty,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共十一條。
注四八:羅惇《庚子國變記》,見《清代野史》,第三八頁。
注五○:JulesVerne(1828-1905),法國幻想小說作家。著有《海底兩萬里》、《八十天環游地球》、《神秘島》等。
注五一:見楊周翰譯《變形記》第二章、一-三二八:〈法厄同駕日神車的故事〉。
注五二:《論語·八佾》。
注五三:「關帝圣君乩語」,孫敬《義和團揭貼》。《近代史資料》第一期,第一六頁。
注五四:「庚子六月乩語」,同上。
注五五:《詩·小雅·大明》。
注五六:《國語·晉語》「叔向賀貧」作「憂德之不建而不患貨之不足」。
- 上一篇:海德格爾良知之思論文
- 下一篇:孔子道德思想分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