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知識和責任研究論文
時間:2022-10-15 03:41:00
導語:哲學的知識和責任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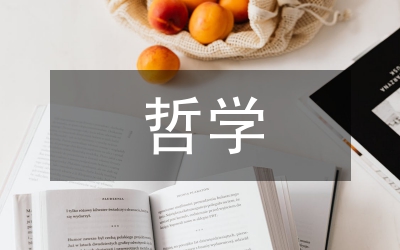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摘要:哲學是對智慧的追求。智慧至少應包含知識和責任兩個方面。一個聰明的人知道對知識的責任。哲學的知識是為理解世界的實在和人生的意義服務的,而人生的意義和道德的原理需要由哲學知識來論證。傳統的形而上學盡管有種種缺陷,但它們作為理性論證的世界圖式曾為這種論證做出過重大貢獻。后現代主義在批判形而上學的時候,把哲學的這種責任也拋棄了,這是導致當代哲學和道德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哲學知識;智慧;形而上學
Abstract:Philosophymeanspursuitofwisdom.Andwisdominvolvesbothknowledgeandobligation.Philosophicknowledgeaimsatunderstandingoftheexistenceoftheworldandthevalueoflife,andthevalueoflifeandtheprincipleofmoralscallforphilosophicknowledgetotheorize.Leakyinmanywaysasitwas,thetraditionalmetaphysicsasarationallytheorizedpatternoftheworld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theorizationofthistype.However,whenit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etaphysics,postmodernismdiscardsthisobligationofphilosophy,whichisoneofthekeyfactorsleadingthemoralcrisisincontemporaryphilosophicconsideration.
KeyWords:philosophicknowledge;philosophicobligation;wisdom;metaphysics
一
自古希臘起,哲學就確立了追求智慧的理念。什么是智慧呢?在我看來,智慧至少應包含知識和責任兩個方面。一個智慧的人懂得對知識的責任。哲學家作為一個追求智慧的人,不僅應該懂得如何獲得知識和運用知識,而且還應該懂得為什么要獲得知識以及對知識所產生的結果承擔責任。
自希臘起,就出現兩種稱呼自己為哲學家的人。一種是意識到對知識的責任的哲學家,以蘇格拉底為代表,他們認為“善”、“正義”與知識是統一的,他們從事哲學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善、美,他們通過學習哲學知識明確人生的目標,并投入到倫理的實踐中去。另一種是沒有意識到或不想對知識承擔責任的所謂的哲學家,以詭辯學派為代表,他們從事哲學工作的目的是為了牟利。他們教別人如何能把假的說成是真的,把非正義的說成是正義的,把丑的說成是美的。這樣,學會這些知識就能在法律訴訟等社會活動中牟利。我們可以把前者稱為真正的哲學家,而把后者稱為偽哲學家。整個哲學史充滿著真正的哲學與偽哲學的斗爭,它的勝負關系到人類的進步和希望。
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在其《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中充分論述了西方哲學史上追求普遍科學的理念的真正的哲學與懷疑論、相對主義和詭辯論的哲學的斗爭,論證由于實證主義、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的泛濫使得歐洲的科學和人的存在陷入危機,論證哲學家不僅要追求知識,而且要對人類的存在承擔責任。他寫道:
我們時代的真正唯一有意義的斗爭是存在于那些已經崩潰的人與那些還保持著根基、并為了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間的斗爭。這種歐洲人的真正的思想斗爭表現為哲學的斗爭,即表現為懷疑論的哲學,或毋寧說非哲學(因為它只保持了哲學的詞語而丟掉了哲學的任務)與那種真實的、依然生氣勃勃的哲學之間的斗爭。[1]16
作為一個哲學家,在我們內在的個人的工作中的這種對我們自己的真正存有所負的責任中,同時也承擔著對整個人類的真正的存有的責任。人類真正的存有是追求理想目標(Telos),從根本上說,它只有通過哲學,——通過我們,如果嚴格地說我們還是哲學家的話,才能實現。[1]19
可惜的是,胡塞爾在20世紀初葉所描述的這種哲學陷入危機的情況,至今仍在延續,而且變本加厲。胡塞爾對哲學家的責任的呼喚,現在聽起來更加切中時弊。
當代哲學危機的一個重要癥狀是這種偽哲學泛濫。試問,在當今哲學界,還有多少人真正把哲學的真理和哲學的責任當作一回事情。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玩世不恭的態度在今天的哲學界蔓延流行。哲學的知識被當作像商品那樣可出售的東西來對待。誰有權、誰有勢、誰有錢,“哲學家”就為誰做論證。就像古希臘時期的詭辯學派一樣,“哲學”成了為那些本來沒有理,而想成為“有理”的人服務的工具。只要誰能出好的價錢,“哲學家”就使誰的主張言之成理。這有點像那些為了錢而替人打官司的律師一樣。不過,律師是直接地為那些個體的人和團體作辯護,而哲學是間接地為那些更大的利益集團作辯護。如果說,律師是用某條法律為某個當事人作辯護的話,那么“哲學家”是在為有利于雇用他的利益集團的法律條文本身的“合理性”作辯護。我經常遇到這樣一些哲學家,他們今天可以為絕對真理作辯護,明天可以為懷疑論作辯護;今天可以為自由主義作辯護,明天可以為極權主義作辯護;今天可以為普遍主義的價值觀作辯護,明天可以為相對主義的價值觀作辯護。不論哪一種類型的基金會,只要能給錢,就為它們所立的項目效力。御用文人成了基金會所雇用的文人。哲學論文成了“基金”購買的商品。基金會提供的錢越多,炮制出來的“哲學論文”也就越多。
“哲學家”為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所中意的作辯護,并不會感到有多大困難。在哲學史上已經存在為各種各樣的觀點進行論證的論據,你只要隱去不利于某種觀點的論據,多找一些有利于它的論據,你就能夠為該觀點論證。正如歷史成了一種記憶(一些歷史事件)和遺忘(另一些歷史事件)的技巧一樣,哲學成了一種掩蓋(一些哲學論據)和彰顯(另一些哲學論據)的技巧。這樣,真正的歷史沒有了,真正的哲學也沒有了。哲學和歷史都成了為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效勞的工具。
由于這樣的哲學不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在弘揚真善美,因此,它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現在,普通人是不喜歡讀哲學著作的,這不是因為它們深奧,而是因為它們似是而非。就連哲學家自己也懶得讀他們自己寫的文章,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無非是為了項目費、為了評職稱而寫作的。這樣的哲學論文成了沒有人看的垃圾,它們浪費了時間、精力和紙張。哲學說到底不是因為其無用而在現代社會中受到冷落,而是它太想被別人利用而喪失了其信譽。
二
哲學為什么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的呢?這既有外部的社會原因,也有內在的哲學自身的原因。我們先從外部的社會原因談起。
當代社會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商品經濟的交換和買賣關系滲透到一切領域,就連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也打上了商品經濟的烙印。學生到大學讀書,被理解為購買知識;教師教書,被理解為出售知識。學術論文也被當作商品。一篇學術論文有助于直接或間接地提高生產效率,企業或社會的有關職能部門就愿意出錢“購買”它。這或者表現為購買專利,或者表現為科研開發提供資助。在當代大學里,人們也用商品交換的眼光看待哲學。一方面,哲學被認為無用,很少有人愿意出錢來購買哲學知識;另一方面,“哲學家”為了能夠出售哲學知識,就把哲學這種本來不是商品的東西制作為像商品一樣的東西出售。這就降低了哲學的品位,使得哲學變質為偽哲學。哲學要表現自己的使用價值,就說自己雖無小用而有大用。時下,經濟哲學、管理哲學、政治哲學、科學技術哲學流行。“哲學家”鼓吹,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科學技術的理論只是在小的方面提高經濟、管理、政治、科學技術的效益,而哲學能從根本上極大地提高它們的效益。我不否認哲學具有大用。但是這種以用為至上的哲學難道不是偏離了哲學的本性嗎?在這種只顧兜售自己的目的的驅動下,哲學本來所具有的那種社會批判的義務完全喪失了。
的確,哲學家也是現實商品經濟社會中的人,哲學教師也是一種職業,哲學家也食人間煙火,也要為自己的生計著想。但是哲學家比起其他的人來,更應意識到要超越于這種商品經濟關系的必要性。哲學家是社會的良心,哲學家要從這種社會的良心出發,反思現實的社會現象,進行社會批判,弘揚社會正義。
柏拉圖曾設想,在一個理想國中,哲學家應過一種沒有私人財產的集團生活。他認為,只有當人擺脫了私欲,才能看清楚哲學的真理。他在那時就意識到把哲學當作一種謀生職業的危害性。然而,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無從實現的,我們也沒有看到過哪一位哲學家是在這種理想的純凈狀態中被培養出來的。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哲學職業也像其他職業一樣,處于商品經濟的關系中。這樣,哲學家始終處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之中。為使哲學不至淪落為偽哲學,哲學家必須在塵世的現實性中獲得某種超越。哲學家更要注意自身的修養。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當代哲學陷入危機的內在因素。這與近半個世紀以來哲學本身的發展有關。可以說,哲學在當代迷失了自己,哲學自己否定了自己,哲學自己宣告了自己的終結。這是哲學在當代陷入危機的內在原因。
當代哲學常被標志為“后形而上學”或“后現代主義”。這兩個名稱本身就包含迷茫的色彩。似乎,我們現在除了用否定的方式來刻畫當前哲學的情景外,再也不能用肯定的方式來刻畫它的特征了,即我們除了能說出它是在形而上學之后、在現代主義之后外,就說不出它究竟是什么了。在16至18世紀,我們能以肯定的方式把當時西方的兩大主流哲學描述為英國的經驗論和歐洲大陸的唯理論。在18世紀我們能用“唯物主義”、“啟蒙哲學”來刻畫法國哲學的主要特征。在19世紀我們能用先驗唯心主義、思辨唯心主義來刻畫德國哲學的主要特征。在20世紀上半葉,我們能用邏輯實證主義、存在主義來刻畫那時西方哲學的主要特征。不論這樣的刻畫是否確切和全面,它們都是以肯定的方式表達的。但是20世紀后期以來,我們實在找不出以一種肯定的方式來刻畫現在的哲學了。現在的哲學只知道否定,不知道肯定;只知道解構,不知道建構;只知道批判,不知道弘揚。我們讀他們的著作,所能看懂的只是他們試圖表明別人所說的都不對,但看不清他們自己所說的究竟對在什么地方。他們以徹底打倒形而上學而洋洋自得。他們宣稱,以往的哲學在打倒一種形而上學之后,自己建立一種新的形而上學。現在,在他們打倒形而上學之后,不會再有新的形而上學建立起來。因為他們不是以一種新的體系哲學來批判一種老的體系哲學。他們在進行否定的時候,不從任何肯定的東西出發;在進行懷疑的時候,不依據任何確信的東西;在論證別人的系統不融通的時候,自己從來不闡明融通的思想。這就是所謂后現代主義的話語。在這樣的話語中,理解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相對主義、懷疑論成為時髦。這樣的哲學給公眾造成極壞的印象。難怪在他們眼里哲學成了一種毫無結果的文字游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哲學在當代陷入危機的內在原因。
三
什么是形而上學以及它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何在?這是當前哲學爭論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后現代主義者已經把形而上學搞成為一個貶義詞。我認為,為了使當代哲學擺脫危機,必須重新認識形而上學的積極作用。
傳統的形而上學固然有很多缺點。確實,沒有一種哲學體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是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各種各樣的科學理論不也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嗎?哲學理論要把各種各樣的知識貫通起來,自然更容易被找到漏洞。正如科學理論都有可能被推翻,不等于說不可能建立新的、更好的科學理論一樣,任何哲學理論都可能被指出問題、被反駁,不等于說不可能去修補它們,或去建立更完善的哲學理論一樣。固然,哲學不能代替科學知識,也不能脫離科學知識光憑自己的哲學玄想構造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但這不等于說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一個得到理性論證的世界圖式。
在我看來,哲學是一種得到理性論證的世界圖式。哲學與常識的世界圖式、宗教的世界圖式的區別就在于它是得到理性的論證的。人活在世上,總會有一種世界圖式。人從有關世界的總看法中獲得對自己人生的看法,指導自己的行為。有關宇宙起源、自然秩序、生物演化的觀點總是影響到對人生的觀點。放棄了形而上學就意味著讓常識的世界圖式或宗教的世界圖式來取代經理性論證的哲學的世界圖式。
常識中包含著世界圖式。但是常識中所包含的世界圖式并不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舉例來說,大魚吃小魚、狼吃羊、狗咬狗,是常識,這里包含弱肉強食的人生觀。母親愛小孩、見孺子入井而施以援手,也是常識。孟子從中得出人皆有惻隱之心,提出人與禽獸之辨,建立了他弘揚仁義的儒家哲學。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弘揚仁義的儒家哲學在中國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就不會有兩千多年燦爛的中華文明。當然也有那些為弱肉強食的人生觀提供論證的哲學。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哲學與哲學之間的斗爭。哲學斗爭是靠論證來進行的。哪一種哲學能夠(在哲學的意義上)獲勝,就在于它是否能夠提供更好的論證。
宗教也是一種世界圖式,并且也是一種提供希望的世界圖式。哲學與宗教的區別在于,哲學以一種理性的方式為世界圖式提供論證,而宗教用一種形象化的語言表述世界圖式。由于宗教的世界圖式常常是用隱喻來表述的,這就存在對這些隱喻進行解釋的問題。哲學可以為宗教中所包含的有關人類的美好理想、人與人之間的友善的關系提供理性的論證。正因為這個道理,宗教解釋學總要用到哲學。同時,哲學應從宗教中學習有關什么是人類的美好希望和理想,并設法用理性的概念來“翻譯"宗教的隱喻。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主要關注的是理想而不是現實,著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的論證,宗教容易產生狂熱和偏信。哲學的理性論證對于宗教的狂熱來說是一支清涼劑,并能起到糾偏作用。
有關哲學的世界觀與宗教的世界觀的關系,一直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的哈貝馬斯近來也承認這兩者在本質上有相通的地方:
有關理性與啟示的哲學討論的一個紐結點是一個一再浮現出來的想法:反思的理性追到深處就發現它自己的起源來自于另一個東西。它如若不想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死胡同而失去理性的導向的話,它就必須承認這另一種東西的命運攸關的力量。理性經由理性,用盡自己的力量,達到一種皈依,或至少引起一種回轉。這或表現為反思認知和行為的主體的自我意識(如在施萊爾馬赫那里)或表現為反思自己的生存的自我確認的歷史性(如在基爾凱郭爾那里)或表現為反思倫理關系的那種令人憤慨的撕裂。理性在一開始并不帶有神學的目的,但當它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時,就轉向另一面:不論它表現在一種與宇宙融為一體的包羅萬象的意識中,還是表現在一種對拯救的信息的歷史結果的捉摸不定的希望中,抑或表現在推進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繪制實現拯救的藍圖中。所謂包羅萬象的意識,傳說中的遠古事件,沒有異化的社會,無非是后黑格爾的形而上學中的匿名的諸神,它們對于神學而言是一眼就能識破的東西。它們可以被破譯為三位一體的人格的上帝的假名。[2]
哲學、日常經驗和宗教都能提供世界圖式。哲學所提供的世界圖式不僅更加精致,而且它提供了一種對世界圖式進行公共討論的平臺。由于哲學對世界圖式提供理性的論證,它的語言是主體間的、可理解的,那么這種世界圖式就是可公共討論的。有關各種各樣的世界圖式的缺點、問題都會在哲學的討論中暴露出來,從而使對它們的改進成為可能。哲學把不同意見引向公共的討論。通過討論,達成一定的共識。哲學把一切論點、論據、論證的過程都公開化了。哲學使人看到真相,哲學以理服人。哲學本身就是民主的。哲學也是民主的政治生活的一個必要的環節。哲學使人在進行民主表決之前,明白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抉擇。
宗教的世界圖式依賴于信仰。常識的世界圖式來源于日常的經驗、傳統和習慣。哲學的世界圖式立足于理性的論證。因此,相對于宗教的和常識的世界圖式,哲學的世界圖式是最容易服從理性的論據而改變的。依靠宗教信仰建立起來的世界圖式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常識的世界圖式是經年累月慢慢形成和慢慢改變的。哲學的世界圖式則會依據新的、更有說服力的論據而迅速改變。哲學最不惜改變自己。因此,總有新的哲學宣告誕生,總有新的哲學起來批判舊的哲學。因此,哲學常常擔當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催化劑的角色。新的哲學思想會逐漸滲透到宗教和常識中去,引起宗教的世界圖式和常識的世界圖式的慢慢改變。
哲學的世界圖式、宗教的世界圖式,就其內容而言,往往是交叉重疊的。我在這里所說的內容是指:世界是實在的還是虛幻的?在世界的多樣性中有無統一性可言?世界有無秩序,其變化有無規律、有無發展方向?對世界的這些看法勢必會影響對人生和人類歷史的看法。這就是所謂世界觀、人生觀、歷史觀的統一性。不同的宗教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哲學對這些問題也有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其中的一些哲學與一些宗教在這類問題上有類似的看法,因此它們能夠互相支持。常識通常傾向于認為世界是實在的,但常識并非是固定劃一的。由于每個人的生活環境和日常經驗不同,他們的常識的世界圖式也會有所不同。哲學的世界圖式在內容上并不一定不同于宗教的和常識的世界圖式,但它們的論證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在哲學的世界圖式、宗教的世界圖式和常識的世界圖式之間,不存在其中的一種世界圖式戰勝另一種世界圖式的問題,它們處在一種互相影響和水漲船高的關系之中。
世界觀和人生觀是統一的。哲學以理性的方式論證世界圖式,同時也為人的倫理原則進行論證。人為什么要認可和遵循倫理的原則呢?這就要追問倫理原則的合理性的問題。哲學要為它所支持的倫理原則的合理性提供論證,而這種論證要以對世界和人生的總看法為基礎。我們不能強迫人們遵循倫理原則。要人們自覺遵循倫理原則,就要提供合理的論證。這樣,哲學教育就成為一種倫理教育的方式。每個人自己學習哲學是一種自我教育和自我修養的方式。通過學習哲學,明白做人的道理,并自覺地按照這種道理來做人。
哲學的論證具有目的論的維度。哲學不僅問現實怎樣,而且問目標是什么。哲學追問什么是理想的社會,什么是人類所希望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樣哲學既不脫離現實,又超越于現實。由于哲學的這一特性,哲學對現實社會具有引導和批判的功能。哲學從人類的遠景和社會正義的原則出發,批判現存社會的不合理現象,引導它向著人類希望的方向發展。
四
20世紀初葉,德國現象學家胡塞爾意識到,實證主義等現代哲學對形而上學可能性的懷疑,使得哲學陷入危機,而這反過來也使得事實科學陷入危機。胡塞爾寫道:
由此必然導致整體思想發生一場特殊變化。哲學自身變得成問題了,并可以理解這首先表現在形而上學可能性的問題上。我們以前已經說過,這蘊涵地涉及整個理性問題的可能性和意義。至于實證科學,初看起來它是完全可靠地屹立在那里。然而,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問題歸根到底也涉及事實科學的可能性問題,因為在哲學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中事實科學有其關系意義,有其作為真理對于存有者的純粹領域而言的意義。在認識的理性規定什么是存有者的地方,難道理性和存有者能分開嗎?[1]12
20世紀中葉,胡塞爾有關哲學與實證科學關系的看法也在英美分析哲學家中得到某種響應。彼得·溫奇(P.Winch)在其《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反對把哲學視為“清除一些知識道路上的垃圾”的“小工”的實證主義的觀點[3]4。他認為:
科學家探求特殊的實在事物和過程的本性、原因和結果,而哲學家則關心實在本身及其一般意義上的性質。……哲學家追問“什么是實在”,這涉及人與實在關系的問題,這使我們超越了純科學。“我們要問,人的心智是否與實在有什么關聯,如果有,這種關聯會對他的生活產生怎樣的改變”。……哲學根本不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概念性的問題,它必定涉及實在的概念的力量。[3]9
分析哲學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特勞遜(P.F.Strawson)也主張不能對形而上學采取一概拒斥的態度,要承認歷史上的許多形而上學起過積極作用,并且至今仍然有必要研究形而上學。在斯特勞遜看來,形而上學無非是有關我們的整個知識的最基本的概念體系或概念綱要(ConceptualScheme)。我們的知識是要使用概念的。這些概念與概念之間有無互相聯系呢?如果有的話,把它們互相聯系的方式和關系揭示出來就是形而上學的一項任務。早期的分析哲學家主張,建立概念體系是科學家的工作。哲學家的任務是分析概念,澄清語詞的意義和句子的邏輯結構。斯特勞遜認為這樣的研究范圍太狹窄了。我們不僅要詢問我們實際是如何使用這個或那個語詞和句子的,而且還要尋找語詞與語詞之間,以及句子與句子之間的相互聯系的普遍規則和基本特征。各種科學理論都有其特殊的概念和對象領域,而哲學要找到它們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和揭示出我們的思想結構的最一般的特征。他寫道: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哲學上最好的、并且也是唯一穩當的方法依賴于對語詞的實際用法的細致考察。但是我們以此方式所能作出的辨別和所能確立的聯系,還不夠普遍和深入,還不足以滿足智性的形而上學的全部要求。因為,當我們詢問我們是如何使用這一或那一表達的時候,我們的回答盡管在一定的層次上進行了揭示,但有作出假定的傾向,而不是揭示形而上學家所想要揭示的結構的那些一般的成分。形而上學家所尋求的結構不是顯而易見地表現在語言的表面層次上,而是潛藏在深層。當那一個唯一穩當向導不能帶領他到達到他所希望到達的如此遠的地方去的時候,他就必須放棄這個向導。[4]
到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家看清楚了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一味反對形而上學的做法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就連曾是后現代主義陣營中重要代表人物的理查德·羅蒂(RichardRorty)近來也起來反叛后現代主義。他在2004年夏天來復旦大學做報告時宣告:后現代哲學一味解構,不搞建構,不提出新的烏托邦,不解決實際問題。后現代主義不是一條出路,后現代主義多半是破壞性的,沒有什么正面的建樹。(注:參見張慶熊《西方技術文化時代的問題和出路——思考羅蒂在復旦大學講演的深層意義》,《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第89-93頁。)
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曾是現代西方哲學的主流。他們反對哲學史上所出現過的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學學說,固然有其正當理由,但是他們在反對這些具有各種各樣問題的形而上學學說時,把一切對世界圖式進行理性論證的哲學都當作無經驗根據的和無意義的東西加以拋棄,這就造成當今哲學和人的生存的危機。試問,當這樣的哲學(形而上學)不復存在的時候,哲學如何能為倫理提供論證,如何能進行自覺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學習,如何能起到社會批判和社會引導的作用。我覺得當代哲學陷入危機的一個內在原因是哲學家忘記了哲學的責任。哲學知識不是一般的知識,而是具有責任的知識。只要哲學家記住哲學的責任,他們就不會只解構不建構,就不會只把哲學當作文字游戲來玩弄。哲學家決不能忘卻哲學文字的千斤重任。
[參考文獻]
[1]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2]JüRGENHABERMAS,JESEPHRATZINGER.DialektikderSkularisierung,überVernunftundReligion,VerlagHerderFreiburg2005,S.29.
[3]彼得·溫奇.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STRAWSONPF.Individuals:AnEssayinDescriptiveMetaphysics[M].London1959:9-10.
- 上一篇:工商局依法行政經驗做法
- 下一篇:司法行政交流發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