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哲學定位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17 05:23:00
導語:我國哲學定位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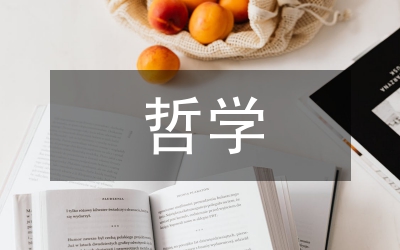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內容提要]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學術始終面臨著合法性危機。上個世紀初,留洋的中國學者以胡適和馮友蘭為代表,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系統疏理中國的文獻典籍,形成了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然而,中國哲學卻不斷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學的難題。本文認為,哲學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就狹義的哲學而論,西方哲學是哲學,中國哲學則不是哲學。但就廣義的哲學而論,中國哲學、印度哲學和西方哲學都可以稱之為哲學。不過,我們不妨以“思想”概念來取代廣義的哲學概念,認西方思想為采取哲學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中國思想具有什么樣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關鍵的問題乃在于中國哲學是否具有應對當今時代之現實問題的潛力。
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中國哲學”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中國古典哲學,亦即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對象,一是指中國古典哲學在現代的傳承和發展,即中國現代哲學。本文在多數情況下對這兩方面的含義并沒有作嚴格的區分,因為它們都關涉同一個問題:中國哲學究竟是“哲學在中國”,還是“中國的哲學”。[1]
嚴格說來,中國哲學被稱之為中國哲學,始于上個世紀初,以胡適為首的一些留洋中國學者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系統,疏理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工作,迄今不過百年。在中國研究中國哲學,自始就面臨著合法性的危機。
通常我們把世界上的哲學劃分為三大形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然而,把中國哲學歸屬于哲學的名下,歷來存在著不同意見。往前說有黑格爾,最近則有德里達。黑格爾的觀點眾所周知,他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從希臘開始,由于東方人的精神還沉浸在實體之中,尚未獲得個體性,因而還沒有達到精神的自覺或自我意識。所以,所謂中國哲學還不是哲學,不過是一些道德說教而已。黑格爾甚至說:“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2]無獨有偶,2001年9月訪華的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亦認為中國哲學不是哲學而是一種思想,不過他并不沒有像黑格爾那樣貶低中國哲學,而是主張哲學作為西方文明的傳統,乃是源出于古希臘的東西,而中國文化則是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的一種文明。[3]有意思的是,當時在場的王元化先生同樣舉孔子為例,稱《論語》只是道德箴言。當然,考慮到德里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當德里達說中國沒有哲學的時候,即使不是贊揚,至少不包含貶義。
然而無論如何,黑格爾和德里達都認為中國沒有哲學。那么,中國哲學究竟是不是哲學?中國哲學是哲學還是思想?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名詞概念使用的合法性問題,它關系到研究中國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問題。研究中國哲學的中國學者之所以困擾于這樣的難題,是因為現在全球的學科分類、概念系統和知識架構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標準。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標準看待中國思想,中國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標準理解和疏理自己的傳統。本來,說中國沒有哲學,就如同說西方沒有儒家、道教和四大發明一樣,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開拓的,而且評價標準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說中國沒有哲學,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種侮辱,這意味著中國古老文明無論多么燦爛輝煌,畢竟沒有達到比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顯然,遭遇這樣的問題,我們很難心平氣和地當它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
但是,除非我們能夠證明“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根本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否則就應該以學術的態度對待之。
我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知之甚少,本來不便亂發議論。但是作為中國人研究哲學,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便有惺惺相惜,唇亡齒寒之深切感受。所以希望從西方哲學的角度,對中國哲學的定位問題說一說我的看法。
一
“中國有沒有哲學”或者“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問題,首先需要確定的是“哲學”的定義。然而,在“什么是哲學”的問題上,哲學家們從來就沒有達到過普遍一致的共識,所以從哲學的定義出發來厘定中國哲學的意義,并不是一個好辦法。從不同的定義出發,可以有不同的結果。不過,哲學畢竟存在了2000多年,一致的對象和籠統的規定還是有的。我傾向于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規定哲學:就廣義的哲學而論,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學都是哲學。但若從狹義上理解,哲學就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確不是哲學。相對于狹義的哲學,我們可以將廣義的哲學稱為“思想”。就此而論,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識形態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則是“哲學”。這就是說,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學”的形式,因而被稱之為“哲學”。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就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和問題而論,中國哲學當然是哲學。但就哲學作為一個學科而論,中國哲學則不是哲學。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哲學”(philosophy)概念是一個外來語,來自日文對英語的翻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是希臘人的創造,經過近代的發展,逐漸成為一門學科。在學科化的過程中,西方哲學形成了特有的概念系統和方法論體系,而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之所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著非常復雜的原因。簡言之,我們可以籠統地將西方哲學看作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它通過理性認識把握自然萬物的本質和規律,以公理化系統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為問題,試圖以層層抽象追問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獲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舉例說,我們可以從許多枝玫瑰花中抽象出“玫瑰花”的屬性,從各種各樣的花中抽象出“花”的屬性,再從花草樹木中抽象出“植物”的屬性……。按照這個思路如此類推,我們最終將抽象到最高的普遍性――“存在”,形而上學或者本體論就是追問“存在”是什么的學問。所有存在著的事物都必須以存在為其存在的前提,同理,所有研究存在著的事物的科學都必須以哲學為基礎。近代哲學的創始人笛卡爾曾經將人類所有的知識比喻為一棵大樹,形而上學是根,物理學(自然哲學)是干,其他科學則是枝葉和果實。在哲學家的心目中,哲學尤其是形而上學在人類知識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當然,這樣一般地規定西方哲學難免失之偏頗,不得已而為之。
我們之所以一般地稱西方哲學為科學思維方式,是因為西方哲學乃是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哲學問題的典型。由于近代以來,這種思維方式在自然科學的領域結出了碩果,以至于使哲學亦義無反顧地踏上了科學的道路。雖然20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們意識到了問題之所在,所以對形而上學科學思維方式展開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激烈批判,其中亦不乏矯枉過正的舉動。但是,大規模批判形而上學的活動,迄今為止也不過百年。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2000多年來,科學思維方式已經滲透到了西方文明的血液里,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一言以蔽之,就狹義哲學而論,判斷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可以視這種科學思維方式為標準,實際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在西方哲學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門”或者“分支”,例如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等等,它們之間界限分明,都有規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論系統,自成一學科,而中國哲學雖然不能說沒有討論過相應的問題,但的確沒有這樣明晰的學科規定,也相應地沒有學科性的發展。例如西方哲學尤其近代哲學以來,認識論得到了廣泛深入的發展,對于認識對象和認識主體以及相應的問題進行了越來越精細的討論。中國哲學雖然也有認識論的問題,但卻沒有認識論――關于認識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當我們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哲學的時候,肯定會發現中國哲學不符合西方哲學的規范。黑格爾說中國沒有哲學,與德里達說中國沒有哲學,雖然立場和態度正好相反,但卻是基于同一個根據: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換言之,兩者都是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哲學究竟是不是哲學的。顯然,如果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看,中國哲學的確不是哲學。
然而,如果從廣義的哲學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國哲學則是哲學,我們不妨稱之為“中國思想”。
那么,什么是思想?二
如果就哲學問題而論,不能說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證明,通過科學思維方式是不可能解決哲學問題的,故而中國哲學的思路便成了一種選擇,雖然這一選擇也不會是唯一的選擇。西方有些哲學家如海德格爾借鑒東方思想包括中國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個人主張,哲學是廣義的人生哲學,因為哲學產生于人類精神試圖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達自由境界的至高無上的理想,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終極關懷”的問題。當然,像美學(文學藝術)、宗教和哲學都是人類精神終極關懷的不同體現。所以僅就終極關懷之問題而論,還不能確定中國哲學是或者不是哲學。中國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從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難區分它究竟屬于哪個學科領域。我們經常說,在中國思想中,不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學者看來亦具有宗教的性質,例如稱儒家思想為“儒教”,實難以西方劃分學科的方式疏理清楚,一旦疏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國思想了。
所以,將中國哲學稱之為“中國思想”,一樣需要說明理由。
從概念上說,與“哲學”相比,“思想”不僅太過籠統,而且也面臨著高低深淺的質疑。我們可以把許多東西歸入“思想”之中:感覺經驗、理論思維、實踐理性、宗教體驗、審美感受……。“思想”如同一個大口袋,什么東西都可以裝進去。另外,一說到“思想史”,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文化變遷、社會思潮或政治思想的歷史。于是,人們可能心存疑慮,如果中國哲學不叫中國哲學而叫中國思想,是不是變相地降低了中國哲學的身份和地位?這與說中國沒有哲學有什么兩樣?就此而論,我們有必要把“思想”的含義說清楚。當然,就“思想”的概念含義而論,恐怕像哲學一樣是說不清楚的,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圍繞“思想”的身份和地位進行一番討論。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在此使用“思想”這個概念的時候,既不是從認識論上規定的,也不是從意識形態的結構上說的,亦與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想無關,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種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韻和精髓。簡言之,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為文明的靈魂的東西,就是“思想”。顯然,“思想”可以是許多“學科”的研究對象:文化、文學、歷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學。不過,“思想”亦比所有的“學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為什么最是標榜創新和發展的西方哲學,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回到古希臘去汲取營養?因為“思想”是“哲學”的活水源頭。
那么,在哲學與思想之間作這一重區分,有什么意義?
在不同的文化、社會、歷史等背景之下,人類精神在追問終極關懷之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維方式或世界觀,這種思維方式或世界觀則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學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世界觀,主要表現為科學思維方式。自近代以來,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這種科學思維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并且將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貫徹于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的所有領域,將整個世界帶上了現代化的路徑。不過,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思想家們開始反思科學思維方式的局限性。人們逐漸意識到,哲學作為科學思維方式雖然在對自然的認識等方面產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對于自然“祛魅”的過程中亦使精神的領域科學化了,而面對終極關懷的問題則越來越顯得無能為力。在某種意義上說,思想的哲學化或許正是西方哲學面臨之種種問題的根源之一。哲學作為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如果我們將思想等同于哲學,勢必使豐富多彩、奧妙無窮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過程中失去它的內在生命。我們可以把“思想”看作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構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學”則是學科化、規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學”。思想是“根”,哲學則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樹干”之一。如果哲學能夠從思想之源中汲取養分,那么就可以茁壯成長。而當哲學遺忘了它的根時,它便喪失了生命的活力。
譬如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的區分。
將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分開,本無可厚非。但是,由于中國哲學史是按照西方哲學的形式從中國思想史中疏理出來的,所以問題多多。而在此基礎上我們卻又常常按照西方哲學的方式將中國哲學史凌駕于中國思想史之上,于是問題就更多了。單就中國哲學而論,不僅將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涇渭分明地分而治之是成問題的,而且應該確立思想史對于哲學史的本源地位。
以上關于“思想”與“哲學”所說的,基本上關乎“思想”與“哲學”的差別。如果我們將“思想”看作是廣義的哲學,則需要另有說明。我想以海德格爾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海德格爾有一篇文章叫做《哲學的終結和思的任務》,他所說的“哲學”指的是建立在科學思維方式基礎上的西方哲學,而“思”則意指對真正本源的源始境域的思想。在此,“源始”不是“原始”,并非時間意義上的古老,而是根本、根據的意思。按照海德格爾,西方哲學鍛造的科學思維方式或許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動中創造了非凡的成就,但其嚴重后果是,人被連根拔起,成了無家可歸的浪子。因此,他主張返歸主客尚未分化的源始境域,提倡一種本源之思。如果說西方古典哲學的基本思路是“向上”抽象,那么可以說海德格爾的思路則是“向下”回溯的。其實,西方哲學史上像海德格爾這樣質疑哲學的哲學家不乏其人,例如康德。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康德和海德格爾排除在哲學之外,不僅不能排除在哲學之外,而且還視之為哲學家中的哲學家。由此可見,把西方哲學規定為一種科學思維方式,主要是從一般意義上說的。另一方面,主張非科學思維方式的思想家如海德格爾亦是偉大的哲學家,哲學因此可作廣義狹義之理解。
那么,我們從什么意義上將“思想”視為廣義的哲學呢?如前所述,哲學產生于人類精神試圖超越自身有限性通達至高無上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廣義而論,這更應該看作是思想的起源。換言之,思想起源于終極關懷問題,哲學則是其中對此問題的一種回應方式。“思想”這個概念雖然籠統,但是當我們通過“思想”來體現文明的神韻和精髓,并且視之為廣義的哲學的時候,就不是什么隨隨便便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思想”的了。“思想”既是一種認識能力,也是思維的結果,更可以看作是思想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思想去思想思想的對象,也就是思想的反思,而反思則帶有自我意識的性質。雖然人類文明創造了許許多多光輝燦爛的偉大成就,然而只有當它能夠反思自己的成就,達到思想的自覺的時候,才能說達到了比較高的境界。中國有句成語道:“殊途同歸”。西方的諺語則是:“條條道路通羅馬”。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一樣都是以某種至高無上的思想境界為追求的目標,只是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罷了。如果可以將思想看作是廣義的哲學,那么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就是兩種不同的哲學道路,這兩條道路殊途同歸,目的是一個,那就是人類的精神家園。
- 上一篇:熱電企業效能監察工作報告
- 下一篇:中小企業經濟運行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