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對立
時間:2022-05-01 02:42:00
導語:透析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對立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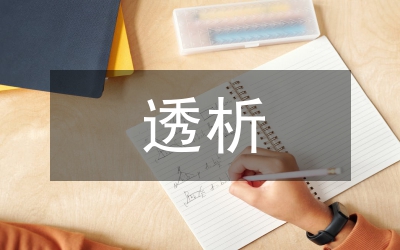
摘要:一些西方學者依據(jù)他們對馬克思自然觀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馬克思與啟蒙主義關(guān)系的理解,把馬克思看做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而實際上,馬克思的自然觀念無論在生存論意義還是實踐論意義上都蘊含著深刻的生態(tài)意蘊;他所說的“控制自然”是對自然有意識、有計劃地合理調(diào)節(jié)和管理;他與啟蒙主義是辯證的二重關(guān)系。因此,馬克思不僅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而且他還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對立,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
關(guān)鍵詞:馬克思;人類中心主義;生態(tài)中心主義
長期以來,馬克思在生態(tài)問題上飽受誤解和非議。一些西方學者往往依據(jù)他們對馬克思的自然觀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馬克思與啟蒙主義關(guān)系的理解,把馬克思看做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泰德•本頓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的極限”的論文中就指出,馬克思勞動過程中對我們不能操縱的自然條件只是輕描淡寫,而對人有意識地改變自然的力量則過分強調(diào),結(jié)果他同其他資產(chǎn)階級學者一樣陷入了人類中心主義。這是對馬克思思想的誤讀和歪曲。筆者認為,馬克思不僅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而且他還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對立,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
一、馬克思的自然觀念
在馬克思那里,自然包括外部的自然界和人自身內(nèi)在的自然,具有生存論和實踐論兩重意義。但無論是在生存論意義還是在實踐論意義上,馬克思的自然觀念都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tài)意蘊。
(一)從生存論的意義來看,馬克思認為,自然對于人類具有“先在性”
(1)人是自然界長期發(fā)展的產(chǎn)物。這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明確表達的重要思想。他指出,那些“現(xiàn)實的、有形體的、站在穩(wěn)固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①,他“本來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類看做自然界的產(chǎn)物,看成自然界的一部分,顯然,人就被放在了自然里面,就不可能被賦予宇宙中心的地位。馬克思的這一思想還深刻地體現(xiàn)在此后他對于人類進化問題的認識之中。1860年,馬克思開始研究達爾文的進化論,并把它作為其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史基礎(chǔ)。達爾文進化論提出,人類起源于較低等的物種,在長期的自然選擇中進化而來,并且還處在不斷的進化之中。這一思想顯然降低了人類在自然層級中的地位,揭示了人類與地球在整個物質(zhì)進化過程中的相互依存。正是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馬克思基于自然科學的基礎(chǔ)進一步明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把人類及其意識看做是物質(zhì)發(fā)展的產(chǎn)物。這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馬克思運用進化論的觀點把人類看做是動物界的一部分,從根本上拒絕那種把人類看做宇宙中心的目的論觀點。這從本體論的意義上反映了馬克思對狹隘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對。
(2)自然是人生存和發(fā)展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自然對人類的意義不僅在于為人類提供必需的生活和生產(chǎn)資料,而且也是人精神生活的來源。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說:“人靠自然界來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xù)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lián)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lián)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可見,馬克思不僅把人作為一種自然存在,而且是以自然為前提的自然存在。其唯物主義思想與生態(tài)學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貫穿其理論的始終,從《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到《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以及《哥達綱領(lǐng)批判》都始終堅持“外在自然的優(yōu)先地位”和“先于人的存在的自然界”的思想。
(二)從實踐論意義來看,馬克思的自然觀念與生態(tài)學也是內(nèi)在一致的
(1)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的統(tǒng)一。馬克思不是單純從客體的或直觀的方面,而是從實踐出發(fā)來理解“自然”的。其自然觀的實質(zhì)就是從實踐的角度不斷揭示自然和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guān)系。在他看來,看不到實踐的作用正是直觀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就批評了費爾巴哈的錯誤觀點。他說:“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xiàn)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yè)——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這樣,“如果把工業(yè)看成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zhì),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zhì),也就可以理解了。”③可見,人通過實踐活動不斷使自然“人化”和自身“自然化”,這是以勞動為中介的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通過勞動,人使自然界消除了原始直接性、對人的疏遠性和異己性,成為對人有用的“現(xiàn)實的自然界”;另一方面,人通過勞動,使自身“特殊的感性的本質(zhì)力量”得到“客觀的實現(xiàn),”以適應“自然界的本質(zhì)的全部豐富性”。在《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明確提出,環(huán)境的改變與人的改造是相統(tǒng)一的。這就是說,自然界的存在固然要受到人的實踐活動的中介,但是,實踐活動的中介并不能取代或取消自然界對人的價值和地位。
(2)自然史與人類史的統(tǒng)一。馬克思非常強調(diào)人類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約和統(tǒng)一,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說:“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lián)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④這里,自然史與人類史的密切相聯(lián)和相互制約恰恰體現(xiàn)了自然和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guān)系。
(3)改造自然與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統(tǒng)一。在談到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問題時,馬克思多次論及人的活動應當遵循自然規(guī)律,否則會帶來嚴重的后果。1866年,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借用比特雷莫在《人類和其它生物的起源和變異》中的一句話明確表達了這一思想,他說:“不以偉大的自然規(guī)律為依據(jù)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⑤恩格斯的著名的“自然報復論”就是對他這一思想更為完整的表達。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nèi)祟悓ψ匀唤绲膭倮τ诿恳淮芜@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jié)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fā)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jié)果又消除了。”⑥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報復”,就是指人類的行為違背自然界發(fā)展規(guī)律而遭到的必然懲罰。
二、馬克思“控制自然”的含義
一些西方學者之所以把馬克思解讀為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往往以他使用了“對自然的統(tǒng)治”、“人對自然的支配”、“自然力的征服”等字眼為依據(jù)。《共產(chǎn)黨宣言》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經(jīng)常被他們指責為反映馬克思在人與自然關(guān)系上所謂“普羅米修斯主義”的代表著作。詹姆斯•奧康納就以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等處曾多次使用對自然的支配這一用語為據(jù),認為馬克思同其他近代的哲學家一樣,也主張主客二分的自然觀。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曾出現(xiàn)過上述對自然統(tǒng)治的字眼。但是不是可以由此就得出馬克思是主張對自然進行野蠻控制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呢?這需要我們具體分析馬克思語境中“控制自然”的含義。對此,帕森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很好的思路。在《馬克思恩格斯論生態(tài)學》一書中,帕森斯從概念分析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他指出,“控制自然”中的“控制”具有多重含義,即高超的技藝或豐富的知識;卓越的智力或一定程度的實踐能力;幾乎完全的或者說是完全的決斷或統(tǒng)治,就像主奴關(guān)系一樣。馬克思“控制自然”的概念,不是第三種意義上的一種主仆關(guān)系,而是人類在追求合理需要的過程中明智地改變自然的一種技巧和才智。也就是說,馬克思是從前兩種含義來談人對自然的控制的。而第三種意義上的“控制”,在馬克思看來,恰恰是資本主義對待自然的態(tài)度,這正是他所堅決反對的。因而,帕森斯提出,對于控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繼續(xù)表明他們的生態(tài)立場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反題:通過關(guān)心而不是貪婪來管理人和自然,慷慨而不是占有,對自然和社會有計劃的管理。
帕森斯對馬克思“控制自然”的理解是正確的。確然,馬克思主張對自然的“控制”,但這里的控制決不是主奴關(guān)系般的統(tǒng)治關(guān)系。馬克思所說的“控制自然”,指的是在利用自然規(guī)律基礎(chǔ)上對自然的有意識、有計劃地合理調(diào)節(jié)和管理。并且,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對生產(chǎn)進行有意識地控制,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生態(tài)問題。他曾指出:農(nóng)業(yè)如果自發(fā)地進行,而不是有意識地加以控制,接踵而來的就是土地荒蕪。在《資本論》中,他不僅指出了人對自然的控制是一種共同的控制,而且還提出了這種控制的制度保證,“聯(lián)合起來的生產(chǎn)者,將合理地調(diào)節(jié)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tǒng)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zhì)變換。”⑦這就是說,只有在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在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中,這種合理地調(diào)節(jié)才能實現(xiàn)。因此,雖然在馬克思那里有控制自然的詞匯出現(xiàn),但我們決不能就此認為他是主張對自然進行野蠻征服的狹隘人類中心主義者。恰恰相反,在馬克思“控制自然”概念中反而包含著深刻的生態(tài)關(guān)懷。
三、馬克思與啟蒙主義的關(guān)系
啟蒙主義是西方現(xiàn)代性的主要象征。啟蒙主義從人的主體性出發(fā),以人性戰(zhàn)勝中世紀的神性,以科學理性戰(zhàn)勝蒙昧。然而,它雖然破除了中世紀的宗教神話,卻制造了對人的主體性的迷信。在啟蒙主義下,自然被看做是為了人的利益可以任意加以剝削的他者,它的存在方式、本質(zhì)和特性都以人的需要為前提。科學與人欲的合流把整體的自然肢解為作為人類可利用的資源和能源的碎片,并被加工成為滿足人的欲求的物品。因而,內(nèi)存于啟蒙主義的是單一主體與客體對立的范式。在這一范式中,抽象的人或單一主體被看做是一切活動價值選擇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這里內(nèi)含著這樣一個目標,即本來源于自然的人要不斷地超越自然的界限,駕馭和控制自然,成為自然的主宰和尺度。因此,啟蒙主義往往被看做是人類沙文主義的思想根源。
由于對宗教的批判、對社會生產(chǎn)的理性規(guī)劃、對自由全面發(fā)展人的追求以及對社會進步的樂觀主義態(tài)度等,一些西方學者就認為馬克思思想中存在著大量與現(xiàn)代性的主導價值完全契合的觀念,從而把馬克思看做是培根和笛卡爾等啟蒙思想家的信奉者,即所謂的“啟蒙運動之子”,并由此推定他主張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瑞尼爾•格倫德曼在《馬克思主義和生態(tài)學》一書中就指出,馬克思是一個培根和笛卡爾等啟蒙思想家的信奉者,他顯然具有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而且也沒想給人探索自然設(shè)置什么障礙。
確實,馬克思關(guān)于人和社會的理念深受啟蒙主義的影響,在他的思想中有深刻的啟蒙主義烙印,如贊揚理性、自由、解放,肯定科學技術(shù)的重大社會進步意義,對現(xiàn)代社會的未來發(fā)展充滿了激情與希望等。然而,這僅僅是馬克思與啟蒙主義關(guān)系的一個方面。馬克思雖然繼承了現(xiàn)代社會思潮所揭示的關(guān)于人及社會的理想,但他從來沒有無限制地為現(xiàn)代社會唱贊歌,他一生從事的工作就是批判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批判資本主義的現(xiàn)代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思想中也存在著對啟蒙主義的反思和批評,而非追求一種本質(zhì)主義、理性主義、中心主義的“元敘事”或“宏大敘事”,不是簡單地主張進化論式的歷史進步論。⑧在馬克思看來,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是一個充滿曲折與沖突的歷史過程,包含著深刻的內(nèi)在矛盾。一方面,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質(zhì)上的富裕和心智上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它又阻礙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地發(fā)展。“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⑨。它既是一種進步,又是一種退步;既有光輝的一面,又有陰暗的一面。現(xiàn)代性的這種內(nèi)在分裂正是由資本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造成的。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既是促進現(xiàn)代文明進步的積極力量,同時又是阻礙現(xiàn)代文明健康發(fā)展的消極力量。正是這樣一種矛盾性,使馬克思對啟蒙主義呈現(xiàn)出辯證的二重態(tài)度:既肯定又否定,既贊揚又批判。他的思想既是現(xiàn)代的,同時也是反現(xiàn)代的。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馬克思視作“啟蒙運動之子”。
由此,馬克思決不可能是一位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其思想與生態(tài)學存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但是,馬克思也絕不可能是一位生態(tài)中心主義者。他從能動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出發(fā),反對脫離人的實踐空談自然的界限,相信人的能動性和科學技術(shù)能夠不斷克服自然的界限;反對自然“內(nèi)在價值”,主張“‘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guān)系中產(chǎn)生的”⑩。而自然有限論和自然內(nèi)在價值論恰恰是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核心思想。可見,馬克思是不贊成生態(tài)中心主義的。從他青年時期的博士論文到后來對費爾巴哈、對18世紀的自然主義尤其是對“盧梭式”浪漫自然主義的反對,以及對一切所謂浪漫式的自然崇拜的批判也都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實際上,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雖然表面對立,但本質(zhì)上卻是一樣的,它們都是偏執(zhí)一端,從人與自然的對立來看待二者的關(guān)系,都屬于機械的二元論的思維方式。而馬克思注重的是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其理論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在于對立的統(tǒng)一體,這種思維方式必然決定了他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主義對立的超越。他既不主張以人為中心,也不主張以自然為中心,而是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未來的共產(chǎn)主義在他那里是,“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馬克思的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不僅為當前生態(tài)危機的解決提供了正確的思路和方向,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②③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56—57、89頁。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0頁。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頁。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3—384頁。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頁。⑧豐子義:《馬克思現(xiàn)代性思想的當代解讀》,《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頁。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6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頁。
- 上一篇:透視孔子仁學與人的發(fā)現(xiàn)
- 下一篇:剖析道家審美學本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