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時重商政策與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16 02:27:00
導語:春秋戰(zhàn)國時重商政策與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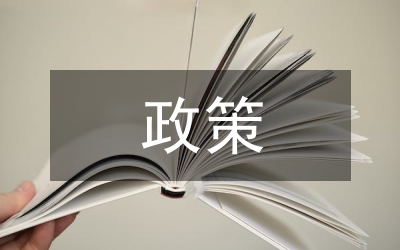
摘要: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為實現(xiàn)富國強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保護和促進作用,使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到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nóng)、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yè)貿(mào)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yè)貿(mào)易和農(nóng)業(yè)、工業(yè)生產(chǎn)一樣成為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經(jīng)濟活動。對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重商政策的主要內(nèi)容以及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作初步探討。
關(guān)鍵詞:重商政策;關(guān)稅;商品經(jīng)濟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這一時期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對于今天我們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統(tǒng)治者出于政治和經(jīng)濟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進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兼并,為求得生存與發(fā)展,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以發(fā)展經(jīng)濟,鞏固統(tǒng)治。
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繁榮必然給國家?guī)泶罅康纳虡I(yè)稅收,增強其經(jīng)濟實力,有利于鞏固統(tǒng)治和爭霸戰(zhàn)爭。雖然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田稅是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但源源不斷的商業(yè)稅收無疑也是各諸侯國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鞏固統(tǒng)治和爭霸戰(zhàn)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戰(zhàn)國策》里面的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guān)之,出入者賦之……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這里,就把征收關(guān)稅作為“富國”、“存韓安魏”的一個重要途徑,說明關(guān)稅收入是相當可觀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經(jīng)濟帶來的直接關(guān)稅收人對于諸侯國的重要性。對此,《管子》說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關(guān)市”作為“輸之以財”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記載了宋國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關(guān)稅稅率的事情說:“去關(guān)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來,如果免征關(guān)稅或降低稅率,就有可能要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統(tǒng)治。
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和社會分工更加精細,商業(yè)活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經(jīng)濟生活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社會分工的擴大和細密,加之生產(chǎn)活動所具有的很強的區(qū)域性,客觀上要求商品交換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使“四民”之間和地區(qū)之間互通有無,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保證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延續(xù)。在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情況下,農(nóng)民不從事手工業(yè),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業(yè)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各自以自己的勞動產(chǎn)品通過市場交換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戰(zhàn)國時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nóng)、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yè)貿(mào)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yè)貿(mào)易和農(nóng)業(yè)、工業(yè)生產(chǎn)一樣成為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經(jīng)濟活動。正如司馬遷所說:“待農(nóng)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給統(tǒng)治者帶來巨大經(jīng)濟利益的同時,還直接參與了一些政治活動,和統(tǒng)治者建立了密切聯(lián)系。據(jù)《左傳》記載,鄭國從建國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鄭桓公在西周末年,聽從史伯建議,率領(lǐng)族屬與商人東遷于虢、鄶之間。并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商人在鄭國創(chuàng)業(yè)奠基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鄭國統(tǒng)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鄭國統(tǒng)治者與商人訂立了互信盟約,“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國家,國家就不強買或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涉商人的經(jīng)營。雙方“恃此質(zhì)誓,故能相保”。后來,當晉國人韓宣子向鄭國一位珠寶商人購買玉環(huán)時,這個商人就回答說:“必告君大夫”,即要報告給政府。可見,鄭國商人和政府之間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傳》記述的“弦高犒師”故事也證明了這一點。這說明,商人在進行商業(yè)活動的同時,還緊緊地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捍衛(wèi)了國家的利益。而作為回報,統(tǒng)治者也就給予商人一定的特權(quán),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業(yè)活動的正常開展,促進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繁榮。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內(nèi)容
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通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晉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寬農(nóng),懋穡勸分”,使晉國很快擺脫了窘境,“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公元前658年,衛(wèi)國被狄人侵劫遷往楚丘后,衛(wèi)文公制定了“務材、訓農(nóng),通商、惠工”等政策,使衛(wèi)國很快富強起來,以致“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喲了維護列國之間的正常商業(yè)貿(mào)易,在春秋時期的諸侯會盟上,也都把維護正常商業(yè)交往,作為重要的內(nèi)容寫入盟約。如公元前651年齊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無忘賓旅”、“無遏糴”的內(nèi)容,即要保護客商,不阻礙糧食流通。這表明各諸侯國都很重視商業(yè)活動。
“輕關(guān)易道”。關(guān)稅是商人的貨物過關(guān)時繳納的稅款。《逸周書·大聚解》說:“關(guān)市平,商賈歸之。”這說明關(guān)稅稅率的輕重直接關(guān)乎商人的利潤,進而影響一個國家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普遍實行了“輕關(guān)易道”的政策。晉文公即位之初,為加強國力,發(fā)展經(jīng)濟,下令“輕關(guān)易道”,“以厚民性”,重視發(fā)展商業(yè)。齊桓公即位后,采納管仲的建議。“使關(guān)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這些政策的實行,降低了關(guān)稅稅率,減輕了關(guān)稅負擔,保障了交通暢通,有利于吸引商人進入本國市場,促進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增強了實力,為其稱霸諸侯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zhì)保障有司者治之”。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設(shè)立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管理機構(gòu),“有司者治之”。“司市”作為市場總的管理機構(gòu),“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體的職責是:“以次敘分地而經(jīng)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征值,以質(zhì)劑結(jié)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蔬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此外,設(shè)立了“廛人”、“胥師”、“司稽”,分掌收稅、監(jiān)督、保衛(wèi)等職責,負責維護整個市場秩序。同時,制定規(guī)章制度,對商品種類、規(guī)格等都作了嚴格的限制。如,為維護禮制和貴賤等級秩序,規(guī)定體現(xiàn)貴族身份的“禮”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
早在原始社會末期,由于地域差異和社會分工的存在,商品生產(chǎn)和交換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生產(chǎn)力獲得了重大發(fā)展,特別是各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進了商品經(jīng)濟繁榮。
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繁榮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市場的發(fā)展和完善。春秋時期,為適應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市”的數(shù)量明顯增加。這時各諸侯國的都城都設(shè)有市。如《左傳》中記載的周“王城之市”。楚國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現(xiàn)了“齊桓公宮中七市”的現(xiàn)象,據(jù)說齊桓公的這種行為還遭到了國人的非議。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鄉(xiāng)之間也都普遍設(shè)有市場。戰(zhàn)國時期,“市”的建立更為普遍,商品種類更為豐富,所有“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東西南北的土特產(chǎn)品,在中原市場上都可以買到。商品交換的地域范圍更廣,“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紆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nóng)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經(jīng)濟之發(fā)達由此可見一斑。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伴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批繁榮的商業(yè)城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nèi),皆為天下名都。”其中,最為著名的當首推“陶”,被譽為“天下之中”。齊國都城臨淄也因商業(yè)發(fā)達而聞名天下。史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跆躪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其商業(yè)發(fā)達和繁榮景象躍然紙上。
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繁榮,出現(xiàn)了一批擁有雄厚商業(yè)資本的豪富巨商。到春秋后期晉平公時,“絳之富商”,“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其勢力也相當可觀了。儒商范蠡,“三致千金”,成為商界鼻祖,被稱為“陶朱公”,為后人所頌揚。到戰(zhàn)國時期,商人勢力進一步發(fā)展,能夠“與王者埒富”的大商人已不在少數(shù),見于史籍記載的如有善于“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白圭;與“陶朱、卜祝之富”相提并論的猗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