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棉花史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02 04:29:00
導語:我國棉花史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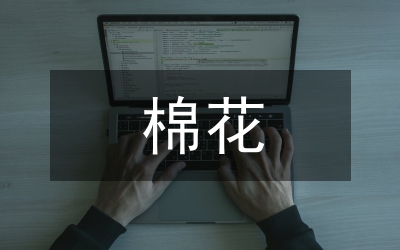
l949年之后的中國人所穿的“司爐工作服”,使他們贏得了某些不了解情況的西方記者賦予他們的“藍螞蟻”的稱號。這些服裝實際上僅僅是自五六個世紀以來由庶民們穿用的粗棉織服裝。該國北方是藍色衣服,南方則著黑裝(北藍南皂)。中國棉花史很久以來就吸引了史學家們的注意力,首先是日本人,其后是中國人。他們主要是接觸了這部歷史的技術和經濟方面。從此之后,這部歷史的基本線條已為人所熟悉,盡管史學家們(個別人除外)都不大關心其社會和制度的方面。本文陳述某些觀點的抱負,僅僅是以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出版的兩部著作為根據,而對該內容做一番總結,這兩部著作對某些未曾做過多少研究的方面進行了新的闡述。
雖然棉花這種植物從古代起就為西域綠洲的居民所熟悉,他們又是從其近東的鄰居那里獲得這一切的。棉花絲毫未引起古代漢人的注意,他們的衣著方式受絲與麻這一對基本對襯物支配。絲綢這種珍貴的織物出自蠶對桑葉的加工,當時就已經被比定為一種植物產品。它僅限于供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穿戴,從而確保了它的一種特殊地位。與生產或制造絲線有關的所有技術操作(養蠶、采摘供幼蟲食用的桑葉、繅絲、紡紗和織綢布)均屬于“女紅”的范疇。從儀禮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紡織絲綢是于座落在封閉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對綢匹要實施非常嚴格的質量監控。平民百姓只能僅滿足于比較粗糙的纖維織物,諸如線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紡織相反卻屬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農”或“工”的勞動范疇。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纖維屬于一種不受法規條律控制的農村手工業之范疇。這些織物并不被計算在由古代社會稽核家們制訂的“標準預算”之中,因為這些稽核們首先將農民視為谷物種植者。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很早就進入了商品流通系統,這種特征便意味著纖維植物是做為“經濟作物”而種植的,以供應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生產活動。考古學家們已經發掘到了一件被斷代為后漢的文書,其中提到了商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這些商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來并于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相反,我們只掌握很少一點有關使用動物原料做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資料,諸如褐布和毛皮等。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考慮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鴉片戰爭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多年來,數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證明了棉花的手工產品(土布)是一種非常強的抗磨損的產品,從而導致史學家們思考這種生產模式的有效性。據此認為,中國于南京條約簽訂的翌日,遂向西方貿易開放,可能會引起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并促使農村社會的解體,于是便加速了該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系。在18世紀時,中國仍以先進的經濟強國的面目出現,既出口其侈奢手工業的成品(絲綢、瓷器、漆器和細棉織品),又出口它幾乎擁有壟斷權的物品(如茶葉或生絲)。它同時又僅僅進口有限數量的“異國”舶來品,以進口白銀而結算其外貿。中國在20世紀時,在其移民地區的范圍內失去了貿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進口成品。有關棉花的研究導致我們使這種景象變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廣州的商人從18世紀末起就已經開始進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運輸費用的價格差。通過海路進口外國纖維,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贛江逆流而上地運輸中國棉花更為便宜一些。毫無疑問,在國門開放之后,商業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反向流動。因為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中華帝國出口原棉,進口制成品、棉紗和棉織品。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們早在1830年就生產普通的棉織品,其效益要比中國的手工業主們好得多,所以他們自認為以其商品充斥中國市場處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陳鐘毅和趙岡提出的論證的話,那么其演變實際上要更為復雜得多。與英國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國在數十年中繼續進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織品,這種形勢僅僅從1880年起才開始顛倒過來。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現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點是棉花纖維生產過剩、出口原棉等與進口棉紗和棉紡品的重大發展相聯系,從而彌補了當地棉紡品生產的逆差。這種新的局面卻僅僅持續了20一30年。從20世紀的轉折時期起,更具體地說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期間),中國利用國內外資本而取得了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至于該國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棉花進口國和棉紗出口國,而外國棉紡品的進口商業都崩潰了。
如果大家僅僅局限于“現代”經濟的觀點上,那么這種常規性的演變就很難理解了。事實上,必須考慮到工業生產所占份額始終甚少的事實。因為在20世紀初葉,更具體地說是即便在工業棉織品的進口迅速發展的時代,國內消費仍由手工業生產確保75%,手工業產品同樣也名列出口產品之首。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聲稱,開放港口的工業化非但遠不會有損于手工業生產,而且相反還會刺激它的發展,激勵手工業匠人們使其技術現代化并創建使用一種經革新設備的大量手工業作坊。在1930—1935年之間,重新占領國內市場之舉事實上業已完成,進口棉紡品的份額已銳減至3%,而中國人所穿的布帛有2/3的份額出白手工業作坊。甚至在上海,這些作坊也很繁榮,一直到達新工業區的附近地帶也如此。
手工業生產的這種令人驚訝的抵制行動,當然是由于政治形勢提供了便利條件。“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就是抵制洋貨成品。后來,中國農民在中日戰爭和內戰期間,與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絕了,他們自我收縮并實行一種自食其力的生存經濟(衣食經濟)。在本世紀50年代初,經過恢復國內的和平和重新啟動棉紡工業之后,農民們仍以他們棉花收成的80%略多一些的數量從事交易。直到集體化時期,才使纖維物由國家機構全部統購以在現代化的工廠中加工。農村人對于加工棉花的酷愛絕不會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完成與纖維品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各項任務能確保一個貧窮的農民階級有一種補充收入。由吳承明引證的那些在1930年左右從事的調查,便會令人信服地證明,參加棉花加工勞動的強度與農業經營的能力成反比。與彈棉花和織布有關的經營可以使農民利用他們之間勞動剩下的空閑時間,尤其是可以占有生產效率不高的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勞動力,他們只能獲得一種低于邊緣工資水平的報酬。這種解釋在有關脫皮去籽、彈花和紡紗方面則似乎特別合情合理,因為這些生產率不高的機械操作收效甚微。然而,經濟方面的考慮卻無法解釋民眾對于傳統棉織品超過了對洋布的迷戀之形勢,這是由于土布那特殊的質量造成的。正如陳鐘毅和趙岡所指出的那樣,“土布”比較暖和和結實,因為它們是在經革新的織機上織成的,用比英國紗粗得多的棉紗織成,但在外國工業家的眼中來看卻收益低微,從而使英國制造商打消了設法仿造它們的愿望。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手工業匠人,不滿足于再現古代的織造程度。他們毫不猶豫地革新并表現出了他們那令人矚目的適應精神,向西方設備借鑒了各種改進措施(金屬框、飛梭、提花織機)。相反,正是這些從手工業匠人的觀點來看收益不佳的業務,諸如紡紗之類,都逐漸遭據棄并讓位于現代工業。這樣就特別解釋了紡織業發展的超前性。
- 上一篇:生態農業發展分析論文
- 下一篇:農業研究機構分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