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的城鎮化對傳統經濟的影響
時間:2022-12-04 10:09:03
導語:地區的城鎮化對傳統經濟的影響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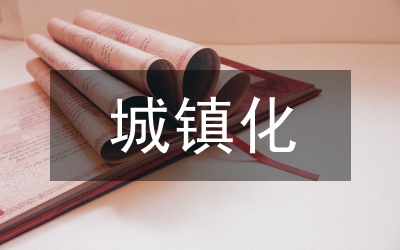
一、寧夏銀北地區回族傳統經濟的變遷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民間個體經濟發展的能量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回族傳統商業集市得以復興并逐步適應著現代化社會生活的發展要求而不斷變遷。黃渠橋集市作為由當地傳統經濟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并與之相適應的貿易形式,構成了一個聯結不同經濟文化區域之間的社會交換網絡,集市貿易使得該鎮成為此地域社會的中心地,成為傳統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市的變遷與農民的生計方式、從業形態、鄉村社會的生活乃至傳統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長足進步密切相連,而集市及其結構長期的演進過程,更印證了當地回族傳統經濟的變遷歷程。透過當地集市的變遷可以觀察本地區回族傳統經濟是如何借助集市這一社會共同體聯結鄉村社會并與市場經濟相互適應與建構,并進一步見出銀北地區城鎮化發展與回族傳統經濟相互整合的邏輯與基礎性機制。目前的黃渠橋鎮市場(當地人稱黃渠橋鎮新市場)是當地每月“三、六、九”日前來逢集的場所。該集市逢集時人流量達3000余人,重要節日趕集人數可達4000余人,每年交易額近9600萬元。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城鎮化進程的日益加劇,黃渠橋集市的變遷呈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征:
(一)集市與農民的社會生活關系日益緊密,鄉村生活的自給自足程度逐漸減弱
該鎮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需求可依靠市場來滿足,是因為市場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更加便宜、便利和更具選擇性,故不需要自己生產,通過前往集市購買就可以實現,客觀上還影響了農民對種植作物的選擇。如以往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米、面、油、蔬菜等生活資料基本都是自己生產的,隨著集市供應能力的不斷增強,很多家庭更愿意從集市上去購買。同時,當地的農戶已從單純的農牧業生產領域走向商品流通領域,進入有關清真飲食產業的經營和其他領域。當地居民依托該集市,發展與自身條件相適宜的個體私營商業,致使居民收入及經濟來源的路徑和方式發生了變遷。就黃渠橋集市中農戶業態現狀來看,集市上的攤位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職業性商販,主要以參與市集交易為生;另一類是半職業性商販,以當地的回族農民為主。第一類職業性商販大53多是從周邊地區批發農副產品到集市上出售給當地居民,其銷售的商品以服裝、日雜百貨、副食品為主。
這些商販常年靠趕集為生,他們一般在該集市都有固定攤位,并在周邊其他集市按固定的集期進行交叉逢集、流動經營,以期達到最大的收益。第二類半職業性商販主要為當地的農民,他們不僅滿足了家庭正常的貿易需求,而且通過集市貿易,將自己種植的初級產品或飼養的農副產品以及自己生產的手工制品,進入市場體系實現向上的流動或直接進入其他百姓手中或繼續向其他基層市場流動。最值得注意的是,市場最西段的牛羊牲畜交易區中還有一類特殊的職業性商販,他們是為實現買賣雙方的順利完成交易并從交易雙方抽取傭金的中介商———牙行。一種是專門為掙取傭金的專事牙紀,另一種是兼牲畜販運的牙行,后者因還擁有自己的其他生意,其經濟資本高于前者。雖然,集市在時代變遷中發生了諸多的改變,但黃渠橋回族商人中作為中介商的牙行們依然按照每個集市固定的日期,在不同集市中單純地以尋找差價作為他們唯一的獲利途徑,并沒有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上述的這些商販半數以上的經營者為本地回族,并且集市內的所有餐飲攤位都由回族經營并掛有清真標識的字樣,顯示出一個地方的飲食文化取決于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回族文化傳統。這一點在黃渠橋集市外,沿109國道的餐飲業中更得到了體現。可以說,黃渠橋的人口構成和民族間的不同生計傳統所決定如此的分布形態和飲食特色,并顯示了一種社會群體力量之間的競爭關系。集市經營商品種類的增多與范圍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農村生活方式的結構變遷以及農村生活與生產的逐步分離,即農村社會在運用傳統集市的方式形塑出帶有現代性的生活方式,簡言之“農村生活的城鎮化”。
(二)集市商品結構的多樣化和功能的單一化程度越發增強
據筆者調查發現:黃渠橋新市場于2013年7月4日作為“縣域經濟觀摩”的代表地點之一,經半年的重新建設,一改往日諸多攤位混雜經營。市場內新建八個大棚,將市場所售商品按種類分區:服裝、農織品各占兩區,百貨、日雜各占一區,牛羊肉和蔬果也各占一區;百貨類攤位57個、蔬果類60個、農織類50個、飲食類16個;市場內的流動性攤位80余個,固定攤位178個,市場大門兩側有店鋪15家。其中家禽、牲畜集中于市場后側的空地逢集交易,總體反映了集市從沿街擺攤式經營到市場化、規范化的轉變。從集市的功能上來看,以往的黃渠橋集市相對于其所依托的鄉土社會而言,不僅是本地農民的生活生產資料市場,而且還為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需要提供服務,同時還擔負著保證傳統經濟生產與再生產正常運轉的職能。集市在滿足當地農村基本生產生活需求的同時,還作為了這一地域內具有綜合性功能的經濟社會文化共同體。逢集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在車水馬龍的集市中討價還價,交易的同時相互交流,彼此溝通。隨著當地城鎮建設的加快,越來越多品種齊全、環境良好的超市以及其他娛樂設施的出現,傳統集市的諸多功能逐漸被分擔,集市的綜合性功能被單一化的社會設置所替代。商品構成逐步多樣化、規范化并與市場周邊的店鋪相聯結的集市結構,使黃渠橋集市在寧夏北部地區的整個大市場系統中步入到鄉村市場系統變遷和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如今的黃渠橋集市正在朝著市場交易功能專業化的方向演化,這也是該集市在近些年來得以快速發展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集市逐漸由一個鄉村社會系統向鄉村市場系統過渡
改革開放以前的黃渠橋集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周邊諸多的傳統村落和村落中的特殊組織,如家族、熟人關系、牙行等來進行建構和協調整合這一地域性的經濟文化生活的共同體。正如波朗尼所指出的,在非市場經濟社會里,“經濟活動嵌入于社會之中”。[20]而且,當時因缺少專門的市場組織和正式的管理機關及其制度,大部分的集市參與者是當地的農民,并通過約定俗成的鄉規村約和經商傳統,在此共同體中實踐商貿行為并與鄉村社會系統互為一體。然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民間潛在的經濟能量得到很大釋放,集貿市場日益繁榮。先后在集貿市場所在地設工商行政管理所,加強市場管理,上內外。如今的黃渠橋街道兩旁,有近120余家以經營爆炒羊羔肉為主的餐館。從當地特色飲食業形成與發展的基礎性因素來分析,主要由于本地區的傳統經濟結構下復合型經濟模式和從業習慣所決定的。據筆者實地調查發現:該鎮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3%,并且每家每戶都飼養數量不等的牛羊,黃渠橋鎮周邊基本沒有天然的牧場,當地的畜牧業發展主要通過牲畜養殖場繁育和家庭圈養兩種主要方式進行,農牧兼顧的傳統生計方式為其特色飲食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與此同時,鎮政府還不斷完善全鎮15個養殖園區,發展小群多戶養殖和萬只羊場建設等措施,以鞏固本地的特色飲食品牌。
當地政府依托作為支柱產業的“黃渠橋羊羔肉”進行招商引資和產業鏈配套建設,先后建成黃渠橋奶牛養殖場、雨潤集團萬嘉羊業公司、金福來羊產業公司、金鑫奶牛養殖場、盛世龍鼎養殖場、通惠村生態養殖場、紅光村欣華農產品批發流通中心、長湖實業清真食品、東方羊毛1萬噸羊毛加工廠等相關產業,這種集約化、產業化發展戰略的推行是基于提升黃渠橋傳統畜牧業效益和補充農業生產不足、增加當地民眾的多元化收入和優化產業結構等多重考慮,并且正在新建的黃渠橋羊羔肉美食娛樂城及羔羊育肥基地,成為增加當地農民收入的主攻產業,有利于夯實“黃渠橋羊羔肉”品牌,擴大黃渠橋清真牛羊肉的知名度,推進農牧業復合型經濟發展。據筆者調查獲知,知名牛羊牲畜繁育基地和養殖場大部分為當地回族經營。同時,黃渠橋鎮通過招商引資在該地所設立的企業,如中糧、雨潤、匯源等落戶于黃渠橋,這些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大量人員從事農副產品的采集、篩選、包裝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部分民眾的就業問題。與此同時,居民在該鎮招商引資的影響下,其從業方式和收入來源也發生了很大改變。
農民經“土地流轉”后,每畝可獲得每年600元的出讓土地使用權補償收益,部分農民或外出務工或從事個體商業;還有部分農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其所經營的土地或從事的農業生產勞動,已不是以往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模式,而是轉變為以“打工者”的業態形式,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其生計方式由原先的以務農為主來維持自身的生計,變為具有“雇傭”關系的務農活動,其收入方式從農產品的出售所獲得的收益相應地轉變成為“工資”支付。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本地區在招商引資的帶動下,清真特色產業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促使當地原本以務農為主的民眾,其業態特征和收入路徑發生了市場化的轉變。由上所述,這一地區在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文因素等諸多條件的綜合影響下,形成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以回族傳統經濟帶動該鎮整體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當地的農牧產業與清真飲食業出現了耦合式的發展形態,從參與到當地“黃渠橋羊羔肉”相關建設項目的企業和農戶家庭的角度來分析,“實際歸屬于經濟學意義上的一種經濟結構的優化”[21],在一定意義上體現出:以當地的回族傳統經濟為基礎,從當地復合型農業中分化出了飲食業,飲食業又促進了社會資本的積累,進而帶動并轉向產業化、工業化生產,即在一定意義上出現了“農業———商業———工業分化而又統一于一體”的復合型的產業發展模式。雖然與嚴格意義上的標準化工業生產還有很大差距,但已初見端倪。這一產業發展的表象背后,折射出黃渠橋當地復合型經濟的形成過程是與一般意義上的產業演進過程存在著很大不同,一般產業的演進先是從農業生產積累中孕育出工業,然后發展到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然而,當地的黃渠橋羊羔肉產業(黃渠橋清真羊羔肉的生產、加工、銷售產業)演進過程卻截然不同,出現了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的演進模式,即當地回族農、牧、商并舉的從業方式孕育出了特色清真飲食業的興起和壯大,黃渠橋清真羊羔肉的馳名使當地以其為品牌進行招商引資從而發展了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的發展又促進和擴大了第三產業的活力與層次,三個產業互補共生。由此可以看出,因傳統經濟新的發展與不斷演進,形成了依托特色清真飲食業為基礎的產業鏈條,進而塑造出頗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清真飲食產業發展模式,成為了本地區回族傳統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經濟現象。
二、結語
寧夏銀北地區回族傳統經濟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生活具有多樣性并呈現出以農為主而兼營牧業、商業的形態,是由該地域整體上的過渡性地理環境和民族傳統復合形成的。歷史時期的這一地區曾是游牧民族征戰、生活及融和的舞臺,也是當時多元文化生成、繁榮和傳播地之一,并為當代的黃渠橋發揮地域、資源及民族優勢的傳統經濟模式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歷史上的黃渠橋鎮,長期處于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農業經濟與畜牧經濟的交匯地帶,由此為基礎逐漸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屬性的民間商業集市。盡管特別時期的阻礙因素,曾使得集市一度停滯,但新時期的社會環境使其再次得以復興。同時社會發展的同一性使得黃渠橋集市的演進歷程印證并成為這一區域社會變遷的真實寫照。黃渠橋集市所蘊含的回族文化底蘊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因不斷調適從而具備了新的社會屬性,這是黃渠橋集市在當代社會發展中顯得有別于其他傳統集市的原因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寧夏銀北地區回族傳統經濟變遷的特征。
黃渠橋這一地區的回族傳統經濟之所以能不斷發展并不被城鎮化的浪潮所淹沒,而且能夠演進出特殊的產業模式即獨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清真飲食產業,筆者認為,其發展動力的“源泉”就在于此區域具有一種包容、開放的文化底蘊。黃渠橋的回族文化是一種交匯的文化,歷史上的引黃灌溉及“招民屯墾”,使其秉承了黃河文化的深厚,同時又被賦予了中原農耕文化的凝重,而且民族間的互市貿易使其具有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開放,同時對現代文明能夠兼容并蓄,這樣的一種特色文化底蘊,塑造出的當地的回族文化是開放的、包容的,這種文化傳統落到今天的黃渠橋回族傳統經濟發展之中,就是文化與生活復合體的形成,成為了承載本民族得以不斷發展的動力源泉。
作者:杜華君單位:寧夏大學
- 上一篇:作風建設保障年活動方案
- 下一篇:街道環境綜治工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