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史學應用管理論文
時間:2022-05-25 05:39:00
導語:心理史學應用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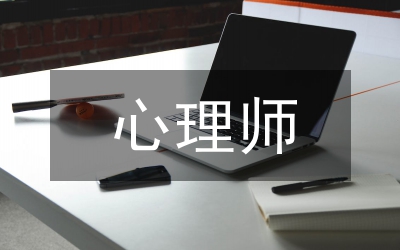
摘要: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是有效的。本文試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以此為例,淺談心理史學的應用。但是,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因此,在史學研究中必須科學運用。
關鍵詞:心理史學;群體心理研究;美國獨立戰爭
心理史學是心理學與歷史學交叉滲透所形成的跨學科研究。應該承認,人們的心理對歷史的發展必定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運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與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類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行為,可以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實際,也為歷史研究開辟新的視角,提供新的思路。當然,心理史學的發展還沒有達到完善,仍然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在此,試對心理史學的應用略作探索。
一般認為,心理歷史學始于精神分析學說對歷史學的滲透,而且這一滲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者弗洛伊德首開其端的,以《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其標志。精神分析學說在心理史學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盡管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學也逐漸進入心理史學的領域。
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進入歷史研究并非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心理學和歷史學都是以人的行為、思想、動機等為研究對象的;此外,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心理學其立論根據必須來源于可信的資料與證據,只是歷史學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學家探究患者的經歷與深層心理因素;兩者在認識論上也有相通之處,心理學家需要追溯研究對象的歷史,歷史學家的研究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心理的分析(將有關心理學的內容納入歷史研究絕對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創,在心理史學作為一個流派被確定之前,歷史研究對相關心理學內容的引入必定早已開始)。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是可行的。
從心理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學雖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但引起的爭議、存在的問題也不少。比較明顯的一點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走入理論模式去硬套歷史的誤區。埃里克森說:我們必須接受“半是傳說半是歷史”的歷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要探究歷史人物的心理必須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這些往往是史料中鮮有記載或沒有記載的,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家應該根據自己所受的訓練去采納一些傳說作為歷史證據,哪怕是無真實根據的也無關緊要,只要不與已知的事實相矛盾,并與心理學理論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認現代證據在歷史上的有效性,并將其作為歷史證據的替代物,這樣對待歷史研究,顯然是不嚴肅的。大量的心理史學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學家完成,而非歷史學家,且存在著將理論套事實之嫌,對歷史資料考證不詳,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來重構歷史,結果造成心理史學無真實性可言,這與歷史追尋的真實性相悖。這種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過了“社會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釋所有的社會活動。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視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礎,卻忽視了人的社會特性心理的社會基礎,片面夸大遺傳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卻忽視社會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發展對人類行為改變的作用。從心理史學的誕生來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學家用歷史證明其理論的產物,而且因而出現上述缺陷就不足為奇,但將心理史學作為一門進行歷史研究的史學方法的話,這種缺陷可能是致命的。應用心理史學作歷史研究,必須依據不同的歷史情境考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重因素對歷史人物心理的影響。集體心理心理狀態是一定群體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對于個人傳記式的心理史學研究,集體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穩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論的弊端。特別是戰爭、動亂、饑荒、瘟疫等歷史事件,集體心理較之個人心理對歷史研究更有幫助。大衛•斯坦納德提出“從理論上說,個人德感知性質乃是獨一無二的,但事實上,同一文化和社會群體中則經常存在著對象感知上廣泛的相似性,它與不同文化和社會群體間存在著的巨大的對象感知差異性同時并存”,“雖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會留心)一個13世紀的公民,一個中世紀的阿日本武士,或一個17世紀教友派信徒的會如何獨特地解釋米勒-萊爾錯覺,但是我們能夠知道并應該注意過去不同社會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認知假定的巨大差異”。在此,試著從宗教、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來把握集體心理,進而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
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原因涉及到諸多層面,這里,試圖將目光集中到一個特殊的群體——新英格蘭地區即獨立戰爭爆發地的英國移民,從這一移民群體的身上來發現、分析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別是17、18世紀時期的宗教,對當時的公共活動和私人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出生、成人、結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際交往等無不與宗教有著密切關系。最早到達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稱為“移民始祖”的群體,最初的移民動機便是宗教信仰問題。他們是一批來自英國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國主張清洗國教內部的天主教殘余影響而受到王室的壓制,慘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國王囚禁,當時的國王詹姆士一世聲稱,如果清教徒不順從,就把他們統統趕出國外。“移民始祖”是為了逃避宗主國宗教迫害,實踐自身宗教理想而來到北美的。所以說,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從一開始心理上便與宗主國有著一定的離心傾向。而且,這一群體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宗教信仰決定了他們總是雄心勃勃,懷有強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識,這點可以從移民領袖溫斯羅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們宣講教義時的預言得到體現,“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因此,我們如果在已經著手的事業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賜予我們的庇佑,我們就將成為世人笑柄,天下丑聞”。肩負神圣使命感來開拓新大陸的新英格蘭人在殖民地追求獨立的重要時刻,也必將責無旁貸,視之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可見,宗教情感為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的獨立意識打下基礎。既然在這里提到了溫斯羅普,那么順便說一下對歷史上領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認為領袖和被領導者是十分近似的,領袖創造性地利用客觀世界、社會制度、語言文化區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會引起成千上萬要求外部世界滿足自己需要的人們的共鳴,他與眾多的追隨者在本質上別無二致。顯然,埃里克森對領袖的解釋很難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樣板,但在此處,對于新英格蘭地區的移民領袖來說,這一解釋是合理的。
其次,環境因素也影響到新英格蘭移民的生活方式、社會發展等。先來看氣候條件,位于北部地區的新英格蘭氣溫較低,冬季漫長而寒冷,“波士頓1月平均氣溫為零下3度,最冷達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氣溫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氣候差異明顯,南部比較炎熱,弗吉尼亞夏天白天氣溫在32度左右,最熱時可達40度,因為此時各種疾病流行,許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長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蘭地區較少受到熱帶疾病的襲擾,各種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壽命較長,因而人口的增長穩定而有序。到達北美后新英格蘭居民比較順利地移植了他們在宗主國時的家庭模式,人口穩步增長,建構起正常的社會關系,并進入良性循環。家庭是社會結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對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體研究中得出的一個結論來說,他認為家庭及其對兒童的撫養形式是將社會價值和社會要求傳遞給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蘭從移民社會向本地人社會的轉變比較短暫。這一轉變可謂意義重大,因為第一代移民總會和英國有著千絲萬屢的聯系,對故土的思念、對宗主國的留戀使他們或多或少有一種漂泊感,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難把北美當作他們真正的家園,所以他們對英國有一種歸屬感,并且仍然會致力于保衛英帝國的利益,使得移民社會仍帶有濃重的宗主國特點。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們適應當地的氣候與環境,更何況他們沒有祖輩的英國背景和故土情結,與宗主國在情感上和血緣上都日益疏遠,他們把北美當作自己真正的家園,關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國的,應該說他們的心理已經是美國化的,而非英國式的,產生獨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來看地理因素的影響,新英格蘭的土地比較貧瘠,土壤中多石塊,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蘭地區發展農業的潛力不大,此后的事實也證明這里從來不是美國的主要農業區。地理環境的限制決定了新英格蘭不可能發展南部種植園形式的經濟,但與農業條件的惡劣相反,新英格蘭發展商業的條件非常優越,新英格蘭沿海的山地多與海洋相接,海岸線曲折,有許多大小港灣。商業貿易的發達使得這里的移民更具開放性,眼界更為開闊,經濟交流也帶動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漸形成。
新英格蘭移民的離心傾向在此后應對英國對殖民地的各項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過程在此不加贅述了。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五層次說”似乎解釋了這一成長過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這五個層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釋新英格蘭地區從最初接受英王特許狀的殖民地走到打響獨立戰爭第一槍的爆發地的演變——早期依附英國的殖民統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長、社會結構的穩定促進了社會交往需要;隨著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應運而生;為達到自我發展的最高能力,必須爭取獨立,這就是自我實現的需要。自己對于心理學理論的認識十分膚淺,分析可能有誤,因而在此不再展開論述。但在個體或社會遭受挫折時,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機制,當自身的發展已經到達相當高度,而且宗主國的壓迫已經難以忍受之時,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擊性反應機制是可以理解的。
針對前文中談到的心理史學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論模式去套歷史的弊端,如何來解決這一問題?托馬斯•科胡特的意見很有借鑒的價值。他主張,不應當用頭腦中預先準備好的理論框架去硬套歷史,而應借助頭腦中的心理學只是增加對于歷史問題的敏感性,雖然可以借助理論來加強對于歷史的解釋,但卻不能用理論來證實對歷史的理解,要證實這種理解應該用歷史的證據。而且,廣泛使用心理分析術語可以掩蓋作者的混亂、矛盾及對心理學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卻使讀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學著作有心理學上簡單化和歷史學上傾向歸納主義的趨勢。歷史家和精神分析學者處理他們所研究的人類對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們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釋問題的方法,因此以歷史家慣常應用的方法便可探知過去歷史的心理側面,因此心理歷史也可以寫成一般的歷史。應用傳統的史學方法,配之以對人類心理的敏感,能夠產生,事實上已經產生了歷史學科標準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尋求對人類心理的理解,托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爾泰的人文科學方法論——靠神會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認識,就是“在彼中重新發現我”,盡管神會的方法往往被認為是反科學的而加以摒棄,但歷史學能夠回答的最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么”,因而神會理解仍然是回答這一問題的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法。總之,歷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側面時既不需要也不應當依靠心理史學方法,但心理側面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問題,每個歷史實踐,每個歷史人物,都有其心理側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學問題,也沒有任何“合理的”歷史問題不包括心理側面。所以,托馬斯.科胡特建議將心理史學成為一般史學,讓心理史學家返回歷史家的行列。托馬斯•科胡特的意見某種程度上過于極端甚至被批判為反科學的,但對于心理史學的在實際中的應用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當然,如果心理史學家能夠接受心理學與歷史學的雙重訓練,或者能夠加強有志于心理史學的歷史家同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的密切合作,都將有效促進心理史學的研究。
隨著心理史學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對群體心理研究的加強,心理史學所應用的理論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其主要趨勢是突破心理學的局限,走向社會學、人口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綜合與交叉。彼得•洛溫伯格對心理史學所下的定義表達了這種認可——心理史學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新方法,是將“歷史學分析同社會科學的模型、人文學者的敏感、心理動力的理論及臨床對心理深層的洞察相結合”,以便形成對往昔更為完滿的觀念。類似的觀點,也可以從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定義中得到,“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就是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結論對過去進行考察。”由此可見,盡管心理史學研究仍以精神分析為主要理論,但其他理論(心理學范疇的和非心理學范疇的)的介入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和不可逆轉的趨勢。并且,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中,心理史學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應用心理史學的方法來作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必須綜合心理史學、計量史學、比較史學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來進行。
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啟發性的,但在具體應用過程中必須謹慎,不能走到心理決定論的極端,必須勇于探索歷史問題的復雜性,尊重歷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爾德的話來結束本文對心理史學的初探——心理學家敢于再現過去,并聲稱“我敘述了歷史事件”,而心理史學家甚至還要加上“我揭示了過去的心理”,這看來真是荒唐之極。但是,如果心理史學家不懈地努力的話,他總有一天會感到:“我從人的心理活動中,發現了人的真相。”
參考文獻:
[1]羅鳳禮.“美國的心理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2]彭衛.“試論心理歷史學的主體原則與理論層次”.載<史學理論>1987.2.
[3]大衛•斯坦納德著,馮鋼等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爾•J•布爾斯廷著,時殷弘等譯.美國人——殖民地的歷程[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
[6]李劍鳴.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絳等譯.美國早期史——從殖民地建立到獨立[M].商務印書館,1994.
[8]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
[9]托馬斯•科胡特著,羅鳳禮譯.“心理史學與一般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10]彼得•洛溫伯格,轉引自羅鳳禮.心理史學.“美國的心理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再來看地理因素的影響,新英格蘭的土地比較貧瘠,土壤中多石塊,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蘭地區發展農業的潛力不大,此后的事實也證明這里從來不是美國的主要農業區。地理環境的限制決定了新英格蘭不可能發展南部種植園形式的經濟,但與農業條件的惡劣相反,新英格蘭發展商業的條件非常優越,新英格蘭沿海的山地多與海洋相接,海岸線曲折,有許多大小港灣。商業貿易的發達使得這里的移民更具開放性,眼界更為開闊,經濟交流也帶動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漸形成。
新英格蘭移民的離心傾向在此后應對英國對殖民地的各項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過程在此不加贅述了。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五層次說”似乎解釋了這一成長過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這五個層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釋新英格蘭地區從最初接受英王特許狀的殖民地走到打響獨立戰爭第一槍的爆發地的演變——早期依附英國的殖民統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長、社會結構的穩定促進了社會交往需要;隨著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應運而生;為達到自我發展的最高能力,必須爭取獨立,這就是自我實現的需要。自己對于心理學理論的認識十分膚淺,分析可能有誤,因而在此不再展開論述。但在個體或社會遭受挫折時,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機制,當自身的發展已經到達相當高度,而且宗主國的壓迫已經難以忍受之時,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擊性反應機制是可以理解的。
針對前文中談到的心理史學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論模式去套歷史的弊端,如何來解決這一問題?托馬斯•科胡特的意見很有借鑒的價值。他主張,不應當用頭腦中預先準備好的理論框架去硬套歷史,而應借助頭腦中的心理學只是增加對于歷史問題的敏感性,雖然可以借助理論來加強對于歷史的解釋,但卻不能用理論來證實對歷史的理解,要證實這種理解應該用歷史的證據。而且,廣泛使用心理分析術語可以掩蓋作者的混亂、矛盾及對心理學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卻使讀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學著作有心理學上簡單化和歷史學上傾向歸納主義的趨勢。歷史家和精神分析學者處理他們所研究的人類對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們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釋問題的方法,因此以歷史家慣常應用的方法便可探知過去歷史的心理側面,因此心理歷史也可以寫成一般的歷史。應用傳統的史學方法,配之以對人類心理的敏感,能夠產生,事實上已經產生了歷史學科標準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尋求對人類心理的理解,托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爾泰的人文科學方法論——靠神會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認識,就是“在彼中重新發現我”,盡管神會的方法往往被認為是反科學的而加以摒棄,但歷史學能夠回答的最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么”,因而神會理解仍然是回答這一問題的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法。總之,歷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側面時既不需要也不應當依靠心理史學方法,但心理側面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問題,每個歷史實踐,每個歷史人物,都有其心理側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學問題,也沒有任何“合理的”歷史問題不包括心理側面。所以,托馬斯.科胡特建議將心理史學成為一般史學,讓心理史學家返回歷史家的行列。托馬斯•科胡特的意見某種程度上過于極端甚至被批判為反科學的,但對于心理史學的在實際中的應用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當然,如果心理史學家能夠接受心理學與歷史學的雙重訓練,或者能夠加強有志于心理史學的歷史家同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的密切合作,都將有效促進心理史學的研究。
隨著心理史學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對群體心理研究的加強,心理史學所應用的理論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其主要趨勢是突破心理學的局限,走向社會學、人口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綜合與交叉。彼得•洛溫伯格對心理史學所下的定義表達了這種認可——心理史學作為歷史研究的一種新方法,是將“歷史學分析同社會科學的模型、人文學者的敏感、心理動力的理論及臨床對心理深層的洞察相結合”,以便形成對往昔更為完滿的觀念。類似的觀點,也可以從理查德•舍恩沃爾德定義中得到,“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就是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結論對過去進行考察。”由此可見,盡管心理史學研究仍以精神分析為主要理論,但其他理論(心理學范疇的和非心理學范疇的)的介入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和不可逆轉的趨勢。并且,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中,心理史學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應用心理史學的方法來作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必須綜合心理史學、計量史學、比較史學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來進行。
總之,心理史學對于歷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啟發性的,但在具體應用過程中必須謹慎,不能走到心理決定論的極端,必須勇于探索歷史問題的復雜性,尊重歷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爾德的話來結束本文對心理史學的初探——心理學家敢于再現過去,并聲稱“我敘述了歷史事件”,而心理史學家甚至還要加上“我揭示了過去的心理”,這看來真是荒唐之極。但是,如果心理史學家不懈地努力的話,他總有一天會感到:“我從人的心理活動中,發現了人的真相。”
參考文獻:
[1]羅鳳禮.“美國的心理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2]彭衛.“試論心理歷史學的主體原則與理論層次”.載<史學理論>1987.2.
[3]大衛•斯坦納德著,馮鋼等譯.退縮的歷史——論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學的破產[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爾•J•布爾斯廷著,時殷弘等譯.美國人——殖民地的歷程[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
[6]李劍鳴.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絳等譯.美國早期史——從殖民地建立到獨立[M].商務印書館,1994.
[8]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
[9]托馬斯•科胡特著,羅鳳禮譯.“心理史學與一般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10]彼得•洛溫伯格,轉引自羅鳳禮.心理史學.“美國的心理史學”,載<史學理論>.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爾德著,姜躍生,張一平摘譯,羅鳳禮校.“對歷史的心理學研究”.載<史學理論>.1987.2.
- 上一篇:音樂教師行動研究管理論文
- 下一篇:商務局科學發展觀活動調研工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