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統帥湘軍評析論文
時間:2022-10-14 03:50:00
導語:曾國藩統帥湘軍評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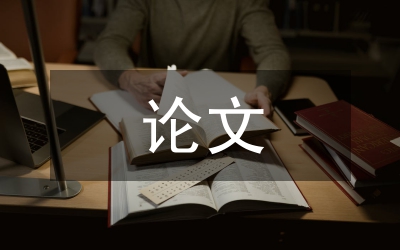
摘要:湘軍是一支針對綠營腐敗進行軍事體制改革而層層招募、層層隸屬的軍隊,它雖然克服了綠營的許多弊病,卻形成了各系備派和下級只服從直接上級因而難以統一指揮的格局。曾國藩作為湘軍的最高統帥,之所以能對湘軍指揮自如,主要是因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踐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關鍵詞:曾國藩;湘軍;道德踐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關后八旗兵逐漸腐敗,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編的漢人部隊即綠營。綠營在乾隆年間也和八旗兵一樣腐敗。到嘉慶年問,歷時九年的川陜白蓮教起義,就是依靠團練才鎮壓下去。咸豐初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清王朝也只有繼續依靠地方武裝,任命團練大臣辦團練。曾國藩就是咸豐帝任命的在湖南辦團練的大臣之一。后來湖南的團練由曾國藩統帥出省作戰,發展成為湘軍。
曾國藩對綠營的腐敗有深刻認識,他說:“以今日綠營之習氣,與今日調遺之成法,雖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氣,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曾國藩全集》第21卷第186頁,岳麓書杜,1994年版)曾國藩徹底否定了綠營。按照新的建軍機制組建湘軍:由統帥挑選營官。營官挑選哨弁,哨弁挑選什長,什長招募勇丁。曾國藩把這種方式組建的湘軍比作“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葉,皆一氣貫通。”(《曾國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由于層層招募,組成“這棵樹”的是利害相關、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會關系相近的人。維系“這棵樹”生存的不是普通軍隊的組織紀律。而是家族、親朋、師生關系。湘軍的招募制,使“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國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湘軍還有另一條原則,如果統領、分統、營官去位,其統部隊一般要解散。由新統領或新營官去重新組建。這就使得湘軍各護其長。心怕頭頭去位后在重新組建中地位降落影響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發財的機會。湘軍的這種建制,雖然克服了綠營的許多惡弊,但也因層層招募、層層隸屬,造成只聽命于直接長官而難以統一指揮的困難。
然而,湘軍的這種建制,并沒有影響曾國藩作為最高統帥的統一指揮。如果不是這樣,湘軍就不能鎮壓太平天國,清廷也就不會對曾國藩既恨且忌。李鴻章在《曾國藩神道碑》說:“公治軍,謀定而后動,折而不撓,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去,皆遵守約束不變”。這話并非溢美。曾國藩不僅在軍時將士聽從他的指揮,即使守制離開了軍隊,清廷的命令他們可以不聽,但曾國藩“一紙千里赴急”。(引自朱安東《曾國藩傳》第33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軍將士之所以聽從曾國藩的指揮。其原因當然是復雜的,如他見識遠大、高人一等的戰備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領銜奏事保舉官員的權力而使人隨從,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踐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對此不論是曾國藩同時代的人,還是后人,都有頗為一致的評論。如作為曾國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閎。他在《西學東漸記》中評論說:“曾文正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亂,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揮若定,全境肅清者,良以其才識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世界上對人征服無外乎兩種,一種是外力控制,威逼加利誘,它憑藉的是權勢;一旦權勢衰退,這種征服便化為烏有。另一種是內心征服,使人心悅誠服,它憑藉的是高尚人格,是道德感動。曾國藩以他的道德踐履和高尚人格去感動湘軍將士,使他們心悅誠服地聽從他的指揮。湘軍將士特別是那些學養深厚的將士,無論心腹與否,無不奉曾國藩為道德圭臬。李鴻章、容閎、薛福成、黎昌庶這些心腹知己自不必說,即使與他有隙甚至交惡的李元度、左宗棠也莫不如此。曾國藩逝世,與之交惡的左宗棠挽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勿負平生。”李元度數次為曾國藩所參,曾國藩逝世,他長歌當哭,撰文祭曰:“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如我。地拓海容。”郭松林的一首挽聯則更具體地表現了曾國藩以德感佩湘軍:“偉業冠古今,滿而不溢,高而不危,統求國計民生,先憂后樂;薦賢遍天下,功則歸人,過則歸己,若論感恩知己,異口同聲。”
以德感人,這種征服是情感的征服,是內心的誠服,這種征服后來被生于韶山開創了一個新時代的偉人稱為“大本大源”。正因為它是“大本大源”。所以是最強大的、最持久的。曾國藩“德業文章,炳耀環宇”,不僅在當時“雖婦孺亦感佩其為人”;(龍夢孫《曾文正公學案序》,《曾文正公學案》)即使在今天,其高尚人格也使人感動至深。曾國藩以德御軍。其高尚人格的道德踐履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述之,主要是“忠、恕、廉”。
忠是理學最高的道德準則。理學認為。道德倫理是理的體現。理,“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劉元承編《二和遺書》卷十六)曾國藩發揮說:“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則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曾國藩全集》第14卷第13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作為理學家的曾國藩,忠無疑是他踐履的最高道德準則。早在京官時期。嚴格深厚的理學修養就使他從謀求個人和家庭的發展升華到了謀求國家發展挽救清朝傾墮的境界,冒死上“三疏”,為國忘身忘家就是明證。太平天國爆發,清帝國風雨飄搖,是忠使他以一介書生投入血與火之中,組建了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殊死斗爭。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對清帝國的忠集中體現在“三個不顧”。
不顧性命。曾國藩墨從戎,從荷葉塘踏上赴團練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場的決心。就任長沙,曾國藩在《與州縣公正紳耆書》中就發表就職宣言:“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以藉以號召吾鄉之豪杰,”以后,曾國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跡。曾國藩對清王朝的忠,不僅表現在疆場視死如歸,更表現在他為朝廷的根本利益而不顧性命屢屢對抗旨意。咸豐三年,衡陽練兵未就,咸豐帝就催迫出師,曾國藩幾次抗旨。即使在咸豐帝震怒的情況下仍冒死上疏陳述不能立即出師廬州的五條理由。咸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墨從戎,為堅持“重扼上流”的戰略方針。曾國藩又一次抗旨。事實證明,如果不是曾國藩屢屢抗旨,或者是羽毛未豐就從衡陽貿然出兵,或者是放棄“重扼上流”的戰略決策,太平天國后的清朝歷史或許就要重寫了。王安定在《湘軍記》中曾評曾國藩成功在于“堅決不動搖,排眾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學力勝也。”在這里,王安定只講了原因的一部分,曾國藩的成功不僅在學力,還在忠心。沒有忠心,沒有把國事看作家事的精神,曾國藩是斷不會屢屢抗旨的。
不顧名聲。作為一個正直的士大夫。作為一個理學家,名聲的重要不亞于生命甚至高于生命:為捍衛名譽而放棄生命的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比比皆是。曾國藩就曾說過:“然君子愛惜名聲,常存水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曾國藩全集》第20卷第841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然而曾國藩為挽救清朝危亡。往往置個人名聲于不顧。為鎮壓湖南農民起義,他殺人如麻,落了個“曾剃頭”的惡稱。針對官場優容茍安、不白不黑、置國事不顧的情況。曾國藩不惜落侵官越權之惡名。衡陽練兵未就,咸豐帝命他出兵拯救安徽,曾國藩抗旨,致使座師、湖廣總督吳文死事。這更要負忘恩負義的罵名。后來曾國藩辦天津教案。他謀國安危不顧譏議紛起,不顧損害鎮壓太平天國而獲得的隆譽,不顧賣國賊的罵名。正是為履行忠這一最高道德準則而不顧個人名聲的繼續和集中體現。
不顧疑忌。清王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漢人實行嚴密防范的既定政策,從來不輕易授漢人以實權。對曾國藩也是如此。清王朝對曾國藩是既利用又疑忌。咸豐四年。曾國藩克武昌,咸豐帝在屢聞敗奏的情況下聞此捷報十分興奮,一喜之下賞給曾國藩一個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當時一軍機大臣對咸豐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數萬人,恐非國家之福也。”咸豐帝王將相聞此言“默然變色者久之”,(薛福成《書宰相有學無識=》,《庸庵全集·庸庵文續編》下卷第7頁)終于收回成命,曾國藩因此客位虛懸。處在既要籌措軍費又無實權的尷尬境地。后來曾國藩欲以守制挾請地方實權。然清廷在局勢好轉的情形下竟順水推舟,允準曾國藩守制。直到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再次被擊潰,在無兵可用的情況下,才給曾國藩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清廷雖然授給了曾國藩實權,但對他既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沒有改變,仍用各種方法加以抑制。或者利用湘軍派系。如在左宗棠與曾國藩不和而袒左抑曾;或者利用督撫矛盾。如在沈葆楨與曾國藩爭厘金而袒沈抑曾。攻克天京時,更是借天京金庫和幼天王逃走事對浴血奮戰的曾國荃嚴厲呵斥。以通過抑荃以抑藩。曾國藩本人對清廷對他的這種防范抑制態度自然有深刻的感受和認識,當他聽到湘軍攻克天京的消息后,繞室彷徨,徹夜不眠。自己效忠的政權竟對自己百般猜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與悲劇。即使是這樣,曾國藩仍未改其初衷,他對忠這一最高道德準則的踐履仍是那樣的沉溺與執著。
矢忠君國本是湘軍的群體意識,特別是高級將領的群體意識。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他對忠這一最高準則的踐履。無疑會使湘軍將領乃至整個湘軍將士的矢忠意識得到強化。感動和激勵他們為拯救面臨滅頂之災的清王朝而效命。胡林翼為曾國藩的忠心所感動,他開府湖北握有地方實權。對曾國藩有求必應。無所顧惜。郭嵩燾感嘆:“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羅澤南說:“天茍未亡本朝,此老必不死。”(引自孟易醇《曾國藩傳》第134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國藩效忠君國不僅感動著湘軍將士,也感動著湘軍以外的許多官僚,如廣東花縣人駱秉章。靖港之戰,湖南臬臺商量,請駱秉章劾奏曾國藩,駱秉章回答說:“不可,國藩謀國甚忠,當靜待之。”(印章鸞《清鑒》下冊第64,7頁)后來湖南成為湘軍后方和軍需基地,駱秉章發揮了重要作用。
恕是儒家最重要的倫理原則。《論語·里仁》記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論語·衛靈公》記載:“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國藩作為一個理學家。不但繼承了儒學恕的思想,而且從理學高度對恕進行了更深刻的闡述,他說:“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門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曾國藩全集》第20卷第1394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曾國藩在這里把設身處地的待人原則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這一原則是他終身恪守的。在統帥湘軍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就是通過踐履這一道德原則來處理與同僚與部屬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從而把他們緊緊團結在自己周圍。曾國藩這一時期對恕這一道德原則的踐履主要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寬容。最能體現曾國藩寬以待人的,是他與左宗棠的關系。左宗棠,湖南湘陰人,恃才傲物,自稱“今亮”;但屢試不中,居鄉里,四十一歲才人佐湖南巡撫張基亮。鋒芒畢露而又科場失意的左宗棠對為人拙誠、科場得意、官運暢通的曾國藩很是輕視。他們那時雖非同僚卻是同鄉,見面時常有齟齷。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妾洗腳,笑日:“為如夫人洗足”。左宗棠反唇相譏:“同進士出身”。有一次。曾國藩出一上聯:“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嵌了進去;左宗棠對下聯:“藩侯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這些雖是傳言,卻也反映了二人的早期的不諧關系。但曾國藩對左宗棠一直是寬宏大量,不計前嫌。左宗棠的大器晚成,終于出將入相,離不開曾國藩的保薦之功。
左宗棠曾為巡撫駱秉章代擬奏折,劾請將私役兵弁、挪用公款的樊燮撤職查辦。樊燮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為劣幕,咸豐帝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咸豐十年,左宗棠被迫離開駱秉章撫幕。后來因胡林翼、駱秉章上疏又得肅順進言,案子才得以了結。這時左宗棠只得投向駐軍宿松的曾國藩,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不久,奏準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幫辦軍務。曾國藩又讓左宗棠回鄉募勇開赴江西戰場,讓他掌握軍事實權。幾個月后,曾國藩上奏左宗棠戰功,使他晉升為三品京堂;成豐十一年,又奏準改襄辦軍務為幫辦軍務。第二年,又奏請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不久,左宗棠被任命為閩浙總督,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要知道,三年之中曾國藩對左宗棠四次舉薦,使他從一個被誣告走投無路的士子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是在二人存在嫌怨的情況下進行的。二是自省。反躬自省的道德修養,曾國藩在做京官時就狠下了一番功夫。與人有隙,不管是友人、仆人還是家人,他都是從自己這方面找原因,都是反省自己。到了統帥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時候,更是把反省精神推及治國平天下。對于處理湘軍與地方的關系,曾國藩總是告誡部下。軍隊要主動。如他告誡蔣學凝說:“地方官挾嫌構釁。在所不免,然軍營每至各縣,其初須力禁騷擾,其繼須獎借官民。若既不禁騷擾,又不能獎借,而反苛責之,怨詈之,則官民之責我罵我。百倍于軍中之責彼罵彼。”(《曾國藩全集》第13卷第300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而最能體現曾國藩自責精神的。還是他處理江西巡撫與他爭厘金的事。
湘軍是一支自籌軍餉與太平天國作戰的部隊,曾國藩曾幾次言及。湘軍不難及籌兵而難在籌餉。曾國藩客位虛懸的艱難主要也是難在籌餉。他與地方的矛盾主要也是因為籌餉引起的。咸豐十年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后。客位虛懸的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但由于長年戰爭,滿目瘡痍,軍餉的籌措仍十分困難。到同治元年圍攻天京時,曾國藩所統湘軍已達12萬,每月食米需5萬多石,而這時米價昂貴,每石米銀價已在白銀3萬兩之外。曾國藩籌措軍餉十分焦急。但就在這時,卻發生了江西巡撫沈葆楨與他爭厘金的事。
同治元年十月,沈葆楨奏準截留江西漕折銀5萬兩,又將九江的關洋稅截留。而這時湘軍已發生因無餉潰逃的事。同治二年,沈葆楨再次截留江西厘金,而這時正是攻破金陵前兩個月的關鍵時刻。而“營中竟有食粥度日者”(《曾國藩未刊信稿》第213頁)曾國藩擔心因缺餉嘩變而功虧一簣,萬不得已才上《沈葆楨截留江西牙厘不當仍請由臣照舊經收餉摺》,在摺中列舉了沈葆楨截留江西厘金不當的三條理由:
1、江西軍餉狀況優于湘軍,江西發八成,湘軍只發四成;江西欠餉五個月。湘軍欠餉十六七個月不等。
2、按權屬,巡撫應由總督節制;按事屬,厘金應由總督直接主持。
3、按情狀,在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應患難相恤,有無相濟。
沈葆楨與曾國藩爭厘金。完全是沈葆楨不顧情理、恃才做上引起的,曾國藩沒有過錯。即使是這樣,曾國藩仍然反省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急躁。在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的日記中他描述自己的焦急心情后內省道:“皆由平日于養氣上欠下功夫,故不能不動心”;“實則處大亂之世,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理,而鄙懷忿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責懲治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三是自悔。曾國藩被湘人稱為“鄉圣”,但它到底不是圣賢。他雖然待人寬厚。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也有過頭的時候,如他幾次參奏李元度。人非圣賢,敦能無過?一個道德修養高深、道德踐履踏實的人與一般人的區別。不在于有無過錯,而在于對于過錯的態度。曾國藩對于參奏李元度之悔,從另一個方面表現了他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恕的道德原則的踐履。
曾國藩曾三次參奏李元度。第一次是咸豐十年的徽州之失,因曾國藩的參奏,李元度被革職微寧地太廣道之職。革職后,李元度不經請示,徑自回鄉招募了一支千多人的隊伍。取名叫“安越軍”。咸豐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軍援鄂有功,經總督官文、巡撫胡林翼奏請,賞還按察使原銜;旋入江西有功,經巡撫敏科奏請加賞布政使銜;這年九月,因浙江巡撫王有齡許諾官升藩司,李元度不顧胡林翼勸阻,改換門庭,投向王有齡,同治元年正月得補浙江鹽運使兼布政使。二月又擢升浙江按察使。就在李元度擢授浙江按察使的上諭發出后的第十九天即二月二日,曾國藩第二次參奏李元度虛報戰功、援浙不力,結果使從厄運中解脫、蘇復的李元度再罹惡運。被革除新授的官職交左宗棠差遣。這年的五月十七日,曾國藩在參奏“私行遠揚”的陳由立和貪生怕死、擾亂地方的總兵鄭魁士的同時,參奏李元度和鄭魁士一樣。都是薄有時名、輕于去就。
曾國藩參奏李元度失之過嚴,有違恕道。首先,李元度并非一個朝秦暮楚、背信棄義之人,他之所以投向王有齡,是因為他急于走出厄運。不是對曾國藩情感上的背叛,這從后來他與曾國藩交往以及為曾國藩所作的挽聯可以看出。其次,李元度有功于曾國藩和湘軍,這正如曾國藩在“三不忘”中所育,在曾國藩的幾次困境中。李元度都給了他可貴的支持。再次,帶兵非李元度所長,但咸豐十年強之帶勇的正是曾國藩自己,徽州失守曾國藩也難辭其咎。第四,李元度雖然措軍不當,但守徽州身先士卒,“身臥城頭,竭力堵御”,絕非貪生怕死、棄城逃命的鄭魁士之流。
對于那樣嚴厲參奏李元度特別是把他與陳由立、鄭魁士一同參奏。曾國藩后來十分后悔。隨著地位的越來越顯赫,這種后悔的心情也越來越強烈。同治四年曾國藩在《加李翰章片》中寫道:“次青之事,鄙人負疚最深。在軍十年,于患難之交,處此獨薄。近歲事機大順,悔之無及。”曾國藩的自悔,從史料看始于同治元年。這年正月,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二月又交部從優議敘,這時被他嚴參的李元度仍寄來情真意切的賀稟,曾國藩看后悔意無窮,三月二日在日記中寫道:“因李次青來一賀稟,文辭極工,言及前此參奏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覺有不安。”此后。曾國藩在書信、日記中多次表現了自悔之意并采取了補救措施。如同治元年六月。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余平生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同治三年,曾國藩給清廷上《密陳錄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摺》,摺中有“三疚”之說。其中“臣兄弟叨竊異數,前后文武官員,無不仰荷殊恩。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臣對之有愧,不得不略陳一二,上干圣聽”的話,確為真誠悔過之言。十一月,曾國藩將上奏的事寫信給李元度:“往者患難相從,為日最久者,于今己無多人,而事會乘除。乖違素志,尤覺欽欽抱歉,不能自己。”(《曾國藩全集》第27卷第4829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向李元度表示了道歉。
廉曾國藩做京官的時候。就把廉作為做官的根本。從那時起曾國藩就立志做一個清官。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他在寫給弟們的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神明鑒臨,予無失言。”(《曾國藩全集》第19卷第18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曾國藩立下的這一志向,他恪守奉行終身。做京官的時候,他從不輕易受人錢財;任圃練大臣組建湘軍,他提出“不要錢,不怕死”;后來統率湘軍出省作戰。經他的錢糧無數。他不妄取一絲一毫。他在湘軍將士面前塑造的廉潔人格形象,形成了巨大凝聚力。這是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把廉作為做官的根本一樣。曾國藩把廉作為治軍的根本,他以廉自律,以廉律下。曾國藩統兵在外,給家里寄錢很少,他在成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家書中寫道:“余寄一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金濟親族,此百金恐尚不敷家用。軍中錢糧。余不敢妄取絲毫……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女輩,概愿儉于自奉。”
“惟儉可以養廉”(《曾國藩全集》第13卷第290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曾國藩總是把儉與廉連在一起來說。曾國藩雖然是湘軍最高統帥。官居要職,權傾天下。但他生活十分儉樸。食,他粗茶淡飯,每餐僅一葷,即使做了大學士也是如此,被人稱為“一品宰相”。穿,他身為宰相,而衣服不足三百金。穿的是布衣布鞋。都是家人做的。30歲生日,做了一件青緞馬褂,平時舍不得穿,只是在有喜事慶賀或過年時才穿。到逝世時,這件馬褂還和新的一樣。住。他平生以起屋買田為仕宦惡習。他曾委托弟們在家為他侈理舊宅作養老之用。但他弟弟曾國莖、曾國潢卻違背他的意愿修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富厚堂。曾國藩對此大為惱怒,他寫信譴責曾國荃說:“新屋搬進容易搬出難,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易孟醇《曾國藩傳》第47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來曾國藩果真終于任所,未踏進新屋一步。曾國藩住所中的擺設也十分儉樸,擺在書房中的書箱每箱不過數百文。曾國藩的一生是儉樸的一生。即使在鎮壓太平天國以后,生活安定了,他仍為打了一把銀壺而自責,為買一部《十三經注疏》而反復權衡書價貴賤,為家中入不敷出而焦心。
對于曾國藩的廉潔儉樸。他的幕僚和湘軍將士無不欽佩。容閎在《東學西漸記》中說:“曾文正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亂,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揮若定。全境肅清者,良以其學識道德均有不可及者。當時七八個省政權,皆在掌握。凡設官任職,國課軍需皆聽調度,幾若全國聽命于一人。顧雖若是,而從不濫用其無限之權威,財政在握,絕不聞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自肥其親屬。以視后來彼所舉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語矣。文忠絕命時,私產四千萬遺子孫;文正則身后肅條,家人之清貧如故也。曾文正一生之政績,實無一污點。其正直廉潔忠誠諸德,皆足為后人模范,故其身雖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
趙文烈在《能靜居日記》記載了與曾國藩這樣一段對話:“材官持一紙示師。師頷之。顧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謝不敏。師曰:“‘此吾之食單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蔬,凡五品,不為豐,然必定之隔宿。’余欽佩儉德。因曰:‘在師署中久,未見常饌中有雞騖,亦食火腿否?’師曰:‘無之,往時人送皆不受,今成風氣,久而不見饋送矣。即紹興酒亦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三百年。不可無此總督衙門。’師曰:‘君他日撰吾墓銘。皆作料也。’相視而笑。”
曾國藩統率的湘軍軍餉自籌。欠糧欠餉的事經常發生,有時欠餉達一年多,有時舉軍食粥;但將士仍然奮戰疆場,潰逃只是個別情況。究其原因,不能不歸于曾國藩在將士心目中樹立的廉潔形象。對此。曾國藩在奏摺中說:“同治二三年間,統軍至十余萬人,欠餉至十五六個月,從未有兵勇向糧臺索餉滋事者,一由于糧臺之銀隨到隨發,從無存留;一由于發餉之際,概由微臣斟酌,不與委員相干。因是差免于浮冒之弊。而即以取信于將士之心”(《曾國藩全集》第9卷第4829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
- 上一篇:開發處副主任競聘演講稿
- 下一篇:科技公司副經理的競聘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