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村落形態探究論文
時間:2022-10-23 04:03:00
導語:漢唐村落形態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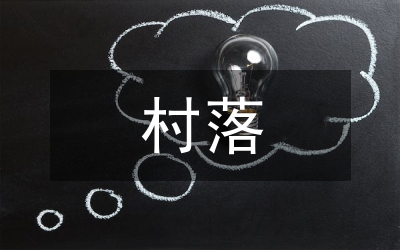
內容提要:村落是與城邑相應的社會單位概念,源于龍山時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茲至漢,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鄉村基本聚居形態。漢代鄉村組織的特點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了里聚分離,作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義;至唐代,里正成為鄉政的主持者,村正開始行使里正職掌,村落的行政與法律地位得到確認,鄉里之制演化為鄉村之制。這一演化實質上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分合變化,并不具有城鄉分離的內容,與“城邦帝國”、“領土帝國”之概念亦無干涉。不論作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時代具有多少稱謂,它一直是與城邑對應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地緣組織與血緣組織的共同體。
漢唐時代,是中國古代鄉里之制與聚落形態演化的重要轉折時期。從兩漢時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里與聚的分離,再到唐代的鄉里合署與村落地位的確認,無論是外在形態還是內在結構,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中國中古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討論漢唐村落形態,首先面臨的是關于村落的發生問題。對此,日本學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宮崎市定、宮川尚志等學者的論述最具代表性。宮崎市定先生認為,自上古到現代,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為都市國家,以大小城邑為地方社會集合體的基本構成,“聚落恰似一個個細胞,在一定面積的耕地中心,存在著細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內,被區分為數個區域,那就是里。不僅是工商業者,就連農民也居住在城內的里中。在漢代,根據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別定級為縣、鄉、亭”。他還認為,城內農民開始移居城外,鄉制開始瓦解,“促使這種瓦解趨勢進一步發展者,是漢代豪族勢力的擴張。可能是一方面便利農耕的負郭、帶郭之田都被有勢力者所獨占,貧民要想擁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須求之于遙遠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們在遠距離的地方開拓莊園,招募勞動者,于是城內的農民漸漸脫出城外,前來居住應募。這里出現的就是另一種新形態的聚落——村(邨)”①。盡管學界對于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說”爭論頗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之說卻被多數學者接受,此后學術界有關中國古代村落問題的研究也多以此為基點展開。宮川尚志提出:“在漢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戶設里的制度。到唐代,雖然單位一樣,但在城市與鄉村分別稱之為坊和村。這是城市和鄉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時也使人聯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遠離中央政權的邊鄙地區呢?”在經過一番分析討論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認為“總體來看,村莊分布在山間河谷地帶以及一般遠離城市地區的實例較多”②。侯旭東先生對此說進行了修訂,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僅見于邊僻之地,城鎮周圍同樣廣泛存在……重要交通線附近亦廣泛分布。”③這是正確的。但他只是較宮川尚志更強調了村落分布的廣泛性,仍未脫出村落是新興聚落形態這一范疇。
源于宮崎市定先生的村落為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說,有一個重要前提值得進一步討論,這就是漢代里的設置問題。依宮崎市定先生之說,漢代的里設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無居民聚落,也就沒有里的設置。但是,從文獻資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獻資料看,并非如此。在兩漢社會,雖然史籍與法律文書都以鄉、里涵蓋整個鄉村社會,然而實際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層單位鄉里之外,還存在著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們實際上是鄉里之制的基礎。這些村落,漢人稱之為“聚”、“落”或“格”。《史記·五帝本紀》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說文解字》釋“聚”曰:“聚,會也。從*,取聲,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謂邑中村落。”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廣雅》曰:“落,謂村居也。”格,為漢人對村落的別稱。《史記·酷吏列傳》:“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垢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司馬貞索隱:“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漢代的聚落同鄉里一樣,也各有名號。如《論衡·書虛》所云:“天下郡國且百余,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認可的居民單位,在兩漢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說,聚只是自然意義上的鄉間聚落,不具備行政與法律意義,更不是基層編制單位。正因為此,在兩漢文獻中,才大量充斥著鄉里的記載,而較少見到關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漢代聚的規模大小不一,有時相差懸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幾戶人家,如東漢南陽郡井水縣的三戶亭,就是在三戶聚所設置的亭;也有的聚多達千余戶居民,如西漢成帝即位后,封史丹為武陽侯,封地為“東海郯之武強聚,戶千一百”。這樣,有些大聚便可能成為縣或鄉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戶數多少,劃分為若干里,像武強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個里;也有極少數的甚小聚落,會若干聚合為一里,像三戶聚這樣的小聚落,便應如此。
①[日]宮崎市定:《關于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1、23~24頁。
②[日]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8、79頁。
③侯旭東:《北魏村落考》,載《何茲傘教授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們與里的設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聚與里是重合的。這些聚落既然錯落參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現有的自然聚落基礎上設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數百戶或小至三五戶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況下,都是每個聚落設置一里,三十幾戶、四十幾戶以至百余戶都可作為一里。史料記載與有關規定,均是舉其成數而已。
這樣,也就出現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說法。但在實際的地方建制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為了保持與規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將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關系上重新切割組合,對此,我們只須看一下關于里的具體記載便會一目了然。例如,《漢書·張安世傳》記道:“(宣帝)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斗雞翁舍南。”這是三十戶為一里者。《漢書·戾太子傳》曰:“故皇太子謚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這是二百家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兩漢時代里與聚的合而為一,《續漢書·郡國志》所記歷城之“巨里聚”其意當同于此。
為張賀所置守冢三十戶以及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為的編制,因此,雖然不合“百戶為里”的說法,但初時還算規整,要經過若干年的變化后,才能呈現出里的本來的自然面貌。就現在材料看,最能反映兩漢鄉村社會中里的真實面貌的,還是馬王堆出土的《駐軍圖》與《地域圖》①,這是關于漢代里的規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駐軍圖》,其上不僅標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戶人家,最大的里為一百零八戶,現將圖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戶數統計并
列為表1如下:
①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編:《古地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頁。
由上述記載特別是《駐軍圖》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戶狀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鄉村社會,它們與各類城市相對應,共同構成了地方社會組織結構。既如此,為什么學術界仍流行著村落為城郭之外新興聚落形態說呢?這是因為人們對村落的考察首先多著眼于其字面記載之由來。比如,要追尋《說文解字》中有無“村”字,要檢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現于何時,在筆記野史中出現于何時,等等。這樣,自然會得出結論:《說文解字》中沒有出現“村”字;關于“村”的最早的記載,正史是《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所載“村落齊整如一”,筆記野史中是《抱撲子·內篇》卷三《對俗》所引東漢陳寔《異聞記》“村口”一詞。因此,“村落”也就出現于東漢,至六朝漸多。其實,從社會組織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與城邑相對應的一種聚落形態。就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而言,村落與城邑的區界點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與農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規模明顯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為權力中心與經濟中心;其三,村落無論大小,都自成一體,有著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緣以及其他組織體系,是社會的基本細胞。這也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村莊是一個社區,其特征是,農戶聚集在一個緊湊的居住區內,與其他相似的單位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在中國有些地區,農戶散居,情況并非如此),它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其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應當是一種相對于城邑而言的社會單位概念,可以稱之為“村”,也可以稱之為“聚”,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莊”、“屯”、“川”、“寨”、“丘”、“店”、“堡”、“鋪”等等。關于村落的起源應當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據考古學研究,特別是聚落考古學的進展,我們已能知道,隨著農耕文明的出現,聚落也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至龍山文化時代,聚落已分化為中心聚落與普通聚落;隨后,便開始了城邑與鄉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為城邑并成為一定區域的權力與經濟中心,普通聚落則成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圍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漢代,這種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漢代社會也就不是所謂的“都市國家”,而是以村落為基本細胞、以城邑為核心的上下貫通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①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②見拙作《中國遠古社會史論》第六章《聚落的分化與消亡》,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 上一篇:環境噪聲管理制度
- 下一篇:電磁輻射設備申報登記工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