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販運貿易研究論文
時間:2022-10-28 10:38:00
導語:漢代販運貿易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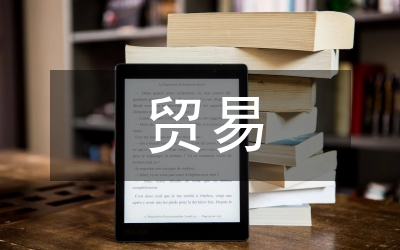
販運貿易是漢代商業活動的重要形態之一,但以往對此缺乏必要的系統研究。考諸史冊,漢代販運貿易的類型,既有私營,也有官營。為便于集中探討,這里僅就私營販運貿易中的若干基本問題做些歷史考察。失當之處,有望大家賜教。
一、販運貿易的興起和發展趨勢
販運貿易,亦稱販運商業。馬克思謂之為“轉運貿易”[①]。在秦漢的簡牘、文獻中,有“行賈”、“中販”、“商販”、“賈販”、“市販”、“販賈”及“私販賣”等用語[②],審其精意,一般都是指從事買貨出賣的販運貿易。這種商業行為,不是生產過程的組成部分或必經階段,而是商人將生產物從有余的地方運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區差價,通過長途販運、賤買貴賣的不等價交易而牟取利潤的一種商業活動。
販運貿易的淵源甚早。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地區間的交往增多,販運貿易便逐漸成為商業活動的重要形式。如鄭國商人弦高,就曾在販運途中機智地救了他的國家[③]。越國大夫范蠡,“乘遍舟浮于江湖”,從事販運貿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④]。陽翟大賈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⑤]。當時,各地方物、土特產日漸進入流通領域。荀子說:“今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國得而財使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下之復,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至其用”[⑥]。不僅地區間的商業聯系加強,土特產的商品化成份增多,而且某些手工業品如銅器、布帛等,也越來越成為販運貿易的商品內容。其時的販運商人,能“料多少,知貴賤”,了解各地物價行情。為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貿賤鬻貴”,他們“負任擔荷,服牛駱馬,以周四方”[⑦]。甚至不顧疲勞,不畏艱難,遠出千里之外行商。這正如文獻所說:“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不遠者,利在前也”[⑧]。“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⑨]。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長途販運商人的活躍和“求利”之急的情景。秦漢時期的販運貿易,正是在戰國基礎上得到興起和發展的。
漢代繼秦之后,國家統一,疆域遼闊,生產發展,交通便利,市場擴大,較之戰國之時,為商品流通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但在這四百多年中,隨著政治、經濟諸因素的變化,當時的商業和販運貿易也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過程。
西漢前期,國家經過一度恢復之后,由于對工商業實行寬惠政策,弛商賈之律,解山澤之禁,通關去塞,開放關市等,使封建社會商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當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⑩],從事商業、販運貿易的人甚為普遍。據載:關中的雍,“隙隴、蜀之貨而多賈”。櫟邑“亦多大賈”[①①]。周地“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①②]。鄒魯“好賈趨利,甚于周人”。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南陽“俗雜好事,業多賈”[①③]“宛、周、齊、魯,商遍天下”[①④],確乎經商成為一種不可遏止的趨勢。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許多地域性的販運商人。如魯人曹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齊刁間“逐漁鹽商賈之利”,“連車騎,交相守”,“起富數千萬”。周人師史“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①⑤]。這些販運商,往往“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①⑥]。他們隨著商販經驗的積累,不僅能區別不同商品組織地區流通對經營盈虧的關系;而且懂得“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①⑦]的道理。即商品太貴,往往是跌價的征兆,太賤則是漲價的苗頭,還值得注意的是,據湖北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簡牘:文景之時,已出現了所謂“中舨共侍約”[①⑧],即合伙做商販所共同訂立的契約。諸多事例表明,西漢前期的販運貿易是比較發達的。在那時有不少販運商發了大財。他們“富至巨萬”,或“能致七千萬”[①⑨],形成了強大的商業資本,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正如《史記·平準書》所說:“富商大賈,或嵽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但漢前期這種商品經濟繁榮的表象,也隱藏著嚴重的社會問題。
漢武帝在位之時,存在著復雜的社會問題和民族矛盾。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當時采取了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均衡平準、謫發商賈等一系列措施,并規定:“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②⑩],加重對商人車船的稅收。這種強化官營,打擊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漢興以來迅猛發展的私營販運貿易,遭到抑制和打擊,也使整個商品經濟進入了一個間歇期。不過,從一些材料看,在西北邊郡,商人勾結官吏,囤積販賣,賤收貴鬻而牟取暴利者仍有。如據漢簡:“同安糶粟四千石,請告入縣官貴平賈(價)石六錢,得利二萬四千,又使從吏高等持書請安二聽入……”[②①]。意思是說,同安其人,趁市場缺糧時,糶粟四千石,以高于平價每石六錢的價格出售,獲取暴利二萬四千錢。而且同安進行如此大宗的投機販賣,只需與官方打一聲招呼即可。于此說明,當時盡管實行“平準”政策,然販運商通過與官吏勾結,對政府的法律并未完全遵守,私販仍存。但從總體上說,武帝時期的私營販運貿易乃不如西漢前期,其經濟實力也明顯衰落。
昭、宣之世,特別是西漢后期,由于廢除了緡錢稅和其他律外苛征,私營工商復蘇,販運貿易又開始活躍。所謂“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民棄本逐末”[②②]。當時也涌現出一大批新的富商大賈、販運商人。這除了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及張長叔、薛子仲等外,突出的還有成都羅裒,他既坐賈京師,又往來于巴、蜀經商,“數年間致千余萬”[②③]。楊惲罷官之后,也從事販運貿易,“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②④]。“其余郡國富民,兼業專利,以貨賂自行,取重于鄉里者,不可勝數”[②⑤]。故貢禹曾經提議:“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②⑥]。可見,當時從事販運商業的情況已較為普遍,且成為勢不可擋。王莽代漢后,盡管實行“五均、六管政策,試圖再次打擊商人,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任用商人理財而失敗,私營販運貿易仍在繼續向前發展。
東漢政權是在豪商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其間政府沒有直接提出過明確的抑商政策,光武帝當政時,桓譚曾經提出過“禁民二業”的主張,然最終未能貫徹執行。因東漢對工商業采取放任、保護態度,故販運貿易以更為通暢的勢頭得到發展。當時從事販運商業的人相當廣泛。例如:吳漢早年,曾“以販馬為業,往來燕、薊間”[②⑦]。朱俊“少孤,母嘗販繒為業”[②⑧]。第五倫因“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居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販賣[②⑨]。崔實自父親死后,乃“以酤釀販鬻為業”[③⑩]。中山大商人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于涿郡”[③①]。故王符說:當時“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③②]這種商業、販運貿易的發展,形成“車船販賈,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③③]的繁榮局面。在交通條件不甚優越的北境道上,烏桓入侵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余兩”[③④],于此可見一般。這也表明,盡管東漢一度實物貨幣復興,然私營販運貿易仍是當時商業活動的最基本形態。
綜上所述,漢代販運貿易發展的趨勢,大體上可以這樣概括:從販運的商品內容看,由主要販運各地名貴珍品,發展到大量販運鹽鐵、馬匹等民間生活、生產必需品,種類逐漸增多;販運商的成份,由六國遷虜、舊貴族后裔、民間自由商人,逐漸發展到地主、官僚等各色人物,其地主化的傾向日益明顯,且官、商結合;販運貿易的形式,既有個體經營,也有合伙進行,并形成一定制度;再從時間上看,私營販運貿易除漢武帝時受到較大抑制外,于西漢前、后期及整個東漢基本上皆處于發展勢態。漢代販運貿易之所以能得到發展,究其原因殊多,但這與當時的工商政策、交通條件及地區性商品生產的發展不平衡等密切相關。
二、販運貿易的經營范圍和利潤
商業的經營范圍,各個時期不一,販運貿易亦然。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受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它通常不是販賣體積笨重、單位價值不高的生活必需品,而主要是供統治者需要的昂貴奇珍或奢侈品。
販運貿易經營奢侈品的情況,秦漢時期仍在繼續。據李斯《諫逐客書》,當時各地匯集于秦的“珍寶”多種多樣:有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太阿之劍,纖離之馬,翠風之旗,靈龜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江南金錫,西蜀丹青,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等。[③⑤]這其中的許多“珠”、“玉”奇珍等,并非皆為秦土所產,而是通過進貢,或商人販運而來供統治者享用的。在漢代,社會上的奢侈之風更盛,“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等,成為貴戚豪富之家熱心追求的對象。王符說:“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致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獐麂履舄,文組彩緤,驕奢僭主,轉相夸詫……。”[③⑥]京師貴戚之家所消費的這些奢侈品,有相當一部分為販運商人從各地轉運到京城來推銷的,此無可疑。貴族富有之家,為滿足其奢侈欲望,炫示富有,夸耀威儀,需要有高質量的精美物品來點綴和裝飾。這就決定了當時的販運商業,必然要將奢侈品列為一項重要的經營內容。
但在漢時,隨著社會生產力提高,商品經濟發展,人們與市場聯系的加強,販運貿易的經營范圍與數量較前有了進一步的擴大,商品種類較前更為豐富。
首先,各地的方物、特產在漢代販運貿易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綦置,此其較大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養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就是說,凡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等地的方物、特產,“待商而通之”,皆得依靠商人的販運或中介作用,使各地物資得到交流。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也曾寫道:“大夫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纑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這里說的“商”,似乎非指坐商,而主要當理解為商販,即販運商。所以,不論西漢前期,還是在其以后,大量的各地方物、特產往往都成為販運商經營的內容。值得注意者,此時有些方物、特產的奢侈品性質已相對削弱,它已非專供貴族官僚所需,而是普通“編戶”也可能消費了。
其二,農、林、牧、漁產品是漢代販運貿易的基本構成。《貨殖列傳》在論及商品生產的情況時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在這里,司馬遷告訴我們:當時的大畜牧主、大林場主、大園圃主、大漁場主所進行的農林牧漁業生產,給市場提供大量商品,但并不需要他們親自把這些產品送到市場,他們可以“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只要依靠販運商人的中介作用,就可“坐而待收”。于此說明,農林牧漁產品,已大量投入流通領域,是販運貿易的重要經營內容。商人販運農副產品的情況,一直到東漢未曾有變。劉秀本人就曾“避吏新野,賣谷于宛”[③⑦],樊宏“世善農稼,好貨殖”,“經理產業,物無所棄”[③⑧],吳漢“以販馬為業”等,這都是例證。又居延新獲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還詳細敘述了甲渠候官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找到寇恩替候粟君載魚5000枚去張掖郡治——觻得販賣的經過。一次販賣5000枚魚,其數量或也相當可觀。據考,甲渠到觻得相距數百里,往返要20余天。數量之多、時間之長、距離之遠,足以證明這是隆冬季節所進行的一起大規模的長途販運。[③⑨]西漢前的諺語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④⑩]。這似乎只是就某一時期或地區的通例而言。但到后來,隨著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某些笨重的生活、生產資料,如糧食、魚肉及名貴木材等,也有長途販賣了。據載:“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轉運數千里到了洛陽加工成棺材后,“東至樂浪,西到敦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④①],便又是例證。
再者,手工業產品日益成為漢代販運貿易的大宗商品。《貨殖列傳》說:當時的“通邑大都”有酤釀、醯醬、軺車、牛車、木器髹者、銅器、鐵器、帛絮、細布、文采、榻布、皮革、漆、鹽豉等等。在市場上陳列的這各色手工業商品,應該說大部分是通過商販的中間作用而進入市場的。司馬遷指出其時形形色色的工商業者中,既有高利貸者、“節駔會”即市場經紀人,擁有“僮手指千”的人販子,更有相當多的販運商人。他們和直接生產過程沒有必然聯系,但“亦比千乘之家”,一年獲利相當可觀。漢代販運貿易中最重要的手工業產品,首推鹽鐵。在未實行專營期間,大手工業主往往身兼商人,工商結合。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以其自己生產的鐵器推銷于滇、蜀地區。程鄭,“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即“通賈南越”,轉賣其本人產品。宛孔氏,“大冶鑄,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④②]。當時冶鐵、制鹽的生產規模較大,要求有廣大的銷售市場和長途販運。《鹽鐵論》云:“鐵器,民之大用也”,“農夫之死士。”[④③]王莽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即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④④]。鹽鐵為國計民生所必需,但由于受資源分布限制,不是到處都能生產,也不是消費者自己所能家作,故遠離產地之人所需的鹽鐵產品,只能通過販運貿易方可滿足,這方面有大量的出土文物資料可證。再就是布帛,此為衣著之源,人們不可不具。漢代民間的紡織品生產已有相當規模,它常被商業資本積聚起來販賣。據稱:灌嬰早年,就是睢陽的一個“販繒者”[④⑤]。當時出產于會稽的“越布”、吳地的“細葛”等,被商人販運到各地去滿足消費者需要,一時譽滿天下,又從漢簡所見,西北邊境地區的布帛種類殊多,計有:七棱布、八棱布、九棱布、練、縑、皂練、白素、皂布、布、絣、鶉縷、帛、白縑、絮巾、緹績、絲絮、絲等。[④⑥]這各種名目的布帛,有的是從中原內腹之地販賣去的,而非本地所產。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銅器、陶瓷等,也是販運商業的常見產品。于此不必一一列舉。一句話,手工業產品在漢代販運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漢代販運貿易的經營范圍與內容大致如上所述,但需要說明的是手工業品、方物與奢侈品有時很難區別。因為多數方物也要經過一定的加工處理,而古代手工業本身又往往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一些經過手工業精心加工制作的方物,也就是名貴的珍品或奢侈品。所以,將經營范圍做如上分目概述,應該說這只是一種大體上的劃分,不宜過于拘泥。在此同時,還當指出的是,漢代販運貿易中手工業品和農副業產品的增多,反映了它和商業資本與產業聯系的加強、奢侈品地位的相對削弱這一發展趨向。
據文獻、簡牘資料,漢代各種商品的價格,往往隨著時空的差異而有別,確乎難于統論,但當時從事販運貿易的人都是以追逐厚利為目的則可肯定。那么,漢代的商業利潤通常為多少?對此,不妨先看如下史實:
司馬遷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④⑦]
貢禹說:“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④⑧]
司馬遷和貢禹所處的時間有先后之別。但他們在言及商業利潤時,卻都說是十分之二。即擁有一萬的本錢一年可得利二千,有百萬資本的商人投入商業周轉,一年可獲利二十萬。可見,所謂“歲有十二之利”,這是漢代私人商業的一般利潤。可能也是私人從事販運貿易的通常利潤。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它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意思是說,不能達到百分之二十利潤的行業是誰也不愿意去經營的。這一點和戰國之時大體相近。如《史記·蘇秦列傳》說:“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故在漢人看來,十分之二的利潤是通常的標準。它確乎沿襲了戰國時期的傳統。
但商業利潤通常為什分之二,這并不排除特殊的例外。漢代,一些“富商大賈,積貯倍息”,“乘上所急,所賣必倍”,其獲利之豐厚是不言而喻的。至于長途販賣奢侈品或奇珍寶貨而牟取暴利者,也有史可證。如《鹽鐵論·力耕篇》引文學之言曰:“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璣、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漢百萬有余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輯而中萬鐘之粟也。”販運美玉、珊瑚等奇珍而百倍其價,其利潤顯然遠遠突破了“什二之利”的界線。當時“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④⑨]進,大有人在。當然,在販運貿易中也有利潤未達“十分之二”者。如“幸有馀祿”的楊惲,“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⑤⑩]。有的甚至還虧了本。如其時有個名叫李岳的人,“官至中散大夫,嘗為門客所說,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向鄴城,路逢大雨,并化為泥,息利很少,乃至貧迫。”[⑤①]孟康在注釋《漢書·貨殖傳》:“貪賈三之,廉價五之”時說:“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這說明貪賈與廉賈的盈利也是有別的。要之,漢代的商業利潤盡管存在一些特例,但就通常來說,乃為“歲有十二之利。”三、販運貿易的活動地域與商品走向
由于自然地理條件及歷史傳統的影響,漢代販運商的地區來源,開初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黃河中下游流域,包括今陜西、河北、河南及山東等省,隨后乃逐漸擴展到各地皆有。因為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故活動能量甚大。
漢代中央集權的大統一局面,為商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活動條件。司馬遷《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漢書·伍被傳》:“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鹽鐵論·力耕篇》云:“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在漢代的商業大潮下,富商大賈、販運商人,為了“得其所俗”、追逐“貨殖”,也就是通過商品經營,不斷實現商品、貨幣的增殖,他們交錯于路,“周流天下”,先后走遍全國各主要經濟區,大凡關中、三河、燕趙、齊魯、江南等地都有他們的足跡,活動的地域相當廣泛。當時的販運商人,在這些經濟區域內部,固然存在商品經營活動,但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販運貿易主要依靠不同地區之間各種物品的轉動流通和賤買貴賣而取厚利。茲按地區分述如下,以窺大概:
關中地區:范圍包括函谷關以西的陜西全部和甘肅、四川的一部分。這里沃野千里,好稼穡,殖五谷,物產豐饒。而“富人則商賈為利”。關中的長安,在地理位置上,北卻戎翟,西綰羌隴,南御巴蜀,東通中原,故“四方幅湊,并至而會”。由于它是政治、經濟中心,財力集中,巨商大賈云集,市場繁榮。所謂“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⑤②]。“瑰貨方至,鳥集麟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⑤③]。全國各地來到長安的商人,多以經營方物、特產及奢侈品為主要目的。作為關中大后方的隴右、巴蜀一帶,經濟各具特色。前者“畜牧為天下饒”;后者除多粟之外,“地饒的巵、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且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⑤④]。農業、手工業的發達引來了大批商人,他們從這里販運皮毛、牲畜、礦產、漆器、蜀布等遠銷中原各地,“以所多易新鮮”。[⑤⑤]同時,他們還與西南少數民族貿易,“南賈滇僰,西賈岷邛”,且從那里販回笮馬、牦牛、邛杖、枸醬等投放內地市場從中牟利。
三河地區:即河東、河內、河南三郡。這是富庶的農業區。《貨殖列傳》云:“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以更居也”。地處中原,綰轂東西南北,是國內交通樞紐與商業都會相對集中的地方。其中,河東以楊、平陽為都會,“西賈秦、翟,北賈種、代”;河內以溫、軹為都會,“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河南以洛陽為都會,“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重要的商業城市。三河地區的人民喜好經商,周流各地,善做買賣。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販運商人,如孔氏、師史等,他們從這里輸出的大宗貨物主要是農副產品,而從各地販來的物品則多為奇貨珍品。
燕趙地區:位處黃河以北。這里開發亦早,為北方商業的集散地。其中,邯鄲是漳、河之間一都會。“北通燕涿,南有鄭、衛”。[⑤⑤]西卻三晉,東近梁晉。殷商遺民居多,“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商賈錯于路”。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稀……有魚鹽棗粟之饒。”[⑤⑥]該地區的東南部除農業外,手工業也比較發達。商人利用地區間的商品差價,往往北賈烏桓、夫余,東賈穢貊、朝鮮、真番,成為中原與東北地區的貿易紐帶。[⑤⑦]
齊魯、梁宋地區:位處中原與東南地區的要沖。這里重農而好商賈。其中的齊、魯區,本為文物之邦,但轉而好趨商賈之利。齊著名都會“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匹于長安”[⑤⑧],商賈往來頻繁。齊魯的販運商人眾多,如曹邴氏、刁間等都是突出代表。他們所轉販的商品,大概主要是鐵器、桑麻、絲織品,又“逐漁鹽商賈之利”。梁安地區,以定陶、睢陽為中心都會,其俗也是“好農”,而又“商賈”。這里由于交通方便,商業發達,已逐漸成為絲麻織物及農產品的集散地。
江南地區:這里是長江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漢時大體屬荊、揚二州的地域面。《貨殖列傳》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不待賈而足”。從總體上說,江南的經濟開發落后于北方,商品交換相對較少。但當時的江南也形成了若干較大都邑。如吳(江蘇蘇州)是江東都會,“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河五湖之利”。凡魚、鹽、銅等商品,一般多在吳市集散。江陵(湖北江陵)是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商賈轉販往來不斷。江南所產的梓、姜、桂、金、錫、丹沙等物品,往往通過江陵北運而轉銷各地。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而取利。又“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⑤⑨]。可見江南雖然一度“無千金之家”,但其豐富的天然資源與自然物產,為各地販運商人提供了廣闊的商品采購市場。
嶺南地區:位處南嶺之南,屬越族聚居之地,是秦漢時期的新開發區。其中的番禺(廣州)是南境的一大都會。而徐聞、合浦、蒼梧也是重要的港口與貨物集散地。《漢書·地理志》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當時漢政權在民族交界的邊境上設有“關市”,民間貿易往來較多。商人從中原運去的有耕牛、鐵器之類;販回中原的商品主要有珠璣、犀角、象齒、玳瑁、銀、銅、果、布等特產。
從以上大量史實表明,漢代商品經濟已形成了一定的流通渠道和購銷結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這種商業關系、商業網絡,使商人一般能夠運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實現其商品與貨幣增值的愿望。當時販運商人的活動地域,遍及全國各個經濟區,除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的關中、三河、燕趙、齊魯等地區外,淮河、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廣大地區也是他們周流所及之處;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和鄰近國家之間也有漢商的轉販活動或貿易往來,只是比內郡更少罷了。所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之說,并非虛言。至于販運貿易的商品流向,情況比較復雜。由于東南西北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重心在北方,加之產品結構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的走向不一。或將本地的農業、手工業產品輸出,販進外地的方物、特產;或南方的天然資源與自然物產,如象齒、翡翠、玳@④珠璣、楠梓、黃金、連錫等往北走向,北方的馬牛、旃裘、筋角等南運,南北商品對流。《史記·貨殖列傳》說:“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這是鹽業產銷區劃的大體反映。海鹽、鐵器等西運,則是漢代商品由東而西流向的又一基本趨勢。
最后要提及者,從事販運貿易還有個貨物如何轉運問題。考諸史實,漢代的商運,除了靠人力擔負之外,馬牛馱運、車船轉漕也已相當普遍。所謂“賈郡國,轉轂以百數”[⑥⑩],“商賈車牛千余兩”[⑥①],這都是具體的反映。
隨著私人運輸業的發展,漢代富商大賈的大量商品貨物,往往雇用民力轉輸。其主要形式有二:(一)雇用“將車人”駕車。如《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補述: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恩從觻得自食為業將車到居延”。在漢簡中有關“將車”、“將車人”的記錄多見[⑥②]。這里的“將車”即泛指駕車。“為人將車”、“將車人”當是受人之雇而趕車的車夫。當時販運商人為了運貨,擁有許多車輛,因此需要“將車人”代勞。(二)雇用“僦人”運輸。如《淮南子·汜論》:“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鹽鐵論·禁耕篇》:“良家以道發僦運鹽鐵,煩費。”何謂“僦”?服虔曰:“雇載云僦”[⑥③]。以“僦載”為生者,乃稱“僦人”。這方面漢簡也為常見[⑥④]。“將車人”與“僦人”,在車輛所有權問題上雖有一定區別,但他們對商販即雇主來說,都存在著雇傭關系。
至于“雇值”與“僦費”,當隨著時間、地點及運輸條件之不同而有別。“將車人”的雇值,因史文簡缺,有待深考。《九章算術·均衡》云:“一車載二十五斛,與僦一里一錢”,這可能是“僦費”運價的通常標準。注釋:
[①]《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67—368頁。
[②]分見:《云夢睡虎地秦簡·日書》、《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敘傳》、《漢書·匈奴傳》、《漢書·貢禹傳》、《后漢書·仲長統傳》。
[③]《呂氏春秋》。
[④][①①][①③][①⑤][①⑥][①⑦][①⑨][④⑩][④②][④⑦][⑤④][⑤⑤][⑥⑩]《史記·貨殖列傳》。
[⑤]《史記·呂不韋傳》。
[⑥]《荀子·王制》。
[⑦]《管子·小匡》。
[⑧]《管子·禁藏》。
[⑨]《墨子·貴義》。
[⑩][②③][④④]《漢書·食貨志》。
[①②][⑤⑥][⑤⑨]《漢書·地理志》。
[①④]《鹽鐵論·力耕》。
[①⑧]李均明等:《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⑩]《史記·平準書》。
[②①]《居延漢簡》:20·8(甲177)。
[②②][②⑤][④⑧]《漢書·貢禹傳》。
[②④]《漢書·楊惲傳》。
[②⑥]《漢書·貨殖傳》。
[②⑦]《后漢書·吳漢傳》。
[②⑧]《后漢書·朱俊傳》。
[②⑨]《后漢書·第五倫傳》。
[③⑩]《后漢書·崔實傳》。
[③①]《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③②][③⑥][④①]《潛夫論·浮侈》。
[③③]《后漢書·仲長統傳》。
[③④][⑥①]《后漢書·烏桓傳》。
[③⑤]《史記·李斯列傳》。
[③⑦]《后漢書·光武帝紀》。
[③⑧]《后漢書·樊宏傳》。
[③⑨]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116頁。
[④③]《鹽鐵論》水旱、禁耕等篇。
[④⑤]《漢書·灌嬰傳》。
[④⑥]《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社1989年版第57頁。
[④⑨]《前漢記》。
[⑤⑩]《漢書·楊敞傳》。
[⑤①]《太平御覽》卷838引《三國典略》。
[⑤②]班固:《西京賦》。
[⑤③]張衡:《西京賦》。
[⑤⑦]參見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湖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頁。
[⑤⑧]《漢書·高五王傳》。
[⑥②]《居延漢簡》:77·3,334·13,334·36,346·39。
[⑥③]《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隱》。
[⑥④]《居延漢簡》:214·125,267·16·502·11,586·5。
- 上一篇:北宋高麗貿易發展論文
- 下一篇:縣域經濟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