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出版科技期刊版式定位
時間:2022-07-19 02:33:59
導語:數字出版科技期刊版式定位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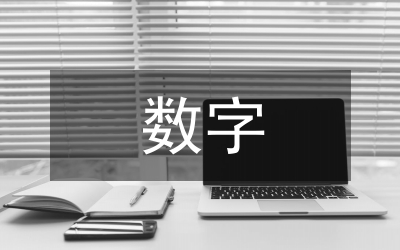
數字出版時代,紙媒體出版物已日漸式微,期刊若想保持長盛不衰,必須直面嚴厲刻酷的生存環境。然而,在信息內爆、紛繁蕪雜、心緒浮躁的數字化讀圖年代,期刊受各種利益的誘惑與干擾,辦刊設計定位易隨俗浮沉,偏離航向。辦刊理念的暫時改變可能為期刊帶來不菲的經濟收益,但長遠來看,這對期刊的品牌定位和學術聲譽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科技期刊能否堅守辦刊設計定位,與期刊興衰直接相關。期刊出版史表明,為了生存與發展,幾乎所有種類的期刊都要求設計定位與出版內容相吻合,以確立期刊的辦刊特色。如消遣、娛樂類刊物多以幽默、活潑的愉悅性見長;詩歌、散文類刊物素以儒雅、抒情的“書卷氣”著稱;而哲學、科技類期刊則以理性、邏輯的秩序感聞名于世。因此,任何一種期刊都應有自己獨特的內涵與相應的面孔[1],無論期刊外封圖文編排,還是內頁文本版式,莫不如是。毋庸置疑,合理、準確的辦刊設計定位,不僅符合期刊內在學術取向,而且也切合讀者對期刊的審美體驗與品位追求。就科技期刊選擇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定位的緣由而言:(1)科技期刊作為媒體的一部分,應同時具備文化屬性和商品屬性,應同時追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2)科技期刊承擔著“傳播科技信息,交流學術思想,傳承科學文明”[2]等學術使命;(3)以數理研究成果為傳播內容的科技期刊強調理性與科學,而理性與科學本身就與數列、秩序等概念密不可分,即秩序的形成源自“數”的比例關系,美感產生于“數”。畢達哥拉斯認為:“沒有一門藝術的產生不與比例有關,而比例正存在于數之中,所有一切藝術都產生于數”[3]。為此,科技期刊只有秉持理性主義的辦刊理念,堅持符合刊物的自身性質、發展取向的理性、秩序的版式設計定位,才能夠順應時代生存的適時選擇。理性主義版式設計方法傳入中國,首先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高校設計教育領域。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代表的書籍設計專業率先開設網格設計課程[4]。之后10年,其他少數有條件的高校也開始設置此類課程。從此,理性主義版式設計方法漸漸傳播至中國出版界,與之相關的普及性教材和學術論文也相繼發表與出版,但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理性主義版式設計總體上還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國內期刊設計界普遍對理性主義版式設計方法的使用并不嚴格。就目前科技期刊的設計現狀而言,大部分期刊采用電腦排版軟件,套用固定文本編排格式,自動生成圖文版式。曾有專家指出:“我國科技期刊尤其學術類期刊不講究版式美學設計,其版式單調呆板,審美效果差”[5]。(2)國內出版界普遍采用模版化、拼貼化手段進行期刊版式編排,使版面構成形式蛻變成理性主義設計的“擬仿”物,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設計,最終導致科技期刊的版式缺少設計含量,缺乏嚴謹、規范的秩序感與科學性。(3)某些缺乏設計成分的版式構成方法,雖然可清晰地表達文本內容,但此類方法僅能滿足期刊最基本的功能需求,與國際高水平期刊普遍采用的理性主義設計所遵循的辦刊設計指標相去甚遠。按理說,期刊內容采用條、塊分割方式安排版面本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許多情況下這種固定套用或采用不規范編排手段且無設計含量的排版容易使人產生概念上的誤解。將貌似理性主義設計的程式化、隨興自由化的文本編排誤以為是理性主義設計,這委實是對高水平科技期刊的極大諷刺。相反,只有那些精心構思,嚴格依照國際網格設計工藝標準[6],依序分割平面版式的設計才可謂之理性主義設計,而只要看著舒服,可隨心編排圖文位置的做法,與理性主義設計內涵毫無關系。如此現象可歸咎為兩點:(1)設計師缺乏嚴謹的設計職業素養;(2)排版公司為降低成本,偷工減料而故意為之。這就使該類科技期刊的設計水平、審美形式與同類國際著名期刊存在巨大差距。依照國際設計標準,國內大多數科技期刊設計師的敬業精神、專業素養、圖文版式創意、編排結構、級數比例等均與歐美同類期刊普遍使用的理性主義網格設計方法存在很大差距[6]。其中,不規范和粗制濫造是版式設計的最大弊端。某些期刊的版式表面效果與理性主義設計形式相似,實質卻是貌合神離的機械復制。此類期刊有悖于理性主義設計一貫秉持的嚴確、規范的工學標準。這一狀況貌似無關宏旨,卻能夠切實影響期刊的設計品質。若想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站穩腳跟,甚至成為出版界的翹楚,科技期刊不僅要堅持理性、秩序的設計定位,并使其真正得到落實,還必須汲取某些具有積極作用的非理性主義設計方法作為版式設計藝術的審美補充。本文就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分析。
1理性、秩序:科技期刊對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定位的恰當選擇
理性、秩序的設計定位不僅是理性主義內在思想本質的客觀反映,也是科技期刊設計定位的重要核心,同時也是以傳播科技思想為辦刊宗旨的科技期刊的恰當選擇。科技期刊是以傳播科學知識、破除封建迷信為宗旨的嚴肅刊物,其學術倫理要求期刊必須遵循理性主義思想內在的科學規律,通過理性、秩序的設計手法呈現出富有節奏感的視覺審美形式。在此,理性是指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數列計算為手段,將開本、比例、圖式、文本按一定比例合理、有序地規劃于版面中,以表達版式秩序的級數美。秩序則以確切的基本元素參數為版式構成物,借助相應的數學計算,使版權、目次、文本、圖片、表格、符號等構成要素依序、合理地配置在頁面中,以此形成版式組合成分之間的和諧級差比[7]。理性與秩序互為關聯,相得益彰,從而形成理性主義設計特有的審美邏輯,其內涵與理性主義思想所倡導的科學觀如出一轍。1.1傳統理性主義思想與科技期刊設計觀念的高度一致性。自文藝復興后,歐洲社會對科技的崇拜與迷戀已近狂熱,理性主義思想與科學創造逐漸演變成為新的精神崇拜。對于狂熱者來說:“即使科學也基于一種信仰,根本沒有所謂‘無前提的科學’,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8]。在理性主義思想燈塔的指引下,科技發明與科學創造層出不窮。與此同時,為工業生產與商品貿易服務的設計業也進入空前繁榮時期。批量化、模塊化、規模化生產是工業社會的典型特征,其設計思維與理性主義思想意識完全一致,反映出西方理性主義精神的歷史同一性。與之并立共生,服務于工業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書籍、期刊、報紙、產品包裝等平面設計實務,其設計理念與工業化生產思維模式一脈相通,形成統一完善的有機整體。由此可見,科技期刊選擇理性主義設計定位,其實質是理性主義思想對期刊功能、審美取向的影響和滲透的現實反映。1.2秉持理性主義思想是現代科技期刊設計的基本特征。風格主義運動是把理性主義思想具體應用于設計實踐,并對期刊設計起直接指導作用的典型范例。早在現代主義誕生之初,荷蘭哲學家遜馬克的理性主義哲學思想曾對《風格》(DeStijl)的設計產生過決定性影響。遜馬克認為物質世界由縱、橫兩種結構組成,他認為世界上的三種顏色是紅色、黃色和藍色。蒙德里安受其影響,轉向完全縱橫直線結構的完全抽象繪畫,色彩也逐步轉向單純的黑色線條結構、白色底以及紅色、黃色和藍色的三原色計劃,走向高度理性化方向[9]。《風格》以此為基礎,選擇基于數學計算的版式設計方法,首先采用縱橫線條為中心線,把平面空間劃分為簡單的幾個功能區域;其次以簡單方格組成方格網底,把每個方格作為基本模數單位;最后采用數學比例和幾何比例進行版面編排,設計上強調排列和順序,把平衡、對稱、比例、對比互補關系等視覺內容以高度理性的方法融為一體,達到完美的地步。這種方法大約可發展出一種大部分建立在數學思維基礎上的藝術[9]。雖然《風格》創辦于20世紀初葉,但其影響力早已超出所屬時代的傳播范疇,并為之后屬于理性主義設計范疇的國際化風格的誕生奠定了系統的理論基礎。可見,堅持理性主義思想是現代科技期刊設計的根本追求。1.3國際主義版式設計風格。現代設計史上,20世紀前30年間產生的網格設計的迅速發展,使國際主義設計風格與理性主義設計內涵一脈相承[10]。國際主義風格力圖通過簡單的風格結構和近乎標準化的版面公式達到設計上的統一性。具體來講,這種風格往往采用方形網格為設計基礎,各種平面因素的排版方式基本采用非對稱式,字體、插圖、照片、標志等都規范地安排在此框架內,排版往往呈現簡單的縱橫結構,字體也采用簡單明確的無飾線體,由此設計的版面往往具有公式化、標準化和規范化的效果,具有簡明而準確的視覺特點[11]。系統、秩序的科技期刊版式設計的關鍵在于如何利用理性的模數原理使復雜的版面組織要素得到合理配置,采取國際主義表現形式則是體現這一思路的準確選擇。換言之,把國際主義設計方法實際運用于現實科技期刊的版式設計是理性主義設計思想的現實反映。愛因斯坦曾指出:“正是由于這么一個比例尺度,它使人做好容易而做壞難”[12]。可見,理性與秩序既是理性主義設計的核心,也是科技期刊辦刊設計定位的支撐點。科技期刊立足于理性主義設計定位,不僅是理性主義思想科學性的正確反映,也是對科技期刊內容的準確體現,是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正如阿恩海姆所說:“人所具備的認識能力(其中也包括藝術創造能力)尋求的是秩序。科學的使命是在多樣化現象中提煉出有規則的秩序,而藝術的使命則是運用形象去顯示這種多樣化的現象中所存在的秩序”[13]。
2偶發、隨機:科技期刊對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的選擇性吸收
設計猶如一面時代的鏡子,在鏡像的世界里,時刻會映現出科技的真實身影。因此,不同的歷史階段,設計必然反映時代的科技華彩。處在高速發展的數字出版年代,科技期刊選擇理性主義設計定位,是順應科技潮流的正確選擇,體現出刊物的外在形式與內在精神的珠聯璧合。然而,盡管理性主義設計擁有無與倫比的科學性、功能性,但也并非完美無缺。若要保持科技期刊經久不衰,設計本身必須與時俱進,以真誠開明的態度接受、設計新生事物,突出鮮明的前衛性與時代感,應對流行于設計界的偶發、隨機、混亂等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采取開放姿態,選擇性地汲取其中的積極要素。紙媒體科技期刊若想采用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唯有以數字科技作為技術保障才能夠實現。而在此之前的傳統科技時期,即便有此想法,但囿于科技發展水平,版式編排存在難以跨越的排版技術障礙,最終難以實施非理性主義的設計手法。在此,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如果沒有進入數字出版時代,或設計師還未掌握計算機輔助設計的技術,將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成功應用于紙媒體出版物中只會成為空談。可見,只有將數字科技與紙媒體結合,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才能順利應用于具體實踐。2.1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對非理性主義設計形式。選擇性吸收的理論探索當代,許多學者采用理性主義版式設計手法對非理性主義設計形式選擇性吸收的理論進行探索。余秉楠[10]認為期刊版式所采用的網格設計重視比例感、秩序感、連續感、清晰感、時代感和正確性,以理性為基礎,與以感性為基礎的美國自由版面設計的自由配置形成鮮明對比。但海倫反對網格編排法,主張自由設計編排,認為網格體系死板拘束,但他也承認編排內容必須以一定的秩序為準則[14]。盡管其觀點十分矛盾,不過也確切地表明,以理性主義觀念為主體的版式設計,離不開非理性主義自由版式設計的介入和修正。書籍設計師呂敬人[15]曾引用杉浦康平“藝術×工學=設計2”的設計觀念,同樣認為藝術思維活動離不開感性創造過程,藝術感覺是靈感萌發的溫床,是創作活動必不可少的一步。顯而易見,“感性創造”和“藝術感覺”等概念指的就是非理性主義藝術設計。英國著名藝術理論家貢布里希所撰寫的《秩序感》長期以來頗受學界推崇。他曾對圖形編排結構中存在的“秩序”與“混亂”現象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指出“不管我們如何分析規則結構與不規則結構之間的差異,最終我們必須能夠說明審美經驗方面的一個最基本事實,即審美快感來自于對某種介于乏味和雜亂之間圖案的觀賞”[16]。在此,圖案特指視覺要素形態;乏味則是指如果設計要素排列過于秩序、規則,將會出現僵化、呆板之感;雜亂則表示編排結構的混亂與不規則。視覺要素編排只有介于二者之間,處于中和狀態才具有審美價值。當然,雙方的比例并非等量等形,中和也不等于平均,唯有秩序處于絕對主導狀態,形成理性主義設計對非理性設計要素的吸納、兼并之勢,排列結構及其審美性才得以成立。一言以蔽之,貢布里希等學者的理論是一個二律背反命題,現實中的設計實務一旦遇到此類現象,采用“中和”方法是解決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對于科技期刊的設計定位來說尤其如此。具體原因和解決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2.1.1突破網格的必要性。盡管理性主義從人的主體出發,運用邏輯推理去揭示事物的內在規律,反映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當人依照客觀規律對具體事物進行支配,并視其為全部生命意義時,客觀上人便失去自我,成為從屬于“物”的奴仆。科技期刊選擇屬于理性主義范疇的數列網格設計,最棘手的問題就在于容易造成設計者把網格變為僵滯的固定圍欄,生搬硬套地將圖文嵌入其中,即網格給人以規矩和約束,這是其優點,同時也正是其缺點。如果不能靈活與創造性地應用網格,則易使版面顯得單調和枯燥。有時為了打破版面過于單調的格局,可采用局部突破網格規矩的方法[10]。為了消除這一弊端,有必要針對版面某些局部,采用偶發、隨機、混亂等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隨機機制,以去除呆板、僵化的機械性。圖1所示為《新克蘭布魯克設計論述》[17]的版式設計,內文編排以網格結構為主體,局部則采用自由版式設計手法,對略顯呆板的文本成功實施了破網處理,凸顯理性、秩序、自由、輕松之感。2.1.2減少消極的冷漠感。理性主義設計作為超越國界、民族、地域特點的國際主義設計方法,采用模塊化、網格化等標準設計模式,其審美評價體系以規范、秩序等相關參數為衡量的基本尺度,必然在某種程度上給人以冷漠感。一方面,理性主義版式設計能夠體現出自身的優點;另一方面,則又表現為淡漠、缺少激情。難怪其常被圖1《新克蘭布魯克設計論述》內文版式設計人指責為“具有刻板、缺乏人情味的視覺特點,流于程序化”[18]。為了彌補理性主義版式設計的缺陷,科技期刊在把理性主義設計作為主體定位的同時,適當引入非理性主義版式藝術隨機機制,將偶發、混沌等藝術表現方法融入到刊物設計中,以消減冷漠,增加期刊設計的情感審美意蘊,這非但不會影響理性主義的辦刊設計思路,反而以開放的辦刊意識增強了期刊的生命力。一旦采納這一設計理念,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將喚醒潛藏在理性思維下真正支配人的意愿和行為的無意識領域[19],而這正是設計藝術所需要的。2.1.3消除設計的同質化。藝術與科學的本質區別在于,藝術講究個體之間的差異與變化,強調不同的個性,把獨創奉為圭臬,而科學則看重邏輯、共性與普遍化。這本來無可厚非,但若不加篩選地把共性與普遍化等科學規律套用于所有藝術設計對象,設計便會出現千物一面的同質感。理性主義設計,尤其是網格設計,將數理觀念引入設計中,竭力主張理性、秩序、趨同與普遍等設計觀念。科技期刊一旦選擇理性主義設計作為設計定位,必然出現設計同質化現象。這就是理性主義設計本身不可避免的悖論,其內在規定性要求自身必須以整齊劃一的紀律性對事物進行約束,排斥以宣揚自我感知、直覺等為主張的非理性因素介入,這必然會引起其與非理性主義設計之間的沖突。與此相反,雖然非理性主義設計在思想上與理性主義背道而馳,如把“否定理性思維能力,宣揚意志、直覺、盲目力量”等作為對理性主義的批判,但并不意味著對理性主義的全然否定與拋棄。非理性主義所要反對的只是理性主義思想及其設計中存在的模式化、同質化弊端而已,這就為消除理性主義設計中存在的同質化現象,有選擇性地引入偶發、隨機機制尋到正確的路徑。2.1.4選擇吸收的甄別性。科技期刊應加以甄別地引進偶發、隨機等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要素,有選擇性地吸收具有積極因素的設計形式。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流派紛繁、魚龍混雜,且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因此,并非所有非理性主義設計形式都適用于消解理性主義設計的不足。只有那些不影響文本信息傳達功能的積極形式才具有可吸收的實用價值,同時還必須保證工藝制作上的可行性。現有數字化出版科技不僅解決了快速、高效的印前制版技術難題,還為各種非理性主義設計形式的誕生提供試驗場,使得科技期刊對紛紜、駁雜的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的選擇性吸收成為可能。簡言之,科技期刊為消釋理性主義版式設計的不足,必須以開放的策略輸入新理念、新形式,以兼收并蓄的態度選擇性吸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非理性主義設計要素,把先鋒觀念藝術中常用的偶發、隨機、混沌等表現形式用于具體的設計實踐。如此定位必然促使科技期刊妙趣橫生、引人入勝,富含獨有的美學意蘊。2.2選擇性吸收的成功范例。科技期刊以理性主義設計為主體對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的選擇性吸收,其成功范例不勝枚舉。例如,Nature創刊于1869年,一向以嚴謹、規范、理性、秩序著稱,是理性主義設計的代表,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便是頂級科學刊物,其設計也并非墨守成規、一成不變,而是不斷選擇性吸收非理性主義設計養分,以彌補理性主義設計的不足。圖2所示的Nature封面設計以網格框架為基礎,文字模塊沿中軸線左右對稱;局部設計則運用平衡手法,將模糊、重疊等非理性主義藝術表現手法融入到設計中,用以對“Gendergap”等局部圖形化字體進行藝術處理,以增加“性別差異”模糊化的藝術感染力,從而使形式與內容兩相烘托,相輔相成。該封面設計很好地體現了對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形式的選擇性吸取。圖3是由美國設計師戴維•卡森設計的《海灘文化》內文版式。雖然此期刊屬于人文社會科學出版物,但其成功的設計手法值得借鑒:版式采用大、小網格編排,雙欄錯位結構,顯得理性、秩序;形式上,運用錯位、疊合、重組等創作手法,使版面生成新的機遇模式[20]。再如,始創于1899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是以理性主義作為版式設計定位的科技期刊,從版式結構來看,成套印刷文字由看不見的復合隱形網格控制,字體相互穿插、錯落有致。其內頁版式嚴格按照預先設定的網格程序編排圖文;而期刊封面則經常采用富于藝術想象力的隨機、混沌表現方法來傳達期刊的學術核心理念,以此增強期刊超然的學術張力。該內文版式呈現出理性、秩序與自由、灑脫并存的視覺感受。其表現手法為平涂漫畫人物與手繪英文相協調,圖文互為借力,達到字圖一體的和諧境界。科技期刊把理性主義作為存在與發展的辦刊設計定位,盡管存在著機械、呆板等方面的不足,但只要本著開放的設計思路,不斷吸收偶發、隨機之類的非理性主義版式設計表現形式,某些不足可全然得以消弭。
- 上一篇:土地儲備資金會計核算探討
- 下一篇:中職學校體育教學素質培養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