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展覽會管理論文
時間:2022-07-13 04:20:00
導語:藝術展覽會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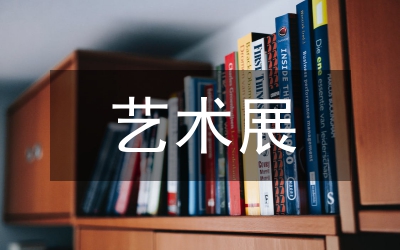
討論當代藝術,就無法回避林林總總,數不勝數的各種藝術展覽,然而言說展覽,我們就會發現從展覽的外部文化環境到展覽本身都遭遇到許多問題,在我看來,當代藝術已進入一個藝術展覽泛濫的時代。那么,今天美術界的展覽是一個什么樣的景觀呢?用形式多樣,種類繁多,蔚為壯觀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有雙年展、有三年展;有個展、有群展;有官方與非官方的展覽,有畫廊、美術館、基金會的展覽;有雕塑展、有油畫展;有行為藝術展、有裝置藝術展;有男藝術家展,有女性藝術展……。同時,除了有各種各樣的展覽外,而且它們都有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名稱,或者便是在展覽名稱前再加一個令人炫目的定語。“新”和“當代”是兩個泛濫成災的詞匯。例如:“新一代”、“新一派”“新銳”、“新界面”……;再如“某某藝術家當代藝術展”、“某某城市當代藝術展”、“當代油畫展”、“當代水墨展”……。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去追問過“新”的背后到底意味著什么?新觀念、新風格、新思潮還是最簡單的以商業利益為目標的“販賣新人”或“販賣新作品”。同樣,我也質疑“當代”一詞為什么會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要知道,20世紀初,馬蒂斯、德蘭等藝術家在舉行“野獸派”畫展,畢加索、勃拉克等藝術家在舉行“立體主義”畫展時,他們為什么就不加“當代”一詞,然后將展覽稱為“當代野獸派”和“當代立體主義”該有多好!我并不知道在那些喜歡藝術的人群里有多少人得了“展覽綜合癥”,也不知道在那些慕名前來看展覽的人中有多少人掃興而歸。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良莠不齊的各種各樣的展覽已到了泛濫成災的時候了,而一個更為嚴重的后果將是,展覽在傷害展覽,藝術在踐踏藝術自身。
實際上,從藝術作品(不同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展覽——藝術的接受者(觀眾、收藏家)這個系統的藝術生態鏈上看,藝術展覽是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同時,我們也知道,只有通過眾多的展覽才能為當代藝術的多元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展示平臺。但是,事與愿違,今天泛濫成災的展覽不僅沒有建起良好的平臺,而且對當代藝術生態的良性循環還起到了破壞作用。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種局面?
顯然,展覽模式的多樣化是導致展覽泛濫的根源所在。如果在八十年代,觀眾可以觀看的展覽大致有兩類,一種是官方舉行的各級美展或某種專題展,如全國美展、油畫展、體育美展等。另一種是地方民間美術團體自發舉行的或者由美術批評家組織的各種展覽,如北京的“星星畫展”、重慶的“野草畫展”和北京“八九現代藝術大展”等。但是,對于九十年代的展覽而言,粉墨登場的各種展覽不僅有著多元化的展覽模式,而且匯集了各方面的展覽力量。具體說來,九十年代的展覽其重心也從官方轉移到民間或者是轉移進藝術市場,它們包括各種畫廊、美術館、基金會,以及各種大型企業或機構所投資贊助的等多種展覽形式。要知道,在八十年代,畫廊、美術館、基金會根本就是鮮為人知的新事物,但是,一旦它們形成藝術的生態鏈,藝術與市場、藝術與名利的結合迅速便集結著驚人的力量。而展覽贊助模式的多樣化無疑也成為九十年代藝術展覽火爆的直接原因。
既然有多樣化的展覽,那么也就有不同的展覽目的。對于官方舉行的各種展覽而言,藝術為政治服務、為人民服務要遠遠高于藝術展覽本身的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例如全國美展的目的便是弘揚主旋律,讓藝術更好的成為繼政治意識形態之后的另一種意識形態;而官方舉辦的像“北京雙年展”這樣的高規格展覽,主要也是借藝術來代表文化的先進性,也是通過藝術來謀求與西方簡單對話的手段之一。顯然,官方的各種展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這個局限則來源于藝術與政治之間潛在的對抗關系。我們應看到,不僅是在西方還是在美國,政治、藝術、道德都處在獨立的三個系統之中。而現代藝術的價值在于,藝術能對既定的政治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提出問題,藝術家便通過捍衛藝術本體與自身的獨立性來保持藝術批判時的精神性。顯然,不管是西方的現代藝術還是中國在八五時期發展起來的“新潮美術”,它們一個共同的特征便是對政治和道德系統保持著一種疏離和批判的態度。所以,就現代藝術的本質來說,藝術與政治、道德的對抗注定了中國的當代藝術無法擺脫這種具有悲劇色彩的命運。盡管,一部分人可能反問,今天官方的美術館不也接納了中國當代藝術嗎?威尼斯雙年展不也有了我們自己的國家館了嗎?但我們應知道,官方對當代藝術的接納仍是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展開的,真正具有先鋒性和批判精神的作品仍然被排除在外。換句話說,在開放和寬容的姿態背后,官方實際上有著一種對當代藝術家進行收編的意味。這是一個悖論。因為,藝術對政治與道德系統的批判注定了與代表官方意識形態的美術館和各種展覽機構潛在的對抗與沖突。然而,藝術家又不得不與官方妥協才能爭取到一張進入官方展覽的入場券。
如果說官方的展覽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那么由畫廊、各種私營美術館,以及各種大型企業或機構所投資贊助的展覽更存在著諸多的問題。從畫廊和美術館的經營性質上看,收藏和出售作品是其最重要的手段和目的。在從收藏到出售之間有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對作品進行展覽。那么,就這些展覽而言,其質量又會怎樣呢?首先從收藏談起。對于畫廊來說,選擇和簽約哪些藝術家便是最棘手的問題,同時,畫廊簽約或的藝術家的名氣大小客觀上也決定了畫廊在藝術市場上的學術定位和經營策略。目前,我們可以大致地將這個潛在的收藏群體劃分為四類:
1、在八十年代中國現代主義藝術運動中,確定了自己藝術地位的藝術家。因為這些藝術家創作的作品具有藝術史上的價值,所以深得國內眾多美術館和大型畫廊的追捧。
2、以中國文化身份挪用中國文化符號的藝術家。因為這些藝術家的作品有著潛在的社會意識形態印跡,在滿足海外買家的審美與投資的欲望的同時,還能滿足他們在后殖民意義上所產生的文化優越感。所以,這類藝術家特別走紅海外,同樣也深受國內畫廊的青睞。
3、身處專業美術學院或者是體制內,擁有既是掌權者又是專家還是藝術家的多重身份的人。因為他們的社會身份、藝術圈子和手中的權力,以及還有他們的作品,可謂一舉四得,所以倍受各種中檔次畫廊的喜愛。
4、一些有著強烈個人圖式和個人風格的年輕藝術家。因為他們的作品收購的成本低、升值的空間大、方便炒作,所以倍受各種畫廊的寵愛。
盡管中國的畫廊可以選擇各種類型的藝術家,但是這里也存在一個問題,藝術家的作品總是一個相對有限的資源,同時,如果一旦某個藝術家被畫廊后,這就意味著其它畫廊便失去了一個機會。而且,優秀的藝術家畢竟是少數,所以對于中國的畫廊來說,如何通過簽約藝術家來提高自己畫廊的學術品味和搶得藝術市場上的先機便成為了關鍵。其次,有了藝術家只意味著畫廊成功了一半,而另一半則在于通過展覽,以及對展覽進行全方位的包裝和炒作來實現。于是,我們發現,對于大多數畫廊的展覽來說,它們已失去了展覽本應有的學術性,相反,展覽變成了展示,展覽成為了藝術拼盤,展覽成為了一次藝術品的集體出售,展覽成為了一個小圈子的聚會………。同樣,在學術價值和市場利益,藝術精神和大眾審美趣味之間同樣存在著一個悖論。一方面,如果畫廊要追求藝術品的精英性,那么畫廊的接受者或賣畫的人必須也是社會的精英階層才行,他們必須要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同時還得要有很強的購買能力。另一方面,畫廊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要捍衛當代藝術作品的精神或藝術價值,而是為了盈利,所以,畫廊必須得考慮接受者的購買力以及富裕中產階級的藝術審美趣味。顯然,畫廊的展覽是無法調和學術價值和市場利益,藝術精神和大眾審美趣味之間的矛盾的。相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種方式是,藝術家為了得到更多的金錢,畫廊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批評家為了爭取更為豐厚的回報,所以,藝術家、批評家、畫廊在藝術市場上自覺地進入一種“合謀”狀態。同時,畫廊又必須在保持自己的學術品味和滿足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之間進行痛苦的抉擇,最終的后果是在金錢面前的相互妥協。
顯然,不管是官方的還是畫廊所舉行的各種展覽,由于其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所以大部分展覽最終都成為了一次藝術的拼盤,一次隆重、盛大的藝術展銷會。即使是近幾年流行起來的各種雙年展,無非也是試圖將官方的力量與藝術市場進行有機的結合,但這種新的展覽模式同樣無法解決學術價值與市場利益,展覽獨立與公眾趣味的矛盾問題。表面看,當前美術界的確是一片歌舞生平、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表面的狂歡和繁華并不能掩蓋當代美術所存在的危機。所以,我們仍然要警醒,如此泛濫的展覽到底會給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帶來什么潛在的后果?例如就當代藝術的審美趣味來說,和八十年代相比,啟蒙理性精神的消退與個性表現的增強,地域文化意識的淡薄與流行文化因素的增多,群體意識的淡化與個人生存經驗的突出,油畫語言研究的減弱與個人圖式的強化……,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出現的新變化。但是,在這眾多的變化中,有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媚俗”趣味正彌散在中國美術界。那就是,空間的表層化、色彩的艷俗化、造型的圖式化、符號的中國化、審美趣味的庸俗化成為大部分藝術家追求的目標。這里邊有著兩個潛在的原因,一是中國當代美術在經歷八五的啟蒙理性運動后,一次自動的向藝術市場靠攏。在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現代藝術品走向市場并不是由單純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海外市場的成熟所引起的,其中包括80年代的現代主義的啟蒙運動在官方的拒絕和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的抵制下,在一種受挫和無奈的情況下被迫調整先前的精英主義路線,然后尋求與市場的妥協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反映在大眾文化對當代藝術的影響中。像我們熟悉的電視、電影、網絡、時尚雜志、各種流行節目、廣告……,它們在滿足人民的消費欲望時,也在改變著我們的審美趣味。在一個文化變成消費的時代里,文化所帶來的一次性、即時性、瞬間性的消費快感已經取代了過去文化在精神上的持久性和永恒性。藝術也不例外。然而,正是這兩種必然的歷史境遇共同營造了一個藝術“媚俗”的時代。因為藝術必須走向市場,而市場是由無形的大眾構成的,而大眾的趣味是表層化和享樂主義的,所以,當代藝術便自然傾向了“媚俗”。同時,由于展覽是作品和觀眾之間的橋梁,由于展覽最終受市場的利益所驅動,而且,如果就中國只有一千個畫廊來計算,如果一個畫廊一年只舉行一次展覽,可想而知,展覽必然泛濫成災。
我們應認識到,如果藝術展覽失去了自身的學術性和喪失了文化的批判力,中國的當代藝術最終不會有太好的前景。但是如何改變這種局面呢?就展覽而言,有兩種途徑是行之有效的。第一種:建立獨立的藝術基金會,然后由策展人和批評家來選擇展覽主題,然后將展覽的理念和思路由基金會組織專家討論,然后再根據可行性舉行展覽。另一種是:由當前的藝術雜志主辦,由部分優秀的批評家參與組織,然后舉行展覽。前者的優勢是,展覽既獨立于官方,也獨立于畫廊,這樣展覽能保持自身的學術性。同時,在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資金來對優秀作品進行收藏,這樣可以為那些致力于藝術實驗的藝術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后者的優勢是:藝術雜志掌握著媒體這個權力,同時,通過媒體自身的宣傳又能對當代藝術的創作方向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當然,這個目標只有在媒體保證展覽的學術性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就國內當前的情況而言,我們應以第二種方式為主,然后大力發展第一種方式。
正如前文中所說,展覽并不是簡單的展示,展覽并不是藝術拼盤,展覽并不是一次藝術品的集體出售,展覽并不是藝術家、畫廊、批評家的合謀……。相反,理想中的狀態是:展覽是對一種藝術現象的呈現,是對一種藝術精神的追問,是對一種未來藝術方向的探索。或許,我們只有真正懷著一種嚴肅、負責的心態去策劃當代藝術的各種展覽,我們才能真正改變今天展覽泛濫的局面;或許,只有出現真正獨立于官方和藝術市場的展覽時,展覽才能重塑自身本應該具有的學術與藝術的價值。
- 上一篇:縣財政局先進事跡材料
- 下一篇:項目經理申報事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