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產品設計管理論文
時間:2022-07-13 09:38:00
導語:時尚產品設計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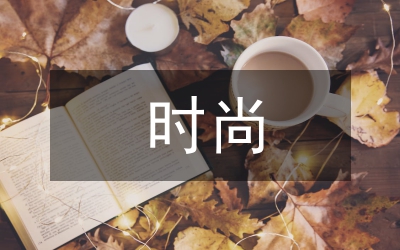
因為著名的瑞典家具販賣商“宜家”搬到了中央美院隔壁,幾乎每個周末我都會循窗外望見那趨之若鶩涌入“宜家”的車流與人流。許多人把消費這里的商品看作時尚,而商家不斷推出的對于新產品的推廣以及對于老產品的打折銷售等等營銷手段更是不斷地制造著消費者的欲望。事實上早在這個著名的品牌搬到望京之前,我這一代設計專業的學生就早已成為了“老宜家”的消費者,但同時也有些沮喪地發現,從“宜家”購買的商品,大多屬于“中看不中用”之列——待你買回家組裝完成之后,就會發現“宜家”的桌椅幾乎都有一種“搖搖欲墜”的感覺。就其使用價值而言,不用說無法與“功能與形式近乎完美統一”的中國明式家具相提并論,甚至不如很多中國同期商品的質量。然而即便如此,風格、形式等等“設計”的力量卻仍在不停地刺激著一代又一代的消費者消費這并不符合功能主義設計理論的商品。
其實,中國的產品設計實際上也經歷著與此類似的情況。1990年代以來,常聽到有人感慨“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大不如前”。有些人抱怨現在的暖水壺形狀、色彩千奇百怪,但很可能不久之后就會發現開始漏水:“還不如八十年代的鐵皮暖壺呢!”的確,七、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綠色鐵質暖水壺,雖然外形怎么說也不好看,但質量的確可稱得上“管用五十年”(“日豐管”廣告語),對于當時的大多數傳統家庭來說,除非意外情況一般不需要更換新產品。而現在這種某個產品使用一輩子的事例卻已經很難再聽到。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自行車、家具、皮鞋、水暖、管材……等等幾乎一切耐用消費品乃至建筑裝修等等領域中。這樣的例子挺多了,會使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工業技術退步了,“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實并非如此,稍對中國工業在改革開放以來有目共睹的成就有所思考就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此其實行內的人早已“心照不宣”——其實這是“有計劃的廢止制”的“宜家模式”在中國市場的一種實踐形式。
很多產品在設計之初就已經決定了其必然在多長一段時間之內報廢,其報廢原因已經逐漸從“時尚”轉向對大眾各個階層都同樣產生影響的質量層面。這是因為過去設計師和文化理論家們所重視的“制造時尚”等等,已經幾乎無法在一個“長尾營銷”的時代切實地影響到那些對“時尚”不甚重視的群體的消費,而作為一個極大的市場,商家是不可能忽視它們的存在的。由此,作為對功能主義的一種修正與反駁,“有計劃的廢止制”作為一種設計方法論在西方設計史上逐漸明朗。畢竟,(請允許我為本行業的利益說一句“公道”的話)設計研究和設計教育的任務,一方面固然不應該忽視如何“為人民服務”等等傳統功能主義層面的內容,但另一方面的確也不應忽視與設計師生存息息相關的再生產問題。面臨新的市場環境和設計處境,對于“有計劃的廢止制”的合理利用,便內在地成了設計師任務拓展的一種必然要求。
在此之前,傳統意義上的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已開始受到越來越沉重的沖擊與挑戰。
盡管文化人類學中的功能主義理論作為一種學術范式早已經衰微,但放眼整個20世紀中國,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卻基本上一直是設計界的主流和理論界的共識。直到今天在設計院校的課堂上,幾乎任何一部《設計概論》教材都會專門設置章節來講授“功能”之于設計的重要性;對于功能的強調總是會引起人們的共鳴,反之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再加上過去設計界總是受到建筑界“形式追隨功能”等等宏大口號的影響,天然地把“功能”的對立面設定為“形式”,并且賦予了“形式”一詞“華而不實”、“形式主義”等方面的聯想,因此“以人為本”的功能主義理論更是“得道多助”。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其實從幾個方面早已開始不知不覺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首先是來自于情感方面的質疑。2003年,美國心理學家唐納德·諾曼的一部過時的暢銷書《日用品的設計(DesignofEverydayThings,請不要誤譯為“每一天的設計”)》被冠以《設計心理學》的中文書名被中信出版社引進,更是曾經激發了不少人對于功能主義設計理論的認同。直到今天,這本書還被很多設計者和決策者奉為圭臬。2006年的另外一部有關網頁設計的暢銷書《Don’tMakeMeThink》就仍應該看作是此一學術范式之內的著作。盡管事實上《設計心理學》一書的作者,早已經開始質疑自己在上個世紀提出的這種忽視人類審美情感的極端功能主義的設計理論。在新書《情感化設計——為什么我們喜歡或討厭日用品(EmotionalDesign:WhyWeLoveorHateEverydayThings)》(中譯本由電子工業出版社2006年引進)中,諾曼竟一反常態地承認,自己寫作《設計心理學》的時候,片面地重視了功能主義設計理論而低估了“情感”在設計中可能產生的作用。
其次是對功能主義忽視審美教育、甚至誤導公眾審美的焦慮。進入21世紀以來,幾則《腦白金》的廣告,讓無論審美教育程度高低的人都不得安寧,為此,還曾經發生過上海市民要求停播低俗廣告、“腦白金”的企業負責人甚至還曾經當面為廣告的低劣水準道歉,并保證日后更改。結果后來的“腦白金”廣告依然有恃無恐,才讓人明白這種“道歉”不過是一種“做秀”的公關手段。其創意構思不說也罷。然而,似乎市場在與所有人開了一個玩笑:盡管廣告創意低速齷齪,但“腦白金”產品的市場銷量卻是一路飆升。一時間,在“銷售額是檢驗廣告成敗的唯一標準!”等等“硬道理”的裹挾之下,人們也不得不屈服于這種幾乎無法辯駁的“功能主義廣告理論”,甚至開始習慣于接受“腦白金”乃至其他跟風的“低俗廣告”。“功能主義”開始和它的追隨者們展現了其自身“悖論”的一面。眼下,中國的一批優秀的專業設計師審美素養與社會大眾接受水平的“落差”已經越來越凸現為一個雙方爭論乃至誤解的焦點問題。的確有很多迎合市場的設計師放棄專業品位而無條件地順從甲方意志,但作為設計師,恐怕不應忘記一種對社會大眾進行審美教育的艱巨的使命。
功能主義設計理論也是與上文中我們所說到的那種“為人民服務”的大眾化設計教育理念聯系在一起的。的確,可以說這種源自包豪斯的理念是走在“設計”行業自身發展規律的正途上,并且也是近年來國內設計教育大幅度擴招之后所必需及時調整適應的市場導向。設計與純藝術不同,相比較“純藝術”,設計更多的可說是一種服務性的行業,如果說受眾是設計師的衣食父母恐怕并不例外。脫離大眾和市場的設計教育恐怕連畢業生的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但這里筆者更想強調的是,任何一種教學思想,我們都不應該走向極端;任何一種外來的教育理念,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由于設計體制和設計組織長期以來處于“缺席”的狀態,至今沒有一個能夠維系起全國設計師的行業組織,因而“設計”行業在社會上沒有以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發揮積極的作用,設計師不但缺乏公信力也缺乏職業認同。在很多人看來,“設計師”只是一種缺乏社會地位、為自己服務的“小工”。并且與歐美國家受眾審美教育程度不同,如上所述,中國的甲方和公眾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對于美和真正的創意的理解與接受,相當一部分人敢于毫無顧忌地用自己未經過專業訓練的審美觀念干涉設計師的創作獨立性。——在這種社會對于設計行業的認知、接受現狀中,倘若設計理論從業者再進一步用一種“平民化的、民主的設計立場”影響公眾和圈外人士對于“設計”行業認知的話,無法保證這不會進一步助長國內各級甲方和公眾自以為是的心理,從而對國內尚未成熟的設計行業帶來更大的傷害。
然而,從根本上說,真正對于功能主義設計理論構成顛覆性挑戰的,可能還不是商品的情感、審美等等藝術層面的屬性,而是在技術層面上如何能夠保證設計師持之以恒地從消費者身上獲得利益和收入——這正是以往功能主義忽視設計主體的一種體現。所以功能主義自身蘊含著深刻的悖論——即一方面,“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倡導尊重產品的使用者、考慮使用中的便利性與耐用性,但同時這種“以人為本”的實踐不可能做得很徹底,因為提倡產品耐用性的同時,往往容易導致對于產品設計者經濟利益的忽視。功能主義理論在重視產品使用功能的同時也包含了一個反命題,即產品的使用功能與商業功能二者很多時候互相抵牾。
毫無疑問,當“有計劃的廢止制”一旦從一種商家隱性的策略變成設計學中一種顯性的設計方法,必然有可能在設計倫理的層面引起了小的波瀾,難以讓廣大的設計用戶接受。因此,即便是“有計劃的廢止制”的典型代表“宜家”,也需要通過各種各樣的廣告宣傳訴求于其“耐用性”的一面——盡管這種宣傳往往隱含著更大的陷阱。諸如在售賣現場用一種機械裝置不斷地撞擊座椅以表明其堅固等等,但稍有常識的人便知道這種表演示的撞擊與我們對于“宜家”產品的使用經驗相去甚遠,真正堅固的家具恰恰不需要通過此種手段來加以證明,而且甚至可以更加干脆地說——人們在市場中傾向于購買“宜家”的產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其產品設計的喜愛,至于“耐用性”的問題反倒不會被優先考慮。因此,這種“撞擊實驗”放在宜家的展廳的時候,總讓人感覺一種歐美人士特有的反諷或幽默。
這并不是說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而是說,功能主義設計理論需要重新檢省自己的理論構成及其邏輯嚴密性。因此,正視“宜家模式”對于傳統的功能主義設計理論所形成的挑戰,是把功能主義的研究視角從受眾轉向設計者和市場,從產品的使用功能轉向商業功能。說到底這還屬于功能主義設計理論范式在新的市場條件下所必須加以回答和應對的“分內之事”。換句話說,真正對功能主義設計理論形成挑戰的,恰恰正是“功能主義”理論自身的邏輯。
- 上一篇:供銷社科學發展觀整改分析報告
- 下一篇:財政部門科學發展觀整改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