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美學(xué)思想研究論文
時(shí)間:2022-11-18 05:18:00
導(dǎo)語:劉勰美學(xué)思想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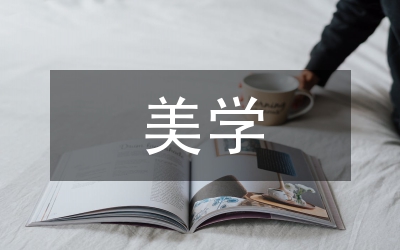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內(nèi)容提要】
劉勰的《文心雕龍》包含的美學(xué)思想,是“龍學(xué)”研究中有待進(jìn)一步開拓的領(lǐng)域。本文論述了劉勰對美的本質(zhì)、審美原則和標(biāo)準(zhǔn)、審美感知等問題的認(rèn)識;對劉勰美學(xué)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見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對劉勰美學(xué)思想的方法論及其思想來源進(jìn)行了探討。
【關(guān)鍵詞】劉勰《文心雕龍》美美感方法論
劉勰的《文心雕龍》博大精深,歷來被認(rèn)為是我古代最系統(tǒng)、最完整的一部文學(xué)理論專著。自60年代以來,“龍學(xué)”研究者開始從美學(xué)角度對《文心雕龍》加以研討,開掘其中深邃的美學(xué)思想,成果顯著,遂使這一當(dāng)代顯學(xué)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但有些問題尚需進(jìn)一步澄清,另有些問題則有待深入開掘和拓展。這里談?wù)剛€(gè)人的見解,補(bǔ)苴罅漏,故名之曰“發(fā)微”。
一
對美的本質(zhì),作為一種美學(xué)思想是必須首先加以界定的。劉勰一方面從宇宙本體論出發(fā),認(rèn)為美就是“文”,而“文”則是一種客觀存在,它作為“道”的一種形式原出于“自然”。這就肯定了美的客觀性。另一方面他又從人類中心說出發(fā),認(rèn)為美是作為萬物的中心的人創(chuàng)造的,“文”作為心靈的顯現(xiàn)原出于人。這就又從另一個(gè)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觀性。同時(shí),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美劃分為三種范疇,即自然美、人文美、藝術(shù)美。從宇宙本體論出發(fā),他認(rèn)為自然美是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從人類中心說出發(fā),他認(rèn)為藝術(shù)美是人的創(chuàng)造,帶有主觀性;而人文美則是天人合一的產(chǎn)物,既有客觀因素又有主觀因素。這就是劉勰對美的本質(zhì)的認(rèn)識。
對自然美,他認(rèn)為這是先于人類,不依賴于人類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產(chǎn)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龍·原道》:“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傍及萬品,動(dòng)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在他看來,天地、日月和動(dòng)物、植物即天下萬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為,而且為人的創(chuàng)造所不及。這種認(rèn)識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數(shù)矣”,“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一類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
對人文美,他從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觀念出發(fā),認(rèn)為人文美是與人類的生成所俱來的,天地萬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與地之間出現(xiàn)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龍·原道》:“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shí)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
在他看來,天、地、人是所謂“三才”,即構(gòu)成世界的三種本質(zhì)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這“五行”的精華所在,是有性靈之物。人有性靈,便會(huì)有語言文字借之以表達(dá)思想感情,這種用以表達(dá)思想感情的語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這也是自然而然的。這種認(rèn)識源于《易傳·系辭》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萬物的本源是“太極”。如果我們把“太極”理解為一種精神實(shí)體的話,那么這種觀點(diǎn)顯然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但這種客觀唯心主義與前面所說樸素唯物主義也不無內(nèi)在聯(lián)系。或者可以說劉勰樸素唯物主義的美學(xué)觀中不無唯心主義成份,客觀唯心主義的某些觀點(diǎn)中又不無唯物主義的含理內(nèi)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與自然美合而為一,相提并論,則是天人合一的傳統(tǒng)觀念的合乎邏輯的結(jié)論。天人合一是我國古代的一個(gè)哲學(xué)觀點(diǎn),《莊子·齊物》說:“天地與我并在,萬物與我為一。”這種物我同一,人與天合為一體的境界為最高境界的觀點(diǎn),即天人合一的觀點(diǎn)。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說就是一種自然美。這也是合乎邏輯的推論。劉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雖然不盡科學(xué),但人體之美,語言文字之美說它具有客觀性也是不無道理的。其實(shí)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來說,人體自身也是一種物,不過是屬別于“無識之物”的“有心之器”罷了。
對包括文學(xué)在內(nèi)的藝術(shù)美,他從人文合一的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藝術(shù)美是人的創(chuàng)造,人具有這種創(chuàng)造能力和需要這種創(chuàng)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龍·明詩》:“人稟七情,應(yīng)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情采》:“若乃綜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wǎng)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fā)而為辭章,神理之?dāng)?shù)也。”
在他看來,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懼、愛、惡、欲等種種情感,人與外界相接觸或受到某種刺激,就會(huì)有所感發(fā),通過不同形式的感發(fā)來表達(dá)思想感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也即人文合一的觀念,它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有更為明確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還認(rèn)為這種性靈的抒寫就是一種美。顯然,如果說《文心雕龍·原道》所說“文之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藝術(shù)美了。而且藝術(shù)之美既包括文學(xué)之美的“辭章”,也包括美術(shù)之美的“黼黻”和音樂之美的“韶夏”。它們都是人的創(chuàng)造,而人之所以能有這種創(chuàng)造性,則為“神理”所支配。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體論,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體論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內(nèi)在的必然邏輯。
在對劉勰的美學(xué)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劉勰論美的出發(fā)點(diǎn)是“心”,美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產(chǎn)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龍》中“‘心’是美的內(nèi)核。”〔1〕與此相近的觀點(diǎn),還有人認(rèn)為“劉勰把感情視為藝術(shù)的本源,靈魂和血液。”〔2〕這種觀點(diǎn)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們肯定劉勰把藝術(shù)美視為人的創(chuàng)造,但同時(shí)也肯定劉勰把這種創(chuàng)造的本源歸之于客觀世界,這在前面的闡述已清晰可見。那么,如果把美或藝術(shù)美的核心、本源僅止于藝術(shù)家的內(nèi)心或感情,那就不僅不符合《文心雕龍》的本意,而且無異于把劉勰對美的認(rèn)識歸之于唯心主義的一派了。這是我們所不能茍同的。
二
美學(xué)原則和審美功能是美學(xué)的基本問題。對美學(xué)原則,劉勰認(rèn)為創(chuàng)造藝術(shù)美尤其是文學(xué)之美應(yīng)當(dāng)以圣人為楷模,以經(jīng)籍為典范,象他們的作品那樣達(dá)到內(nèi)容與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即自然和諧之美。這也就是《文心雕龍》在《原道》之后設(shè)《征圣》,《宗經(jīng)》的本意。《文心雕龍·征圣》:“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shí)者也。”《文心雕龍·宗經(jīng)》:“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熔匠,文章奧府。”這就是說,追求文學(xué)之美就應(yīng)當(dāng)向圣人學(xué)習(xí),應(yīng)當(dāng)以他們的《詩》、《書》、《禮》、《易》、《春秋》這五經(jīng)為典范。它們的創(chuàng)作原則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又要有華美的語言和巧妙的表達(dá)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說“文附質(zhì)”,“質(zhì)待文”;《才略》所說“文質(zhì)相稱”,“華實(shí)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統(tǒng)一亦即“自然”這美的最高境界。
對審美標(biāo)準(zhǔn)或批評標(biāo)準(zhǔn),劉勰提出了“六義”說和“六觀”說。《宗經(jīng)》“六義”是:“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fēng)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里的“情”、“事”、“義”主要是從思想內(nèi)容方面提出的標(biāo)準(zhǔn),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實(shí)具體而不虛妄,觀點(diǎn)正確而不詭詐。
“體”、“文”主要是從藝術(shù)形式方面提出的標(biāo)準(zhǔn),即文風(fēng)簡煉而不繁冗,語言華美而不靡麗。“風(fēng)”則主要是指作品在社會(huì)中能產(chǎn)生積極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亂。《知音》“六觀”是:“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位體”是謀篇立體,“置辭”是遣詞造句,“通變”是繼承與創(chuàng)新,“奇正”是新奇與雅正,“事義”是選材與用典,“宮商”是平仄與韻律。這里包括了文學(xué)作品的諸多方面,既有題材、主題問題,又有語言、風(fēng)格問題,乃至創(chuàng)造方法問題等,劉勰對審視文學(xué)作品考慮得是非常全面的。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對“六義”和“六觀”到底什么是審美標(biāo)準(zhǔn)或批評標(biāo)準(zhǔn),過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學(xué)術(shù)界引起過一些爭議。郭紹虞和羅根澤等人認(rèn)為“六觀”是批評標(biāo)準(zhǔn),趙盛德等人沿用此說。而陸侃如、牟世金等人則提出異議,認(rèn)為“六義”既是劉勰對創(chuàng)作的要求,也是論文的六個(gè)批評標(biāo)準(zhǔn)。“六觀”則是需要考察的六個(gè)方面。后來牟世金又在《劉勰論文學(xué)欣賞》一文中說:“六觀,不過是從六個(gè)方面來進(jìn)行觀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條衡量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六觀’就與批評標(biāo)準(zhǔn)毫不相干。”〔3〕馬白進(jìn)一步指出:“‘六義’是劉勰所主張的文藝批評標(biāo)準(zhǔn)。其中‘情深’、‘風(fēng)清’、‘事信’、‘義直’是政治標(biāo)準(zhǔn),‘體約’、‘文麗’是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4〕如何看待這一分歧?我們肯定《宗經(jīng)》“六義”是批評標(biāo)準(zhǔn),也可以說是審美標(biāo)準(zhǔn),但從《文心雕龍》全書總體來看,它主要是從作家的創(chuàng)作角度來要求的,所指藝術(shù)范圍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學(xué)作品的鑒賞與批評來談的,所以它出現(xiàn)在總論《宗經(jīng)》之中。然而我們也沒有理由就此來斷言“六觀”與批評標(biāo)準(zhǔn)“毫不相干”,因?yàn)閯③脑凇吨簟诽岢觥傲^”之后,緊接著就說:“斯術(shù)既形,優(yōu)劣是矣。”這里的“術(shù)”固然可解釋為方法、方面,那么,這里的“形”也不可忽視,“形”即表現(xiàn)。因而,這兩句話就應(yīng)當(dāng)疏解為:看看這六方面的表現(xiàn)怎么樣,作品的優(yōu)劣也就顯現(xiàn)出來了。如果作此疏解,劉勰所說“斯術(shù)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說無涉批評標(biāo)準(zhǔn),因?yàn)槿藗兂Uf的“這方面的表現(xiàn)怎么樣”本身就是標(biāo)準(zhǔn),自不待言。只不過是“六觀”主要從讀者鑒賞文學(xué)作品這個(gè)角度看問題罷了,所指藝術(shù)范圍也狹窄一些。
如果我們再在內(nèi)涵上把“六義”和“六觀”加以對照,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它們存在著一致性,即都強(qiáng)調(diào)了要從內(nèi)容和形式兩個(gè)方面的諸多因素中來要求和衡量文學(xué)作品,都強(qiáng)調(diào)了藝術(shù)的和諧完美。不同之處在于“六義”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會(huì)效果問題,而“六觀”則補(bǔ)充了創(chuàng)作方法(通變)和藝術(shù)風(fēng)格(奇正)方面的問題。綜觀“六義”與“六觀”,它們與前面所提審美原則是一致的,不過是在和諧統(tǒng)一這一美學(xué)原則下所派生的具體命題,“六義”側(cè)重于創(chuàng)作方面來談,所指范圍大些,“六觀”側(cè)重于品評方面而言,所指范圍小些,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gòu)成了劉勰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和批評標(biāo)準(zhǔn)。
對審美功能,劉勰很強(qiáng)調(diào)文藝的美感作用,認(rèn)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龍·征圣》:“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文心雕龍·宗經(jīng)》:“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jì)。”《文心雕龍·程器》:“禽文必在緯軍國,負(fù)重必在任棟梁。”劉勰認(rèn)為一個(gè)國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養(yǎng)性,乃至軍事都貴于有文采。特別是人文關(guān)系,文章因人的德行產(chǎn)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傳。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見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學(xué)中在研究美這個(gè)對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個(gè)對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審美活動(dòng)中的感知、移情、聯(lián)想、思維及情感等實(shí)踐活動(dòng)內(nèi)容。關(guān)于劉勰的美感論以前人們論及較少,一般都以為在劉勰所處的時(shí)代,對美感這一較復(fù)雜的美學(xué)問題還難以從理論上加以把提。我們認(rèn)為,雖然《文心雕龍》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詞,“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國譯介西方美學(xué)著作時(shí)產(chǎn)生的一個(gè)概念,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文心雕龍》并未論及有關(guān)美感的一些實(shí)質(zhì)性問題。實(shí)際上,對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審美的認(rèn)識過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異性等問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都有所論及,只是尚未運(yùn)用“美感”“審美”等現(xiàn)代美學(xué)概念罷了。劉勰美感論的基本觀點(diǎn)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總術(shù)》、《養(yǎng)氣》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礎(chǔ)包括人的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等。生理基礎(chǔ)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我們對客觀世界的一切感知、認(rèn)識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覺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覺器官是我們產(chǎn)生美感的窗口。從這個(gè)角度來說,感覺正是產(chǎn)生美感的源泉。沒有感覺器官也就無所謂美感。感官的審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還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內(nèi)心,即實(shí)現(xiàn)對美的心靈觀照,從而成為特定的思想感情,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礎(chǔ)。劉勰《文心雕龍·養(yǎng)氣》說:“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就是講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美感的心理基礎(chǔ)不僅是生理基礎(chǔ)的高級階段,而且是生理基礎(chǔ)的依存條件和原動(dòng)力。馬克思曾說:“對于非音樂的耳雜,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5〕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多處論及創(chuàng)作和鑒賞中美感的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的這種關(guān)系。他這樣論及創(chuàng)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文心雕龍·神思》:“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tǒng)其關(guān)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jī)。”“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dòng),心亦搖焉。”“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劉勰認(rèn)為,文學(xué)家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對客觀世界產(chǎn)生美感而后才能萌發(fā)創(chuàng)作沖動(dòng),而文學(xué)家之所以能對客觀世界產(chǎn)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覺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還”,通過聽覺和視覺捕捉、接受客觀世界美的信息。舍此,無所謂美感,也無所謂創(chuàng)作。同時(shí),劉勰還認(rèn)為,感覺器官的審美感知還需要上升而為審美的心靈觀照,即“神與物游”、“心亦搖焉”、“心亦吐納”。這種心靈觀照也就是現(xiàn)代美學(xué)所說的“內(nèi)在感官”或“黑箱裝置”對客觀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層感知。如果說感覺器官的審美感知只是知覺到客觀世界的現(xiàn)象,那么通過心靈觀照所構(gòu)成的則是審美意象了。
他這樣論及藝術(shù)鑒賞中美感的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文心雕龍·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dá)。”《文心雕龍·總術(shù)》“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劉勰認(rèn)為,無論對自然美、人文美還是藝術(shù)美的鑒賞,美感的產(chǎn)生也都首先起自作為生理基礎(chǔ)的感覺器官,即“目”、“視之”、“聽之”,舍此,無法進(jìn)入鑒賞過程,美感也無從談起。但在鑒賞中感覺器官的審美感知同樣有待于上升到作為心理基礎(chǔ)的心靈觀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過心領(lǐng)神會(huì),通過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觸及美的意境和真諦。無論在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還是在藝術(shù)鑒賞中,劉勰認(rèn)為生理基礎(chǔ)和心理基礎(chǔ)都是不可或缺的。關(guān)鍵在敏銳的洞察力和較高的審美情趣。
美感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鑒賞中都有一個(gè)心理過程,即審美認(rèn)識過程,只有通過這一過程在創(chuàng)作中才能構(gòu)成藝術(shù)形象,在鑒賞中產(chǎn)生審美愉悅。審美認(rèn)識過程是復(fù)雜而微妙的。劉勰對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龍·物色》:“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文心雕龍·知音》:“夫綴文者情動(dòng)而辭發(fā),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yuǎn)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nèi)懌,譬春臺(tái)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玩澤方美。”
劉勰認(rèn)為,在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沖動(dòng)由客觀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辭這種美的表現(xiàn)形式則產(chǎn)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發(fā)的思想感情。在創(chuàng)作中美感表現(xiàn)為“物——情——辭”這樣一個(gè)心理過程。而在鑒賞過程中,審美主體首先接觸到的是文辭,由文辭而在自己的心靈中喚起作家所體驗(yàn)過的情感,由此而認(rèn)識世界。在鑒賞中美感表現(xiàn)為“辭—情—物”這樣一個(gè)相反的心理過程。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以意逆志”。對由審美鑒賞所喚起的審美愉悅,即“深識鑒奧”“歡然內(nèi)懌”。劉勰引用了《老子》中的兩段話來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tái)”。一是三十五章中的“樂與餌,過客止”。這兩個(gè)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說明了藝術(shù)鑒賞中的審美快感。
在美感的心理過程中離不開移情和聯(lián)想。所謂移情就是審美主體把情感外射到與“我”相對立的“物”上去,使審美主體的情感也為外物所具有,即達(dá)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劉勰對這種移情現(xiàn)象也有生動(dòng)的描述。《文心雕龍·物色》:“春日遲遲,秋風(fēng)颯颯。情往似贈(zèng),興來如答。”《文心雕龍·神思》:“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
劉勰認(rèn)為,“情”本為人類所有,自然物無所謂“情”,但在審美的心理過程中人的情感便會(huì)自覺不自覺地轉(zhuǎn)移到物上。譬如,無論春暖花開之日還是秋風(fēng)蕭瑟之時(shí),都會(huì)牽動(dòng)人的感情,在觀賞自然景物之際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饋贈(zèng)那樣賦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興致又象它對自己的酬謝一樣,通過心與境的交融達(dá)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藝術(shù)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臨大海似乎一望無際的海面都洋溢著自己的情。只有通過這種移情才能創(chuàng)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無動(dòng)于衷,泰然處之,也就不會(huì)有美的創(chuàng)造。
所謂聯(lián)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關(guān)的其他事物的審美想象,通過這一橋梁構(gòu)成的以少總多,以一統(tǒng)萬的意象。對此劉勰也有論及。《文心雕龍·物色》:“詩人感物,聯(lián)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qū)。”劉勰認(rèn)為,詩歌的藝術(shù)美的創(chuàng)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礎(chǔ)上,通過無窮無盡的由此及彼的聯(lián)想,才能構(gòu)成具有美學(xué)意義的意境。其實(shí)這也就是在現(xiàn)代美學(xué)中所說的藝術(shù)想象或形象思維。
美感有其共同性,這種共同性使審美成為全人類的活動(dòng),使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藝術(shù)鑒賞在人與人之間溝通起來,但美感又有其差異性,它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五彩繽紛,也滿足了人們在藝術(shù)鑒賞中的不同需求。劉勰論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論,它是全人類相通的“性情之?dāng)?shù)”,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構(gòu)成的客觀規(guī)律,亦即“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劉勰還注意到了美感的差異性。《文心雕龍·知音》:“夫篇章雜沓,質(zhì)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jié),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劉勰認(rèn)為,由于美感的差異性不僅創(chuàng)作會(huì)有不同的風(fēng)格,鑒賞也會(huì)有偏愛和異趣。
四
劉勰的美學(xué)思想在我國6世紀(jì)空前地達(dá)到了時(shí)代的高度,可謂獨(dú)步當(dāng)時(shí)。對其后的美學(xué)思想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而且為后來的中國古代美學(xué)論著所難以企及。先進(jìn)的理論成果總是與先進(jìn)的方法論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龍》美學(xué)成就的取得與劉勰掌握了比較科學(xué)的方法論分不開。
早在50年代范文瀾就已指出:《文心雕龍》既是文學(xué)批評,也是“文學(xué)方法論”〔6〕。60年代劉永濟(jì)也認(rèn)為,“彥和此書,思緒周密,條理井然,無畸重畸輕之失。”〔7〕70年代楊明照也曾盛贊“他那嚴(yán)密細(xì)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論有所論及,但專門進(jìn)行探討的論文還較為少見。80年代馬白的《論〈文心雕龍〉的系統(tǒng)觀念和系統(tǒng)方法》及《從方法論看〈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兩文則是以新的科學(xué)方法探討《文心雕龍》的方法論的專論。他認(rèn)為,“從方法論著眼,我們不難看出,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一條紅線便是樸素的初步的辯證思維方法。正是這種辯證思維方法,不僅使全書結(jié)構(gòu)嚴(yán)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視鞭辟入里,思想閃閃發(fā)光;也是這種辯證思維方法,引起中國美學(xué)史第一次歷史性的轉(zhuǎn)折,從而使《文心雕龍》獨(dú)立于世界美學(xué)之林,占踞極其重要的地位。”〔8〕應(yīng)當(dāng)說這是一個(gè)十分大膽而有見地的論斷。還有人認(rèn)為,劉勰的方法論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務(wù)折衷’確實(shí)是貫穿于《文心雕龍》的基本方法。這個(gè)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對立的方面,并且把這些方面統(tǒng)一起來,而不要只孤立地強(qiáng)調(diào)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劉勰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是比較全面,客觀的。”〔9〕如果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調(diào)節(jié)過與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辯證思維方法的一種含意。
總體來看,辯證思維方法是《文心雕龍》闡述其美學(xué)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層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龍》的辯證思維方法表現(xiàn)在劉勰論美和文學(xué)的各個(gè)范疇和命題之中。諸如美與丑、道與文、心與物、情與采、文與質(zhì)、通與變、古與今、奇與正、形與神、風(fēng)與骨等相對范疇及相關(guān)論斷,他都能夠“撮舉同異”(《明詩》),“左右相瞰”(《熔裁》),“會(huì)通合數(shù)”(《體性》)“棄偏善之巧,學(xué)具美之績”(《附會(huì)》),即把握它們的對立統(tǒng)一和相反相成。具體來說,諸如文學(xué)活動(dòng)中的作家與作品的關(guān)系,作品與讀者的關(guān)系,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整體與局部的關(guān)系,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在本質(zhì)與外在形式的關(guān)系,文學(xué)風(fēng)格的異同關(guān)系,創(chuàng)作方法的繼承與革新的關(guān)系等等,他都能夠運(yùn)用辯證思維方法來加以考慮和闡述。
例如就作品與讀者的關(guān)系,劉勰是這樣論述鑒賞與批評的。《文心雕龍·知音》:“夫篇章雜沓,質(zhì)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這里一方面談到作品本身的復(fù)雜情況,即文體的駁雜,內(nèi)容與形式的諸多方面結(jié)合等;另一方面又談到讀者的復(fù)雜情況,即人們審美情趣和學(xué)識見聞的差異等。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復(fù)雜情況造成了鑒賞與批評的見解多異,因而必須有一個(gè)正確的態(tài)度。這樣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對整體與局部的關(guān)系,劉勰是這樣論述作家創(chuàng)作的決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龍·體性》:“然才有庸俊,氣有剛?cè)幔瑢W(xué)有淺深,習(xí)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者矣。”這里劉勰視文苑為一整體,每一個(gè)作家都是一個(gè)局部,文苑的整體是由每一個(gè)作家的作品所構(gòu)成的,所以出現(xiàn)了豐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門的局面。同時(shí),他又視每個(gè)作家為一個(gè)整體,每個(gè)作家的創(chuàng)作又由他的才、氣、學(xué)、習(xí)這四個(gè)局部因素所決定,所以出現(xiàn)了風(fēng)格各異的作品。這樣就把問題看得很全面了。
對內(nèi)在本質(zhì)與外在形式的關(guān)系,劉勰是這樣闡述情與采的關(guān)系的。《文心雕龍·情采》:“夫水性虛而淪漪結(jié),木體實(shí)而花萼振,文附質(zhì)也。虎豹無文,則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資丹漆,質(zhì)待文也。”劉勰對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們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著指出了內(nèi)容對形式的決定性作用,這樣就使人們對作品的構(gòu)成有一個(gè)全面、透徹的認(rèn)識,而且在論述中,他把理論與意象的對立統(tǒng)一起來,給人以十分生動(dòng)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謂手段高超。
再如《通變》中的“夫設(shè)文之體有常,變文之?dāng)?shù)無方”,“參伍因革,通變之?dāng)?shù)也”。則從歷史的縱向闡述了繼承與革新的辯證關(guān)系。同時(shí),我們還應(yīng)看到,劉勰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層面上展開的,而且有其系統(tǒng)觀點(diǎn)和系統(tǒng)方法。
五
劉勰美學(xué)思想的哲學(xué)基礎(chǔ)是對儒、道、釋的博采眾長,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們的合理內(nèi)核的基礎(chǔ)上,上升到了一個(gè)新的高度。其美學(xué)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釋的深刻影響。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論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說、辯證法思想等,對此前賢已有所研究,但對其美學(xué)思想方法論淵源的研究卻有待深入和拓展。
關(guān)于劉勰美學(xué)思想方法論的淵源,60年代劉永濟(jì)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為多。”〔10〕而后,楊明照也認(rèn)為“他那嚴(yán)密細(xì)致的思想方法,無疑是受了佛經(jīng)著作的影響。”〔11〕王元化和馬宏山等人則對此進(jìn)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學(xué)和“中道”論認(rèn)識論的影響。這一點(diǎn)是應(yīng)當(dāng)給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說憾在闡發(fā)欠詳。我國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為國教,而佛學(xué)中的因明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的哲學(xué)領(lǐng)域還是一種比較先進(jìn)的方法論。古印度在公元5世紀(jì)由哲學(xué)家無著和世親汲取了重邏輯和認(rèn)識論的正理派的學(xué)說而構(gòu)成的因明稱為古因明。古因明繼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來進(jìn)行推理,五支即:宗(論題)、因(理由)、喻(例證)、合(應(yīng)用)、結(jié)(結(jié)論)。6世紀(jì)古印度的陳那及其弟子將古因明發(fā)展而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論題)、因(理由)、喻(例證)。比起五支作法更為簡捷明了。如:“宗”為某處有火,“因”為發(fā)現(xiàn)了煙的緣故,“喻”為若是發(fā)現(xiàn)了煙就會(huì)有火,象廚房等處。這“喻”、“因”、“宗”,其實(shí)也就相當(dāng)于我們今天形式邏輯所說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結(jié)論所組成的三段論。這是一種科學(xué)的演繹推理方式,它的特點(diǎn)在于通過中項(xiàng)把大項(xiàng)和小項(xiàng)聯(lián)系起來,從兩個(gè)前提必然地推出結(jié)論,它反映了事物屬與種之間的包含關(guān)系。劉勰撰寫《文心雕龍》時(shí)正是古因明學(xué)隨佛教傳入我國的歷史時(shí)期。劉勰在定林寺依沙門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諳熟因明,運(yùn)用自如,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龍》說理合乎邏輯,部類分明,嚴(yán)密細(xì)致,有條不紊。
另外,佛門的“中道”說也使劉勰的理論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說的“圓照”、“圓覽”。佛典《大智度論》卷四十三:“常是一邊,斷滅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密。”佛門的“中道”論認(rèn)為,“常見”和“斷見”都是偏執(zhí)一端的,只有離開“常見”和“斷見”二邊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遷流無常和又相續(xù)不斷,才能把握真諦。這其實(shí)與儒門的倫理思想和思維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龍》中對因明和中道的運(yùn)用,可以說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便是明顯運(yùn)用因明所作的演繹推理。《序志》“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qū)分”便是對因明學(xué)中屬種關(guān)系劃分的運(yùn)用。正因如此,所以全書在整體上“上篇以上,綱領(lǐng)明矣”,“下篇以下,毛目顯矣”。至于“中道”論也是貫穿全書,《序志》批評“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dāng),應(yīng)《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卻又不無自負(fù)而自信地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論方法就在于“彌綸群言”,“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wù)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騎墻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wù)撸抢淄玻瑒葑圆豢僧愐玻挥挟惡跚罢撜撸瞧埻兀碜圆豢赏病薄F洹爸械馈钡暮诵倪€在“勢”與“理”。
《文心雕龍》美學(xué)思想方法論的第二個(gè)來源是以《周易》為宗的儒、道、玄各學(xué)派中的比較科學(xué)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對此一來源,80年代之前人們關(guān)注不夠,專門研究甚少,范文瀾和王元化等人對《文心雕龍》繼承《周易》中的某些觀點(diǎn),曾有所提及,但尚未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加以評說。馬白的《從方法論看(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首辟此說并加以探求,他說:對劉勰而言,“蘊(yùn)含于《周易》、《老子》、《莊子》等典籍中的儒則是他辯證思想的重要淵源。”〔12〕該文從劉勰分析文學(xué)現(xiàn)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對立統(tǒng)一內(nèi)容的命題,指出了他對《周易》中“分而為二”的思想方法的運(yùn)用;從劉勰考察文學(xué)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勾勒“變動(dòng)不居”的思想方法的運(yùn)用;從劉勰辨別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輪廓,指出了他對《周易》中事物的異同,深入揭示藝術(shù)思維規(guī)律,建立完整的文體論,指出了他對《周易》中“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運(yùn)用。這些都是頗為深刻的。關(guān)于“分而為二”的觀點(diǎn)和方法,除貫穿于劉勰的文學(xué)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風(fēng)格論和批評論中而外,似還應(yīng)補(bǔ)充上:劉勰對創(chuàng)作與鑒賞、批評中的主觀因素的辯證思維,即對主觀因素的對立統(tǒng)一問題的分析,也是運(yùn)用了“分而為二”的觀點(diǎn)與方法。關(guān)于主觀因素中的對立,《周易·系辭》:“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運(yùn)用此法,劉勰在《體性》中分析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不同時(shí),認(rèn)為由于作家“才”、“氣”、“學(xué)”、“習(xí)”的不一,“則數(shù)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yuǎn)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四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在《知音》中分析鑒賞與批評中的不同見解時(shí),認(rèn)為“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jié),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這一切情況都是由“分而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關(guān)于主觀因素統(tǒng)一方面,《周易·系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運(yùn)用此法,劉勰在《體性》中分析不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相反相成時(shí),認(rèn)為“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八體雖殊,會(huì)通合數(shù),得其環(huán)中,則輻輳相成”。這是它們統(tǒng)一的一面。在分析鑒賞與批評中又需有大體一致的標(biāo)準(zhǔn)時(shí),他于《知音》中又認(rèn)為,“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這“衡”與“鏡”則是它們統(tǒng)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創(chuàng)作與鑒賞、批評中主觀上的對立與統(tǒng)一,才能全面地、客觀地把握創(chuàng)作與鑒賞、批評,這其實(shí)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為二”。另外,劉勰對儒、道、釋、玄的認(rèn)識,也是把握了“見仁見智”和“殊途同歸”這兩面的,因而能有一個(gè)空前透徹的看法。
六
我們認(rèn)為《墨經(jīng)》中墨家的形式邏輯應(yīng)當(dāng)是《文心雕龍》方法論的第三個(gè)重要來源。這一點(diǎn)似乎并未引起人們應(yīng)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邏輯大體分為六個(gè)部分:明辯,言法,立名,立辭,立說,辭過。所謂“明辯”,《墨子·小取》說:“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jì),明異同之處,察名實(shí)之理,處利害,決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確立是非的標(biāo)準(zhǔn),否則無是非可言;“明異同之處”即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復(fù)雜事物中,把握同在何處,異在何處。他把“同”分為四類:“重同”即二名稱一實(shí)體,“體同”即部分在全體之中,“合同”即共同組成為一集體,“類同”即以類相從而同。“異”也分為四類:“二”卻二必異,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體”即不由“兼”分出,不連屬之體,“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圍不同,“不類”指分屬各類。“察名實(shí)之理”即考察名與實(shí)的關(guān)系,概念與對象的關(guān)系,思維與存在的關(guān)系。總之,“明辯”講邏輯的對象意義。
所謂“言法”,《墨子·非命上》說:“言必立儀”,“言”是立論,“儀”是法度。確立思維的兩大原則,即理由原則和同異原則。理由原則是“立辭必明其故”,同異原則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經(jīng)上》說:“同異而俱于之一”,這是同一律,大體如我們所說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一個(gè)思維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經(jīng)下》說:“彼彼、此此與彼此同,說在異”,這是矛盾律,大體如我們所說在一個(gè)思維過程中,一個(gè)思維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經(jīng)下》還說:“合與一,或復(fù)否,說在拒”,這是排中律,大體如我們所說在一個(gè)思維過程中,一個(gè)思維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總之,“言法”是講思維規(guī)律。
所謂“立名”,《墨子·小取》:“以名舉實(shí)”,即通過下定義來確定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他把“名”劃分為三種:達(dá)名,即范疇;類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單稱概念。至于下定義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劃分為三種:“以形貌命者”,“以居運(yùn)命者”,“以舉量數(shù)命者”。確定概念的外延離不開對概念的分類即屬、種劃分,《墨子·經(jīng)下》:“區(qū)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唯是。”這就是說要把同一屬的事物劃分為若干種。總之,“言辭”是概念論。
所謂“立辭”,《墨子·小取》:“以辭抒意”,即聯(lián)合兩個(gè)概念來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聯(lián)系,屬判斷論。所謂“立說”,《墨子·大取》:“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即演繹推理。“故”類于因明之“因”,“理”類于因明之“喻”,“類”類于因明之“宗”。《墨子·經(jīng)下》:“在諸其所然未然者,說在于是推之。”即歸納推理。所謂“辭過”則為謬誤論。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運(yùn)用墨家的形式邏輯之處也貫穿于全書。如關(guān)于“明辯”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確立是非標(biāo)準(zhǔn),劉勰論創(chuàng)作與鑒賞、批評所確立的《宗經(jīng)》“六義”和《知音》“六觀”即是非標(biāo)準(zhǔn)。“明辯”中的“明異同之處”,即把握同在何處,異在何處,《序志》所說“同之與異,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關(guān)于“立名”中的屬種分類“區(qū)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說“論文敘筆,則囿別區(qū)分”即是此法的運(yùn)用,劉勰把天下文章分為“文”、“筆”兩屬,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又各分為20種,每種里又有子目,如《明詩》中再將詩分為四言、五言、雜言、離合、回文、聯(lián)句等,十分細(xì)密。“立名”中的“以名舉實(shí)”下定義并以實(shí)加以說明,《序志》所說“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運(yùn)用,劉勰在論及每種文體時(shí)都首先下定義加以規(guī)范,并例舉典型篇目加以說明,如《明詩》“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xùn),有符焉爾。”再如“立辭”中“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的演繹推理,《物色》所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fā)。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fēng)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運(yùn)用。“立辭”中“在諸其所然未然者,說在于是推之”的歸納推理,《比興》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云’,此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yōu)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luò)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xí)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即是對此法的運(yùn)用。
劉勰的美學(xué)思想及其方法論都空前地達(dá)到了時(shí)代的高度,它不僅對我國古代美學(xué)思想的發(fā)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而且對我們今天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xué)理論體系也有著重要意義。而我們對這方面的研究只能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頁,而決不是它的終結(jié)。(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釋:
〔1〕胡學(xué)遠(yuǎn),趙伯英:《“心哉美矣”》,《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劉勰論美的原則》,《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龍集》,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頁。
〔4〕〔8〕〔12〕馬白:《美學(xué)縱橫論》,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頁。
〔5〕《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shù)》(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頁。
〔6〕范文瀾:《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頁。
〔7〕〔10〕劉永濟(jì):《文心雕龍校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頁。
〔9〕李澤厚、劉綱紀(jì):《中國美學(xué)史》第二卷下,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9—610頁。
〔11〕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