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美學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18 05:21:00
導語:我國美學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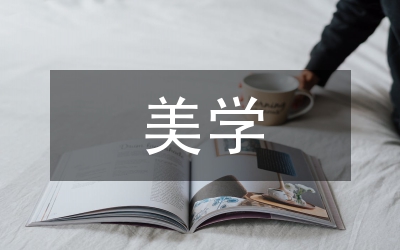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一種學術思想發展到了某種程度,一旦獨立構成一門學科,便有了追溯思想先驅的需要,以顯示其淵源有自,源遠流長。特別是當它不僅獨立,而且成為一門顯學的話,這種要求便成為一種更為強烈更為自覺的行為。
美學也有歷史,情形也大體上如是。
不過,由于美學做為一門西學,乃是西學東漸在20世紀初才為中國人所了解,對于美學的歷史追溯,首先便是西方美學歷史的追溯。美學史研究的第一批著述產生于19世紀的歐洲,這大約一方面是由于美學自鮑姆加通為之命名,使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后,經歷了德國古典美學這一輝煌時期,使美學由附庸蔚為大國。特別是自康德以來,美學思想成為構建民族國家現代性的重要思想資源,美學地位突顯。②而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出,始自19世紀現代知識型的建立,歷史原則取代了秩序原則,這種知識型以探求根源(origin)的歷史性為特征。③
華勒斯坦等人的研究報告中指出,自19世紀以來,歷史學等學科取得了社會科學中主導學科地位,在于它們有利于鞏固民族國家的權力。④因而,也正是這樣一種知識增長與思想歷史背景,美學史的第一批著作便是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出現,而鮑桑葵、克羅齊、吉爾伯特與庫恩等人所著的具代表性的美學史著作也都是形成于先發民族國家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美學這門學科自鮑姆加通建立之初就名實不符,引發了一場持久的爭論。因而,也使得美學史的撰寫,在內容與范圍上便有了各自的不同。在早期美學史撰寫中,不同的方式就已經存在。鮑桑葵在其《美學史·前言》中就明確地擺出自己的撰寫原則與述史立場:我認為我的任務是寫一部美學的歷史,而不是一部美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功績。……事實上,我是想盡可能寫出一部審美意識的歷史來。⑤而懷抱著要“把鮑桑葵那部精心寫成的歷史著作加以完成,并續寫到今天”的李斯托威爾,則在他的《近代美學史評述》中體現了不同的撰寫原則。⑥克羅齊在他的美學史中指出“我們列數了借以達到發現美學概念的辛勞和疑難;列數了它的被遺忘,后又復活和又有所發現之變遷;列數了在確切界定美學概念時的搖擺和不足。”⑦由吉爾伯特與庫恩合著,一出版就成了經典的《美學史》則提出“本書的寫作”“是依據一種以最好的方式來滿足”“更渴望知道美學術語的意蘊的人員之用”,是研究“人們對藝術與美之本質的認識”的幾千年積累。⑧顯然在這幾部頗有代表性的美學史著述中,其撰述原則與方法、范圍與對象都是各不相同的,鮑桑葵要研究審美意識的發展,故在美的哲學理論之外,尚廣泛涉及文學與各門藝術發展及與審美意識的關系。而李斯托威爾則集中于種種美學理論流派,克羅齊以及吉爾伯特與庫恩的兩種美學史則把關注點放在藝術與美的概念、本質及相關范疇、理論的源流、演化、發展上面。波蘭著名美學家塔達基維奇在他80年代出版的重要晚期著作《西方美學概念史》中談到美學史研究的不同方法:美學的歷史,也如其他學科的歷史一樣,可以以兩種方式來研究,既可以被看作是在這一研究領域里從事創作的人的歷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其研究之中所提出來的和解決了的問題的歷史。⑨
因此,美學史研究的范式已有的大體是三種:一則是美學家的歷史,二則是美學范疇、命題、理論的衍生歷史,三則是審美意識的發展歷史。二本世紀早期出現過的幾種中國人寫的美學史的小冊子,均為將英文著述漢譯或者通過日文轉手翻譯過來的產物,自然也都實際上是西方美學的歷史,⑩這也充分體現了作為后發國家的知識分子在接受一門西學時,除了照單全收、心悅誠服之外,幾乎沒有其它選擇的歷史圖景。而像王國維那樣不僅引入美學,以其介紹和開創性研究,成為中國現代美學開創者,而且以其冷靜的史家的頭腦和卓越的思想者的眼光,透視出西方現代美學、文化的內在矛盾性,隱約領會到西方現代性思想的內部的反抗現代性的不和諧之聲,從而陷入某種思想矛盾與精神困境之中,這樣的人物,實在是鳳毛麟角。何況,這樣的思想先驅與先覺,在當時除了遭受被誤解的命運和蒙受落后、封建逆流等種種罪名的不白之冤而外,在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中,也難有其它的可能性了。
中國美學史的系統研究起步很晚,幾部關于中國美學史的系統著述的出版均在80年代后。起步晚,也有其幸運的一面,這就是從一開始就盡量避免建國后相當長時期存在的某些學術研究的框架與范式。但是,卻不能避免中國美學史研究對西方美學史研究范式的借用與挪移。與中國美學史研究最靠近而又有可資借鑒的是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這兩門學科都有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歷程,但也基本上是挪用西方既有模式。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開頭就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而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朱自清指出:
“文學批評”一語不用說是舶來的,現在學術界的趨勢,往往以西方觀念為范圍去選擇中國的問題,故無論將來是好是壞,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由于有了這樣的先在研究范式,中國美學史研究對西方美學史研究范式的挪用就成為自然了。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以為“美學史就應該研究每個時代的表現為理論形態的審美意識。……美學范疇和美學命題是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識的理論結晶,……一部美學史,主要就是美學范疇,美學命題的產生、發展、轉化的歷史。”
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認為美學史研究有廣義、狹義之分,大體上也就是審美意識研究和美與藝術的理論成果研究。敏澤《中國美學思想發展史》認為“美學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最根本之點,就是要研究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審美意識、觀念,審美活動的本質和發展的歷史。”幾種觀點表述不一,寫作上其實沒有太大區別,基本是研究理論形態的美學歷史文獻,從而成為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三這種美學史研究,從今天的學術語境看來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其一,是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合法性問題。傳統的中國學術中,只有詩論、文論、詞論、畫論、書論、曲論、小說評點等等,卻沒有西方美學意義上的美學這樣一門學科。西方美學學科建立與獨立雖只是二百多年之事,但從柏拉圖《希庇阿斯篇》就開始專門系統研究美之所以為美,美本體的問題,并以此為核心成為專門的知識,這在中國歷史上本是不存在的。其實,名稱的缺如,決非僅僅意味著一個名詞的有無問題,而是隱在地召示了我們,在中國思想傳統中,也沒有恰合這一名稱的西方本義上的知識、思想與學術。關于美與藝術的思考、見解,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當然有,但是必然因此而建立一門專門的知識學科體系,這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看不出來。中國美學史的合法性何在,終極依據為何,始終是一個問題。何況,以西方美學的種種觀念、范疇、術語來描述中國古代有關美學知識與思想,是否具有普適性,顯然是成問題的。如何才不會對中國傳統思想與知識造成誤讀與曲解,造成削足適履、圓柄方鑿,也同樣是很大的問題。古代美學中如感興、妙悟、神韻、風骨等等大量美學范疇,理論的特質常常是沒法“翻譯”為、闡發為分析質態的現代西方美學知識范疇。那種表面化、形式化的范疇比較研究,實質上只是將中國古代美學范疇簡單化歸于西方美學范疇,而失落了其傳統內涵特有的質態與意蘊。近年來對西方現代美學知識體系普適性與客觀性的質疑與瓦解,也進一步質疑了中國美學史挪用西方美學史研究范式,借用西方美學史理論框架、術語、范疇,來化歸中國美學史中的知識、思想與范疇,也即所謂“對中國美學的概念、范疇、原理等等進行科學的分析解釋”這種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從而也進一步動搖和質疑了中國美學學科本身存在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依據。如何在運用現代美學眼光透視中國美學思想史之時,避免簡單套用西方美學范式、采取西方美學“他者”眼光,從而能夠真正把握住中國傳統美學的獨特品格。清醒地意識到中西美學思想因其孕育時期就走向不同的發展方向,中國美學傳統所思考的美學核心問題與西方美學思想有著極大的區別,因而研究中國美學史應該注意去開啟、敞亮、揭示那些被西方美學“他者”眼光所忽視、遺忘、遮蔽甚至壓抑的中國美學的固有思想(而這也恰恰是獨特思想)便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其二,中國美學史研究既存范式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更為根本的。我們的美學史研究(其實多種學科的歷史研究同樣如此)宣稱歷史與邏輯統一的研究方法,深受黑格爾主義的影響。結果是往往以先在的觀念來邏輯地演繹美學思想的歷史,將歷史文獻的事實,加以邏輯地編織,因而,歷史的維度往往僅具有編年的意義,只是看如何運用歷史文獻去邏輯地勾勒出美學理論、范疇、命題的演進,乃至于規律性的發展了。其實,長期以來,我們的多種“史”的研究也就是這樣寫就,也習慣于這樣的寫法,久而久之,也就仿佛原本應該如此,覺得天經地義了。然而,當福柯的一系列思想史著述開創著新的研究范型,當法國年鑒學派,比如其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的皇皇巨著被譯介過來,展示著不同的研究范型時,我們便不得不對這種習慣的美學史寫法投去質問與懷疑的目光了。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提出思想史的不連續性、形成歷史的“斷裂”的思想觀點,他指出:那些傳統分析老生常談的問題———在不相稱的事件之間建立什么樣的聯系?怎樣在它們之間建立必然的關聯?什么是貫穿這些實踐的連續性或者什么是它們最終形成的整體意義?能夠確定某種整體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連貫。習慣于尋求起源并不斷地沿著以前建立的譜系追溯,習慣于重構歷史傳統,習慣于沿著進化的曲線前行,習慣于將目的論投射于歷史,習慣于不斷地重復生活中的隱喻。因而,正是靠了福柯所揭出的這種傳統的研究方式,將連續性、整體性以及連貫的脈絡成為歷史研究的追求目標,從而使那些思想史上孤立的、四散分離的現象、思想、事件被組織起來,邏輯地編織進思想演進的歷史大網之上,似乎都朝著某種規律性或目的性在演進或進化。使用生物學的模式,演化甚至進化的概念,在單一、有條理的原則下把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聚合起來,融貫成一個連續發展的統一性的思想理路。然而,這并非人類思想歷史的真實面貌,而無疑是研究者通過邏輯編織的,通過話語符碼化構成的一幅臆想的整體性思想歷史的圖景。
受福柯影響而又努力超越解構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新歷史主義學者也同樣強調上述問題。其重要代表美國學者海登·懷特反對各種元歷史的理論假設,指出歷史思辨哲學的編撰使歷史出現歷史哲學形態,并帶有詩人看世界的想象性、虛構性,充滿虛構、想象和加工。雖然我們未必要全盤接收福柯等人的觀點,但至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讓我們質疑那種連續性、進化論式的歷史的真實性,令我們思考:思想史的斷裂現象發生于何時、何處,如何發生,又產生何種效應、影響,令我們對思想史的發展有更為復雜的思考,在思想的連續與斷裂的交互作用下發生的思想史中,尋索其可能的線索與理路。以一種整體性、連續性加以敘述的思想史,還存在著另一方面的問題,這就是無08
論是依據何種“元歷史”假設所建構起來的思想演進的歷史,雖然其描述內部也可能會包含著矛盾、差異、斗爭等等復雜因素,但由于其本質主義的思想傾向與特征,即把同質性、整一性看作思想史發展的內在景觀,思想史家們也總想為種種思想的歷史尋找一種一元化的解釋框架,把握住某種本質,概括出某種規律,從而使其研究具有強力話語的巨大整合能力。而其結果,也就使得遠為復雜的,充滿矛盾與悖論的,缺少目的性與發展向度的思想史的原生狀態被輕而易舉地抽象掉、整合掉了,從而體現出一種對于思想史上的異質性和無法整合到其敘述理論框架中的思想事實和現象的排斥、壓抑、遮蔽的強烈趨向在中國美學史的描述過程中也同樣存在上述問題。例如當李澤厚建立起所謂四大主干的解釋框架來敘述中國美學的歷史演進時,則那些異質性的無法編碼進入到這一敘事框架的思想內容也就被遺忘和排斥掉了。比如漢代神學美學,便是至今仍少有人涉及的一個領域,尤其是有關道教美學這一自六朝以來對中國文化藝術、審美實踐影響極為深遠的思想內容,由于在文化層面、思想體系諸方面都是一種異質性存在,從而根本就沒有進入其研究視野之中。就是對于被納入到其框架中的某些思想理論,比如禪宗美學,也僅僅是涉及外部的影響研究,而難于納入其儒家美學中心論的敘述框架的禪宗美學的“內部研究”則仍然加以遮蔽。
五由此而引出對美學史研究方法另一個方面的質疑,這種普遍性的只剩下幾條理論、命題和幾個美學范疇的由美學思想家們貫串起來的美學史研究模式,能否真實地反映出美學思想實際的歷史過程?法國年鑒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提出了“長時段”的著名理論,他研究歷史的時間尺度,不再是傳統歷史研究中的王朝更替與政治變動,而是緩慢卻又深刻地掩藏于歷史中的生活樣式的變化,從物質生活水平到日常生活中這一更深層、也更基礎的人類的歷史過程。一般知識的發展是緩慢平和的,可能看不到它有什么令人激動人心的場面。正如布羅代爾所指出:“從這個一半處于靜止狀態的深層出發,由歷史時間裂化產生的成千上萬個層次也就容易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靜止的深層為轉移。”正是在這樣一種深層同時又是底層的歷史背景下,支撐著各種思想史的變化、發展、沖突、斗爭,使思想史上的種種奇異、悖論、矛盾成為可以理解的,而思想的歷史一旦脫離了這樣的土壤與背景,也便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文化、歷史語境。在對思想史的新的思考與審視中,福柯指出不同于傳統思想史的研究與視角、對象與方法的另一種思想史的寫法:它講述鄰近的和邊緣的歷史。它不講述科學的歷史,而是講述那些不完整的、不嚴格的知識的歷史,這些歷史歷經坎坷卻從未能夠達到科學的形式。……講述這些縈繞文化、藝術、科學、法律、倫理直至人的日常生活等領域中的影子哲學的歷史;講述數百年的主題史,這些主題從未在某種嚴格的和個體的體系中得到提煉凝聚,但它們卻構成了那些不作哲學思考的人們的自發哲學。同樣,在中國美學史研究中,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研究的范圍并加以擴大,而不是僅限于講述高度理論化了的美學思想,因為以編年史形式確定下來的、高度理論化的美學思想的貫穿,并非就是中國美學思想史的真實面貌與原初圖景———真實面貌與原初圖景要遠為豐富的多、復雜的多———而真正影響了不同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審美趣味、審美風尚也往往并沒有記錄、提煉在這些高度理論化的美學思想之中。我相信蕭統的《文選·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要遠遠超過像劉勰《文心雕龍》這樣大部頭理論。這從《文選》在唐以后的盛行與選學的形成,而《文心雕龍》卻極少被理論家、文學家們提及形成鮮明對照。而《文心雕龍》成為顯學,又形成龍學,則是相當晚近之事。是在近代知識型轉換背景下,西方美學“他者”眼光刺激下對中國傳統美學再發現的產物。而像王夫之的理論著述就更是屬于后人挖掘的,在當時,王氏在深山中所寫的東西又有幾人能夠讀到呢?錢鐘書便曾指出:詩、詞、隨筆里,小說、戲曲里,乃至謠諺和訓詁里,往往無意中三言兩語,說出了精辟的見解,益人神智;把它們演繹出來,對文藝理論很有貢獻。……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罷。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銷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而未失去時效。……往往整個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脫離了系統而遺留的片段思想和萌發而未構成系統的片段思想,兩者同樣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長篇大論,瞧不起片言只語,甚至陶醉于數量,重視廢話一噸,輕視微言一克,那是淺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懶惰粗浮的借口。
正如美國學者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所指出的:近些年來已經在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假設和方法方面發生了范式危機,“這次危機以發端于人文科學的后現代侵擾為基礎。”而由上述理論思考,我們切實地感受到了這場危機對于美學研究的基礎性范式所帶來的范式危機。雖然我們并不完全贊同福柯、新歷史主義等思想家們的理論、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理論、觀點的確揭示了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與缺欠、甚至基礎性錯誤,也促使我們尋找新的、可行的基礎性假設與方法,以建構新的合理的研究范式。
反觀中國美學史研究,我們認為,在討論中國美學問題時,需要重建更為復雜的歷史敘事:
一、連續性(深層)與斷裂性(表層)問題:不僅應當研究建立于血緣宗法社會與內陸型農業文明構成的連續性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上的中國美學史的基本精神的連續性問題,也應當研究由于既有思想意識形態體系崩潰(比如漢末)或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元王朝)等因素導致的美學思想發展的某種斷裂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問題;
二、不同體系及其關系的思考:宏觀而言比如儒、道、釋美學思想體系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相互關系。中觀而言,儒、道、釋美學思想體系從來就沒有過千古不變的同一的思想,各個派系之間,居于主流和處于邊緣的思想之間,甚至在主流與異端思想之間都存在著極為復雜的情況,都需要做細致的梳理;
三、異質性的美學思想及延續:美學思想史的研究,應當回到美學思想的原初歷史景觀中去,直面美學思想原初復雜的、不可化約的,呈現為碎片、沖突的、悖論式的思想圖景;
四、不同層面的美學思想、觀念、趣味、風尚研究:思考歷史上不同層次的美學思想,并為了更切近美學思想的歷史真貌而增加不同的層次性研究,像荒誕不經的神話,考古出土的遠古各類器物、甲骨、青銅、秦磚、漢瓦,佛教的石窟造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說……往往能反映出特定時代的某些普遍觀念、心理與時尚;五、形成上述諸方面的原因、結果、社會效應及影響:探索那些孕育、影響、制約并使中國美學的基本精神延續存在并不斷演化的文化心理、思想學說、知識背景、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社會結構、權力話語等一些以往中國美學研究中未能涉及的深層次問題。溝通思想史與社會史,在文本與語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釋美學思想的歷史,不僅研究美學思想文本的意義,而且進一步分析它所賴以產生的知識生產的主體、結構、體制和功能,美學思想的傳播與接受等等。由此,我們可以期望更能貼近歷史真實的對中國美學思想的發展輪廓加以描述、闡釋、顯現與揭示的中國美學史的誕生。
參考文獻:
①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譯,第2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參見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王杰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③《福柯集》,杜小真編選,第104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參見華勒斯坦等著:《開放社會科學》第一章,劉鋒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
⑤鮑桑葵:《美學史·前言》,張今譯,第2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⑥李斯托威爾:《近代美學史評述·序言》,蔣孔陽譯,第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⑦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王天清譯,第25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⑧吉爾伯特、庫恩:《美學史》,夏乾豐譯,第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⑨塔達基維奇:《西方美學概念史·前言》,褚朔維譯,第1頁。學苑出版社1990年版。
⑩參見呂澄:《美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呂澄:《現代美學思潮》,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陳望道:《美學概論》,民智書局1927年版,范壽康:《美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等。
劉方:《百年美學:現代與中國傳統》,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中華書局1984年重印本,第1頁。
《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冊第539頁,第54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緒論》第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第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發展史·序》,齊魯書社1987年版。
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第13頁。
參見劉方:《現代建構中的承續與轉換》,載汝信、王德勝主編《美學的歷史:20世紀中國美學學術進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版。
對黑格爾主義的分析、批判,參見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陸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貢布里希:《理想與偶象———價值在歷史和藝術中的地位》,范景中等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等譯,第2、14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譯文參用《重新解讀偉大的傳統》,第10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參見White,TropicofDiscourse,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8。
李澤厚:《華夏美學·前記》,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參見劉方:《詩性棲居的冥思———中國禪宗美學思想研究》,導言,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等譯,第18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
福柯:《知識考古學》,第173頁。
錢鐘書:《七綴集》,第33-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詳參見劉方:《錢鐘書與20世紀中國美學》,載《文學前沿》No.1,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張國清譯,第10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
- 上一篇:區委常委會科學發展觀活動方案
- 下一篇:室內設計中的古董陳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