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北村宗教小說
時間:2022-08-25 11:35:00
導語:略論北村宗教小說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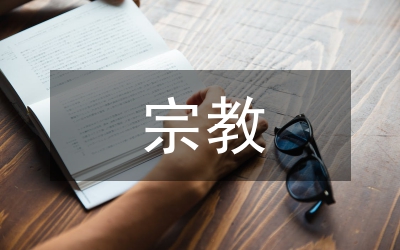
內容摘要:“先鋒作家”北村1992年以后的寫作通常被稱作“神性寫作”。他立足基督的信仰,力圖傳揚上帝的救贖和永生之道,宣揚圣經“神圣啟示”的權威性和唯一性。本文通過對北村后期小說的介紹,試分析基督教文化在其小說中的體現。
關鍵詞:北村小說基督教救贖
北村是當代文壇一位“重要的作家”(南帆語),他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壇,以一系列挑戰傳統小說創作理念和表達方式的作品引起人們的注意。北村也因此與余華、蘇童、格非等一同被稱為“先鋒作家”,他的初期小說,如《諧振》、《逃亡者說》、《歸鄉者說》、《劫持者說》、《披甲者說》、《聒噪者說》、《陳守存冗長的一天》等專注于技術形式的實驗與創新,設置小說語言的迷宮,迷亂讀者眼球的同時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一個被商品和技術置換的生存空間,文學首先面臨的是來自生存領域的尖銳詰問:你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存活?[1]反映社會人生的文學作品究竟該寫什么?怎樣寫?它們有什么意義?
1992年3月所發生的對北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精神事件,他在廈門受洗歸入基督。北村自述,“1992年3月10日晚上8時,我蒙神的帶領,進入了廈門一個破舊的小閣樓,在那個地方,我見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揀選了我。我在聽了不到二十分鐘福音后就歸入主耶穌基督。”3年之后,當他談起這段神圣而奇妙的經歷時,他仍然說我可以見證“耶穌基督是宇宙間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2]可見他對基督耶穌是神的絕對地信與敬畏。
自皈入基督教,北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義,他的創作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作品不再沉迷于聒噪而是轉向神性書寫,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及生命的焦灼狀態、并渴望從中解脫出來的生命訴求。
信與寫
北村深信耶穌基督是個人生命中惟一的救贖者,他認識到“人活著是有意義的,沒有神人活著就沒有意義,”[3]在這樣的信心里,他以“一個基督徒的目光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創作了《施洗的河》、《張生的婚姻》、《瑪卓的愛情》、《孫權的故事》、《傷逝》等一批宗教小說。這些小說在主題上都有著相似性,那就是注視人類的精神困境和出路,追問存在的意義。北村改變以往的敘事策略,不再執著于“先鋒”語言技術革命,而是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把所看見的現實記錄下來。[4]他的小說里容涵了許多的生活意象和片斷,如逼仄的生活空間,混亂的醫院,骯臟的病房,出版社給編輯分配草紙,上漲的肉價,,卡拉OK,審訊的場面等等。但北村決不停留在新寫實作家的創作階段,允許他的小說主人公在自我安慰中妥協于這些塵世意象。北村所設置的小說情節終要將主人公逼上絕境,迫使他們在精神困境中明確回答:為什么而活?
北村認為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絕不是愛情,名利、地位、財富的獲得,也不能在投身于藝術中得到生命的滿足。中篇《瑪卓的愛情》中,美麗而多才多藝的瑪卓在學校被多名男生暗戀,而平凡不起眼的劉仁卻用晚上借著手電筒寫出的一千多封情書打動了瑪卓的心,他們由此進入婚姻。然而奇怪的是,婚后他們才意識到:他們并不知道如何去愛。他倆的愛情只表現于那一千多封情書。劉仁可以在單相思的夜晚每日借著手電筒寫情書,一次又一次將強烈的愛寄于筆端,在結婚的當晚卻說不出一句“我愛你”,他們不知道如何與那個真實的妻子或丈夫相處,不知道如何面對一個逐步展開的人。瑪卓在看情書中誤解愛情,以為對方給自己寫了那么多封情書,這就是愛了。劉仁在寫情書中想象愛情,以為瑪卓就是他愛情的寄托。在現實生活中他們都是不懂得愛的人。失去了本真之愛的婚姻生活如同監獄,使人時時想逃,劉仁終于找了個借口:瑪卓的短褲破得像漁網一樣,并逃去日本賺錢。瑪卓認識到再多的金錢也挽不回愛情與婚姻,在到達日本車站時投身車輪之下,在她周圍,是那一千多封情書在飄散。《傷逝》寫一名渴望愛情卻不斷受到傷害的女主人公——超塵自殺的故事。超塵對物質沒有太多的需求,她生命中只有一個愿望——得到愛情,這是她婚姻的基石,也是她賴以生存下去的理由。她讀書時期喜歡的李東煙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卻在一次莫名的跳樓自殺未果之后消失,而現在的丈夫張九模趁機苦苦追求超塵并順利地與她結婚。婚后張九模很快露出自己的丑惡嘴臉,唯物質是上,言談舉止俗不可耐,對超塵也無應有的尊重,并懷。超塵仍將獲得愛情的希望寄托在消失的李東煙身上。一旦李東煙出現,即使是對她多番利用,超塵也心甘情愿。無奈李東煙早已不是當年的才子,他是個沒有目標,失去了生活方向的人,頹廢,卑鄙,殘忍,他活著也只是肉體活著,對超塵所做的一切利用也只是為這殘存的肉體。當超塵小心翼翼地問他當年為什么自殺時,他迅速地再一次從樓上跳了下去。超塵出于困惑的提問迫使李東煙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就像在讀書時期一樣,他仍然沒有想通自己為什么活著,死是必然的結果。超塵跟初戀情人有來往的事情被張九模知道后,張九模在超塵的單位當著眾人的面毒打超塵,并出言侮辱她。超塵在認識到愛情的幻滅與婚姻的丑陋后割腕自殺。
超塵、張九模、李東煙、瑪卓、劉仁,還有《周漁的火車》中的周漁,陳清……北村塑造的這些主人公有的愛人,有的被愛,對愛情的追求是很多現世之人所當成的人生的追求。然而從人而來的愛畢竟有限,“人只有殘缺的情感,這就是離開了神之后的人性的缺陷,人既沒有愛的內容,也缺乏愛的能力。文學離開揭露人性的缺陷就沒什么意義。如果非但不指證罪惡甚至給它一個接受的態度,那就是背德了。至少,詩人必須有哀哭的心。”[5]北村以一顆哀哭的心,將超塵、瑪卓等人的生命指向絕望。人只有獲得基督之愛的能力,愛才是完全的。無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世人舍身,這是一種犧牲之愛,是在自我的意愿之下的自由付出。“愛是神的專利和基本的性情。”[6]
有的人在精神的空虛面前,以追求名利、地位、財富來肯定自己。北村同樣指明這條道路的不可行。“我們這代人(60年代出生)要承受時代變遷之苦。前代人(60年代以前出生)的生存沖突主要表現在人生的境遇中,他們的疾苦就是所謂的遭遇之苦;而我們這一代人的苦不是表現于生存的遭遇,我們這代人既沒有階段斗爭之苦,沒有受饑餓之苦,沒有勞作之苦……但我們卻承受了存在之苦。前代人的痛苦可以通過改變生存境遇而解除;而我們這代人的痛苦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的,他的痛苦是存在本質的痛苦。前一代人想改變命運,而我們這代人卻是充滿了對生命的厭倦”。[7]人對生命的厭倦,存在本質的痛苦并不能從塵世的事業中解脫。《消失的人類》中的孔丘事業有成,妻子賢慧忠貞,外面還有女人熱戀著他,在商業競爭與世俗生活中,孔丘戰無不勝,所向披靡,是一名典型的成功人士。他在令人羨慕的生活中仍然感到了莫名的空虛,不明白“活著到底是為了什么”,靈魂在現實的困惑中找不到歸依之所,肉體的存在也就毫無價值。《施洗的河》里的劉浪也是如此。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罪人,惡人,殺人,搶女人,無惡不作。經歷一番爭搶打斗,劉浪繼承了財富,又成為蛇幫幫主。正在這金錢和名利都收獲之時,劉浪陷入了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些什么了。他嘗試以抽大煙,探訪老朋友等方式打發時間,告別空虛。這些都無法驅遣他內心的孤獨、絕望。劉浪曾經在樟板這個地方為所欲為,他有充分的自由選擇得到什么,丟棄什么。極度的自由換來的是極度的空虛。劉浪即使是住進墓穴,人對終極意義的思考及對解救之道的渴望依然如影隨行。活著即是痛苦。在揭示人生的苦痛之外是北村一顆憐憫的心,他希望世人能明白人生是痛苦的,但信仰是可以超越苦痛的。北村說,“我不過是站在良心的立場上寫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難和尷尬,但這并不是說我本絕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著有暗一樣,你若退出光明就必進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視,但不意味著接受它,而是給它一個良知的態度。”[8]
罪與拯救
“對苦難的揭示是我的小說承擔的責任,圣經說‘在世間有苦難’,所以我不明白小說除了發現這種人類的悲劇之外還能干什么。”[9]北村從自己的信仰出發,揭示人類的悲劇,并指出造成這些悲劇的原因——罪。“人類在伊甸園子里起先犯了一個很清潔的罪,吃了那顆果子,神明明那么絕對和肯定地告誡人不得吃善惡樹的果子……人棄絕了神的愛,起首走上了一條背逆的路。”[10]圣經對罪的定義并不單指世俗間法律意義上的殺人、放火、打劫,罪乃是人里面的自私、詭詐、驕傲、論斷等等一切劣根。周漁對陳清的愛有極度自私的一面,她按自己的訴求來要求陳清,束縛陳清,使陳清在她面前活得完全不是自己,并終使陳清承受不了“我不是我”的壓力發生婚外情。李東煙也十足是個社會的“零余人”,他滿口所謂的個人理想,要如何如何,卻終日碌碌無為,誘騙他人,欺誨愛他的超塵。劉浪就更不用說了,他做盡惡事,毀滅他人的同時也毀滅了自己。在北村的小說這里,我們看到罪所帶來的精神危機,罪使人與愛隔絕,罪更帶來死。“我們必須正視人的罪惡及其在文化中的后果。”[11]一個有罪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拯救的,也不能自以為義。罪人得拯救必須得是在一位真神面前悔改,并求他來指引自己的人生道路。北村筆下的人物除了死,另有一些得蒙神的光照,信主皈入基督并由此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劉浪在痛苦絕望之中遇到了一位“圣經女孩”,受到她的言語啟發之后找到了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人的有限,認識到以前的自己實在是個罪人。他在神面前徹底悔改,仿若重生。“因信稱義”,信是前提,行為是結果。信帶來行動的改變,劉浪的悔改并不只是表現在言語之上,也表現在行動之上,他愛人如己,并努力向自己的仇敵馬大傳福音,使他也有獲得新生的機會。在看到人生有那么多的悲劇之后,罪人重生所帶來的良善與愛給人多么喜悅的溫暖!
除了劉浪,《張生的婚姻》中的張生在愛情的困惑之中讀了福音書信主,《孫權的故事》中的孫權是個蠅營狗茍的人,從不知道活著是為了什么,直到住進監獄,受到一位楊兄弟的啟迪,不僅開始了更積極的人生,也在獄中為自己的情敵禱告。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我所期待的拯救者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穌,我不能否認這個神圣啟示。”[12]
北村的一系列宗教小說常給人宣講福音的僵硬之感,對于不信的人來說,“苦難——絕望——拯救”的主題單一模式會讓人產生審美疲勞。作為作家與基督徒雙重身份的北村一直追求一種真誠與良知的寫作,他的創作在1992年3月之后的轉型正是以自己的切身體驗抵制這個時代的價值淪落。“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們的時代更為顯目。這些作家未必擁有大師的精湛和成熟,他們的意義首先體現為——劈面與這個時代一批最為重要的問題相遇。他們的作品常常能夠牽動這一批問題,使之得到一個環繞的核心,或者有機會浮出地表。換言之,人們可以通過他們的作品談論一個時代。”[13]
- 上一篇:深究共創性美術教學
- 下一篇:透析從篡位君王形象看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