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民族化與本土性論文
時間:2022-11-18 06:06:00
導語:美學民族化與本土性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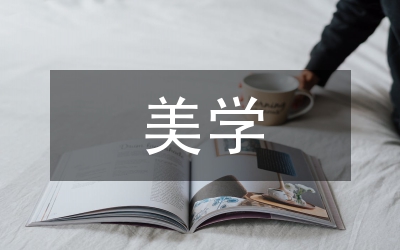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研究學科,美學在中國已有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百年時間不可謂短,然而迄今為止,中國的美學研究從基本觀念、概念范疇到體系構架卻基本上依然都是從西方輸入過來的,只是從作為印證觀點的部分藝術實例和少量中國美學思想史研究中才讓人依稀感覺到一點點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跡,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國美學的歷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學在中國”,而“美學的民族化”卻仍是一個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實現的理想。這種狀況自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今,從這樣的起點上展望未來,人們于不滿足之外又多了幾分焦慮,因為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學術的民族化包括美學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應該說,如果我們繼續因循著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慣性運動,繼續追隨在西方學者后面鸚鵡學舌,做學術上的二道販子,從而把學術領域里的全球化語境理解為并實際地弄成單向的西化取舍與被動摹仿,美學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為一個水月鏡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對全球化有一個正確的對待,對美學研究與民族發展和本土文化創生之間的內在關聯有一種深切的理解和正確的處理,真正找到美學研究與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聯結通道,美學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為現實,就可能結出我們所期望的豐碩理論果實。對中國美學來說,最終是收獲苦澀還是收獲喜悅,全然取決于我們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經濟領域里資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動與擴張為動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確來勢洶涌,將所有的國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為一種歷史發展趨向絕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西方化,僅僅是世界向歐美中心的向心化運動。英國學者齊格蒙特·鮑曼在其《全球化》一書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預期的全球性效應,這種全球性效應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傳達的最深刻的意義就在于世界事務的不確定、難駕馭和自力推進性;中心的‘缺失’、控制臺的缺失,董事會的缺失和管理機關的缺失。全球化其實是喬伊特的‘新的世界無序’的別稱。”[1](p.57)因此之故,“全球化過程缺乏人們所普遍認為的效應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聯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亞于它的聯合——分化的原因與促進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現全球范圍的商務、金融、貿易和信息流動的同時,一個本土化的、固定空間的過程也在進行之中。”[1](p.2)這就是說在全球化的同時,也伴隨著本土化的運動。鮑曼是從全球化的消極后果角度談論這一問題的。在他看來,在全球化進程中,由于技術因素而導致的時間/空間距離的消失并沒有使人類狀況向單一化發展,反而使之趨向兩極分化,它把一些人從地域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他們史無前例的自由,成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卻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壞了這些人傳統上由與他人的時間與空間距離所造成的與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親合性聯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虛癥。因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處于本土化,就成為被社會剝奪和貶黜的標志。
撇開鮑曼對全球化的某些消極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當不論,鮑曼的全球化理論言說其實是很有啟發性的。首先,以經濟一體化為基本動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新的以歐美為中心的單一世界秩序的建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世界各國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經濟利益和發展目標,最終的全球性的效應是由不同利益主體既相互依賴又相互沖突的互動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著建立多極世界的可能,意味著不同利益主體多元存在、能動創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純粹是一個超國界、去民族化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依然有一個國家主權與國家責任范圍內的民族利益問題。其次,全球化與本土化是當代世界發展的一體兩面,是一個趨向相逆的矛盾運動過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觀時我們應該有一種基于民族本位立場的本土化關懷,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關問題時又應該有一種基于全球化視野的世界性互滲、互動的眼光,這樣理論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絕對化。
從這樣兩個認識前提出發,對近來人們關注頗多的美學與文學研究的民族化問題,我們當會形成一種更具時代意味的理論自覺,獲得更為明晰的理論言說語境和問題分析構架。既然全球化不純粹是一個去民族化的過程,還有一個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問題,因而美學研究的民族化問題就不是那個理論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話語生成的現實基礎,不存在是否狹隘與保守的問題。那種認為全球化語境下的美學和文學研究只有摒棄理論話語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體說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認可的話語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才有出路的觀點是片面的。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夠向全人類說話,我們不懷疑那些倡導用世界通行的話語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的學者是懷有這種追求的。但是任何有價值的對世界學術有所貢獻的理論話語,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學研究也不例外。通觀古今美學思想的發展歷程,真正有價值的世界性美學話語,如古希臘的美學、德國古典美學、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美學、現代歐洲的存在主義美學和英美的分析美學等等,無不帶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與世界性眼光與胸懷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學而后才有望提升為世界性的美學。而那些企圖抹去民族的印記和痕跡,一味跟在西方學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謂美學研究,雖有一種所謂“世界性話語”的眩人名份,究其實卻不過是重復與模仿別人的“世界性”,與自身的創造是毫無關系的,通常也是沒有學術生命力的。
鑒于上述的認識,當前我們應該在理論層面上形成這樣一種自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強調美學的民族化建構從消極意義上,是要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而可能帶來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趨同現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單向文化趨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樣才顯得豐富而多彩;從積極意義上,就是要努力確立和保持中國美學和文學研究的獨特民族身份,并藉由這種身份而在世界美學和文學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結束西方美學在中國單向的擴散狀態,從而在美學的世界性建構中也融入中國美學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論貢獻,在中外美學的交流中既拿來又輸出。既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我們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沒有被時代大潮所淹沒,那么我們也應該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學研究中會做得同樣好。
在以往的中國美學研究中,人們通常是用一維的歷時性時間尺度評價和認識民族性和現代性問題,把民族性等同于傳統落后的東西,把西方的美學等同于現代進步的東西,認為用西方現代的東西取代傳統上民族的東西是學術進步的必然;而現在,我們把民族性的追求作為全球化語境下美學現代性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把民族性與世界性共時性地置于新世紀現代美學的建構目標之下,這應該說是對以往研究心態與思路的一個根本性的超越和轉換。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應該選擇怎樣的美學發展策略,如何在美學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學的互識、互滲、互動與共建呢?對此,學界已經提出了不少有見地的意見,并做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嘗試。比如有人主張暫時借用西方的話語與之對話,并不時向西方學者介紹和宣傳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輝煌遺產,同時加進一些本土的批評話語,使他們在與我們的對話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啟迪,以達到積極介入國際理論活動和爭鳴,發出中國理論家自身的聲音之目的[2]。也有學者認為,在全球性的視野中,應充分而深入地探討傳統中國美學思想的特性和歷史存在形態,通過本土學術資源的現代轉換,找到對外進行平等有效的學術溝通的“對話性”的基點和根據,促成中國美學在新世紀具有世界性的現代學科建構[3]。這里,前一種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后一種主張是吸取傳統的營養以健全現代的肌體。兩種思路都著意在中國美學的現代性建構中凸現民族化問題。從中不難看出,將美學研究的民族化追求與全球性視野有機地結合起來,基本上已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過,以上兩種主張,基本上還只是一種宏觀研究理路上的考慮,具體到美學民族化的建構來說,則尚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比如說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話語呢,美學話語又是如何獲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說本土傳統的學術資源是如何獲得現代轉換的動因的,又是如何獲得進入現代中國美學學科建構的“歷史的現實合法性”的呢?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許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問和探討。只有通過這類追問和探討,本土性話語才能逐漸地凸現出來,民族化的美學才有望被建構起來。換言之,在大的發展理路明晰之后,問題意識的確立,尤其是與全球化進程相關聯的本土性問題的叩問和凸現,又成為中國現代美學學科建設走向民族化的關鍵所在。
我們知道,任何一門理論學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支撐其體系構架的,學科發展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歷史,也就是新舊問題叢生與延伸、交替與更迭的歷史。而問題生成與解決的歷史即是理論生成與發展的歷史。鮑桑奎在其《美學史》中經常用“美學哲學的問題”、“美學問題”之類術語,并有諸如“近代哲學的問題”、“康德——把問題納入一個焦點”、“美學問題在他的體系中的地位”、“為什么審美判斷是美學問題的解答”等提法,這里的所謂“問題”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說“問題”的理論本身而言的。可見,問題與理論實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通常我們常說某人的學術研究有新意和創見,實際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夠提出自己的理論問題或者能夠對業已存在的問題提出有創見的解決思路和辦法。因此,問題意識對學術的發展是必須的,是學術理論向前推進的內在動力因素。美學研究亦復如此。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臘美學、德國古典美學、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美學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響,在美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隱含了各自獨特的美學問題,而且這些美學問題又都不完全是從抽象的思辨與玄想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美學家們各自身處其間的民族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處境中孕育和誕生的。然而在很長一段時期里,當我們的學者追隨著西方美學家的思想理路,運用著由他人那里摭拾的理論話語進行美學的研究時,卻恰恰忘記了從自身生存處境生成的問題意識對美學研究的重要性。學術界所謂中國美學與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失語癥”正是與自身問題意識的缺失緊密相關的。就此而言,盡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學研究有時顯得很熱鬧,很有學科建設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學而言美學的基本傾向,且過分地流入對美的本質之類形而上學問題的抽象思辨(雖然這種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較少與民族的生存處境及文化創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動人和吸引人的,不能讓人經歷一種文化創生的痛楚與喜悅。因而在與時代、人生與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動方面,比起上世紀前半葉王國維、梁啟超、魯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學研究開端期的作為來就遜色得多。20世紀初葉,當王國維等人篳路藍縷,在傳統學術的園地里開拓美學研究的新路時,是頗具問題意識的。王國維痛感于國勢衰微、民心不振的“當時之弊”,而倡導美育,以為形成“完全之教育”、培養“完全之人物”之助;魯迅痛感于中國因個性不張乃成沙聚之國的現實,而向國人推介“摩羅詩派”,鼓吹浪漫主義美學精神,倡導“立人”的教育;梁啟超針對當時學校情、意教育的缺乏和知、行割裂的現實,而鼓吹以“新民”為旨歸的“情感教育”;蔡元培則針對袁世凱封建復辟以后社會上宗教活動的猖獗而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從王國維到蔡元培,他們之所以于美學領域特別突出和推重美育,正是強國新民的時代性民族吁求使然。王國維曾經撰文期望以美育來祛除國人篤嗜鴉片和嗜于“利”與“官”等種種卑劣之嗜好,治療由此引生的精神上的空虛,這在有些人看來可能覺得太功利化,太不具有高深的理論品位了,然而從其用心和動機中我們卻分明感覺到其美學思想中那種對于民族生存與發展深切動人的情感關懷,體會到一種活力充盈沉實渾厚的思想力度。可惜的是,中國美學研究早期所具有的這種從民族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出發,勇于探索與叩問本土性問題的理論品質在后來卻漸漸弱化乃至消失了。這恐怕是中國美學至今沒有形成大氣候的一個根本性原因。今天,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互依共生而又沖突背反的時代語境之中,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要想真正獲得充實的內容、活潑的生機,獲得參與世界性美學對話的主體資格,回歸王國、蔡元培們的上述美學研究思路,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可喜的是,最近幾年中國美學研究中已有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意識,這突出地表現在圍繞實踐美學的理論缺陷而展開的相關討論以及對近二十年來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大眾審美文化有關問題的研討。問題意識的增強,使新近的中國美學研究逐漸突破了舊有美學的研究格局,而顯示出了一種新的生機與活力。應該說這兩方面的美學討論都是從我們自己的美學研究現狀和審美文化現實出發的,有較強的理論針對性,同時又有一種世界性的眼光,能夠從西方現代美學成果中大膽地有所借鑒和吸取。不過,從更高的要求來看,對中國美學的研究現狀我們還是感到不滿足。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的美學研究與民族生存與發展之間的關聯還是不夠緊密,對全球化進程中與本土化相關的諸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問題缺乏足夠的敏感和關懷。以實踐美學問題的討論來說,有的同志提出要以審美自由的超越性糾正實踐美學偏于理性蘊含和物質活動的缺陷,有的同志則主張以生命美學取代實踐美學作為美學的新方向。實在說,主張美學的自由性、超越性及其生命根底的確有其理論上的合理性,然而總的來看,這些新的美學理論主張依然給人凌空蹈虛的感覺,與中國人當下的社會實踐和民眾生存缺乏有機的聯系,理論問題的言說依然盡可以在純理論層面上操作而無須涉及現實人生向題,從而就只能停留在極少數人感興趣的純學術層面,而不能播散到更廣大的社會群體和文化創造領域里去。就當代大眾審美文化研究來說,雖然比之以往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理論收獲,但此類研究基本上也是借用他人的理論武器,對問題的言說沒有超出國外同類研究已有的廣度和深度,很多研究就像是他人成果的克隆,至于說新崛起的大眾審美文化究竟在中國文化的當代轉型和當代中國人審美理想的建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和中國人精神文化心理的塑造會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在全球化時代中國本土審美文化的特色和優勢究竟何在,未來的前途又是如何,如此等等,這類問題,我們的確還較少看到既具有強烈問題意識又具有特立獨行的學術識見和理論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美學研究也是如此,關在書齋里做學問,對國人當下的生存處境和生存問題觀察不夠、體驗不深,因而缺乏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問題意識,可說是一個通病。比如說,對生活在現代都市底層的人們,對農村里的廣大農民,且不說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界,就是以人文關懷自詡的中國學術文化界包括美學研究工作者又有多少人真正給予他們以人文關懷,對他們的生存處境、精神世界,究竟又有多少了解?美學家們樂于抽象地談論基于生命意識的審美自由,可審美自由的暢想往往正是從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產生出來的。我們為現代化歡呼,為全球化的到來而激情涌動,但天下從無白赴的盛宴,現代化的實現,全球化的到來是要以一些人的血淚和犧牲為代價的。美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懂得這些道理,并且應該勇于從自己個人的生命體驗和理性之思中切入這類與美學研究相關的問題。一味地躲在象牙塔里做學問,是永遠也產生不了具有時代氣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論成果的。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語境中,追求美學研究的新氣象、新境界的學人,萬萬不可忘記了對自身生存其間的本土性問題的叩問。這是時代賦予新世紀美學學科建設的一個使命。中國美學的未來發展前景,美學民族化的實現程度,都與這種叩問的廣度和深度有著直接的聯系。
參考文獻:
[1][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后果[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王寧.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文學理論的國際化[J].文學評論,2001,(6).
[3]王德勝.清理與轉換:本土學術資源與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J].北京社會科學,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