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的發(fā)展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18 09:24:00
導語:舞蹈的發(fā)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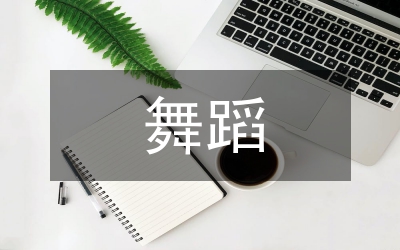
【內(nèi)容提要】一種舞蹈在生成之后能否發(fā)散甚至兼融,能否拓展自己的疆域并使自己長存,取決于它是否具有功能與觀念上的合理性和包容性,取決于隨著功能與觀念變化而產(chǎn)生的審美變化。本文以佛舞文化圈中的藏傳佛教舞蹈為個案,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分析與闡釋。
【關鍵詞】舞蹈文化圈/發(fā)散與兼融/功能與觀念/羌姆主題的孔雀舞/審美。
【正文】
一、漣漪狀的佛舞文化圈
1.身體人類學
釋迦牟尼在《般若經(jīng)》中對佛法在世間的傳播作出預言:我涅槃之后,此般若經(jīng)將從印度向南方傳播,此后將從北方再向北方傳播。印度次大陸的東南西面面臨無邊大海,而北方則是人口眾多的廣闊大地,遵照佛陀的旨意,小乘佛教的布道者穿過孟加拉的森林沼澤進入緬甸和中國的云南。大乘佛教則一路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進發(fā)新疆;另一路爬過喜馬拉雅山的茫茫雪原進入雪域西藏,并再向北方蒙古、向東南的中國中原、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傳播,最終成為亞洲大陸傳播領域最廣的宗教。與之相伴隨,作為弘揚佛法的佛教舞蹈也因其功能和觀念上的巨大兼容性變得流布廣遠,色彩繽紛,成為亞洲乃至世界藝術的一大景觀。
與繪畫、音樂、雕塑不同的是,佛舞的流布與色彩是用身體的媒介實現(xiàn)的,是靈肉一體的特殊的文化與審美的呈現(xiàn)。
1977年,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約翰·布萊金編輯出版了《身體人類學》,將人類學劃分為體質(zhì)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傳統(tǒng)二分法打破,論證了二者的一體化:“社會性的身體制約著生物的身體被感知的方式。由于身體的生理經(jīng)驗總是被社會的范疇所調(diào)節(jié)修飾,因此它確認著一種特殊的社會觀點。在這兩類身體經(jīng)驗之間的持續(xù)的意義交換,使得每一方都會強化對方的范疇。作為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果,身體本身就成為某種高度限定的表現(xiàn)媒介。”布萊金強調(diào):“真正的學問是從全部的有意識的肉體產(chǎn)生出來的,不但從你的腦里和精神里產(chǎn)生出來,而且也從你的肚里和生殖器里產(chǎn)生出來。”①布萊金的同胞、愛爾蘭踢踏舞王弗萊利從舞者的視角印證了這一點:“我的血液中流淌著愛爾蘭人的鮮血,祖先將音樂和舞蹈的基因埋藏在我的身體之中,正是這些因素,讓我完成了《大河之舞》,也正是《大河之舞》的成功,讓我更享有超越的機會,《王者之舞》就是這種超越的結果。歷史上的愛爾蘭不斷地被外族侵略,我們的人民沒有權利表現(xiàn)自己的歡樂,即便是舞蹈的時候手臂也只能放在身體的兩側,但是現(xiàn)在愛爾蘭的文化已經(jīng)遍布世界各個角落,我們就要釋放自己的激情,讓所有人都感受到愛爾蘭的文化。”②
從現(xiàn)代的愛爾蘭踢踏舞反觀傳統(tǒng)的佛教舞蹈的生成、發(fā)展和變化,亦同此理,只是佛舞來得更加久遠、闊大和深邃。
2.從中心輻射
宏觀地審視佛教舞蹈的發(fā)散與兼容,我們可以看到一組漣漪狀的佛舞文化圈。
這一文化圈最初以印度為激起漣漪的中心,此后向北向東北擴散。東北面的上座部佛教(小乘)一路往由緬甸東南亞一帶落腳于中國的云南,而后又向中原,與儒道兼容而成漢地佛教一支。北面一路一取絲綢之路穿入中原;一取西藏為落腳之地,形成了中國大陸佛教舞蹈的風格分布光譜:西南部以優(yōu)美輕柔為主而不失肅穆;西北部以獰厲粗獷為主而夾以飄逸;中原地帶則被雜糅為光怪陸離。
為了集中論述,我們在這里只抽取中國佛教舞蹈文化中“藏舞文化圈”的構成、發(fā)散與兼容作為個案進行分析(見圖)。藏族學者扎路先生有《菩提樹下》一書,勾勒出了藏族佛教的建構與發(fā)散:其核心區(qū)域是以山南、拉薩為中心的衛(wèi)藏地區(qū)。這里不僅是藏族古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也是佛教的最先立足之地和佛苯之間最早的碰撞之地。在現(xiàn)實生活中,突出表現(xiàn)為全民信教、政教合一。這些文化因素高度成熟的狀態(tài),表明藏傳佛教文化在功能和觀念上具有由這個中心向外呈波浪式輻射的力量。
藏傳佛教舞蹈的構成、發(fā)散與兼容圖示
內(nèi)層區(qū)域主要指青藏高原上以藏族聚居區(qū)為主的廣大區(qū)域,這一區(qū)域的藏傳佛教文化是在吐蕃時期隨著統(tǒng)一大業(yè)的完成而播及的,是文化圈內(nèi)最早的傳播區(qū)域。內(nèi)層區(qū)域實際上是擴大了的文化中心,它在文化圈次層區(qū)域的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次層區(qū)域是指在青藏高原周圍從高原向平原過渡的山地丘嶺地帶,如北方的土族、裕固族、西夏古國,東部的羌、納西、普米、怒、傈僳等族,其歷史在11—14世紀時都不同程度地處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古老的原始文化尚未解體,在急劇變化著的歷史中接引了藏傳佛教。外層區(qū)域是指廣袤的蒙古草原和中原漢地,在這一區(qū)域,政治上的劣勢地位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使藏傳佛教文化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這也預示著在外層區(qū)域藏傳佛教文化更易受到其他文化的挑戰(zhàn)和取代。從整個藏傳佛教史來看,它的向外傳播經(jīng)歷了三次大的高潮,即:吐蕃時期、藏傳佛教各大宗派形成時期以及格魯派建立之后。這三次大的傳播高潮使藏佛教文化在空間上獲得了巨大的拓展,自西藏向四周遞減形成了三大層次區(qū)域:內(nèi)層區(qū)域、次層區(qū)域和外層區(qū)域。③
“以舞傳佛”和“佛舞一體”的藏傳佛教舞蹈文化圈在時空上也是這樣構成的,這在“敦煌舞”的舞姿、西夏舞蹈的特征、“羌姆”的生成與變異、“密宗”舞蹈由宗廟而宮廷化以及“孔雀舞”所顯示的不同形態(tài)等舞蹈現(xiàn)象中均可見出。當初,印度教的再興和伊斯蘭教東侵,使印度佛教最終不再成為印度的主流文化,一部分佛教徒帶著佛經(jīng)和佛舞走進喜馬拉雅,以藏傳佛教為后盾,劃地固守。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在態(tài)勢上主張和平、慈悲避世的佛教及其舞蹈比處于攻勢的伊斯蘭舞蹈更豐富多彩且疆域廣大。中國之外,其時空一直擴散到日本的“能樂”、韓國的“僧舞”和美國現(xiàn)代舞中的《香爐》以及法國貝雅1962年取材西藏《亡靈經(jīng)書》的《旅行》……
二、美在功能與觀念之間
1.功能效應
作為靈肉一體的舞蹈,其存活與流布的前提是美的品格,而這一品格的建立,一面離不開形而下的功能性,一面也離不開形而上的觀念性。功能性使舞蹈具有活生生的效應,而觀念性則使舞蹈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永占一席之地,并以此劃開與雜技、武術、體操的本質(zhì)界限。曾經(jīng)是粗礪的苯教藏舞最終定型為松腰、懈胯、身體前傾的柔順虔誠,不能不歸功于佛教在功能與觀念上的法力。
《空行益西措杰傳》載:“苯教每年秋天要舉行‘鹿角祭’,殺死許多公鹿,取血肉獻祭。冬天要各殺死三千只綿羊、山羊、牦牛等公畜,獻祭苯教神祗。春天要舉行名叫肢解無角母鹿的祭祀,將四只無角母鹿四蹄折斷,以血肉獻祭。夏天要舉行苯教祖師祭,以各種樹木和糧食煨桑祭祀,在有人病痛時,要施舍贖命,視個人經(jīng)濟情況從最多殺公畜各三千到殺公母畜各一頭獻祭神祀。人死以后為了制伏鬼魂,也要像上述那樣殺牲祭祀。此外,還有祈福,送鬼、贖替、卜算、預測生死等儀式內(nèi)容。”如此大規(guī)模的殺牲祭祀,于藏民生產(chǎn)和生活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而佛教以“禁止殺生”楔入苯教,使藏民誠信悅服于佛給予人的最基本需要。
佛教的聰明和寬容特別表現(xiàn)在它很少強令制止或取消“異教”,而多是采取將計就計的方法轉換之,以為我所用。“靈嘎”是藏語“Lingga”一詞的譯音,是邪惡鬼魅的象征物和替代物,指神舞儀式中用糌粑和酥油捏的人替身鬼俑。靈嘎源于西藏的苯教。據(jù)敦煌石室發(fā)現(xiàn)的藏文手卷記載,早在吐蕃的止貢贊普(第8代贊布)時期,使用替身的宗教儀軌已出現(xiàn),并成為苯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主要是用動物和活人作為替身來贖取死者軀體和靈魂。或驅除災病。這一習俗至佛教大舉傳入西藏的公元8世紀后發(fā)生了變化。由于佛教公開反對血祭。并以替代物保持這一習俗,所以11世紀以后,以殺殉生靈為特征的祭祀活動逐漸消失,活的祭物被供物所取代,致使我們今天看到的保留在佛教舞儀中的風格已經(jīng)不再像《春之祭》那樣慘烈和恐怖了。
2.觀念效應
在觀念上,佛教傳入之前,藏區(qū)就有“人死以后轉生為鬼和神,而神鬼死后也轉生為人”的轉世觀念,即“輪回說”。敦煌出土的吐蕃《禮儀問答寫卷》中言:“無論何時,行惡得善者百中得一,行善得善者比比皆然”,“俗語云因禍得福,但無論何時不會有因福得禍者”,④與佛教因果報應思想暗合。不同的是,苯教認為善惡禍福都是與天神發(fā)生感應而得到的不同報應,而佛教認為有因必有果,不需要超人的天神來主宰,無論貧富貴賤人人皆可成佛,強調(diào)的“輪回觀念”的普世性,因而更容易被廣大藏民以積極狀態(tài)接引,心悅誠服于佛。
在西藏,西來的大乘佛教在觀念上不僅兼容了苯教,而且自身的顯、密之分也在喜馬拉雅山脈相互兼容,并以藏密的觀念和實踐顯現(xiàn)出來—密宗是顯宗的更高一層級,因而藏傳佛教常被稱之為“藏密”。藏密“緣起性空”的世界觀,直接形成“即身成佛”和觀念,即每一信徒現(xiàn)世即可成佛。“即身”,即現(xiàn)實的生身、肉身。《菩提心論》記載:“若人求佛慧,通達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佛)位”故亦稱“肉身成佛”。⑤密宗視身體與天地宇宙溝通的身體觀,發(fā)展出了繁復而精致的儀式和其中的表演。密宗相對于大乘其他派別,將儀式和表演放在比以往更為重要的地位,并將其作為自己最顯著的特征,身體行為代替了過去抽象的禪定思維。以前的儀式和其中的表演只是引領修行者入道的手段,“然而現(xiàn)在儀式的本身成了‘道’,而且取代了契經(jīng);教義理論必須用一種摸得著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不是單純心靈上的理解”⑥在身體儀式中,舞蹈此時已和修行融為一體,諸如密宗金剛乘編制的儀式舞蹈《金剛舞》:
善哉於心住灌頂二金剛
於心示日形右肘住左拳
二掌及於口左蓮右開勢
左心劍殺害旋轉如火輪
金剛二口散金剛舞旋轉
一如南懷謹先生所言:“三密的加持功德,使人容易得到即身成佛的效果。而且花樣百出,可使修學密宗的人,晝夜忙著有為而求達無為涅槃的成果。這是人們多么喜歡的事,也可以說,它是經(jīng)濟價值高而成本較為低廉的成佛捷徑。所以釋迦牟尼遺言中提到,后代末世的時期,大乘佛學的智慧成就之學—衰落,唯獨密宗與具有宗教性信仰的凈土宗,才能流布不息。以此證之于現(xiàn)代的趨勢和事實,卻甚為相似”⑦
三、向北向東
1.舞蹈遺跡
在藏傳佛教舞蹈文化中,不僅有精美的舞蹈遺跡以過去時態(tài)保存了這一切,而且還有充滿生機的“活化石”以現(xiàn)在時態(tài)述說著這一切。
舞蹈遺跡包括文物和文字。敦煌壁畫舞蹈文物中的佛教因素除絲綢之路外,還有藏傳佛教的巨大力量。“以舞傳佛”的代表之一是156窟供養(yǎng)人《張儀潮出行圖》、《宋國夫人出行圖》,前者八個番裝舞人頗似今藏族踏足張臂的矯健舞姿,而后者四個漢族舞伎舞姿則酷似今藏族典雅優(yōu)美的弦子。“佛舞一體”的壁畫當屬465密宗“歡喜佛”的雙人舞。南懷謹先生曾對“歡喜佛”舞蹈造像有過獨到的見解:“密教還有一特點,其精神雖然出離世間,其方法不是完全遺世,它是聯(lián)合人性生活而升華到佛性境界的。因此他們的修持,有一部分包括男女雙修的雙身法……如《大智度論》卷二十一所謂:‘是人淫欲多為增淫欲而得解脫。是人嗔恚多為增嗔恚而解脫’……如觀密宗像法,由藝而至于道也,亦何不可”。⑧“由藝而至于道也”即“佛舞一體”,而且是從身體感應上悟出大道理。此外,史學家王克芬先生認為大量造型優(yōu)美的“反彈琵琶”舞姿與西藏定日地區(qū)“反彈三弦”的舞姿亦有動態(tài)的連接點。這些連接點所具現(xiàn)出的,無論是舞儀,是修煉,還是裝飾性舞蹈,它們都包含著功能、觀念和審美因素,前兩者隱而審美因素顯,但前兩者卻是審美的鐵錨。正如捷克舞蹈家凱利·基里安所言:舞蹈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贊美上帝”,我們的“身體的動作不外是相對于空間中某些定點圓形運轉。我們在尋找身體與心靈的定點,同時也是生存意義的依憑。在過往與未來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一個和平與寧靜的所在。”⑨
藏傳佛教舞蹈文化圈次層的又一指向,是當年吐蕃時期的西夏王朝及其舞蹈。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王國(1038—1227)與佛教關系密切,敦煌壁畫的“飛天”舞中,西夏飛天獨具一格,其直線的、帶角的非“S”型舞姿一面透著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獷,一面又用柔和的綢帶顯示出其對佛祖的謙恭。敦煌畫家霍熙亮先生在榆林東千佛洞3窟發(fā)現(xiàn)了一組西夏供養(yǎng)伎樂壁畫。在一幅舞圖上有兩個舞者雙身緊緊勾連纏繞,造型奇妙罕見。雙人高托供品盤,皆為裸身,肩背飾以挽結飄帶,手指、手臂及雙腿相互勾繞,既表現(xiàn)了敬佛的虔城,又具舞蹈美感,其他如甘肅肅北五個廟和安西千佛洞等石窟有多幅西夏伎樂壁畫,其舞姿大都是主力腿半蹲,開胯,另一腿端抬于主力腿膝部;舞伎有托花盤、執(zhí)花傘、揮巾或空手而舞的。這種以開胯為特點的舞姿,具有馬上游牧民族的生活烙印及審美情趣。如果我們更進一步仔細審視這個屢屢出現(xiàn)的舞姿,就會發(fā)現(xiàn)它與佛教密宗歡喜佛雙身像中女身的姿態(tài)造型是完全一致或基本相同的。⑩
特別重要的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宗教信仰正是因西夏佛教而與藏傳佛教建立了聯(lián)系,從而揭開了藏傳佛教由西藏→寧夏→蒙古→中原傳播的鏈條。可以說,藏傳佛教文化在從唐中期到元代的河西走廊文明中占據(jù)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故而當漢地會昌法難,佛教橫遭劫難的時候,吐蕃統(tǒng)治下的敦煌卻大規(guī)模開窟不止,合計今莫高窟中92個窟中保留有吐蕃時期畫塑遺存,若按每年的平均數(shù)計,甚至超過了初唐和盛唐”。(11)
在古籍文字記載中,有關藏傳佛教舞入中原的精致者莫過于《十六天魔舞》。從舞蹈文化圈來看,它橫跨西藏、蒙古和漢地三個圈層;從舞蹈語境來看,它是從西藏密宗寺廟堂經(jīng)由蒙古萬神殿踏進中原宮廷;從舞蹈功能來看,它由“舞以載道”變?yōu)樯眢w修煉又變?yōu)橐曈X娛樂,并從“宮官受秘密戒者得人,余不得預”(《元史·順帝紀》)的主流文化墮入民間的非主流文化以致最終消失……其間功能與觀念漸去漸遠,審美愉悅搶得領銜主演的位置,最后“美”得無影無蹤。盡管佛教寬宏大量,但作為舞蹈卻應自忖:當舞蹈擺脫了形而上的觀念和形而下的生存功能時,其“純美”有多長的生命力?作為專題研究和歷史個案,茲不累述。
2.從“羌姆”到“查瑪”到“十六天魔舞”
應該詳細闡述的,倒是舞蹈活化石的流變,因為它們還手舞足蹈在我們今天的視野中,典型的范例是西藏的“羌姆”—盡管它并非純美,但它卻一直“活著”。
在舞蹈活化石的流變中,有兩個要明確的概念:“族群”和“民族”。全民信佛、政教合一的藏民族既有鮮明的族群標志,又有鮮明的制度化的民族標志,藏傳佛教舞蹈之所以能成為內(nèi)層核心的震源,正因為具有這雙重的標志,包括其生成的神秘的地域、深厚的信仰、第三地理臺階特有的體質(zhì)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tǒng)。這種“族群”和“民族”概念的合一,使得藏族舞蹈和藏傳佛教舞蹈也具有了某種同一性,其表征之一就是“羌姆”。藏民們認為,羌姆是他們與神溝通的橋梁,跳一次或者觀看一次,其功德有如讀一篇藏文大藏經(jīng)《甘珠爾》,并可以得到神靈的保佑。
“羌姆”是藏語對喇嘛寺廟舞蹈的稱謂,本意為“舞”,后成為專指用于驅逐疫鬼、酬謝神靈的戴面具表演的宗教儀式,為喇嘛教各教派所共有,風格獰厲肅穆。羌姆儀式包括了動作表演之前大量經(jīng)文念誦儀式、音樂儀式、面具造像規(guī)則、服飾造像規(guī)則等。其舞儀是一種由印度佛教密宗的金剛舞與西藏苯教擬獸舞、鼓舞和土風舞等融合構成的以驅鬼逐邪、弘揚佛法為目的的藏傳佛教法事舞蹈。(12)在未開化時期,藏族在崇拜眾多的自然神靈的同時,還要膜拜人間之神—即作為天神化身的贊普和具有非人之力的苯波(巫祝階層)。這些“專司之苯”兼有自然和社會雙重主宰身份,其地位發(fā)展甚至要越居自然神之上。古老的諸多神靈猶存,新的神祗又被不斷產(chǎn)生,使得身陷貧困與恐懼中的普通藏民不僅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時間來頂禮膜拜,還要在精神上負重著天神(贊)和巫(苯波)的兩重人格壓力,因而他們希望有一個較簡便且單純的神直接和人相對。時勢造英雄,以“傳授密法,戰(zhàn)勝外道,降伏妖魔”著稱的蓮花生大師因勢利導,在功能和觀念上雙管齊下,將佛以審美的儀式化過程體現(xiàn)在藏民面前,一舉成功。
《蓮花生大師本生傳》有大量這樣的記載……
蓮花生來到香波溝
(雅拉)香波山神變成山大的白牦牛
蓮花生用鐵鉤手印扣其鼻
繩綁繚銬使之難動彈
又用鈴子手印變其身與心
二神馴服獻名號
護法守衛(wèi)大伏藏……(13)
“羌姆”中的“牦牛舞”和其他被馴服的各類護法神的舞蹈,就是這樣構成了“獰厲而肅穆”風格的二重組合。(14)
當“羌姆”隨著吐蕃的擴張和藏傳佛教的北向發(fā)散而駐足于河西時,即變形為金剛乘密宗壁畫中的形象:神秘、艷麗而怪誕,具有極強的超現(xiàn)實意味。在人稱“秘密寺”的第三465窟,頂上畫以大日如來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畫妙樂金剛、勝樂金剛、吉祥金剛等雙身像,東壁畫有鋪人皮、掛人頭、騎騾子的怖畏金剛。“雙人舞”的歡喜金剛主尊藍色,八面十六臂,佛母裸形,相擁主尊,色彩艷麗,對比強烈,裝飾味道很濃,融合了中亞和中原的審美意識,成為敦煌壁畫中舞蹈的一種審美定型,與“飛天”和“伎樂天”遙相呼應。
今天,“敦煌舞”中的“金剛舞”已在漢地的一些舞蹈團體和院校中復原,但其成功的劇目和接受的程度,遠遠不及“飛天”和“伎樂天”。究其原因,與漢地的信仰與審美不無關聯(lián):菩薩女性化的慈愛、飛天的飄飄欲仙和伎樂天的“S”形優(yōu)美為漢地之追求;換成了男性的怒目金剛,則無人喝彩了。這正像南懷謹先生解釋漢地國人質(zhì)疑爭論密宗畫像之形態(tài)問題一樣:此類畫像已失去顯教佛像莊嚴慈祥本色,使人生起猙獰怖畏之反感,大多不類人形其故為何?曰:“在佛而言佛,一切佛皆就體、相、用而取法、報、化三身之別名。顯教佛像之奇形異態(tài)者,乃表示化身、異類身等等,統(tǒng)為佛學內(nèi)涵之表。舉一言之,如大威德金剛像之怪異,即表大乘九部契經(jīng)。二角者,表真俗二諦……其他畫像如六臂者,即表說度法相。四臂者,示慈悲喜舍風規(guī)。凡此等等,皆為佛經(jīng)義理之圖形,故為淺智眾生,由識圖而明義而已。是以經(jīng)說大威德金剛,即為大智文殊師利化身。舉此一例,余由智者類推可知,不必一一詳說。”(15)問題是,漢地國人已身在藏傳舞蹈文化圈之外,不大愿意再做“智者類推”的苦差事,所以“羌姆”及敦煌的“金剛舞”也就而已而已了。
經(jīng)由邊緣地帶的次層后再向北,便是外層的蒙古舞蹈文化圈了。使兩個圈層相連的標志性舞蹈便是“查瑪”。“查瑪”是蒙古族喇嘛教寺廟舞蹈的名稱,是羌姆一詞的蒙古語讀音。查瑪?shù)男纬蛇^程,有意無意地伴隨著蒙古族由一個簡樸的游牧民族上升為世界之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原本信奉薩滿教的蒙古貴族面臨著一個重大抉擇:如何在精神信仰層面中選擇出一統(tǒng)臣民的具有政治功能的神靈。
薩滿教多神并存的宗教形態(tài)與新的民族構成和統(tǒng)治秩序大相徑庭。因此,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大汗臺吉們極需尋找一種統(tǒng)一的精神凝聚力,而執(zhí)意向北發(fā)散的藏傳佛教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因而立刻被接納。
藏傳佛教是印度佛教、漢地佛教傳入西藏后與藏族的傳統(tǒng)宗教苯教相結合而形成的,具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與蒙古薩滿教在教義、教規(guī),特別是祭祀禮儀(含舞儀)等方面極具相似性,又在功能與觀念上高出薩滿一籌,這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施行兼容的兩個必要前提。《蒙古風俗態(tài)》載:薩滿教頻繁的殺牲祭祀活動,對蒙古游牧經(jīng)濟有很大的破壞性,因此藏傳佛教大師索南嘉措使蒙古大汗在開化后的首要措施之一便是:“倘若依舊殺人殉葬,則要依法處死;如果宰殺牲畜殉葬,則要依法沒收其全部財產(chǎn);若有謾罵毆打上師和僧伽者,則抄沒動手者的全部家產(chǎn)……從今以后,要燒毀那些偶像(指薩滿諸神),嚴禁殺生進行年祭月祭。如果違法宰殺牛馬祭祀,則罰其十倍的牲畜”。(16)從政治信仰的統(tǒng)一到生產(chǎn)力的保護,索南嘉措走的是蓮花生的同一條路,所以“羌姆”自然地換成“查瑪”的稱呼,開始了“以舞傳佛”。
蒙族認為自己跳的神舞“查瑪”與藏族的“羌姆”有別。“羌姆”所崇奉的是“現(xiàn)在佛”釋迦牟尼,而蒙族的“查瑪”所崇奉的乃“未來佛”彌勒。(這又直接影響了“跳布扎”),其形式說唱舞皆有。“查瑪”舞的風格同時具有喜馬拉雅山的神秘和蒙古草原的粗放,并且夾帶著游牧民族的矯健靈活,《白老頭》、《黑老頭》、《水神舞》等都帶著這樣的審美特征。最典型的是“鹿神舞”,它不像西藏跳神舞時把鹿作為反面形象,而是把鹿視為吉祥、康樂、和平、自由之神。因為早在喇嘛教傳入蒙古之前,民間就曾流傳著靈活敏捷的“鹿神舞”,牧民不忍心把可愛的鹿神形象丑化,表演中專挑一名伶俐活潑的小喇嘛充任鹿神。各舞段之間穿插老壽星撥浪鼓與鹿嬉戲,還穿插一些民俗舞蹈,以及壽星與娃娃戲劇性表演。(17)就像在蒙古草原佛教的萬神殿中既有肅穆莊嚴的佛教神祗,也有許多粗放靈動的薩滿教神靈。急于統(tǒng)一的蒙古貴族曾以“異教”嚴厲打擊過薩滿教,但薩滿教卻是“野火燒不盡”;倒是滴水穿石的佛法以其廣博與睿智最終溶解了不屈的薩滿。
當“羌姆”經(jīng)由兩個踏板跳到中原時,它已經(jīng)隨著蒙古人的南下而演變成為《跳布扎》以及全然變形的《十六天魔舞》了。在蒙古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對峙中,中原文化的功能需要和觀念意識無聲地抵制著“查瑪”,而佛教的寬容,將這種抵制化為融合。蒙古人定都元大都后,已然爛熟的中原漢族文化的華麗恢宏和紅塵之樂使他們目瞪口呆,自身的粗放矯健,漸漸向精致美艷靠攏,小至造像,大至巡游,還有夾在這靜態(tài)與動態(tài)之間的舞蹈。瑪哈嘎拉為梵語,為密宗一怒相護法,來自是印度,藏語稱“貢保”,漢地稱“大黑天”,為元代上層所尊崇。其像極為精致,身有六臂,披白象皮,象頭朝下,四腿搭在兩肩和雙腿后。最上右手向上抓著象腳,左手拿三叉戟,中間兩只手右手拿骷髏鼓,左手拿索子,主臂兩手拿著骷髏碗和月刀。脖子上飾以青蛇、項鏈,腳腕和手腕上有白蛇纏繞,象征著降服一切龍王和藥叉。兩腿左屈右展,跨在一頭仰臥的白象身上,珠光寶氣,威德逼人。游皇城活動始于對大白傘蓋佛母的崇拜,亦為元代社會一盛事。《元史》祥記其事:“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zhí)抬舁二十六人,鈸鼓司云和署掌大樂鼓、板板鼓、篳篥、龍笛、琵琶、箏、蓁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zhí)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伏,俱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金銹,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18)
這種精致、美艷和夸飾的風格在舞蹈中可以具現(xiàn)于宮廷內(nèi)《十六天魔舞》,其“瓔珞垂衣稱艷妝”、“清歌曼舞世間無”便是順理成章了。想當初,佛祖拋離嬌妻弱子,舍棄王國宮殿,金銀珠寶,六年周游,修習苦行,四十天顆米未進,消瘦衰弱,靜坐冥思,終于覺悟,證得正覺。如今,中原漢地佛教“相似佛法”的以舞傳佛竟如此奢華,佛祖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羌姆”在北京的“正宗傳人”是雍和宮的《跳布扎》,因為它畢竟不是在宮廷宴樂上而是在喇嘛寺中,不是女樂來跳而是由和尚來跳的舞蹈。但就其功能和觀念的差異而言,漢地的相似佛法還是直接影響了《跳布扎》的風格類型。雍和宮跳布扎與藏族的羌姆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從內(nèi)容上看,雍和宮的“跳神”多為正面形象,如“跳金剛”“跳天王”、“跳護法神”、“跳彌勒佛”等。而羌姆的跳神卻多以反面形象出現(xiàn),如“兇神舞”、“骷髏舞”、“牛神舞”等。跳布扎除第八幕“跳護法神”為戴獅、虎、象、豹、牛、狗等面具表演外,大都為菩薩等神靈戰(zhàn)勝邪惡。從形式上看,“跳布扎”分幕表演,整個過程猶如一出戲曲,每一幕都圍繞一個故事展開,情節(jié)生動活潑。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幕“跳星神”由28人扮演的28星宿神靈(道教崇拜的主要神靈)。這顯然是將漢族傳統(tǒng)文化吸收進來,并以符合漢民族的審美需要呈現(xiàn)。這里要特別提到“跳彌勒”。除“大彌勒”外還有6名“小彌勒”,他們面具雖大小有別,但面部造型卻都是漢族寺廟笑面彌勒佛的形象,與眾神明顯不同,而且是紙?zhí)ビ刑最^面具,笑容可掬,和今日的“大頭娃娃”相似。與之相呼應的還有靜坐觀看的“哈香”(戴大頭和尚的施主)的笑容。皈依佛門的漢地眾生,多看重今世而看輕來世,所以要把“未來佛”弄得喜氣洋洋地活在今世。紅塵自娛自樂的生存功能和觀念直接導致“與佛共樂”的舞蹈形態(tài)—無論是跳彌勒的舞蹈主體還是看彌勒的舞蹈受眾……
但無論如何,“羌姆”的主旋律—斬鬼送崇、布法揚威還是貫穿了佛教舞蹈文化圈的整個圈層,使同一題材按照同一主題變化出不同的審美風格。這其中不僅要求以包容精神尊重每一圈層的功能與觀念的特殊性,同時也要求每一文化圈都要在終極追求的目標上恪守舞蹈文化內(nèi)層核心的“質(zhì)”。正像解構主義所描述的:新文本(包括舞蹈文本)的蹤跡在暢游后仍會不止一次地返回“書”【注:德里達將“書”一詞作為傳統(tǒng)權威的符號,而“書寫”(writing)一詞在其解構理論中卻是一種宏觀的創(chuàng)造活動,在語言文學方面,它不同于有形的書面定寫作,而更多的是指無形的、扎根在無意識中的無形心靈書寫(psychicwriting),也即語言運動本身。當然也應包括舞蹈身體語言】這個傳統(tǒng)的符號,但卻拒絕受其約束。這種出走而又復返的創(chuàng)新與繼承運動如同一個不完整的新的圓與舊圓重疊,新的圓每次都出現(xiàn)在舊圓的影子里,二圓相似而不等同。它們的關系如一位17世紀的詩人所說:“新月在舊月的懷抱中”。兩個月亮都不完整,相似而不相等。這種離去又返回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運動,德里達稱之為“圓的重復”。創(chuàng)新無法從零開始,它必須在原有的場地畫自己的圓,這種不完整的圓的“不斷的重現(xiàn)”(是重現(xiàn)而非再版),由此才能成為德里達所稱之的精力充沛“游戲”(play)。
四、“羌姆”主題的“孔雀舞”形態(tài)
1.向東南
當初,大乘佛教不滿足于部派佛教出家僧侶只求獨善其身、灰身滅智的理想境界,于是依據(jù)佛的慈悲精神提出“普渡眾生”。由此而衍化出的藏傳佛教從理念上肯定了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是“肉身成佛”,只不過有圓頓遲緩之別而已。這種觀念夾帶著由觀念誘導的身體一面向北,一面也向東南拓進,開辟了滇西北的又一邊緣地帶的次層舞蹈文化,并與小乘佛教的舞蹈文化圈牽手對視。
如果說“羌姆”的主題向北、向中原延伸時舞蹈形態(tài)發(fā)生了變形,衍化出了粗放、靈動、美艷、詼諧;那么它在向東南拓進時也必然“入鄉(xiāng)隨俗”地發(fā)生形態(tài)變化,但也依舊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其中,納西族的“孔雀舞”便是范例,恰與由印度生成而經(jīng)由緬甸、泰國定型的中國傣族的“孔雀舞”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審美風格。
費孝通先生在《民族與社會》一書中指出,在我國西部,北起甘南,中經(jīng)川西,南至滇西北、藏東南,這個南北向的區(qū)域,可稱做是“藏彝民族走廊”。今天生活在滇西北的藏、納西(包括摩梭人)、普米、怒、傈僳、獨龍、白等民族,就是在長期的征戰(zhàn)遷徙分合之后定居繁衍而形成的。納西族是這些民族中的一支,其信仰為東巴教。東巴教是納西人在吐蕃統(tǒng)治時期將本民族原始宗教與藏族苯教結合而成的宗教,亦可以說是藏傳佛教的納西化過程。與“羌姆”舞儀的主題相近,“下鎮(zhèn)鬼怪,上祀天神,中興人宅”自古以來都是東巴們的主要宗教活動,包括舞儀中的“孔雀舞”。
在納西,孔雀是降魔鎮(zhèn)邪之鳥,是神界神靈之坐騎,飛落到人界為護法開路,專食鬼界蛇之類的邪物,有類于鷹。這在《東巴經(jīng)》中多有提到。記載東兵天將在攻術鬼的第三個山頭時,有劇毒炭黑猛虎和黑蛇在那里防守,阻擋東兵天將前進。東格、優(yōu)麻天將作變化,變出一只亮燦燦的金孔雀,攻破了黑蛇防守的第三道防線。舞蹈描述的是孔雀從天上降臨人間,在溪流邊梳妝打扮、喝水、抖翅戰(zhàn)斗時的動態(tài)。“碎步走七步”代表孔雀從天上下來的步態(tài),弓步俯身雙展翅代表孔雀汲水,雙腿半蹲碎抖肩代表孔雀汲水后抖動羽毛時的動作。此外,還有一些法術式的動作,如順腳走搖板鈴或鼓,勾腳單盤腿,勾腳前抬腿雙展翅,單跪腿搖鈴,轉身單跪腿等。整個舞儀剛勁、拙樸、粗礪。(18)正如珍妮·科恩所說:“所謂舞蹈風格,指的是有一部帶有作者階層、宗教或學派特制的舞蹈作品表現(xiàn)出來的特性”。(19)
2.風格定型
作為舞儀中的風格定型,首先是在形而上的層面確定其“特性”。在對外傳播中,佛教為了消除納西族對佛、菩薩的陌生感,將當?shù)氐母鞣N神靈吸納進自己的神靈殿堂,使它們都具有歸屬感,成為佛教的神祗。滇西北當?shù)赜忻淖匀簧耢笕缛龎伟姿_神、麗江玉龍雪山神、永寧的瀘沽湖神,當然還有丁巴什羅之類神靈的坐騎—孔雀,他們都先后成為佛教萬神殿中的一員。不可否認,神靈角色的兼融,使藏傳佛教、東巴教和汗規(guī)教在神靈系統(tǒng)上都表現(xiàn)出一定的混雜性,而恰恰是這種混雜性,使民眾在信仰過程中能以一種模糊的認同感兼而取之,這就減緩了不同文化圈層之間的對抗而擴大了對話的張力,在若即若離中走向一種共存共榮的發(fā)展格局。盡管滇西北文化圈的許多風俗傳統(tǒng)與佛教教義相牴牾,但是藏傳佛教的高僧仍以積極的態(tài)度和特有的寬容性吸納了這些“異端”,發(fā)揮了佛教隨類施教、隨順眾迷的思想。
形而上的寬容導致形而下的認同。神靈角色的互換和外形特征上的相互模仿,引發(fā)了東巴與喇嘛們在舞儀中的角色替換。一元主宰變成二元共同主宰,在所有祭山神、水神、祖先的活動中,喇嘛與東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東巴們雖然仍運用傳統(tǒng)的皮鼓,但東巴舞中的佛教浸染卻越來越濃。舞者不僅頭戴五佛冠,身穿長袍,手里增加了銅鈴、法杖、鎮(zhèn)邪塔等法器,而且吸收了藏傳佛教的某些簡短經(jīng)咒,如《祈福經(jīng)》、《求壽經(jīng)》、《驅邪經(jīng)》等,甚至孔雀舞中的許多手勢和步態(tài),也帶著“羌姆”的風格。當來自小乘佛教的“孔雀舞”在為娛佛展示優(yōu)美的時候,來自藏傳佛教的“孔雀舞”則在為驅逐魔怪一展粗礪。模仿和借用雖然只是文化交流中的最初方式,但由此而引起的審美情趣的變化卻有其深廣的語境。
當下,包括商業(yè)性舞蹈在內(nèi)的各種孔雀舞都被中國人—特別是漢地中國人所接納了,而且其速度如同中國人接受佛教一樣,實在是很快的。這一面是因為接受者“相似佛法”的功能與觀念所致,但更為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為傳播主體的合理性、特別是寬大慈悲的包容性所致。荷蘭著名漢學家、佛學家高羅佩(R.H.VanGulik,1910—1967)對此有他獨特的解釋:“東來傳法的佛教僧侶—跨進中國大門,只是一味地說佛教如何如何好,卻從不夸耀印度文化或政治理想多么多么高超。這說明佛教傳法僧很了解中國人的脾氣,很知趣地不碰中國人護若命根的民族自尊心。另外,佛教傳教士們從來不說自己是外國某一強大教會派出的使徒,而中國的信徒必得嚴守該教會的一切規(guī)訓。這樣一來,中國人就明白了,他們?nèi)绻帕朔鸾蹋矝]有必要因此放棄自己原有的一套思想和生活方式。說得形象點兒,在佛教傳教士身后,中國人不會遙遙地感到有一個麥加或羅馬。”(20)同樣,在漣漪漸弱的佛舞文化圈走勢中,也越來越少有人追問“大頭和尚舞”和“孔雀舞”的深遠背景一旦作為舞蹈研究者則應該追問到底。
注釋:
①參見葉舒憲《身體人類學隨想》載《民族藝術》2002第2期第9頁
②參見《北京青年報》2004年1月11日
③④(11)(13)(16)參見扎洛《菩提樹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5頁,16—17頁,92—93頁,26頁,213頁
⑤任繼愈《佛教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頁
⑥郭凈《心靈的面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
⑦⑧(15)參見南懷謹《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第289—302頁、第299頁
⑩參見王克芬《中國舞蹈發(fā)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3頁
⑨劉青弋《西方現(xiàn)代派舞蹈》北京舞蹈學院內(nèi)部教材第388頁
(12)(14)(17)(16)(19)參見劉建《宗教與舞蹈》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八、第九章,第292—293頁、294—295頁、參見283—305頁
(18)參見北京舞蹈學院2003屆研究生馮莉碩士論文《舞儀中的文化記憶與保存》
(19)珍妮科恩《對舞蹈風格與舞蹈作品的反思》載《舞蹈藝術》總18期第175頁
(20)參見《讀書》三聯(lián)出版社2004年第11期第81頁
- 上一篇:我國民間舞研究論文
- 下一篇:信息產(chǎn)業(yè)局民主生活會剖析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