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野而俗詩歌風格的嬗變論文
時間:2022-07-13 03:48:00
導語:由野而俗詩歌風格的嬗變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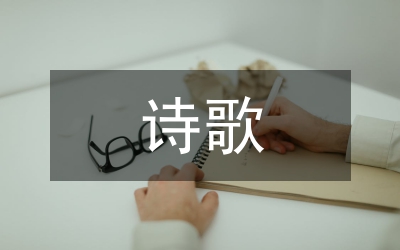
論文摘要:游子詩在古代詩歌中數量不少,由于社會形態的不同,表現手法的各并,價值觀念的更新,導致詩歌中的思念主體有所不同。《詩經》所處落后的農耕社會,思念的主體是故土和父母,因較少受禮教的影響,風格直樸坦率《古詩十九首》所處私有制社會,思念的主體則是妻子和家庭,因受封建禮教的影響,其風格婉轉溫麗。
《詩經》大約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除少數作品為當時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所寫的以外,大多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民歌。其中有不少是游子和思婦之詩。《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估計《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大概不出于東漢后期數十年之間,即至早當在順帝末年,至晚亦在獻帝以前(約公元140-190)。
同是游子和思婦之詩,但思念的主體、表達方式及詩歌的風格也各有所不同。
游子思鄉作品在《詩經》中較多,思婦閨怨之詩就更多了,這時期作品的思念對象主要是家鄉故土和自己的父母,體現了落后的農耕社會中人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如《衛風·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政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這是一個宋國的游子在衛國所唱的思鄉曲。黃河雖然很寬,但在游子的眼里,只用一片葦葉便能渡過河去;故鄉宋城雖然遠隔大河,但在游子的眼里,只要踮起腳就能看得見。可見游子渴望回家的迫切心情。
如《小雅·黃鳥》(第一章):
黃烏黃鳥,無集于敷,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較。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烏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泰。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朱熹說:"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它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全詩懷念的還是故鄉、兄弟和父母。
《檜風·匪風》寫游子經年累月地流徙四方,出入風塵,受驚磨難。偶見車馬馳騁于大路之上,不禁喚起萬般鄉愁,希望有人帶給自己家人一封家書。最后終于喊出"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的祈盼。朱熹說:"誰將西歸乎?有則我愿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
《邶風·擊鼓》是一首遠征異國、長期不得歸家的征夫控訴。詩的第四章寫自己對妻子的無限思念:"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朱熹說:"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陳風·月出》是寫游子在月下懷念愛人的詩所寄托的是月夜幽思。對那"佼人"情態的詠嘆,乃為憶念之詞。景物依舊,伊人渺渺,觸景傷情,發而為歌。
《唐風·鴇羽》是一首征人思念自己父母的詩歌。詩中講由于自己長期在外,家中的田園荒蕪了,父母生活沒有著落,面臨著餓死的危險。他瞻前顧后,無可奈何,痛苦地呼喊著老天,無休止的徭役給他帶來了悲慘與不幸。朱熹在《詩經集傳》中說:"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從以上反映的內容看,盡管有思念故土、兄弟、父母和妻子之別,但詩歌風格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真摯感情的流露,有憤怒心聲的傾吐,有對手足親情的貪戀,有對長輩父老的思念。總之,表達的是實實在在的感情。這里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纏綿的感傷。一切都顯得樸實無華,但又真實可信。
《古詩十九首》是一組形式成熟的抒情詩,沈德潛將它的內容歸納為"逐臣棄婦,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四類,L4其中游子思婦為內容的詩幾乎占十九首的二分之一。十九首詩歌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們身在他鄉,胸懷故土,心系家園,每個人都有無法消釋的思鄉情結。他們和《詩經》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屬于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家鄉,奔走權門,或游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他們長期出外,家屬不能同往,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憂別的情緒。這對思婦來說,就會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嘆息;對游子來說,就會產生"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和"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的感慨。和《詩經》的游子詩有所不同,《古詩十九首》的思鄉焦點則集中在妻子身上,思鄉和懷內密不可分,鄉情和男女戀情是融匯在一起的,體現了這一時期封建社會士人的仕途意識、經濟意識和價值觀念。
如《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緯。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這首詩寫一個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對著照射羅幃的皎皎月光,愈加觸動了他對遠在家鄉的妻子愁緒言。通篇只起頭二句是寫景,以下全是寫情,而月明如晝的景色悉在其中,那個"憂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鮮明。天涯芳草,他鄉明月,都沒有給游子帶來心靈的慰藉,相反,倒是激發起難以遏制的思鄉懷內之情。
游子思鄉,在以往的史傳作品中,人們經常見到的是富貴以后流露的鄉情,衣錦還鄉的熱烈場面《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們在窮困潦倒之際所彈奏的思鄉曲,語悴情悲,充滿天涯淪落人的凄楚,引來的是同情和憐憫。
即使是思婦詩,"這些詩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摩思婦心理而作,但都寫得情態逼真,如同出于思婦之手"。
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風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這首詩寫的是思婦對丈夫久別不歸的思念和怨悵,一首千古傳頌的抒情杰作。詩的前六句回憶離別的往事,突出"生離"的哀苦,這是全詩的主題。詩的后十句通過女子的衰老、消瘦、衣帶漸寬的自我情態描寫,傾訴出難以排解的相思之情,這是全詩的濃情部分。以上所舉詩歌,盡管同是游子詩,但與《詩經》中的游子詩在風格上卻大為不同。已沒有《詩經》中主人公發自內心的質樸的感情披露,作者運用了比喻、象征、夸張等藝術手段,使詩歌更有文彩,更顯得個性張揚。總之,詩歌的風格正發生著微妙的嬗變。從《詩經》的四言到《古詩十九首》的五言,一字之差,卻改變了詩的節拍,擴大了詩歌反映現實的容量;且語式變化,詞匯選擇也有了更大的自由。又加上文人模仿過程中進一步的加工和完善,最終發展為一種有固定格式的新詩。
《詩經》表現出詩人對現實的強烈關注,充滿憂患意識和干預政治的熟情。國風中的作品,更多針對戰爭徭役、婚姻戀愛等生活抒發詩人的真實感受,在對這些生活側面的具體描述中,表現了詩人真摯的情感、鮮明的個性和積極的生活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總之,《詩經》牢籠千載,衣披后世,不愧為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
《詩經》的產地,主要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包括今天的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和湖北北部地區,多屬于北方地域,所以它的表達手法帶有北方民歌的特色,具有直樸、坦率的特點。而《古詩十九首》就有明顯的不同。所處私有制社會,思念的主體則是妻子和家庭。因受封建禮教的影響,其風格則婉轉溫麗。劉勰說它"婉轉附物,怊悵切情"。鐘嶸說它"文溫而麗,意悲以遠"(詩品),都說明其與《詩經》的不同。這些詩歌從思想內容和語言風格看,它們顯然是經過文人潤色的民歌,或者是文人模仿民歌寫成的。劉勰把這些詩歌的風格概括為"直而不野",準確地指出了它和其他詩歌尤其是《詩經》的不同特點。"直"是指它具有直率表情達意的民歌本色,"不野"是指它富于文采,是文人在民歌的基礎上的加工潤色。
《詩經》游子思婦詩的作者,大多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奴隸們,他們心里有話,直接坦露,甚至于暢開心扉,直陣其事。風格直樸坦率。雖幾經儒者附會,以服從于儒教的需要,但畢竟沒有太多地受傳統禮教的影響,故或說有點"野"。《毛詩序》說:"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就是指那些反映現實而少受禮教影響的詩歌的特點。而《古詩十九首》的游子思婦的作者,大都是文人士子,他們徘徊于禮教與世俗之間,既有合乎傳統禮教的價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選擇;時而有違禮之言,但見不到違禮之行,不及于亂。游子即使決心"蕩滌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對燕趙佳人,又"沉吟聊躑躅"。(《東城高且長》)妙齡女子先是埋怨對方的迎娶過遲,但隨即又表白:"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冉財孤生竹》)如果說游子從立功立名轉向佳女美酒體現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趨勢,那么徘徊于禮教世俗之間的做法,則是東漢士林風氣的折射。
- 上一篇:國際工程結構模式及選擇探討論文
- 下一篇:儒學社會與社會學的關系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