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牡丹亭劇本結(jié)尾的研究
時(shí)間:2022-05-09 04:45:00
導(dǎo)語:有關(guān)牡丹亭劇本結(jié)尾的研究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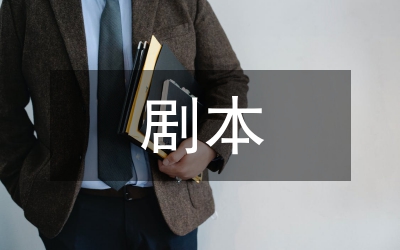
《牡丹亭》又名《還魂記》,完成于明萬歷26年(1598年)至今已經(jīng)四百余年,是湯顯祖的代表作,湯顯祖本人也對(duì)該作頗為得意,云:“一生四夢,得意處唯在牡丹。”而似乎正如湯顯祖所期望的那樣,這部傳奇一直受到文學(xué)界和戲劇界的重視。很少有古典劇作像《牡丹亭》這樣在舞臺(tái)上常演不衰,受到不同時(shí)代觀眾的歡迎。本世紀(jì)以來,學(xué)術(shù)界在《牡丹亭》的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對(duì)《牡丹亭》的思想藝術(shù)價(jià)值進(jìn)行了更加深刻、更加哲學(xué)化的闡述這也使得更多的讀者和觀眾更好地認(rèn)識(shí)和理解了這樣一個(gè)古典劇作。然而,作為一個(gè)戲劇作品,《牡丹亭》的魅力更多地應(yīng)該體現(xiàn)在其舞臺(tái)展示上,戲劇演出是二度創(chuàng)作,是對(duì)戲劇文本精神的實(shí)現(xiàn)和創(chuàng)造,而對(duì)于經(jīng)典作品的詮釋更能反映出一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文化心態(tài)和審美趨向,以及這些趨向與社會(huì)或歷史的關(guān)系。在對(duì)文本的認(rèn)識(shí)已經(jīng)達(dá)到一定高度的時(shí)候,演出形式是否與之相適應(yīng)、相匹配呢?
一、發(fā)現(xiàn)一種現(xiàn)象
《牡丹亭》現(xiàn)存的演出多為昆曲演出,少數(shù)一些地方戲也將《牡丹亭》搬上過舞臺(tái),但也都是在昆曲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加工和改造而成,所以昆曲《牡丹亭》的演出可以看作是《牡丹亭》的現(xiàn)存演出方式。
全國的六大昆曲團(tuán)體雖然各有其特點(diǎn)和代表劇目,但《牡丹亭》作為經(jīng)典是每個(gè)劇團(tuán)都能夠在舞臺(tái)上演的,經(jīng)過長期的演變可流傳,《牡丹亭》最終成為昆曲的代表劇目,這是一個(gè)現(xiàn)存的事實(shí)。在搬演《牡丹亭》上最具代表性、最突出的是江蘇、上海一帶的團(tuán)體,當(dāng)然,因?yàn)槔デ郧宕_始衰落,曾一度瀕臨滅絕,所以作為昆曲代表劇目的《牡丹亭》處境也不甚美妙(民國時(shí)期雖然也有《鬧學(xué)》、《驚夢》等出目得以演出,但總體來講是非常有限的),昆曲再次較為自由而活躍地發(fā)展不過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并且奠定了《牡丹亭》在當(dāng)今舞臺(tái)上的面貌。
《牡丹亭》從誕生到今天經(jīng)歷了四百多年的演出歷史,發(fā)展至今日,演出形式大致有兩種:折子戲和整本演出,這里的整本演出不光指全本(事實(shí)上,真正的全本演出是極少數(shù)的),也包括不同創(chuàng)作者對(duì)其不同的理解而加以改造后的演出。
以江蘇昆劇院和上海昆劇團(tuán)為例,在最近二十多年的舞臺(tái)實(shí)踐中就有過多種版本的《牡丹亭》演出,1981年,江蘇昆劇院上演的《牡丹亭》為:游園、驚夢、尋夢、寫真、離魂五出。上海昆劇團(tuán)1982年公演的《牡丹亭》為:閨塾訓(xùn)女、游園驚夢、尋夢情殤、倩魂遇判、拾畫叫畫、叫畫幽遇、回生拷園七場。1993年,上海昆劇團(tuán)重新排演了《牡丹亭》,這次演出在導(dǎo)演、舞美方面作了較大的創(chuàng)造,其劇本內(nèi)容分為:花神巡游、游園驚夢、寫真尋夢、魂游冥判、叫畫幽會(huì)、掘墳回生。(1)
通過這幾次演出的比較,雖然各種演出都各有側(cè)重各有創(chuàng)造,但是他們對(duì)與演出內(nèi)容的選擇大都是到《回生》結(jié)束,江蘇八一年版的甚至至《離魂》止,連一個(gè)可以由“回生”完成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都舍棄了,這當(dāng)然有當(dāng)時(shí)具體的社會(huì)歷史環(huán)境的原因,無論如何,這些演出都在《回生》之前做文章,對(duì)《回生》之后的內(nèi)容幾乎沒有涉及,有的,也只是輕輕帶過,只表現(xiàn)最后的《圓駕》只是人為的為演出安上了一個(gè)“尾巴”,換言之,這些演出雖然是整本,但實(shí)際上還是原有折子戲的的連綴,或是以折子戲?yàn)榛A(chǔ)的改編,都沒有離開折子戲限定的范圍。
1999年,上海昆劇團(tuán)排演過一臺(tái)三本的《牡丹亭》力圖重現(xiàn)原著面貌,但是最近的一次上海昆劇團(tuán)為入選“國家舞臺(tái)藝術(shù)精品工程”而復(fù)排《牡丹亭》,在曾經(jīng)1999年三本的基礎(chǔ)上縮編為兩本,由于時(shí)間和容量的限制,最終在采納了各方面的意見之后,還是將《回生》之后的內(nèi)容刪去,集中精力豐富和完善之前的部分,到此為止,似乎是畫了一個(gè)圈,又回到了原點(diǎn),《回生》似乎是《牡丹亭》演出中難以突破的關(guān)口。
二、原因是什么
其實(shí),整本《牡丹亭》至《回生》結(jié)束不過是前35出,其后還有洋洋20出的內(nèi)容,是一小半,目前的情形,讓后面20出更多地只能作為案頭讀物,這樣似乎有些遺憾,但是觀察《牡丹亭》的演出史,我們會(huì)看到康熙末葉以迄乾嘉之際,昆劇進(jìn)入折子戲時(shí)代,從有案可考的的文獻(xiàn)資料來看,《牡丹亭》至少在清朝中葉的折子戲演出中就開始偏重《回生》之前的部分,(至于之前的家班演出和一些作家對(duì)其進(jìn)行的刪改的具體情況,已經(jīng)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是更多地對(duì)《回生》之后部分的舍棄),及至后代數(shù)百年間,依著這個(gè)路子一直走了下來,數(shù)代的藝術(shù)家對(duì)于《牡丹亭》都作了這樣的選擇,一定有其原因。
原因之一,昆曲與《牡丹亭》的結(jié)合。
《牡丹亭》剛剛誕生時(shí),在湯顯祖的主持下進(jìn)行的當(dāng)是全本的演出,石韞玉說:“湯臨川作《牡丹亭》傳奇,名擅一時(shí)。當(dāng)其脫稿時(shí),翌日而歌兒持板,又一日而旗亭樹赤幟矣。”湯顯祖在《七夕醉答君東二首》中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huì),自掐檀痕教小伶。”(2)《牡丹亭》完稿后湯顯祖便開始指導(dǎo)伶人演出《牡丹亭》,但那時(shí)的演出情況如今已經(jīng)不得而知,各種零星的記載卻明顯地表示這些演出忠實(shí)于湯顯祖的原本。
不管湯顯祖的《牡丹亭》是否為昆山腔而作,昆山腔選擇《牡丹亭》并將之迅速推廣卻是個(gè)不爭的事實(shí)。
昆山腔,又稱昆曲,約于元末明初產(chǎn)生在江蘇昆山一帶,腔調(diào)圓潤柔美,咬字清楚,表演細(xì)致,身段動(dòng)作和歌唱結(jié)合得很緊,舞蹈性強(qiáng),其伴奏樂器主要是笛子,有時(shí)用三弦和月琴。這是一般對(duì)昆曲特征的描述,從我們對(duì)昆曲的感性認(rèn)識(shí)也可以看到,昆曲柔麗婉轉(zhuǎn),抒情性強(qiáng),唱段尤以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情感見長,所以昆曲表現(xiàn)抒情寫意的場面是非常適合的。
而綜觀《牡丹亭》中各出目的內(nèi)容,顯然在回生之前的《驚夢》、《尋夢》等顯得如夢如幻,著重表現(xiàn)“至情”的美好,這些戲抒情多于敘事,矛盾沖突隱含而不尖銳外露,所以最適合昆曲表現(xiàn),昆曲藝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驚夢》、《尋夢》等加以舞臺(tái)表現(xiàn)就不足為怪了。至于《回生》之后的部分則是回到了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矛盾之中,柳夢梅與杜寶之間的斗爭是兩種思想之間的斗爭,是新事物戰(zhàn)勝舊事物的艱難過程,反映社會(huì)問題多于男歡女愛,這些部分的自然就偏重寫實(shí),卻不是昆曲所擅長的,這種劇作前后風(fēng)格的不統(tǒng)一,造成昆曲演出對(duì)其進(jìn)行取舍,雖然昆曲也有很多表現(xiàn)日常生活的小戲,但究竟不是主要,況且在一個(gè)戲中前后使用反差強(qiáng)烈的手法,對(duì)于昆曲這種成為“雅樂”的劇種來說也太過冒險(xiǎn)。
事實(shí)上在《牡丹亭》與昆山腔的結(jié)合過程中,為了對(duì)其中不適合昆曲演出的情節(jié),包括曲詞加以刪改,許多劇作家和藝人都和湯顯祖之間有過爭論甚至斗爭,這些竄本所表現(xiàn)出來的神韻和趣味特色及思想深度都與原作無法相比,甚至有些是誤讀,但是這些竄改本的最大貢獻(xiàn)在于使得《牡丹亭》更加適合昆曲舞臺(tái)演出,使《牡丹亭》在昆曲舞臺(tái)上站穩(wěn)了腳跟,進(jìn)而成為昆曲最重要的曲目之一。
所以,昆曲與《牡丹亭》的緊密結(jié)合,使得舞臺(tái)上流傳下來的折子戲以《回生》之前的內(nèi)容為主,經(jīng)過歷代藝術(shù)家的揣摩和加工越發(fā)成熟精致,集中了昆曲最高的表演藝術(shù),而那些昆曲不常演的的折子,便漸漸被忽視,沒有流傳下來的演出可參照,缺少積累,使得后代演員的創(chuàng)造無據(jù)可依。同時(shí),現(xiàn)今的昆曲與經(jīng)過魏良輔改革后的昆山腔相比基本沒有什么變化,依然適合抒情寫意的表達(dá),所以演出到《回生》結(jié)束就有它的道理了。
文本與其所依托的載體之間的矛盾,使得全本《牡丹亭》的演出面臨許多困難,而今日,如何在現(xiàn)代的劇場里體現(xiàn)昆曲又是一個(gè)新的問題。
原因之二,觀眾欣賞習(xí)慣的驅(qū)使。
五十五出的《牡丹亭》,不言而喻是一個(gè)鴻篇巨制,包容著愛情、社會(huì)、哲學(xué)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其中單獨(dú)一樣拿出來都足以成為一個(gè)完整而獨(dú)立的篇章,完成一個(gè)好看而深刻的戲。但是湯顯祖卻一股腦兒地將這些都放到《牡丹亭》這樣一個(gè)作品當(dāng)中,令觀眾看來難免有目不暇給之感,太大的容量帶來的是一種無形卻實(shí)在的壓力。
事實(shí)上,對(duì)于一般觀眾而言,一個(gè)死去活來,纏綿浪漫又有點(diǎn)意味可以思考的愛情故事已經(jīng)足以滿足他們的欣賞需要,《牡丹亭》到《回生》止已經(jīng)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務(wù),之后的戲由于劇作風(fēng)格的原因容易破壞觀眾的興趣,太多的枝節(jié)也容易產(chǎn)生疲勞,雖然與原作而言損害了不少,但是對(duì)于觀看者來說,劇作的意謂層面上的東西似乎與他們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關(guān)心的人就更少了,演出者能夠獲得最佳效果的節(jié)點(diǎn)就在《回生》,加之《牡丹亭》曲詞過于文雅工整,理解起來頗為艱澀,能懂者本就不多,若太長則尤為不可,所以若是硬要搬演后面的戲,則說不定適得其反。這也正說明了為什么湯顯祖極力反對(duì)竄改《牡丹亭》而最終還是讓竄改本在舞臺(tái)上大行其道。
原因之三,各種社會(huì)歷史環(huán)境。
雖然全本演出《牡丹亭》有許多困難,但是在演出史上還是存在一些全本或接近于全本的演出的。
在昆曲盛行的年代,“四方歌者皆宗吳門”,在昆曲如此興盛的前提下,《牡丹亭》自然也會(huì)隨著流布廣遠(yuǎn),在這種情況下,偶爾會(huì)有機(jī)會(huì)讓全本《牡丹亭》得到展示的舞臺(tái)。
當(dāng)時(shí)主要有兩種演出樣式,一種是家樂、一種是營業(yè)性的戲班,戲班主要是在社會(huì)上演出,以獲得收益,所以其觀眾也多為下層百姓,因而,搬演全本的機(jī)會(huì)較少,而家樂則是由士大夫豢養(yǎng),供廳堂娛樂,士大夫們又能文通墨,所以家樂最有可能上演全本《牡丹亭》。
全本演出過《牡丹亭》全本的家樂據(jù)考證可能有:其一、鄒迪光家班,原因是鄒本人對(duì)湯顯祖十分尊重,他的家班演出曾邀請(qǐng)湯顯祖前往觀看,所以有此一說。其二、吳越石家班,其演出“一字無遺,無微不極。”另外還有些串客也唱過全本,但這些全本演出遠(yuǎn)遠(yuǎn)不及刪改本的演出的普遍。(3)
待到折子戲盛行之時(shí),根據(jù)史料記載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現(xiàn)今所存折子戲的模樣了,換言之,折子戲一盛行,幾乎就斷絕了全本《牡丹亭》演出的機(jī)會(huì)。及至后來昆曲日漸式微,按照全本演出《牡丹亭》簡直就是一種奢望,低迷的昆曲根本負(fù)擔(dān)不起巨大而冗長的演出了。
民國時(shí)期,昆曲早在長期的演變中脫離觀眾,加上這一時(shí)期反對(duì)舊文化思潮的影響,昆曲進(jìn)入了最低谷,瀕臨滅絕的邊緣,全國找不到一個(gè)純粹的昆曲戲班,在及少數(shù)的昆曲演出中,《牡丹亭》占據(jù)著一個(gè)重要部分,而此時(shí)能演的只有一些經(jīng)典的折子戲了,正是《驚夢》等折子戲給昆曲提供了一個(gè)生存的土壤,不至于從人們的視野中徹底消失,為昆曲爭取觀眾作出了貢獻(xiàn),也顯現(xiàn)出《回生》之前的這些折子戲在表演藝術(shù)上的高超,后人難以逾越。
解放后,因?yàn)檎螌?duì)文藝的直接指示,使得文藝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十五貫》的成功使得昆曲得到了國家領(lǐng)導(dǎo)人的重視,昆曲的活躍也帶來了《牡丹亭》演出的活躍,但是這種活躍是有局限的,由于受到行政命令的直接指導(dǎo),演出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舞臺(tái)凈化”要求使原來折子戲中的某些曲詞被刪除,有“不良傾向”的睡魔神、陰曹地府等也被凈化,可以演出的內(nèi)容僅限于對(duì)封建惡勢力抗?fàn)幍摹洞合泗[學(xué)》、《游園驚夢》、《拾畫叫畫》等折子,這些也都是在原有折子戲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篩選,至于后半部分的演出,沒有政府的具體指示,任何個(gè)人都是不好拿捏“分寸”的,估計(jì)連考慮的空間都沒有。
直至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文藝生活才得以正常化,但是長期的演出習(xí)慣的沿襲,這一時(shí)期出現(xiàn)的好幾個(gè)版本的《牡丹亭》演出都還停留在折子戲的連綴上,從一種思維中解脫畢竟需要時(shí)間,并且,當(dāng)時(shí)戲劇的演出剛剛經(jīng)過了一場浩劫,正需要修養(yǎng)恢復(fù),而這種回歸傳統(tǒng)的做法正合適,創(chuàng)新的念頭還沒有真正萌芽。
直到上世紀(jì)末,文化的開放讓世界完整的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對(duì)于傳統(tǒng)人們開始懷疑并重新解讀,于是出現(xiàn)了上演全本《牡丹亭》的嘗試,雖然最終的結(jié)果并不如期望中的那樣美好,但不管怎樣,這起碼都應(yīng)該是一種文化心態(tài)的進(jìn)步。
當(dāng)然,思想意識(shí)進(jìn)步了,禁忌放松了,經(jīng)濟(jì)允許了,條件成熟了,新的問題又隨之出現(xiàn)了,社會(huì)生活的快節(jié)奏催化了文化的快餐化,各種傳媒和娛樂手段最大限度的刺激人的感官,對(duì)于昆曲這種需要時(shí)間和耐心來欣賞的藝術(shù),則顯得太不經(jīng)濟(jì),昆曲面臨又一種尷尬,作為經(jīng)典的《牡丹亭》故事依然是感人的,但能夠在快節(jié)奏的社會(huì)以其自身魅力吸引觀眾的還是那些經(jīng)典的折子戲,《回生》之后的戲有可能思考它的二度創(chuàng)作了,但是留給創(chuàng)作者的空間太小,不能在短時(shí)間內(nèi)創(chuàng)造出能與傳統(tǒng)折子戲相匹配的表演藝術(shù),往往讓這類的嘗試失敗,上世紀(jì)末全本演出最后的結(jié)果追究到底還是因?yàn)樗囆g(shù)被急功近利所殘害。
三、后二十出的價(jià)值
《牡丹亭》被認(rèn)為是湯顯祖高舉“情”的旗幟向“理”的世界宣戰(zhàn)的檄文,在開宗明義地表示創(chuàng)作這個(gè)劇本的目的是反對(duì)“理學(xué)”的情況下,湯顯祖用一個(gè)“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極至的愛情故事來闡發(fā)他的思想,在反對(duì)舊的理學(xué)秩序的同時(sh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社會(huì)觀,即關(guān)照人性,從人的發(fā)展和需求出發(fā)的社會(huì)道德觀,湯顯祖塑造了杜麗娘這樣一個(gè)鮮活可感的人物,寄托著自己的藝術(shù)理想,“兵風(fēng)鶴盡華亭夜,彩筆鸚銷漢水春。天道到來哪可說,無名人殺有名人。”杜麗娘正是這樣打動(dòng)了古今的讀者、觀眾。
作品這種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完成僅僅靠到《回生》結(jié)束的一個(gè)愛情故事是不足以做到的,其實(shí)像這樣一種可以超越生死的愛情故事,感人則感人,但并不獨(dú)特,在中國古代的戲劇作品中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比如《倩女離魂》等),《牡丹亭》本也是根據(jù)明代話本改編而來,之所以《牡丹亭》成為經(jīng)典,不在于它這個(gè)故事,其主旨也不僅限于反封建,他超越前人的地方還在于它獨(dú)特的“情”,它所提出的人性獨(dú)立的主張。所以,可以說《回生》之前是情感層面的鋪墊,《回生》之后則是思想意蘊(yùn)上的提升,若沒有后半部分,《牡丹亭》就不是完整的《牡丹亭》。
事實(shí)上,除了杜麗娘,另一個(gè)人物柳夢梅在劇中的分量,以及他在體現(xiàn)湯顯祖思想上的地位是和杜麗娘不相上下的,如果說杜麗娘更多的是歌頌了“至情”,而柳夢梅的出現(xiàn)著重反對(duì)了“理”,對(duì)于柳夢梅,有些觀點(diǎn)說他前不及張生,后不及寶玉,思想平庸,配不上杜麗娘。作為藝術(shù)形象,其生動(dòng)性也許不及張生、寶玉,但從對(duì)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賤視和批判來說,他倒堪稱寶玉的先輩。柳夢梅是一個(gè)飽學(xué)之士,“受雨打風(fēng)吹”的貧寒生活,使他深思唐代的韓愈做了一篇《送窮文》,柳宗元寫了一篇《乞巧文》,為什么到他這個(gè)柳宗元的二十八代玄孫,其間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仍然“不曾乞得一些巧來”,“送的個(gè)窮去”?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改革現(xiàn)狀的強(qiáng)烈要求,使他把自己比作傲雪的梅花。要沖開冰雪般嚴(yán)酷的黑暗世界,敢于批判尊孔談經(jīng)、“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謬論。(4)與杜麗娘相比較,柳夢梅顯得更加真實(shí),杜麗娘是一個(gè)夢,一份情,柳夢梅雖有夢的成分,有理想主義的光彩,但總體上他不脫離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湯顯祖情與理斗爭中,情的世界與理的世界的溝通都是通過柳夢梅來完成的。柳夢梅有兩重性,在與杜麗娘夢中相會(huì)、和鬼魂相戀時(shí)的大膽癡情,表現(xiàn)出他不畏權(quán)貴的反抗性格,但同時(shí)柳夢梅又熱衷功名,急近女色,是一個(gè)實(shí)實(shí)在在的“世俗中人”。柳夢梅的完整形象在前35出是不能完整體現(xiàn)的,加之許多的演出為了“單純”起見,只保留《驚夢》、《玩真》等有柳夢梅出現(xiàn)的折子,只體現(xiàn)了一個(gè)“理想主義”的柳夢梅,而且很不完整,這些演出往往讓柳夢梅退到一個(gè)還不如春香的配角地位。舍棄了后二十出的表演,對(duì)柳夢梅的形象是一個(gè)極大的損害,同時(shí)也損害了劇本的應(yīng)有之意。
湯顯祖認(rèn)為:“無情不足于生夢,無夢則不足以見真情。”情是文學(xué)的基礎(chǔ),夢是文學(xué)的境界。“情”在湯顯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湯顯祖的心中心中燃起了一盞“情”的明燈,讓他一生都在執(zhí)著地追求和實(shí)踐著“至情”的社會(huì)理想。“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一個(gè)“情”字道破人之為人的秘密,是極為宏大的人文關(guān)懷,從四百年前一直關(guān)照到今天。這讓我們試圖深入分析和揭示湯顯祖之“情”的層層內(nèi)蘊(yùn)。首先,它是與程朱理學(xué)所宣場的理相抗衡的(不是"對(duì)立",湯思想中的情與理既有對(duì)立的一面,又有統(tǒng)一的一面);其次,湯氏所贊美的“情”已包含著恩格斯所說的“現(xiàn)代的成分”,帶有鮮明的近代色彩;再次,湯氏所推崇的的“情”又始終帶有夢幻色彩,并在夢的自由境界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同時(shí),《牡丹亭》與王實(shí)甫《西廂記》和曹雪芹的《紅樓夢》及洪昇的《長生殿》相比較,也使同類作品相形見拙,難以企及。《牡丹亭》縱橫馳騁在情的天地,自由遨游在情的海洋。因此,時(shí)賢前哲有這樣一種定性評(píng)價(jià):湯顯祖是一位高舉“情”大旗向明代黑暗的封建社會(huì)及吃人的封建禮教沖鋒陷陣的勇士。
但是湯顯祖并沒有被情的海洋所吞噬,他絕不是為言情而言情,其言情的最終目的是關(guān)注理,我們已經(jīng)說過,《牡丹亭》的前半部分是以“情”為中心的感性鋪墊,而后半部分則是理性的升華,在《榜下》、《硬拷》等出目中借柳夢梅之口表達(dá)出湯顯祖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憤懣之情,人欲高于天理的主張。同時(shí)應(yīng)該看到湯顯祖反對(duì)現(xiàn)實(shí)中有悖人性的秩序,但是他不反對(duì)應(yīng)有的社會(huì)秩序,從他對(duì)杜寶勸農(nóng)、平亂和柳夢梅取得功名、皇帝裁決柳杜之事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
中國文學(xué)歷來就有鮮明的現(xiàn)實(shí)性特征,“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以形象的文字畫面展示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湯顯祖繼承和發(fā)揚(yáng)了自古以來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始終關(guān)注著社會(huì)的風(fēng)云,積極倡導(dǎo)著時(shí)代的精神,精心描繪著世俗的生活。首先,《牡丹亭》表現(xiàn)了哲學(xué)意蘊(yùn)上的更高的人生,文學(xué)藝術(shù)面對(duì)的是社會(huì)人生,描寫社會(huì)人生的目的是“為人生”,這是我國古代大多數(shù)戲劇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湯顯祖認(rèn)為“發(fā)夢中之事”的戲曲必須對(duì)社會(huì)人生發(fā)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其次,情真,即感情的真摯。戲曲“之能動(dòng)人者,惟在真切。”古人通過對(duì)夢的研究發(fā)現(xiàn):情真莫過于夢。所以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牡丹亭》也是一出以情感關(guān)照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力作。
在明代中晚期,舊的價(jià)值觀念已經(jīng)遭到破壞,封建社會(huì)制度本身的許多無法調(diào)和矛盾日益顯露,作為湯顯祖等具備真知灼見的高層知識(shí)分子,對(duì)這一切早已有了敏銳的覺察,但是作為封建統(tǒng)治機(jī)構(gòu)內(nèi)在組成,他們不能真切地認(rèn)識(shí)這一切不合理現(xiàn)象背后根結(jié)所在,他們的苦悶彷徨在于試圖尋找一種有理據(jù)地解決之道。所以,在新的價(jià)值觀念尚未建立起來之前,情的激揚(yáng),最終走向理的回歸,有其客觀必然。當(dāng)然,湯顯祖因其自身的局限而未能明確地提出他的理性主張,他的生命追求實(shí)際上是對(duì)一個(gè)理想世界的渴望,這個(gè)理想世界又是以情為內(nèi)涵的,但這種情又是受理性所支配的,這種秩序世界在精神層面和現(xiàn)實(shí)層面都是復(fù)雜的,這種復(fù)雜性源于他對(duì)傳統(tǒng)秩序的理想化期待、對(duì)現(xiàn)實(shí)秩序的理性認(rèn)識(shí)、對(duì)最高人生境界的執(zhí)著探索。湯顯祖在理想與現(xiàn)實(shí)、愿望與期待、背叛與以依賴中彷徨苦悶。
《牡丹亭》中對(duì)這一切的體現(xiàn)都集中在《回生》之后的部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表達(dá),理性的回歸或許是《牡丹亭》更高的價(jià)值所在。同時(shí),能支持《牡丹亭》進(jìn)行四百多年的演出,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五十五出的劇作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深刻內(nèi)涵,這些思想的光芒從每一出精彩的折子戲里折射出來,讓觀眾感受并認(rèn)可,建立在這樣偉大作品之上的演出,才能經(jīng)受住時(shí)代更替,潮流洗禮。
四、尋找合適的表現(xiàn)方式
《牡丹亭》是一出經(jīng)典,所謂經(jīng)典應(yīng)該:與時(shí)俱變、百變不離其宗。一代有一代的創(chuàng)造,隨著時(shí)代的理解及其審美取向而變化是《牡丹亭》生命延續(xù)的動(dòng)力,尊重和正確認(rèn)識(shí)它本來的主題精神、文化內(nèi)涵是其生命延續(xù)的支點(diǎn)。
所以對(duì)于《牡丹亭》,其《回生》之后的演出是重要的而且是有價(jià)值的,對(duì)于這樣一個(gè)經(jīng)典作品不作完整的舞臺(tái)呈現(xiàn)是一個(gè)很大的缺陷,也是不太正常的現(xiàn)象。二度創(chuàng)作既然是創(chuàng)作,就鼓勵(lì)創(chuàng)造性的突破,《回生》之后的戲少有傳統(tǒng)折子戲可依照。這給創(chuàng)作增加了難度,但同時(shí)又讓創(chuàng)作者少了束縛,可以自由發(fā)揮。
我們已經(jīng)分析過《牡丹亭》的舞臺(tái)演出僅限于《回生》結(jié)束的種種原因,會(huì)發(fā)現(xiàn)時(shí)至今日,觀眾對(duì)于戲劇的審美要求已經(jīng)是多方面的,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于欣賞一個(gè)純粹的、長期不變的愛情故事,對(duì)于《牡丹亭》這樣的作品,他們希望能從中看到更多的人文關(guān)懷,能夠關(guān)照到他們的生活,能夠有值得思考的東西出現(xiàn);而社會(huì)環(huán)境方面,也算進(jìn)入了一個(gè)較好的時(shí)期,由于聯(lián)合國的原因,昆曲漸漸為人們所關(guān)注,多元化發(fā)展的文化局面讓創(chuàng)作者有可能嘗試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對(duì)《牡丹亭》后二十出的二度創(chuàng)作進(jìn)行探索。
上世紀(jì)末,東西方幾乎同時(shí)出現(xiàn)了三個(gè)版本的《牡丹亭》演出,除了美國導(dǎo)演PetterSellar與譚盾等人合作的具有后現(xiàn)代解構(gòu)與拼貼性質(zhì)的實(shí)驗(yàn)演出之外,比較完整而嚴(yán)肅的體現(xiàn)《牡丹亭》全貌的有兩個(gè)。
1998年,美國林肯藝術(shù)中心出資,邀請(qǐng)導(dǎo)演陳士爭與上海昆劇團(tuán)合作,將全本五十五出《牡丹亭》搬上舞臺(tái),但這個(gè)全本的演出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在中國公演,直到次年,出現(xiàn)在美國林肯藝術(shù)中心的舞臺(tái)上,但主創(chuàng)人員已經(jīng)不再是原班人馬,導(dǎo)演找到了一些旅美的昆曲演員和京劇、川劇的演員湊成了一個(gè)團(tuán)隊(duì),演出的表現(xiàn)方式大膽多樣,導(dǎo)演陳士爭的闡述可以表達(dá)出這個(gè)戲在舞臺(tái)呈現(xiàn)上的特征:此劇不能只當(dāng)作昆曲來看,它事實(shí)上是一個(gè)以湯顯祖?zhèn)髌鎰∽鳛橹行牡奈枧_(tái)創(chuàng)作,昆曲雖然是其中最重要的表演形式,但畢竟昆曲在這兒只不過是用來表現(xiàn)劇本內(nèi)容的媒介之一。顯然,這一個(gè)版本的《牡丹亭》的排演,導(dǎo)演試圖拓寬道路,尋找一種適合《牡丹亭》的表現(xiàn)方式,而不受昆曲所范囿,將不同的中國戲曲、曲藝表演藝術(shù)綜合或者累加起來表現(xiàn)《牡丹亭》一個(gè)戲,這樣的嘗試在此之前還沒有過。
同樣是在1999年,上海昆劇團(tuán)再次將全本《牡丹亭》搬上舞臺(tái)。由上昆老中青三代演員聯(lián)袂出演,這一次的的演出力圖展現(xiàn)湯顯祖原本的神韻,在編劇上尊重原著,采取只減不增的“縮編”方法,選擇了能夠反映出原作全貌的幾十出戲,刪去一些繁多的枝節(jié),力圖不損害原作精神。這次演出自然是全部以昆曲形式表現(xiàn),主創(chuàng)人員嘔心瀝血,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新的昆曲《牡丹亭》。為了前后的一致性,對(duì)于杜寶、陳最良等一些過去表現(xiàn)得簡單、平面化的人物,進(jìn)行重新塑造,杜寶不再是蠻橫專制的封建家長制的代表,他雖思想頑固,但同時(shí)也是個(gè)正直的清官,以國家利益為重,為保衛(wèi)國家不惜犧牲;陳最良也不再是一個(gè)愚蠢的腐儒,他有善良的一面,春香的頑皮他雖氣惱,但還是很疼愛,對(duì)人物這樣的重新解讀是值得肯定的。
這兩全本《牡丹亭》的演出給出了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打破常規(guī)不拘泥于昆曲,采取一切與表達(dá)作品主旨有益的方式;另一種則是在昆曲的世界里發(fā)掘可能性,努力打造昆曲《牡丹亭》,尋找昆曲與《牡丹亭》的最佳結(jié)合。兩種方法是對(duì)經(jīng)典作品的兩種態(tài)度,各具優(yōu)勢,又各存缺憾。林肯中心的演出版將五十五出全本搬上舞臺(tái),完成了一個(gè)浩大的工程,其不拘一格的表現(xiàn)手段也讓人耳目一新,但是這種方式難免削弱《牡丹亭》作為一個(gè)戲劇作品的系統(tǒng)性,例如:《寫真》、《玩真》二折戲用評(píng)彈演出,難免突兀,且作為重要場次,缺少了舞容歌聲的戲曲表達(dá)未免可惜。同時(shí),導(dǎo)演雖說不把該劇當(dāng)作昆曲,但昆曲還是劇中主體的表演形式,整個(gè)戲還是昆曲的路數(shù),并沒有完成對(duì)昆曲的突破。而上昆1999年版的《牡丹亭》雖在人物塑造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一批表演藝術(shù)家的精彩表演也讓這次演出的可看性大大增強(qiáng),但是這次演出沒有解決好劇作前后風(fēng)格不一致的問題,因而,《回生》之后的戲依然不好看,也難免在2003年,這一部分再次被砍掉,其實(shí)宣告了這次全本演出最后的不成功。
對(duì)于兩種解決方案,我個(gè)人偏向后者,即:昆曲演繹《牡丹亭》。畢竟幾百年的積累,昆曲《牡丹亭》已經(jīng)為大眾所熟知和接受,也沒有哪個(gè)地方戲在《牡丹亭》的表演上能夠超過昆曲,現(xiàn)在有不少人認(rèn)為昆曲就是《游園驚夢》,可見昆曲與《牡丹亭》在一般意義上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gè)整體,搬演全本《牡丹亭》還是昆曲更加合適。
如果使用昆曲進(jìn)行演出,在今天至少要解決兩個(gè)問題,第一個(gè)當(dāng)然就是昆曲表現(xiàn)與文本風(fēng)格的問題,既然《回生》之后少有折子戲可以依據(jù),給創(chuàng)作帶來諸多困難,但同時(shí)又留下更多的創(chuàng)造空間,其實(shí)四百多年的《牡丹亭》演出史,就是歷代藝術(shù)家不斷創(chuàng)造的過程,以上的兩個(gè)全本演出至少已經(jīng)作了這方面的探索,只不過是否合理和完善的問題。我想,對(duì)于昆曲《牡丹亭》全本演繹應(yīng)該有兩種道路,其一,圍繞昆曲,以一種統(tǒng)一風(fēng)格貫穿全劇,改造那些風(fēng)格不統(tǒng)一的部分;其二,本著原著的精神,豐富昆曲的表現(xiàn)手段,不必將昆曲限制在“如夢如幻”、“抒情重于敘事”的表達(dá)能力上,創(chuàng)作者完全可以大膽發(fā)揮,將《硬拷》、《問路》等寫實(shí)、通俗化的折子的特點(diǎn)表達(dá)出來,主旨體現(xiàn)出來。其實(shí),昆曲在表現(xiàn)生活化的、有機(jī)趣的內(nèi)容上的能力一點(diǎn)也不亞于其他劇種,昆曲本身也有許多這類的小戲和折子戲,對(duì)于《牡丹亭》這樣的經(jīng)典的解讀,不能常規(guī)地、單純地從“浪漫主義”或是“現(xiàn)實(shí)主義”出發(fā),原本中國戲曲也就沒有這樣的劃分方式,中國戲曲大多是浪漫主義的抒情性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沖突性相結(jié)合的。我認(rèn)為,上昆版的全本演出所出現(xiàn)的問題就在于其徘徊于兩種“主義”兩種“風(fēng)格”之間,因?yàn)樵鳜F(xiàn)實(shí)性強(qiáng)烈的風(fēng)格,所以二度創(chuàng)作上難于沿襲前半部分的抒情性特色,但是又不敢于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表現(xiàn)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于是呈現(xiàn)在舞臺(tái)上的作品就呈現(xiàn)出一種左右不是的尷尬,又怎么能好看?
昆曲《牡丹亭》在今天面臨的另一個(gè)問題是:現(xiàn)代化的舞臺(tái)聲光效果如何與古老的昆曲相結(jié)合?這其實(shí)是中國戲曲必須共同面對(duì)的問題,但在昆曲這里尤為突出而已,作為“百戲之祖”的昆曲,代表了戲曲的程式化、寫意化高度成熟和完善,在這個(gè)自足的系統(tǒng)中,不需要任何外界燈光、音響等西方傳來舞臺(tái)手段,但今天的舞臺(tái)、劇場和觀眾的欣賞習(xí)慣都使得戲曲與這些現(xiàn)代化的聲光手段的碰觸難以避免,大多數(shù)的導(dǎo)演選擇了接受這些手段而運(yùn)用到戲曲當(dāng)中,從而也引發(fā)了許多的爭論。無論如何現(xiàn)代化的舞臺(tái)聲光手段只能是手段,對(duì)它們的使用要從為作品服務(wù)的角度出發(fā),不能因此而削弱了戲曲本身的表達(dá)力度。觀念的先進(jìn)和意識(shí)的現(xiàn)代化比單純使用現(xiàn)代化的舞臺(tái)手段更重要。
上世紀(jì)的最后幾年,東西方幾乎同時(shí)出現(xiàn)的三個(gè)《牡丹亭》的全本演出,不管存在怎樣的問題,都是有益的探索,這三個(gè)版本風(fēng)格內(nèi)容各有千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帶來長期的爭論,這些演出以各自的形式將《牡丹亭》介紹給世界的觀眾和文化,這一陣風(fēng)潮過去之后,曾有一段長久的寂靜,這寂靜應(yīng)該不是沉寂而是新一輪的醞釀吧,不論是發(fā)現(xiàn)問題還是得到啟發(fā),都是成果。
參考資料
(1)、(3)金鴻達(dá)《<牡丹亭>在昆曲舞臺(tái)上的流變》
(2)《湯顯祖詩文集》P735
(4)金登才《中國戲曲名著選讀》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