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批判到社會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轉變的精神實質
時間:2022-04-17 12:40:00
導語:從宗教批判到社會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轉變的精神實質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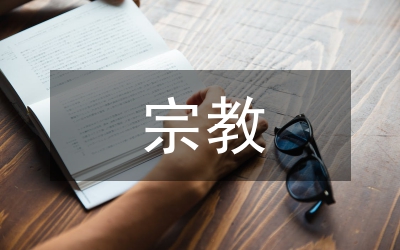
【正文】
[中圖分類號]B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8466(2000)06-0015-05
通常認為,在對近代哲學的批判和繼承中,特別是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批判繼承中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它的哲學的新的思維方式。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性的切入點是什么?為什么它要求社會批判?如果追索近代哲學所要完成的歷史使命,我們便發現:近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行宗教批判,中世紀的信仰與理性的二元對立變成了理性與現實的二元對立。馬克思認為,“宗教把人的本質變成了幻想的現實性,因為人的本質沒有真實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斗爭間接地也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慰藉的那個世界的斗爭”[1](P1)只有徹底的社會批判才能使宗教批判徹底化,因為真正被上帝所異化的是現實的人的生活及其本質。因而,上帝的秘密在于人及其社會--對宗教的批判最徹底的就是訴諸社會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使命。而“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1](P2)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揭露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的宗教批判始,實質是為了“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的社會批判。
一、宗教的理性批判
近代以來的啟蒙運動人們一般認為是理性啟蒙,聯系到當時宗教與哲學的張力關系,我們可以把啟蒙運動看作是對宗教的理性批判。
在中世紀理性是抽象的理性,主要是被用作論證上帝的存在,因此,“真理還不是現實世界的基礎”[2](P326),宗教與現實、教會與世俗、信仰與理性是二元對立的。對基督教而言,只有對上帝信仰的合法性,才能有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的合理性,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的合理性根據只能在對自身統一的人格神的上帝的信仰之中才能顯現出來。所以馬克思認為對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1](P1),只有揭示出自然、社會或人類精神的獨立本質、自我統一,才能使它們具有現實性的品格。
上帝在虛無中創造了自然、創造了物質世界:“上帝在它作為一個純粹的精神本體的理、道中,直觀其自身而在表現它自己的呈現事事物物的觀念世界,人作為由上帝所創造的有限心靈實體,也在上帝作為最高真理的照耀與制約中,而表現其形形色色的時空經驗世界”。[3](P5-P6)這種關于上帝的邏輯意義在近代哲學中形成了經驗論和唯理論。從經驗論這條線索上看,培根作為近代經驗論的創始人提出“二重真理論”,認為人的知識按來源說分為兩類:神學知識從天上降落,是神的啟示所激起,屬人的道德領域;從地下引起、由自然的光亮所激發的是哲學和科學知識,兩者互不干涉。他要為人的理性清理出一個適當的邏輯,以保證理性的恰當使用而實現科學和哲學的任務。[4](P344)洛克首先批判各種形式的天賦觀念論,認為一切觀念都是由感覺或內省而來的,人類的知識有三個層次:直覺的、解證的和感覺的。上帝的存在就是憑借解證而得的知識,故“任何命題只要和我們的明白的直覺的知識相沖突,則我們便不能把它作為神圣的啟示。”[5](P691)原始啟示則是上帝在人心上所直接印入的印象。所以自洛克開始已經用分析的方式表明對上帝的信仰是人類知識的一種。貝克萊否定心外之物的存在,認為人類知識的對象是各種觀念,“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觀念的復合”,“我亦不能在思想中設想任何可感物可以離開我對于它的感覺或感知。”[6](P504)所以“Sensiblethingsthereforearenothingelsebutsomanysensiblequalities,orcombinationsofsensiblequalities(感知的事物因而就是那些感知的條件或感知的條件的復合)”。[7]我們只能看到事物的現象而看不到它們的真實性質。人的感知是被動的、惰性的,而上帝就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感知。休謨認為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我們自己的感覺,最生動活潑的思想還是抵不上最遲鈍的感覺。至于在感覺之外,不管是物質實體還是像上帝那樣的精神實體是否存在,經驗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只能保持緘默,因為我們根本不能證實它們的本質、特征、能力和作用。對于上帝的存在只有靠啟示——宗教信仰不是知識經驗的對象,只是人們的生活情感的要求。
從唯理論這條線索上看,近代哲學的另一個開創者笛卡爾首先論證“我思故我在”,以此為其唯理論哲學的最高出發點:“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點以便存在,也不依賴任何物質性的東西”。[4](P369)但是因為“我懷疑”所以“我是不完滿的”,然而“認識比起懷疑來是一種更大的完滿性,……這應當是從一種事實上更加完滿的本性而來的。”“我是不能夠從我自己把這個觀念造出來的;因此只能說,是由一個真正比我更完滿的本性把這個觀念放進我心里來的,而且這個本性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滿性,……它就是上帝”。[8]上帝在笛卡爾那里不再作為信仰的存在,而是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觀念而存在。這同經驗論試圖把上帝作為人類知識的對象是截然不同的。斯賓諾莎的哲學可以被看作是在批判笛卡爾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沒有獲得清楚而且明晰的神的觀念之前,我們就不能確信任何東西,而在我們不知道我們本性的創造者是否欺騙我們以前,我們就不能有這種觀念”。[9](P51)人在進行理智活動時需要“天賦力量所制造的理智工具”即“真觀念”(也即斯氏所說的“神”)作為我們一切推理知識的本源。而神就是自然,是按照客觀必然性而活動的自然,“神的概念包含著必然存在”,“單獨考察神的本性,就可以知道神的存在”。[9](P61)我們具有神的觀念的客觀實在性既不是“形式地”(即存在于我們所具有的觀念所表象的東西之上,亦即真實地、實在地存在于我們的觀念之所本的對象上)包含在我們心中,又不是“超越地”(又譯“卓越地”:指存在于高于自己而且包含了自己的東西——作者注)包含在我們心中,并且它不能包含在其它事物中,只能包含在神自身中。萊布尼茨設計既不可分又是實在的“單子”(真正的實體)這個“形而上學之點”,認為萬物都是由精神性的“單子”組成,每一個單子都有知覺,全部單子都各自從每一可能的知覺中反映著宇宙;單子的數目是無限的,構成一個無窮序列,其中有“隱德萊希”、“靈魂”、“心靈”,直到最高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唯一創造其它單子的單子即上帝。“單子的自然變化是來自一個內在的本原,因為一個外在的原因不可能影響到單子內部”。[4](P478)人的認識當然也是單子內部的知覺活動所發出的(但它是如何知覺的——知覺原理是什么,這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人的知覺的連接是根據單子的記憶能力而造成的,這與動物無異,但人的“理性靈魂”或精神能使人與動物區分開,并認識人自己和上帝,形成對于必然和永恒真理的知識。憑著這種知識而達到的“反省的活動”“使我們思想到所謂‘我’,使我們觀察到這個或那個在‘我們’之內;而由于我們思想到自身,我們也思想到存在、實體、單純物或復合物、非物質的實體和上帝本身,理解到在我們這里是有限的東西在上帝那里則是無限的”。[4](P481)這些反省活動為我們的推理活動提供了主要對象。
從經驗論與唯理論的對比,我們看到:前者把上帝作為知識的對象,并最終被休謨所否認;后者把上帝作為人的觀念,由觀念進而知識。對唯理論來說存在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內在于人類觀念之中的上帝,何以可能超越于人類觀念之上(按現在流行的說話方式可以如此提問:上帝就是說上帝)?而對于經驗論來說,雖然它否定了在人的認識過程中有任何預成于人心的思維規則,但它把知識感性化、思維規律心理聯想化了,摧毀了知識基礎的堅實性。那么上帝能否作為人類的知識或觀念而存在?正是在對二者批判的前提下,康德“批判哲學”認為:認識分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與此相應,知識分為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人的知識是在感性與思維的相互規定中建立起來的,思維規律則是人們反思思維的結果。因為感官印象以“自在之物”為基礎,所以“思維規律在其對感官印象的關系中所產生的一切思維規定,雖然對感官印象是普遍而必然客觀有效的,但它們卻不反映感官印象的內部規律。”[3](P11)一切知識自感官始,進一步達到思維作為悟性的綜合,而終于理性,理性在經驗世界中把握不到超經驗的經驗統一性,從而一切自在之物和超驗的實在性皆不可知。上帝作為知識形態的形而上學的對象,康德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作為實踐理性的公設卻是有意義的(盡管在實踐理性中上帝是什么,我們仍然是不可知的)。至此,上帝是作為人的觀念或者還是作為人的知識仍然是一個懸案,這便是由黑格爾來完成的。黑格爾哲學認為,以往哲學把上帝(形而上學)觀念設置為知識的終結點的思維方式,要么從預成的諸如上帝的、天賦的、先天的觀念出發論證“確實可靠性”的知識,要么以知識經驗去理解上帶或形而上學觀念,這被他稱為“知性思維”和“物的思維”。它們把靈魂、世界、上帝這些屬于理性的理念當作表象,當作現成給予的題材。[10](P99)宗教是人類精神的自我異化,而從意識發展的諸環節上看,由于意識尚未達到“精神”階段,“宗教以這些環節的經歷過程為前提,并且是這些環節之單純的全體或絕對的自我或靈魂。”[11](P182)只有達到精神以自我為根據的絕對理念即全體的自由性與各環節的必然性的統一時,宗教才“消失”在其所起根據作用的環節當中。其實,就絕對意義而言,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理論理念和實踐理念的統一,生命的理念與認識的理念的統一)只能是人類意識的辨證理想或自的指向。可以說黑格爾完成了對宗教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但這并不是宗教批判的完成。
二、宗教的社會批判
如果說宗教不是正常的現象,那么產生這種不正常現象的社會也是不正常的。因此,只有徹底的社會批判才能是徹底的宗教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把宗教批判訴諸社會批判的基本思路。
對馬克思主義而言,經過了宗教的理性批判的“現實世界還不是真理的基礎”(對比黑格爾: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那里“真理還不是現實世界的基礎”)。近代以來,康德以前的哲學認為上帝至少是不可否認的,但與經院哲學不同,它們以肯定的方式理解人(也請注意:這里不能說經院哲學就是把人當作否定性的存在,它們否定的是人的現實存在;“否定人”和“人否定”是不一樣的)。黑格爾哲學想要指出的是,上帝的不可否定性是與人的自我意識的異化相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則要指出:如果把意識作為人的本質,那么“掌握了自己本質的人,僅僅是掌握了對象性本質的自我意識”,但那不是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2](P111-P112)宗教是人的自我異化,而人是社會性的存在,因此,宗教實質上是社會的自我異化。這就是說,以往的哲學的合理性在于揭示出宗教隱匿的小前提(自我意識中人的本質),其不合理性在于沒有揭示出宗教隱匿的大前提(社會中人的本質)。
費爾巴哈也把宗教歸結為“人跟他自己的本質的分裂”[13](P67):“人異于動物的本質,不僅是宗教的基礎,而且也是宗教的對象”[13](P30),“人的絕對本質、上帝,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本質”[13](P31)。然而,他所理解的人“就是理性、意志、心”[13](P34)。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他把人的本質理解為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類的本質(與動物相比照的“類”),而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費爾巴哈“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但是,毋庸諱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對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動’,……而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1](P50)
首先,宗教是人的意識與社會對立的產物。“宗教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1](P1)社會對人類而言是從來就有的,而意識任何時候都是人所意識到了的社會意識,意識作為社會的表現形式“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4](P83)只能在社會現實中而不是在與宗教的對立或和解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社會實踐伸展得有多遠,意識內容及其本質的展開就有多遠。正是在社會與人的意識的對立統一中,宗教才能產生與消滅。
其次,宗教同時直接的就是人與社會對立的產物。“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然而,“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產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1](P1)在“顛倒了的世界”里,人只能獲得“顛倒的世界觀”——宗教或異化了的自我意識,那么“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于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1](P2)在給“自由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個小組)的一封信中,馬克思也曾指出:應當從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中來批判宗教,而不是從宗教批判中來批判社會現實,否則,對宗教的批判就是一個無根的批判。而且,隨著以宗教為理論的被顛倒了的現實的消滅,宗教也將自行消滅。[15](P64)所以我們可以得出:只有經過社會批判的宗教批判才具有現實基礎,其理論才具有現實性同時也獲得真理性。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再次,宗教是人對“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會現實的幻想的自我意識,所以,徹底的宗教批判對社會批判的徹底性要求必然是:“對于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這種矛盾的方法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1](P17)”否則,宗教就將是一種永遠存在的現象。沒有自覺的社會批判必然產生宗教或宗教式的“幻想的批判”,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P40)
最后,馬克思主義將宗教批判訴諸社會批判,最終目的是為了從這種批判中揭示出隱藏著的人的本質,進而實現人的本質。而“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它不是一個既定的存在物,只有在社會關系和社會“歷史的進程”中才能得到理解,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因此,要實現人的本質只能訴諸不斷發展著的社會批判。我們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不是只針對某個特定現實社會的批判,而是對任何特定社會里的既定現實的批判。這樣,才能使人的本質作為既定的現實社會里的否定性而顯示出其自由的本質。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不是“在我們的牧師的領導下”,而是我們自己“處于自由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社會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6](P46)
與此相應,從對宗教的理性批判(揭示出人本質的表現即人的意識)到把宗教批判徹底化為社會批判(揭示并實現人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地完成了其世界觀的徹底轉變。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轉變
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在揭露宗教所蘊含的社會自我異化中,開始其社會批判的。我們不妨說它就是一種社會批判的哲學。其社會批判大致經歷了從意識形態批判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發展,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它是針對任何導致人的自我異化的現象進行批判的。一切批判必須是在人的社會關系中才是有意義的,這是因為:首先,社會及其結構是人的實踐所創造的,其制度、傳統既不是上帝的作品,也不是自然的作品,而是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的結果。其次,只有人的社會關系(或者納入人的社會關系之中)才是真正的“關系”,“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動物說來,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而存在的”。[1](P35)并且,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對人的社會關系必須持批判態度,在對現存社會的肯定性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社會的必然的否定性的理解。所以,這種社會批判是對任何社會的批判,惟其如此,人的本質才能揭示和實現出來。
正是對現存社會的批判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了世界觀的根本轉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批判要求從傳統哲學的“解釋世界”轉變到“改變世界”中來。“解釋世界”的哲學是一種離開實踐(”人的感性活動”)的思維,只有改變世界(“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才意味著社會批判的徹底化。“人的思維是否具有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1](P16)離開現實的人的社會,任何理論將只能變成上帝的置換物,只有改變世界才不至于使人的本質“迷失”于其所肯定和占有的對現實世界的解釋之中。
也正是在對現存社會的批判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表明了任何一個社會得以成立或被消滅的條件:一個社會在其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釋放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14](P82)這一方面結束了那種企圖設定“理性的千年王國”和烏托邦社會的空想,另一方面也結束了那種尋求最高統一性的哲學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結束的那種思維方式和空想只能是異化了的社會里的宗教式的幻想。所以,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批判預示著它是現代哲學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