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哲學與意識形態研究
時間:2022-03-06 09:40:00
導語:馬克思哲學與意識形態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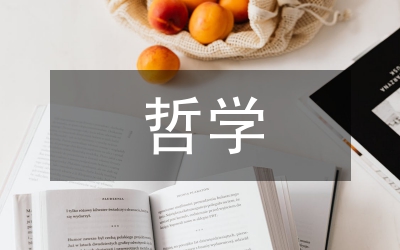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多年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直擔當著政治意識形態詮釋者的角色與功能,事實上,與意識形態的這種關系也關涉著馬哲學科的市場資源。但是,隨著諸多社會領域的分化(特別是經濟領域躍居為核心領域)而帶來的政治意識形態大一統局面的瓦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經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顯赫,不僅如此,從社會變革的趨勢看,這一功能還會不斷弱化。事實上,在學術意義上,馬哲近年來已不斷呈現邊緣化的境況。在這樣一種情勢下,究竟如何開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已成為令人困惑的問題。最近幾年學術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回撤到“馬克思哲學”,如果說前者是意識形態式的指認,那么后者則是一種本文性的指認,這種指認一方面試圖向馬克思的著述回復,另一方面,則是從學理上展開與當代哲學的對話與溝通,呈現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學術性的(至少看起來是學術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專業化”(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實現了“專家化”),據說這一趨向是為了回應當下學界所謂“思想淡出”的學術化走勢。筆者雖然一直是這一努力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但同時也心懷一種疑慮,那就是,當我們把馬克思哲學有意地從意識形態中區分出來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對象時,是否忽視了馬克思哲學與意識形態的應有的歷史性關聯,而這一關聯本身就應該是我們從事馬克思哲學學術研究時無法割棄的思想前提,換句話說,當我們撇開馬克思哲學與意識形態的應有關聯時,很可能同時也抽掉了馬克思哲學與時代的內在關聯。我越來越感覺到,學界關于這一時代意識形態淡化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弱化的判斷有些武斷,并且本身就是認同于某種意識形態的結果。
二
我們知道,正是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這一問題變得復雜起來。特拉西的意識形態(Ideology),即觀念學或觀念體系,還只是一個中性的稱謂,不附加價值判斷,馬克思正是通過對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批判,指出對任何意識形態的理解都必須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經濟政治關系為核心的人的實踐活動,正是通過這一路數,馬克思發現了傳統意識形態與經濟政治關系的反向的關聯,那就是意識形態總是掩蓋了其關聯著的經濟政治關系的本質,而“占統治地位的將是愈來愈抽象的思想,即愈來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3頁。)。馬克思的結論是明確的,資產階級的看起來帶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念體系所掩蓋的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對立的階級沖突關系,而一切看起來賦予了某種理論中立性的抽象哲學理論都有為其辯護的階級基礎,從這一意義而言,馬克思顯然要揭開意識形態的真理幻相(從哲學必須是抽象的形而上學而言,馬克思就已經終結了哲學,在此,我們也許只能稱為馬克思思想)。馬克思是從否定的意義上看待意識形態概念的。實際上,馬克思揭示意識形態與實踐的表里關系,本身就要求從意識形態批判向實踐批判的轉變,即“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頁。)。
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是意識形態批判,馬克思并不相信意識形態與實踐的直接同一關系,他也不會沉浸于意識形態的體系建構和誘人的理論說教中,而是要深入到與一定意識形態發生作用的權力關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構甚至顛覆意識形態。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識形態本身,因為意識形態的形成正是通過真理式的話語系統替代并遮蔽真實的權力關系發生的,因此,對意識形態話語與真實的權力關系的批判,就不可能憑借純粹觀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識形態觀念,從人的實踐活動入手,揭示意識形態發生作用的境遇條件并強化人的歷史性的實踐活動的自為性。傳統哲學是無法跳出意識形態的,不僅如此,在馬克思看來,傳統哲學的癥結就在于意識形態化,傳統哲學的看起來遠離世俗意識形態的抽象的觀念體系所表達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資產階級的抽象的法權關系。當馬克思指責以前的哲學家不可能真正將唯物主義深入到社會歷史領域時,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當馬克思在實踐意義上展開其意識形態批判時,所謂意識形態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政治領域(馬克思意識形態批判的典型當然是政治領域),而是應該擴展為更廣泛的社會與文化生活領域,并表達為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在這一意義上,當代馬克思主義在新的境遇下展開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科學技術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眾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馬克思意識形態批判的歷史的延伸,也值得通過與馬克思建立在實踐哲學基礎上的意識形態批判的互動展開自我批判。
馬克思拒絕承認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過“批判現在的生活關系”去揭示意識形態的虛假性與暫時性,不過,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看不到意識形態的巨大的社會效用,“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頁。)。在此,馬克思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對于歷史主體的教化與啟蒙功能,而其理論基礎正是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性的考察與馬克思關于唯物史觀以及世界歷史時論的構建是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把代表先進歷史前進方向的主體確定為大工業社會的無產階級,進而構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為核心、以人類解放為最終要旨的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理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包含了知識社會學,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價值立場,馬克思是要為無產階級建構一套意識形態學說,在同樣的歷史唯物主義及社會主義旨向中,這套學說也可以看成、且事實上已經被看成是被剝削、被壓迫國家、民族以及社會群體的意識形態。
在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中包含著兩種價值立場或關懷,一是哲學人類意義上的人道主義關懷,一是基于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及群體的立場以及由此擴展開來的社會主義關懷。這兩種關懷統一于馬克思的實踐觀,不過前者更為強調實踐理念的建構,而后者則在于如何實現這一實踐理念。這兩種價值立場或關懷本身也客觀地構成了早年馬克思與成年馬克思思想的差異。早年馬克思關注的是實踐理念,這就是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更確切的稱為“共生主義”(注:參見彭富春《馬克思美學的現代意義》,《哲學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馬克思實際上建構了一種個人、社會以及類主體之間具有共生結構的生存論存在論結構,而成年馬克思關注的則是如何通過現實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運動實現實踐理念的問題。當阿爾都塞把早年馬克思和晚年馬克思的思想分別等同于“意識形態”和“科學”并由此認定馬克思思想發展中存在一種“認識論斷裂”時,實際上是忽略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內在連續性。首先,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與“科學”對立起來的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恰恰是通過對傳統的抽象的、實質上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利益要求的人道主義做出了科學的批判之后提出來的實踐的和歷史的人道主義,而馬克思由此展開的關于人的實踐活動的生存論存在論結構,就不再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動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開放性的理論結構,在此,馬克思同時也展示了意識形態的新的存在樣式。其次,作為實踐理念的人道主義或共產主義關懷本身就是作為一條主線貫穿于整個馬克思思想與學術研究過程中的,不過在前期表達為顯性的理論,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論努力中則歸屬于某種隱性的理論承諾,正如在早年的實踐觀中已經潛在地蘊含著一種從理念到實踐的現實的實踐活動一樣。當馬克思將人道主義與共產主義統一起來時,就已經敞開了一條通向以人自身為目的的共產主義道路,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結構的剖析也正是為了內在地表達其實踐人道主義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種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與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之間的截然對立,而那些建立在這種對立之上的學術努力看起來也需要對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別。三
我們說馬克思使政治意識形態發展為一種新的樣式,并且也使得自己的哲學活動與意識形態之間展開了一種新的關聯形式。這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對中國社會發展也特別具有思考價值。傳統的意識形態是忽略了實踐的抽象的意識形態,而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則是通過不懈的意識形態批判、從而表達著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雙重旨趣的新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政治意識形態通過馬克思本人所謂“無產階級的普遍化”從而引入了自我批判機制并體現為高度的反省與自檢能力。在此,作為馬克思政治意識形態的實際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思想后果與歷史承繼者,這是當我們聯想到馬克思哲學的歷史功能時必須承認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把馬克思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等同起來。作為馬克思思想后果的馬克思主義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與實踐系統,馬克思哲學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也承擔著對這一系統的解釋與建構功能,但馬克思哲學的更重要的功能似乎還是在于建立一種實踐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相對獨立的意識形態批判功能是不能取消的,事實上,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若取消了這一功能,政治意識形態也會因此失去了一種有效的制衡,而成為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極端的和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晚年要求把自己與“馬克思主義”區分開來,實際上就已經表達了這份憂慮。馬克思自己實際上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既存在著內在的關聯,也不能完全等同。馬克思一方面努力在展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與此同時,他也在努力地跳出這一具體的實踐并反思和觀察這一實踐。正是后一項工作使得馬克思即使在自己的理論學說成為意識形態之時,仍然能夠保持一種超然的和冷靜的思考,并在這一意義上培植起了一種歷史理性功能。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這種既積極參與又冷靜旁觀的方式提示了一種特別值得提倡的學術研究方式,這一方式也間接或直接地確定了馬克思哲學的學術研究方式。一方面,馬克思哲學研究不能完全介入意識形態,在理解意識形態之時一定要保持適度的距離,只有適當拉開與意識形態的距離,我們才能明確地意識并思考意識形態的存在。“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哲學之謎:哲學是對意識形態的意識,說得更明確一些,哲學是旨在達到批判意識形態的自覺意識”(注: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意識形態只有通過反省的方式才能成為我們的自覺意識,而人們用以反省意識形態的憑據就是生活實踐,“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頁。)。在這個意義上,把馬克思哲學從馬克思主義中適當分離開是有必要的,這既是一種基本的學術態度,也是基本的思想立場。另一方面,與意識形態拉開距離并不意味著漠視意識形態的存在,拉開距離不是遠離,更不是逃避。相對于生活事實的直觀性與事實性而言,意識形態給人提供的解釋總顯得表面化、僵化甚至于是假相,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干脆懸置意識形態,直接面向生活事實,以使研究活動保持一種客觀中立的態度。這種做法或許對于純哲學的研究有一定道理,可是對于馬克思哲學來說恐怕行不通。在馬克思看來,就像任何純粹觀念體系都存在著使這一觀念體系發生作用的利益基礎一樣,并不存在純粹的生活事實,在此,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直接的生活現實與意識形態都看成是哲學批判活動得以展開的“生活關系”,對“生活關系”的批判不可能繞開意識形態,不能把對意識形態的價值態度代替對意識形態的研究活動,實際上,對意識形態的反感乃至厭惡情緒,不僅不可能確立起客觀中立的研究立場,還會反過來影響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合理認識,進而影響到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學術質量與應有的社會功能。馬克思哲學以及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工作者需要自覺地思考意識形態并把這一思考活動及其結果融入到整個研究活動中。在此,思考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地思考問題其實是應該區分開來的。
馬克思哲學當然應當支持純學術化的研究方法,并保持較高的學術水準,但中國的國情決定著這仍然不是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惟一路數。基于目前的現實,有不少學人提出馬克思哲學隊伍應該分化,即把研究隊伍與宣傳隊伍分開,各司其職,這看起來不錯,但是,從馬克思哲學研究者應有的社會啟蒙功能和馬克思哲學宣傳工作者提高理論素養這兩方面看,研究隊伍還需要向宣傳隊伍滲透和影響。事實上,將近些年來在“論壇哲學”已經取得若干共識的成就向“講壇哲學”擴展和滲透,把馬克思哲學或思想中包含的豐富的內涵及其當代價值以恰當的方式向公眾說明白,已經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馬克思哲學研究必須關注意識形態問題,這與馬克思哲學應該承擔的理論使命有關。馬克思哲學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馬克思哲學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方面,馬克思哲學的學術研究應該對意識形態的進步有所作為。當我們把馬克思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做出必要的區分時,其實是為了更好地體現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先導功能,在此,馬克思哲學與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著更為內在的聯系。作為整合社會系統的觀念體系,意識形態本身是不可或缺的,高明的決策者、管理者以及明智的思想家及學問家都需要充分地考慮意識形態的現實存在及其社會功用,政治意識形態需要注入一種反省與自檢能力,并使它能夠相對公允地表達社會公眾的價值訴求。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及其作用方式也需要與時俱進,在一個社會領域高度分化、價值觀念事實上已經多樣化的今天,要推行一套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及其功能體系看來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也難以有效的實施。在一個現代公民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最恰當的方式是作為制度文明的理念基礎而存在,它的理論內涵是政治的和道德的,而其作用的方式則應該是潛在的和藝術性的,而且,在當代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不僅承擔著政治的和道德的功能,還應該對正在崛起的科學技術、大眾文化等新的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對話和制衡作用。相對于科學技術與大眾文化的外在的和商業性的造勢與炒作,政治意識形態作為公民生活的基本的價值觀更具有一種道德人心方面的穩健和感召力,但這本身是以政治意識形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創造性轉換為前提的。這是在我們思考諸如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時,特別需要加以關注的問題,馬克思哲學更需要給當代社會貢獻出積極務實的政治智慧。
- 上一篇:馬克思主義教育創新研究論文
- 下一篇:馬克思哲學意蘊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