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馬克思主義審視論文
時間:2022-08-24 03:49:00
導語:庸俗馬克思主義審視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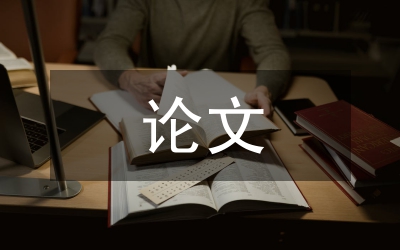
在馬克思主義史研究中,關于庸俗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我們比較側重于對經典作家的思想作正面闡述和發掘,在回顧蒲魯東主義、杜林主義、馬赫主義等等這些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戰對象的思想時,也是從屬于正面理解的需要的。而對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庸俗馬克思主義思潮往往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沒有充分地注意到它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在理論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堅持”和“發展”的問題,堅持什么和怎樣發展?就有賴于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不能夠僅僅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歷程的正面敘述上,應該在正面敘述的同時也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曾經遭受到的歪曲和篡改。多年來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僅僅看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觀點并不等于能夠做到“堅持”,反而會經常受到教條主義的困撓。因此,在今天回顧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主義遭到的歪曲和篡改,對于我們思考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對于如何在改革開放中選擇正確的思維取向等等都有著啟發意義。
一
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主義被肢解了。其實,早在馬克思在世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和歪曲就已經開始。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并且廣泛傳播開來。挑選和集結無產階級的力量、使無產階級作好迎接未來戰斗的準備的過程,正在緩慢而持續地向前發展。”[1]隨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增強和信奉者隊伍的擴大,一種誤解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因素也在增長。這就迫使馬克思作出聲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
馬克思逝世后,特別是90年代初開始,幾乎在西歐各國都存在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一些青年著作家往往把它作為一種裝飾品塞進自己的作品中。德國社會內崛起的“青年派”就是在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把馬克思主義“歪曲的‘面目全非’”的,他們把歷史唯物主義庸俗化為一種經濟唯物主義和社會宿命論。保爾·恩斯特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認為歷史是完全自動地形成的,絲毫沒有人的參與,經濟關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樣地玩弄人。所以,恩格斯憤怒地指出,“青年派”這批“聰明透頂的博士”對馬克思的歪曲是一場“大學生騷動”。
同樣的事情不僅發生在“青年派”身上,就是在拉法格、梅林、考次基、普列漢諾夫等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與追隨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機械化的傾向,盡管他們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的貢獻已有定論。比如,拉法格把馬克思主義稱作“經濟唯物主義”,這看起來只是用語上的不準確,實際上卻表明他思想中存在著經濟決定論的傾向,而這一點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極力反對的。在梅林的理論著述中,較多地注重社會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關系問題,特別是他在反擊論敵時,“是一個善于當馬克思主義者的人”[3],而當他研究歷史時,卻同樣犯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因而,他不善于充分地揭示社會生活各種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總是過多地注重經濟的方面。當然,梅林是幸運的,他的錯誤立即被恩格斯指了出來。
二
在第二國際后期,特別是在考茨基那里,馬克思主義被曲解成一種帶有濃重宿命論色彩的機械決定論,盡管“考茨基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來的人;從考茨基的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或腦袋里一定有許多小抽屜,把馬克思所寫的一切東西放得井井有條,引用起來極其方便。”[4]然而,考茨基對“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一點也不理解。”[5]他割裂歷史中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辯證關系,片面強調經濟必然性,把歷史規律理解為某種凌駕于人和階級之上的力量。特別是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宿命論的觀點越來越變成了他的世界觀的基礎,并從此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片面化、教條化、庸俗化。當代西方學者把考茨基謔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教皇”,如果是就他片面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從經濟事實出發來考察歷史和社會的原理演化為宿命論的經濟決定論并作為教條這一點而言的,那是不無道理的。
由于考茨基不懂得辯證法,割裂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僅僅把理論的作用歸結為指出實踐的目的和描述經濟的機制,不認為理論可以在與實踐的結合中直接結出碩果。所以,在第二國際領導人中,他是最輕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活動對社會的改造作用的一個。當震驚世界的十月革命爆發時,考茨基關于經濟必然性的宿命論就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放棄自己的錯誤觀點,而是為了維護這種觀點去攻擊布爾什維克的偉大革命實踐。在十月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正是用馬克思的實踐精神及時總結經驗和發展理論的大好時機,而考茨基卻寧愿為了決定論的信念而犧牲實踐。所以,他淪落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
《唯物史觀》是考茨基用來總結自己一生理論活動的著作,也正是在這本書中,考茨基把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貫徹到了社會歷史的一切重大領域,用達爾文主義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唯物主義”的過分推崇竟使他站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對立面。比如,在解釋國家起源問題時,他甚至批評恩格斯關于“國家在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從社會內部分化的基礎上產生”的觀點還不夠唯物主義。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征服而對財富的掠奪才能真正唯物主義地解釋國家的起源。同樣,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等一系列問題,考茨基都試圖把它們抽象地納入他的機械論范疇之中加以解釋。
與考茨基相比,普列漢諾夫有著高度的哲學素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唯物史觀的理解,遠較第二國際的其他理論家們深刻得多。不幸的是,經濟決定論的幽靈也同樣糾纏著他,他為歷史唯物主義描述出了一個簡單化一的機械圖式。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文中,普列漢諾夫這樣寫道:“如果我們想簡短地說明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現在很有名的‘基礎’和同樣有名的‘上層建筑’的關系的見解,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東西:
(一)生產力的狀況;
(二}被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系;
(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經濟直接所決定的,一部分由生長在經濟上全部社會政治制度所決定的社會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的各種思想體系。
這個公式是十分廣泛的,對于歷史發展的一切‘形式’足夠給一個相當的位置,同時是跟折衷主義完全無緣的,這種折衷主義除了說明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影響之外,就不能更進一步,甚至它沒有懷疑這些力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的事實還沒有解決它們的起源問題。這是一元論的公式。這個一元論的公式徹頭徹尾貫穿著唯物主義。”[6]這個“一元論的公式”也恰恰是后來斯大林進行“宣教”時的“圣經”。由于普列漢諾夫所遵從的是這樣一個公式,所以,他同樣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意義,不能理解革命政黨、革命理論的意義,只能宿命論地消極等待革命的自然發生。所以,他斥責列寧1917年4月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常稱《四月提綱》)中所提出的在俄國搞社會主義革命是“夢話”,是“完全脫離時間與地點的情況下寫成的”。[7]
三
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的思想路線被斯大林繼承并加以發展了。與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相比,斯大林所具有的只是對世界和歷史的常識性理解,而這種理解又成了他系統概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所以,他比第二國際理論家更具有機械決定論的色彩。作為偉大的革命家和社會主義積極的實踐者,斯大林也竭力想使自己在理論方面有所建樹。但是,在19世紀以來的哲學成就和科學成果面前,斯大林表現出了極端的外行,這就決定了他不能象列寧那樣站到馬克思主義史中巨人的行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中,斯大林力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以整體描述,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血肉之軀變成了干癟癟的教條。他作出了努力,但在別人看來僅僅是隨意畫出的一條線,至多也只是畫出了主干的骨胳結構,而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的豐富內容被全部忽略了。這也就是許多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斯大林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線性決定論”。
在斯大林那里,論斷多于證明。既使證明也只是引用一些個別的經驗事實,整個世界被他納入到了決定與被決定的簡單圖式之中:自然界是一個規律的體系,是聯系和發展的必然性驅使著的由量變向質變的過渡,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只在于復制著自然界的規律。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8]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就被排除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范疇之外了,成了一門應用和推廣“自然觀”的具體學科。
斯大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理解表明:他不懂得社會歷史領域的復雜性和社會歷史規律的特殊性,他一味地根據自己的主觀意愿,使“社會歷史科學……成為例如同生物學一樣的精密的科學”。[9]他沒有意識到,當自己宣布“社會歷史科學能夠成為例如同生物學一樣的精密的科學”時,與宣布“人是機器”站到了同一個基點上了。社會歷史與自然界不同,它是人的活動的結果,人是人的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在社會歷史科學中,撇開了人和人的實踐,簡單地用自然規律來類比社會規律,還遠遠未達到考茨基的經濟決定論的水平。斯大林一方面宣布歷史唯物主義是自然觀的推廣和應用,另一方面又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一整塊鋼鐵鑄成的”有機整體分割開來,使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相分離。在斯大林這里,辯證法在唯物主義的堅定性面前相形失色,即使他在談論辯證法時,也僅僅是相互聯系、變化發展、量變質變等等幾條簡單的結論和一些現象描述,辯證法的本質根本未被揭示出來。斯大林的這部著作是專門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但除了術語之外,它的基本觀點和思維方式都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去甚遠。
四
肇始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是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形式。這條思想路線帶有較多的人本主義色彩,它在批判考茨基的“經濟唯物主義”的借口下企圖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用康德主義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用關于世界和人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來取代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伯恩施坦是以恩格斯思想遺產繼承人的面目出現的,他把恩格斯1895年為《法蘭西階級斗爭》所寫的“導言”看作他改良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出發點,而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則是他用來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然而,由于他與康德主義、費邊主義調情的時間太久,以致于對馬克思主義缺乏整體的認識,僅從經典著作的單篇文章或只言片語出發,這必然要曲解馬克思主義。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要借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為他的改良主義張目。
伯恩施坦強調社會歷史領域“因素的多樣性”,反對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主義和決定論的偏重。他認為,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不是純粹唯物主義的,更談不到是純粹經濟的了。”[10]“純粹的經濟原因首先只是創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質,但是這些思想怎樣興起和傳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決于一整系列影響的協助作用。如果一上來就認為,堅決地強調除了純粹經濟性影響之外的其他影響和考慮到除了生產技術及其預測到的發展以外的其它經濟因素,就是折衷主義,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絕,那么,這對于歷史唯物主義是害多于利的。”[11]在這里,伯恩施坦名義上是要否定一種推崇“純粹經濟因素”的庸俗觀點,實際上他的目的則在于拋棄唯物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修正,以便在社會歷史領域中讓“意識形態因素特別是倫理因素有比從前更為廣闊的獨立活動的余地。”[12]應當肯定,伯恩施坦的用心是良苦的,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以及無產階級政治斗爭在這種新形勢下應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手段,是他思考的中心。而且他也極其敏銳地覺察到教條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危害及其所具有的空想性質。伯恩施坦指出,教條主義者“畫了一條界限:這邊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邊是社會主義社會。根本不談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有系統的工作。”[13]在他看來,“既使是最科學的理論,如果對它的結論作出教條主義的解釋,也會引導到空想主義。”[14]伯恩施坦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是無可指責的,但當他用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相對立時,當他因反對經濟決定論而拋棄唯物主義時,無疑是走得太遠了,以致于邁出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陣營。
因為,伯恩施坦雖然提出了一種用康德主義來補充和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嘗試,但他與他的論敵,即第二國際的其他理論家一樣,對哲學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無法實現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全面修正的宿愿。只是到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麥克斯.阿德勒和奧托.鮑維爾)那里,修正主義才得到系統的哲學表述。
麥克斯.阿德勒“一貫主張以認識批判論的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他一方面承認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幾乎全部的基本觀點,另一方面卻始終堅持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作極端唯心主義的解釋。”[15]阿德勒深得康德哲學二元論的精髓,即把物質的東西和觀念的東西分離開來,然后進一步論證社會歷史過程的精神性質。阿德勒也談論社會歷史過程中的經濟關系,但他所理解的經濟關系,“不是什么別的東西,而是人的關系,那么這種關系同時在本質上也就是精神關系,這就是說,經濟關系永遠包含著人們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動。”[16]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基本立場在阿德勒那里也被“修正”了,他經常使用的“唯物史觀”這一術語的準確含義應當是“唯心史觀”。
既然阿德勒抽去了“經濟關系”的物的性質,那么人與人關系的徹底改變并不取決于廢除剝削與被剝削的私有制度,而是依賴于精神的解脫、文化的發展和政治自由的實現。為了實現這一點,最方便的途徑就是與資產階級進行合作。作為奧地利社會領導人的奧托.鮑威爾則努力使阿德勒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成為該黨的行動綱領,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置于民主奪取政權的統攝之下,認為任何其它的方式都只不過是這一方式的消極補充而已。
與考茨基等人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不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主義理論的倫理判斷或價值判斷來自某種自律能力和能創造自覺責任原則的人類意志,建立于一般的、抽象的人的價值基礎之上。應該說,在經濟決定論那里,達爾文主義的虛假的科學形式抹殺了馬克思主義所固有的價值因素,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重新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有著很大的價值。但當他們走向另一極端時,其結果也與考茨基等人一樣,回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模式中去了。他們之間的區別只在于考茨基撿起了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則重新用人的意志理解世界和構造世界。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馬克思主義遭到這般肢解不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悲劇,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悲劇。就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來說,它并不包含著產生這種悲劇的因素。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無論是在創立自己偉大學說和闡發其思想時,時刻注意理論的全面性,一旦發現由于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過多地強調了這一理論的某些方面而遭到誤解時,總是及時地預以訂正。然而,第二國際后期開始出現的“兩種馬克思主義”傾向卻是事實,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悲劇性結果。形成這種悲劇的根源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性質泯滅了,不管考茨基、斯大林,還是伯恩施坦、奧地利馬克思主義都從這一總體中分解出自己可以接受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他們各自都可以扮演著半個馬克思主義的形象并獲得一種片面的理論。而用一種片面的理論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是必然要失敗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80年代未以來,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重大變故,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展開改革運動,馬克思主義遇到了一個全新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種思維向度作為前車之鑒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們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堅持決不意味著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既有論斷。我們的事業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事業,但發展決不意味著可以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是發展著的思想體系,它必須隨著科學和社會的發展改變著自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包含著通向未來的向度,如果失去這個向度,馬克思主義就會被僵化、片面化和教條化。相反,如果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已有成就,借口著眼于現實和未來,就會走向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馬克思主義是已有理論、現實經驗和關于未來的思考這三個方面的統一體。這是我們通過批判地回顧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所形成的認識,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這種認識也是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保證。
注:
[1][3][4][5]《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3頁;第18卷,第372頁;第35卷,
第234頁;第43卷,第369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頁。
[6]《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三卷,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195-196頁。
[7]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7頁。
[8][9]《斯大林選集》下卷,第424頁,第435-436頁。
[10][11][12]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的任務》三聯書店1973年,
第59頁,第55頁,第57頁。
[13][14]《伯恩施坦言論》三聯書店1973年版,第28頁。
[15][16]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頁,第405頁。
- 上一篇: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異化觀論文
- 下一篇: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