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主體開放特征論文
時間:2022-08-28 04:28:00
導語:我國主體開放特征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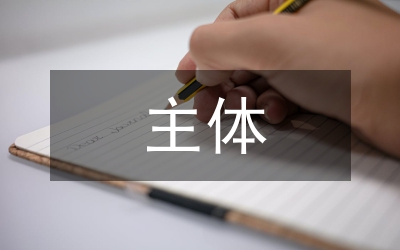
內容提要:中華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亙古亙今的老問題,既有“一元”論也有“多元一體”論的觀點。這些論點的依據和面對的問題不同,所以解釋方法和得出的結論必然相異。本文認為,中華民族的主體開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長而又可作進一步的發揮。“一元”論可視為主體族群的核心,“多元一體”論可更多地闡明主體族群的開放性特征;主體族群的核心作用規定著整體民族的發展方向,開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體族群與邊緣族群的聯系,同時也使整體族群中某些成分異化成為其他異質族群。這種由主體開放特征形成的動態平衡使中華民族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持久、最龐大的民族,也使中華民族形成了獨特的、開放性的文化認同心態,并以之接納或傳遞不同民族間的信息,回應世界民族發展的潮流。
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及其主要特征一直是所謂“好學深思之士”所關注的,從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到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論都是這種努力的結果。雖然中華民族的形成史和特征只是一種客觀事實,但認識和解釋它們的視野和方法則應該是多樣性的。這并不是說,歷史因此會成為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說我們應該借鑒各個時代和各種學術見解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和便利,不斷地推進我們的研究,使其更接近所蘊涵的真理。
一、民族的文明與人類的起源
人類文明的進程既包括人類體質的進化又包括人類創造性活動(物質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積累。人類的體質進化是人類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基礎,所以在揭示以人類的創造性活動為依據的各種文明時,我們往往也要證明這種文明在人類體質上的根據。這種情況在中國,一個以保持了五千年古國文明傳統而又相對獨立于其他文明傳統而自豪的國家,是較為明顯的。
費孝通先生在界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在中華大地上已陸續發現了人類從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進化階段的人體化石,可以建立較完整的序列。說明了中國這片大陸應是人類起源的中心之一。”①為了證明中華民族文明的多元一體性有自己人類起源的根據,我們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一些與早期舊石器時代相吻合的直立人化石依據,如云南元謀人,以及年代與之相若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北小長梁與東谷坨舊石器遺址。這些年代的大體時間被界定在距今170萬年左右。
20世紀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獻將舊石器時代人類的起源界定在200萬年前的東非。只是到了公元前100萬年左右起源于東非的直立人才通過近東、歐洲、東亞和印度尼西亞走向世界。②按年代算下來,中華民族的原始文明可以被認為是原發的,而不是移入的。至少在沒有確認有比元謀猿人更早的直立人之前,或沒有發現其他與元謀猿人年代相近的直立人化石之前,中國人種起源的一元性(即以元謀猿人為最早的一元)則是很難回避的。如果中國人種起源的一元性很難回避,那么,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當然包括少部分古代和近現代社會中移入的人種或民族)與這種人種起源的一元性當作何種解釋?況且,西方文獻中東非直立人最早的化石被界定在200萬年前或他們在100萬年前走向世界的說法,都還在不斷地為新的考古發現和科學鑒定所修正,所以,我們目前還很難就人類起源的性質作出明確的判斷。例如,當2000年10月科學家們在肯尼亞挖掘出距今600多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時,一下就否定了此前在中國河北蔚縣發現的距今300萬年的石器化石作為中國人種獨立起源的依據。中國5家權威科研機構“通過對Y染色體單倍型在全國22個省市漢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證實中國南北人群的Y染色體單倍型組成有較大的差異。結果顯示,早期現代人類自南方進入中國,隨后由南向北逐漸遷移,隨后逐漸遍布整個中國。這一觀點,再一次支持了人類非洲起源說。”③可是,在此前數月,同樣是科學家的新發現,證明“人類遠祖起源于中國”。因為,中美科學家證實了在中國發現的中華曙猿和世紀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萬年至4000萬年之間的中始新世。④據稱,此觀點由中美科學家聯合發表于英國權威的科學期刊《自然》雜志上。盡管如此,其科學性仍因新的考古發現被不斷質疑。
就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來看,我們仍很難就人類起源的舊石器時代的許多情況,諸如古猿向猿人的進化、古人類的生活、遷徙、工具等,作出明確的判斷。不過,我們也可專就這些材料作一種邏輯推論:如果有關古人類起源的考古材料時間越久遠就越少,空間分布就越集中,無論這些年代相去數百萬年的稀少考古材料出自何地,這種情況會不會蘊涵人類起源的單元趨向呢?無論如何,人類起源于何處?是一元還是多元?這些問題恐怕在短期內都不能給予確切的回答。而解釋人類文明或民族文明的理論又不能忽視這些文明的最基本載體———人類本身的起源和進化,以為立論的重要依據。因此,無論是基于或是忽略人類起源的人類文明或民族文明研究模式,都會留下可作進一步討論的余地。例如,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構成的“多元一體”論,其立論無論是基于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還是基于近現代中華民族的現實狀況,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在此之外,仍有一些關乎中華民族文明的問題需要用新的視野進行討論。例如,中華民族文明在其人類起源方面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這種特性與后來形成的民族文明的關系當作如何表述?中華民族在形成時的多元性何以發展成以華夏族一元為主體并以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標準?從過去發展的歷史和未來發展的進程看,中華民族這個統一體中的各種單元有的在歷史過程中消失了,有的異化了,有的是綜合而成的,有的則是體外移入的;這種情況將來也不可避免,在此情況下中華民族的體元關系單純:論中華民族的主體開放特征變化又當作何種解釋?
有了這些考慮,本文也想討論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另一特征,即主體開放。這個討論將依據見諸文字的史料包括部分傳說和已出版的相關研究成果,而不涉及人類起源的考古材料。因為就筆者的觀點來看,人類的起源與人類的文明既聯系又有區別,以人類數百萬年的起源史來觀照數千年的文明史有大而不當之虞,可取的方法倒還是用數千年的材料研究數千年的人類包括民族的文明史。
二、以黃帝為核心的主體形成
華民族被廣泛地稱為“黃帝子孫”(thesonsoftheyellowemperor),現代社會中也有人將其稱為“炎黃子孫”。其實,這個代稱應指中華民族最早形成時的三個氏族混合體:黃帝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中蚩尤支系,其中又以黃帝氏族部落為核心,融合了炎帝氏族部落和九黎氏族部落蚩尤支系,形成最早的中華民族主體———黃炎部落聯盟。值得多說一句的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排序并不是“炎主黃輔”、“炎先黃后”或“炎強黃弱”,而只是一種習慣性說法,一如中國人說“陰陽之學”,其實是指“陽剛陰柔”、“陽上陰下”或“陽主陰輔”;又如“人皆可以為堯舜”、“六億神州盡舜堯”等皆與此相類。因此,中國人習慣說法的真實涵義往往要在知道更多的信息之后才能確定。作為中華人文始祖的黃帝氏族部落與另外兩支較大的氏族部落炎帝和九黎的興起和發展大約都在同一時期和距離并不太遠的地點,以使他們能夠彼此接觸并融合。黃帝氏族為姬姓,號軒轅氏,本在陜西黃土高原一帶活動,后沿北洛水南下至今大荔、朝邑,再東渡黃河順中條山和太行山麓向東邊前進,在今山西南部的黃河之濱與另一小族嫘祖聯姻,成為壯大了的部落聯盟。從其生活環境和遷徙傳統來看,黃帝氏族部落是一個頗有戰斗力的游牧部落族群。司馬遷說黃帝氏族“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⑤依其游牧部落強悍的作戰能力,一路遷徙一路征戰,“教熊羆貔貅虎”,這些以動物為其圖騰的小氏族皆歸其麾下(黃帝族,號有熊氏,以熊為圖騰),及止其北上遷徙至河北涿鹿一帶,已演進成一龐大的氏族部落聯盟。而在此地其面臨的對手是炎帝氏族部落聯盟。依神話傳說和古典文獻記載,炎帝氏族也發源于陜西黃土高原。其長期的聚居地應為關中渭水流域,族宗姜姓,最初的生產、生活方式可能也是游牧、征戰、遷徙。有學者以為“姜姓的炎帝部落號神農氏,這與他們最早從事農業有關。”⑥不過,以農業民族安土重遷的傳統,炎帝族與九黎族、黃帝族的戰爭不會在與其發源地較遠的地方發生,那倒可能是它遷徙、征戰、安居后的結果。因此,神農氏族的農業民族特征應晚于其游牧民族的特征。炎帝族的遷徙路線大約是沿渭河東行,至今河南西部和山東西部,在那里與九黎族遭遇,戰敗后退居今河北涿鹿一帶,在此形成較為穩定的農業產生方式和居住地,其經濟能力和作戰能力都得到加強。這樣,黃帝族的部落聯盟要“三戰,然后得其志”;在戰勝并融合了炎帝族的基礎上才能與九黎族一戰而擒殺蚩尤,才能代神農氏而主霸中原。司馬遷在寫黃帝族與炎帝族的阪泉之戰與黃炎兩部族聯盟后與九黎族支系蚩尤的涿鹿之戰時,運筆的氣勢是不同的。黃炎聯盟是兩個實力強大的游牧與農業民族的聯盟,其與九黎族支系蚩尤之戰勢如破竹,其他中原部族則望風披靡,最終使以黃帝族為核心、以黃、炎、九黎族(蚩尤支系)聯盟為基礎的華夏族得以確立。“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⑦司馬遷這樣的描述和運文氣勢可以作為上述推斷的依據。在華夏族聯盟中被征服而融入的九黎族,原是居住在現中國東部的夷人,其活動區域大約在今山東北部至安徽中部一帶,西至河南東部,東到海濱,以漁獵為生存手段。蚩尤或是其支系的頭領或是其主流氏族,敗于黃炎聯盟后遂被融入,使黃炎聯盟
成為一個擴大了的聯盟體。以此推論,九黎族當是當時中國東部的一個族群聯盟,其支系苗裔除蚩尤之外,尚有后來叛亂的三苗。據日本漢學家解《史記·歷書》“九黎亂德”句說:九黎“南方族名,言九者,非一族也。”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注,也認為三苗是九黎族的一支后裔。⑨如此算來,中華民族的原始核心主體———華夏族群,可以認為是由三支較大的部落聯盟通過遷徙、轉戰,最終在中原穩定形成的。
黃帝族聯盟、炎帝族聯盟和九黎族聯盟在各自形成前,都將其周圍或遷徙途中所遇的氏族征服并融入;最后,這三大族群聯盟再交手,確立了以黃帝族聯盟為核心地位的華夏族群,游牧、農耕和漁獵三種生產方式融匯而成華夏族群的經濟基礎,其中又以生產能力較為穩定的農耕為主導,輔之以游牧和漁獵。由于華夏族群形成的這種歷史傳統和這三種經濟方式的關聯性,定居中原的華夏族群成了一個對外開放的核心體,以自己主體內涵(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強弱盛衰形成引力場,對四周的其他族群產生作用,維系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同時也見證著周邊民族群體的演變。司馬遷說:“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⑩這個總結可以看成是對中華民族原始形成期及其后來發展、演變的一個較為穩定時期的歷史描述,它不大可能像漢代以后的學者所理想的那樣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禮記·禮運》)之世,而是一個基于黃帝族群為核心的主體開放、擴大、演變的過程,體現著宗親氏族向聯姻部落、部落聯盟和國家社會的演變,在這個主體開放演變的過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早期形態———華夏族群。
三、華夏族群與文化認同
按先秦的傳說,華夏族群的起源應是先三皇后五帝,即中華民族開天辟地就該從三皇五帝說起。而司馬遷在其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群史之首《史記》僅以五帝啟篇,“而不言三皇,大概是由于三皇的事跡更‘不雅訓’的緣故吧!”11那么,關于五帝的傳說,特別是從黃帝開始進而演變成一個華夏族群主體的傳說,照太史公看來還是可以成立的:“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12從黃帝族群的征戰、遷徙,對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中蚩尤支系的戰爭兼并,形成穩定的部落聯盟主體進而演變至夏代,最早的華夏族群的主體形成不僅有史據、傳說備考,而且還成了華夏族群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礎,以使華夏族群主體及其周邊的族群將其視為族群親和的標準,以將自己族群的經驗和理想投射其上。
太史公幾乎是對中華民族起源的經驗、傳說作了中國人最早的文化人類學田野調查,其得出的結論恰好揭示了華夏族群文化認同的特征,即中華文明起源時所有的豐富內涵都與黃帝或他的后代子孫有關。
按照通常的傳說,黃帝首先創造了舟車,以減輕人們運輸的勞累;他的妻子嫘祖發明了養蠶、繅絲,以使人們能織絲穿衣;他讓倉頡創造文字,讓隸首創造了算術,讓大撓創造了甲子干支歷法,讓伶倫創造樂律;他還與岐伯、雷公討論,創造了醫學。這些傳說不大可能都是真的。但是由于黃帝族群在征戰、遷徙、兼并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原部落聯盟的核心,人們不得不將各種文化傳統附會在黃帝身上,以使其具備最高的權威性。“強權即真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幾乎是所有原始文明的共同特征。當然這種確立在原始文明基礎上的文化傳統權威也有它的優點,那就是為最早的離散而又因沖突聯系著的各中原部落族群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完成了從暴力征服到文化凝聚的第一個階段。
依此理解,早期的傳說和歷史記載哪些是真的呢?為應付暴力沖突包括對部落聯盟內的和外部落的武力征討,為克服自然災害和提高管理部落聯盟的生產及社會分配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鞏固黃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聯盟和文化心理,以使其經過數代人甚至數十代的努力演變成夏代的諸夏族群(包括商周兩族的部落聯盟)和三代的文化———夏禮(包括后來形成的法、儒、墨、道、兵、農、名、雜各家的學說),有關黃帝族群內部的“選賢與能”、“傳宗接代”和以這個族群為核心的對外開放,接收其他族群的人員和文化的傳說和記載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按司馬遷記載的推算,五帝的關系既體現著家天下的宗法制特點,又開始奠定了一個對其他族群開放的基礎,以使后來中華民族的發展有一個穩定、持續和擴大的局面。五帝中開宗的部落聯盟首領是黃帝,其次是黃帝的孫子顓頊,其次是黃帝的曾孫帝嚳,再次是帝嚳的兒子帝堯,最后是顓頊的六代孫帝舜。這是原始社會的宗法制傳統中正常的“家天下”局面。不過與我們后來所說的封建社會中的“家天下”局面所不同的是,為了應付各種問題,五帝的“家天下”不是按嫡長子維系的,而是由宗親族系中的“賢能”者維系的。五帝傳至三代,華夏族群是以黃帝族群為核心,以黃炎九黎(蚩尤支系)為基礎,不斷對周邊諸多部落征服、兼并、開放、融合而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華夏族群同時也完成了由“家天下”向對其他族群、部落開放的“公天下”的轉變,民族認同心理也由宗法制的血緣認同轉變為三代文化———夏禮的認同,后來因有“因禮而辨夏夷”之說,“禮”既被認為標準,“夏”作為定語也就省略不用了。過去的理論認為,夏、商、周三代都是嫡長子或嫡子相傳的,要比五帝的庶子相繼更有“家天下”的特征。如果不僅僅從形式,而是放大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歷程來看,情況就恰好相反了。五帝傳統中雖有庶出且多有“賢能”者,但他們的選擇市場僅限黃帝族群,不出宗法制的“家天下”。三代以至明清,各代帝王雖傳諸嫡子,可改朝換代后每一姓“家天下”者仍自認其承襲的是中華民族之正宗,此種各家各族皆不見外的“天下”胸懷全拜認同中華民族文化之賜。而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傳統則起源于五帝,大成于三代。對中華民族來說,文化傳統的認同高于宗姓種族認同,這種轉變又是在三代完成的。所以,三代之后宗姓的朝廷興衰,對中華民族來說,遠比不上文化的“天下興亡”重要。顧炎武所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濕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3,即屬此意。反過來講,也正因此關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文化認同,才有蘊涵很深的社會潛力,輔助著三代后嫡傳的宗姓朝廷雖昏君多于明主而仍然能長期地茍延殘喘,而五帝時代絕無此景象。因此我們又可以說,中華民族歷史上形成的諸多利弊都可由此得到一些啟示。
歷史者結中華民族的起源時說:“華夏民族乃中國民族之主干,因此中國古代史也以華夏民族為正統。在中國古史傳說里,最早而比較可信的,有神農、黃帝的故事。這便是華夏族中的兩大支。”14考古學者蘇秉琦在總結中華民族從五帝時代到三代的發展特點時也說:“‘五帝時代’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組合與重組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另一個重要階段則是自距今四千年至兩千年夷夏斗爭及夷夏共同體的重組與新生階段。在這一大階段中,如果說夏、商兩代還是以‘諸夷猾夏’,‘諸夷率服’,夷、夏較量,互為消長為特點的話,那么西周至春秋時期則是以‘以夏變夷’為其主流。”15把兩位先生的結論再深化一點說,中華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特點可分為兩個方面:其一,就民族形成的特點言,五帝時代是以黃帝族群的武力征服開始,進而演變融合成一個黃炎九黎(蚩尤支系)的部落聯盟主體,再通過開放式地武力兼并與人文化成,吸收進更多地周邊部落或族群,終于至三代而成華夏族群主體。此主體又成為秦漢后中華民族對外開放、文治武功的核心,奠定了中華民族更大規模發展的基礎。
其二,就民族認同的特點看,五帝時代的文化積累至三代已綜合成華夏族穩定的認同內涵———禮,其作為一種認同標準又規定著三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新分子的融入和舊分子的化出。這種開放的以文化為民族認同的特征,既使中華民族的“體”添加了新的“元”,也使某些“元”異化成為其他族的“體”。中華民族“體”的開放性激發了各種“元”的活力。
四、四夷的形成及其與華夏族群主體的關系
在華夏族群主體形成時,其周圍已有一些文化上與華夏族群相異的族群。在此可借用南宋貰冶子解釋《唐律疏議》時的一段話來作說明:“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中華。非同夷狄之俗,被發左衽,雕體文身之俗也。”16在華夏族群周圍的族群因文化習俗不同被稱為“四夷”,即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分成四種大類,現在又通稱為少數民族。再籠統地說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有時又用“四裔”指稱。
而關于“四夷”的起源,民族史的專門學者已有論斷:“到目前為止,我國所有各省區均已發現新石器文化遺址,據不完全統計總共有7000余處,年代大約始于公元前6000余年,一般延續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邊疆地區結束得要晚一些。鄙意認為中華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已可看出一些萌芽。”17以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證明“多元一體格局”中“四夷”的源發性是據理兩備的。還可以進一步補充說明的是,“多元”中“四夷”的形成也有很明顯的由主體部分開放向四周異化發展的特征。
為了說明“四夷”的由主體開放向外異化發展的特征,我們先從古代典籍中常用的“四裔”中的“裔”字說起。
“裔”,按《說文》講,最初是指衣服的邊緣。后延伸指地理空間中的邊遠部分,如裔土;再延伸指血緣關系上的疏遠部分,如裔胄;再延伸指被放逐而離開原居住地到邊遠地區的人
,如裔民;最后指因在邊遠地區而認同其文化的人,如裔夷。從“裔”到“夷”的轉變,是中國人判斷其民族主體和開放的邊緣部分的關系的一種認識變化。《左傳》說的“裔不謀夏,夷不亂華”18(《左傳》定公十年),即已將“裔”向“夷”的引申作了解釋:裔夏是空間上的差異,夷華是文化上的差異。
講裔夷關系的演變,使我們知道了中華民族的主體與其邊緣部分的關系。而這邊緣部分,除了民族史學者的多元原發觀點外,還有因貿易、婚嫁、逃亡、遷徙、占領、被俘、流散、游說、流放而至邊緣地區或至主體民族文化影響較弱的地區所形成的特征。在中華民族包括華夏族群和四裔族群形成的初期,兵敗或獲罪流放而至邊緣地區進而演變為四裔是較常見的。古代典籍稱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19太史公對此不持異議,記入《史記》曰:“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20東漢經學家馬融在解釋《尚書》中的這句話時也說:“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羽山,東裔也。”21他們都相信,從華夏族群主體中被流放出去的獲罪者最終演變成了四夷族群,當然,四夷族群的形成也不排斥其有原發性的一面。之所以要標明其從主體異化出去的特征,是想要揭示主體族群與邊緣族群有共同的歷史經驗,以成為其文化認同的基礎。
從馬融講“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22,到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說明,將民族主體的人流放至少數民族地區已是一種政治文化的傳統。
當然,從中原華夏族群的主體中異化出去的族群并不僅僅見于流放一種,但其作為古典文獻的最初記載和中國政治文化的一種傳統在理論研究中卻可列為典型。借此,我們可進一步說明中華民族的主體與開放的邊緣部分的區別與聯系。先說主體與其開放的邊緣部分的區別。這里我們借用王夫之的一段話:“裔夏者,如衣之裔垂于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即天氣之分;為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所不順,命之所不安。”23他認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異最終也導致了文化和習俗上的差異;當然這其中也含有主體對其異化的邊緣部分的優勢心理。不過,他要表述的歸根到底還是文化上的差異,只要認同主體的文化,差異自然也就消除了。如果僅僅只是這樣看,是有主體文化本位主義或后來我們所說的大漢族主義的傾向。
如果我們再從主體與邊緣部分的聯系方面看,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應該視為主體的文化加上其開放的邊緣部分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就是指核心的華夏族群或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認同一個更高的中華民族文化,只不過在這個整體文化的框架中,主體族群的文化規定著整個民族文化發展的方向,其他族群的文化豐富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容。因為中華民族歷史上“夏裔”之別比“夏夷”之別聯系更密切,“君不忍刑,宥之以遠”,“衣之裔垂于邊幅”都是這層意思,所以邊緣認同主體的方向,主體認同邊緣的多樣性,共同認同整體的民族文化都是有基礎的。清人在解釋“中國”與“四夷”的關系時作過很好的比喻:“京師為首,諸侯為手,四裔為足,所以為中國人也。”24“足”按“首”指揮的方向運動并不因此而變成身體上其他的部位,“首”規定著“足”的運動方向而并不因此代替“足”,它們都是身體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這種主體開放的特征,在中華民族的主體與邊緣部分的聯系中,文化認同可以獲得三種基本解釋:(1)主體與邊緣的文化認同的性質是大同小異的,因而能長期維系民族共同體的關系,如中華民族中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2)主體與邊緣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社會經驗基礎,主體和邊緣中都有諸多分子因開放而演變成為對方的,如秦楚和熟黎及白族;(3)邊緣部分有因文化認同產生質變而異化成為其他主體民族的,如駱越中的越南人及尉佗的后裔和穢貊中的朝鮮人及衛滿的后裔。
五、主體開放的意義
中華民族形成史上的傳說和文獻在描述其主體性特征的時候,往往帶有英雄史觀和文化優勢的色彩,對黃帝族群的記述即其顯例。因此之故,也容易生出中華民族形成的一元論觀點。《史記·五帝本紀》中關于黃帝族群與四夷關系的記載,“認為中國各民族均起源于黃河中游,其在中原發展者為華夏,流徙于四邊發展者為四裔(夷),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尤其是華夏/漢族起源的一元說。”25這個觀點的進一步發展往往又導致了民族文化認同的單極化標準,即將華夏族群或漢族的文化等同于中華民族的文化。這些情況都是值得加以重新思考的。
費孝通先生關于中華民族形成的“多元一體格局”的論斷,考之以中國新石器遺址,證之以當今中華民族的現實,是可謂高屋建瓴。對歷史成論重新思考,此其選也。受此鼓勵,本文也以中華民族形成的視野談點對中華民族主體開放特征的看法。雖然材料于原“一元論”者無多新補,而解釋的立場卻與先賢儕輩有所不同,其意義如下:
1.主體形成有單元性核心。五帝時代中華民族最初的主體就是以黃帝族群為核心的;由于這個核心的凝聚作用使黃帝族群與炎帝族群和九黎族群(蚩尤支系)相互融合,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面形成為一個穩定的族群共同體,成為華夏族群形成過程中早期的主體。在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這個主體又成為另一個更大的主體———三代的華夏族群的核心,它規定著中華民族的穩定性和發展方向。由此逐級發展、演變,構成中華民族形成的動態平衡:原始的單元演變成一個核心,再演變成一個主體;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高層次上,這個已形成的主體又成為一個連續發展階段上的核心,不僅保持著原主體的穩定而且還規定著原主體的發展方向,使新的單元不斷融入,演變成更大的主體。這種核心→主體……主體→核心……核心→主體連續遞進模式的穩定發展使現代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2.推動中華民族的核心→主體……主體→核心連續遞進模式的基本動力是什么?從人類發展都經歷過由野蠻到文明的普遍規律來看,中華民族的發展并不是這個規律的例外。在本族群內部的權力更迭和征討異族群的過程中,殘酷的戰爭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軒轅戰涿鹿,殺兩蚩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先帝(漢武)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26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民族雖南征北戰、武功顯赫,然也不能卓然自立、垂之恒久,如波斯人、羅馬人和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何以中華民族能有不同的表現?答案在于,中華民族在訴諸武力的過程中也在進行著兼容并蓄的文化創建。遠古的傳說和古代典籍將中國人最初的文明功績都記在黃帝的賬上,漢武帝三件大事之一(其他兩件為打擊匈奴和抑制商人)就是定儒家于一尊,宋儒能“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27,將儒家文化光大成為宋明理學,直至現代中國人接受市場經濟觀念、人權觀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念等,都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創建。這些附著于民族主體的文化創建活動,使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從血緣氏族認同、部落聯盟認同、政治權力認同轉變為主體族群的開放性的文化認同。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發展體現著由武力擴張向文化包容轉變的趨向,最終確立了穩定的文化認同模式。這個模式的形成克服了五帝時代以血緣氏族為紐帶的“家天下”在維系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先天不足,代之以文化認同為紐帶的“天下為公”或“大同世界”,以此維系著中華民族雖經朝廷興替、族群遷變而仍未更改的整體性。中華民族的這種主體開放的文化認同特征也使它們在二十世紀初接受共產主義和二十世紀末接受全球化觀念時都沒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礙。
3.在民族認同的相關特點中,文化認同要比其他的特點如血緣、地域、語言、政權、身份有更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主體族群的擴大要依賴它,主體民族和邊緣(文化上的大同小異)族群也要依賴它。這是解釋中華民族能保持長期動態平衡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在中國的民族關系史中,“(1)落后民族在先進民族經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逐漸融合于先進民族。(2)先進民族的部分成員因處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28這兩種情況表明,倚重于文化認同的民族認同思想能確保主體族群與邊緣族群的統一和動態平衡,處于統一體中的整個社會不至于因純粹的民族問題而引起動蕩。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也不至于因不同的族群“入主中原”而被中斷,因為文化認同所具的開放性張力不僅使邊緣族群在“入主中原”前就受到同化,而且在“入主中原”后使其自身也完全融合成為主體族群了。另一方面,邊緣族群中至少有很大的成分是由原主體族群中遷徙演變而成的,它們與主體族群在政治、經濟、化方面都有許多共同的經驗,所以與主體族群能長期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使相互間的轉換較為平和地完成。
4.中華民族的主體開放性特征還表明,文化認同和文化異化也是對立統一的。在作為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內部,文化認同和文化異化表現在主體族群和邊緣族群的關系方面:主體族群的開放使其中的一些分子連人帶文化經驗一同加入進邊緣族群中,邊緣族群因此得以保持與主體族群的緊密聯系并吸收主體族群的優秀文化;同樣,主體族群的開放也使邊緣族群的一些分子連人帶文化一同融入主體族群,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整體民族———中華民族。另一方面,在世界背景的民族關系里,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文化異化也要面對兩種情況。一是要開放接納與自己沒有同源(指新石器以
后形成的文明)基礎的新成分融入,如元代的回回人和現代在東北的俄羅斯人、在香港的英國人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同時,中華民族整體中的邊緣族群由于種種原因其文化異化到與主體族群的文化“小同大異”甚至是完全相異時,中華民族中的這些成分就會失去,如歷史上曾為中國人而今卻為越南人和朝鮮人或現代西方世界中的華人“香蕉人”者。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異化而成為其他族群的人甚至是外國人,按“以夏變夷”的觀點來看,都是會令人扼腕嘆息的。這往往也導致了文化異化的緩慢進程和文化認同慣性力的極值效應(thresholdeffect)。西方人對中華民族能保持如此漫長的歷史感到大惑不解,而且對海外華人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需要花那么長的時間更感到難以置信。他們勉強找了一個答案安在中華民族成員的頭上,叫“民族排外”(xenophobia)。其實,如果他們認識到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和主體開放的特征,認識到文化心理的轉變比語言、國籍、空間位置、經濟地位、政治態度的轉變要持久得多,他們或許就有足夠的耐心來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主體開放特征了。轉
- 上一篇:我國海權問題歷史反思論文
- 下一篇:我國和諧民族關系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