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信仰與社區整合
時間:2022-03-18 11:26:00
導語:民間信仰與社區整合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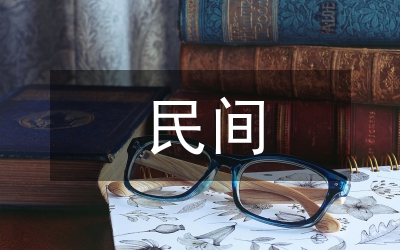
一、仙圃寨風雨圣者信仰圈的形成及其發展
1.仙圃寨建寨的歷史原因及概況
明朝中后期,戰爭迭起,社會動蕩,山賊海盜趁機作亂,侵害村民;[1](P65)同時,村落械斗之風甚盛,大村吞食小村,同宗欺負異姓的現象不時發生。有些村落為了增強力量、確保自身安全,聯合友好村落,組成會鄉進行械斗。這種會鄉械斗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危害也更嚴重。村民為了有效抵御山賊海盜的侵犯和敵村的進攻,就在鄉的周圍筑起圍墻,從而形成一個寨堡。仙圃寨的形成就屬于這種情況。仙圃寨最初是由辜厝、田頭黃、廠頭吳、賴厝、廖厝、上官路、南埔黃、黃厝巷、張厝巷、陳厝巷10個村組成的。明朝末期,黃厝巷、張厝巷、陳厝巷和橫隴,辜厝和仙樂,賴厝、廖厝和仙都,廠頭吳和古樓林、下隴之間互有矛盾,吵架械斗時常爆發,于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這10個村結成聯盟,建立仙圃寨。“仙圃寨與東莆金石市接界,距城三十五公里。”(注:參見清代吳道róng@①所纂《(光緒)海陽縣志》(卷三)之《輿地略二》,1900年版,第25頁。)它長約2公里,寬約1公里,北鄰龍下村,東鄰仙樂村,南面宏安,西面仙都,地勢開闊,寨內除賴厝的西厝屬于海陽縣東莆都外,其余各村都屬于海陽縣上莆都。
2.仙圃寨信仰風雨圣者及組織巡游會的緣由
仙圃寨建寨的確切時間無從考察。但據寨中老人說,建寨是由“戊辰八賢”之一的辜朝薦(注:辜朝薦:字端敬,號在公,海陽縣上莆都仙圃寨人,崇禎元年進士,永歷二十二年病逝。《金石鎮志》(卷2),1978年版,第245頁。)主持的。(注:筆者調查材料。報告人:翁和坤,男,翁厝村人,71歲,退休教師,高中文化。調查時間:2001年12月11日。)可知建寨時間應在明末清初。而仙圃寨信仰風雨圣者是至清嘉慶三年(1798)才開始的。據記載:
“蓋仙圃寨所祀風雨圣者,原于浮洋斗文。清仁宗嘉慶三年(1798),吾寨干旱,鄉紳自斗文恭請圣者金印、香火設壇求雨而得甘霖。回鑾之期,神示駐駕仙圃,民以寨中諸神裁定,示警大路頂黃林謝莊合建之娘宮前殿,故設廟刻金身奉之。后有鑒于各地會鄉之風甚盛,為增全寨團結,共御外侮,便遵斗文村舊例,每年正月二十二日為神游期,并拈鬮以定燈首,主全年神事。至于神游所行之路,則由神降乩于黃厝巷烏門一位十余歲童子之身,由其前導而確立之。燈首則由嘉慶六年(1801)始輪排。”(注:仙圃圣廟石刻《潮州仙圃寨風雨圣者史略》。該碑存于風雨圣者廟內,1993年立,寬116厘米,長232厘米。)
那么,風雨圣者究系何方神圣,為何仙圃寨要以它為主祭神并組織規模浩大的巡游會呢?陳景熙在《孫雨仙信仰研究》一文中已作概述:風雨圣者姓孫名道者,南宋人,生于揭陽孫畔村北厝,小時候就能預知風雨。13歲時,他在開元寺看到官民設壇求雨,于是登壇代之,雨果然大至。第二年,他在寶峰山上牧牛時忽然不見,人們認為他是鉆入巨樟中遁仙而去,于是伐樟刻像建廟奉拜,皇帝也封其為“風雨圣者”。[2](P237)由于風雨圣者很靈驗,又是皇帝親自冊封的,因此信仰它的人很多。每逢大旱之年,不少鄉村從擁有“雨仙真像”的浮洋斗文恭請雨仙金印、香火設壇求雨,立廟祭拜。
仙圃寨內各村歷來都是以農業為主。在古時水利灌溉系統不發達、人力對自然的改造無法取得實質性成果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對自然的依賴性很大,特別是在旱魔的威脅下,人們只能仰仗神力,祈求神明的幫助。仙圃寨的雨仙信仰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建立起來的。至于把風雨圣者作為全寨的主祭神并組織隆重的巡游會,則是適應“增全寨團結,共御外侮”的需要。當時,仙圃寨各村都有自己的信仰神,但要把寨內別村的神作為自己的主祭神,村民也不愿意。于是,新誕生的風雨圣者信仰及其巡游會適應形勢的需要被全寨村民共同接受了。這個以風雨圣者為中心的超村際的祭祀圈,經歷了兩百余年復雜紛繁的內外部社區整合,直至今日還是一個非常緊密的地域組織,這也可以看出民間信仰超凡的凝聚力了。
3.翁厝加入風雨圣者祭祀圈的始末
在調查中,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盡管翁厝也祭祀風雨圣者,有一段時間在行政上也歸屬仙圃寨,但在仙圃寨村民的意識中,翁厝卻不屬于仙圃寨,“老爺”無份;而翁厝也有自知之明,寨中“大鬧熱”(即風雨圣者巡游日)時,其他村祠堂前掛的繡匾寫的是“合寨平安”,惟有翁厝寫的是“合鄉平安”。那么,究竟是何種原因使得翁厝雖也祭祀風雨圣者,其寨內成員的身份卻得不到承認,陷入妾身未明的尷尬境地呢?這還得從翁厝信仰風雨圣者的始末說起。
翁厝在古時與仙圃寨并不在一個“都”里,它當時屬于海陽縣東莆都。古時翁厝是屬于下九社的。這個社由陳厝隴、翁厝、李厝、盧厝、董厝、王厝、吳厝、曾厝、謝厝九個村組成。和其他會鄉一樣,下九社也通過信仰儀式增強凝聚力,他們所信仰的神是陳堯佐王公。但是,下九社在清末就解散了。盧厝在村落械斗中被東鳳陳氏所滅;李厝則因盜賊襲擊,村民奔逃而散;王厝、吳厝、曾厝等村則遷移的遷移,絕丁的絕丁;到最后只剩下陳厝隴和翁厝,于是它們分別接管了這些村的王公,把他們作為本村的地方神。陳厝隴和翁厝還是繼續聯合游神,直到1921年發生了一件不大卻足以改變現狀的事情。事情是這樣的,陳厝隴和翁厝聯合游神,游完“安路”(神所經過的特定路線)后,兩支隊伍在村交界處分手。當時盛行著一種“擲石頭”的習俗,即兩村的村民拿石頭互擲對方,據說這樣做會使自己的霉運飛向對方,從而使自己興旺發達。這種習俗使得每年都或多或少有人受傷,但因受傷的是平民百姓,習俗還是得以繼續盛行。1921年游神中,翁厝一名10余歲的孩子被石頭擲傷,翁厝才決定不聯合游神。為何一名小小年紀的孩子的受傷可以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習俗呢?原來,這名孩子的伯父是縣長,(注:翁梓光,20世紀20年代初曾任大埔縣長。)家族中還有達官貴人,這個顯赫的家族對其生活地方的社會生活,權力分配,沖突解決起著關鍵性的作用。10多年后,這名孩子榮任仙圃寨鄉長。(注:筆者調查材料。報告人:翁克庶,男,翁厝村人,91歲,退休干部,大學文化。調查時間:2001年12月16日。)
下九社散了,翁厝需要重新尋找盟友。翁厝之所以選擇仙圃寨,是因為翁厝與仙圃寨不僅地理位置緊鄰,而且在信仰、社會生活中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翁厝還屬于下九社時,因為風雨圣者巡游時恰好要經過翁厝,因此,有些村民已有祭祀風雨圣者的習俗。下九社散后,翁厝為了尋求安全保障,就加入了仙圃寨;又因為風雨圣者在寨內諸神中的地位最高,翁厝也就入寨隨俗,把它作為全村的主祭神,而原來供奉的王公反而降到次要位置。
對于風雨圣者為何要經過翁厝,這里補充說明一下。仙圃寨10個村有9個村都完全屬于上莆都,只有賴厝比較特別,以村南厝和西厝的水溝為界,分屬上莆都和東莆都。當時,在確定寨墻時,負責人考慮到不同“都”之間如果圍起來可能會發生稅收等糾紛,因此沒有把屬于東莆都的西厝圍在寨墻內,(注:筆者調查材料。報告人:廖鎮漢,男,廖厝村人,71歲,高中文化,風雨圣者廟理事人員。調查時間:2001年12月23日。)但作為賴厝的領土,它又確實屬于仙圃寨,風雨圣者巡游時還是要經過其地。而賴厝西北與翁厝接壤,東南緊靠廖厝,東北隔一小溪與廠頭吳相望。這樣,巡游隊伍無論是從賴厝到廠頭吳,還是從廠頭吳到賴厝,都必須經過翁厝,這就為翁厝加入仙圃寨創造了客觀條件。
翁厝加入仙圃寨,參加祭拜風雨圣者時,10個村的風雨圣者燈首已經確定。風雨圣者理事會經過商量,認為翁厝與賴厝在地理位置上是鄰村,決定讓翁厝與賴厝一起擔“燈腳”(潮州音譯,即組織巡游會之首席),所以人們總是說:“翁倚賴”(指翁厝依靠賴厝)。而人口比賴厝多,經濟比其發達的翁厝人認為自己雖然沒有“燈腳”名分,一樣可以把祭祀活動辦得熱熱鬧鬧,根本不需要借助賴厝“燈腳”的名義虛張聲勢,因此不愿意接受“翁倚賴”這種說法;而寨內人一方面認為風雨圣者翁厝無份,另一方面又認為翁厝不愿意接受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盡管翁厝是后來加入的,仙圃寨還是最終確定了風雨圣者信仰和祭祀的地域范圍,即11個村共同信仰和祭祀風雨圣者。
4.風雨圣者巡游會
風雨圣者巡游日即本地人俗稱的“大鬧熱”。每逢“大鬧熱”到來,全寨彩旗飄飄,鑼鼓陣陣,爆竹震天,人潮涌至,到處一派升平歡樂的氣氛。在“大鬧熱”的一系列活動中,最能體現風雨圣者對全寨的影響的首推風雨圣者巡游會。風雨圣者巡游會開始于嘉慶六年(1801),第一個組織巡游會的是陳厝巷,其次分別是黃厝巷、上官路、賴厝、廖厝、田頭黃、張厝巷、辜厝、廠頭吳,最后是南埔黃。每村十年輪流一次。風雨圣者的巡游路線是逆時針方向(見圖1)。燈首和巡游路線是通過拈鬮和神降乩確定的,這表明仙圃寨各村盡管有強弱大小之分,但在風雨圣者面前一律平等。這種平等性還體現在圣駕的停留時間上。在確定圣駕的停留時間時,曾有人主張在大村的時間應比較長,但最后經過一番爭議,還是決定在每村的停留時間都為15分鐘。當然,當屆組織巡游會的村落也有一些特權,這些特權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優先祭祀權。祭祀風雨圣者一般在正月二十二日圣駕巡游本村時,村民才將祭品集中拿到祠堂前祭祀,惟有“燈腳”村的村民可先祭祀。(2)請劇團。劇團是指由真人現場表演的潮劇團,而非道具戲。自有風雨圣者巡游會,只有“燈腳”村才有權請劇團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約定。這條約定是否是為了防止“燈腳”村的風頭被別村超過,已經不得而知了。也因這個規定,未獲“燈腳”資格的翁厝村就成了全寨中惟一在“大鬧熱”中沒有請過劇團的村落。(3)組織鑼鼓標隊進行表演。鑼鼓標隊是由標旗隊、鑼鼓班、英歌舞隊等組成的,一般在正月二十二日上午八、九點風雨圣者巡游后舉行。近幾年,鑼鼓標隊在正月初二到鎮政府及鎮內其他村政府那里去拜年,正月初三則游行寨內各村。代表仙圃寨地區保護神信仰的鑼鼓標隊到寨外其他村游行,這是其他神明信仰所少見的,從中也可以看出風雨圣者信仰的影響有多大。
附圖
圖1風雨圣者巡游路線
翁厝村雖然不能享受上面三種特權,但也有其他村落所沒有的特權。這就是:無論輪到哪村擔“燈腳”,其巡游隊伍經過翁厝,都會在村口把神轎交給翁厝人,讓他們抬到祠堂供人祭拜,而經過其他村時,卻不曾有這樣的事。為什么翁厝人有這樣的特權?原來,“在鄉村社會中,神明往往起著地域分類的作用。”[3](P163)神明在巡游時,足跡是不能踏進其信仰范圍之外的其他地方的,否則會被視為侵犯了他人的領土,從而引起鄉村間的矛盾和沖突。在翁厝不屬于仙圃寨時,為了確保翁厝人不搗亂,仙圃寨決定,在翁厝村口讓翁厝人抬神轎護送“老爺”過境;翁厝人認為這樣做能使“老爺”保佑自己,也就樂意去做。后來,雖然翁厝也加入風雨圣者祭祀圈,這一做法卻保留下來,這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翁厝未能獲得擔“燈腳”資格的遺憾。
由于不能承擔“燈腳”角色,翁厝一直不被視為仙圃寨的一員,但翁厝也并非沒有機會獲得這一資格。據寨里老人講,1940年,南埔黃曾提出把“燈腳份”讓給翁厝,因為南埔黃一直人丁不濟,只有20幾戶人家。每次輪到它擔“燈腳”,辜厝、田頭黃、黃厝巷都得鼎力相助,盡管如此,南埔黃人還是感到組織巡游會確實力不從心,因此想放棄“燈腳份”。當時翁厝也同意。但南埔黃一名富有的華僑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有損村的體面。這名華僑剛做生意時,曾在風雨圣者面前許過愿:如果能賺到錢,就分一半給神。后來他果然生意興旺,他認為現在是兌現諾言的時候,于是他提出組織巡游會的費用由他負責,再請辜厝、田頭黃、黃厝巷幫助出人出力。因此讓“燈腳”沒有成交。后來華僑生意衰敗,無力再承擔這種費用,又提出讓“燈腳”,但時過境遷,翁厝卻不要了。
二、風雨圣者以外的其他信仰
人類學者岡田謙指出,“共同奉祭某一位主祭神的居民的居住地域為一個祭祀圈。這個地域范圍隨著主祭神影響力的大小而有不同,它可小至某一村落中的一個‘角頭’,大可包括整個村落,甚至無數的村落,形成一個超標際的祭祀圈;在另一方面,祭祀圈的范圍是相互重疊的。”[4](P177)在仙圃寨,除了以風雨圣者作為文化標志確定這一地域外,在這個社區內還以其他地方神為標志,形成地域層次較低的祭祀圈。
1.以龍尾圣爺為中心的祭祀圈
廖厝、翁厝、賴厝、廠頭吳以龍尾爺為社主組成儀象社。龍尾爺的祭祀儀式較簡單,沒有組織巡游會,只是在農歷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分別由廠頭吳、賴厝、廖厝、翁厝迎它到本村祠堂祭祀,并于當晚在本村游神。龍尾爺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如風雨圣者。它的興起主要是四村聯絡感情、抵抗外侮的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村落大械斗的現象不再時常發生,龍尾爺的這一作用已經減弱了,因此近年來它的香火不如過去旺盛了。這說明民間信仰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有密切的聯系。
廠頭吳、賴厝、廖厝和翁厝作為一個祭祀圈,還創辦了維正學堂。據《金石鎮志》記載,維正學堂是廖厝僑胞廖正興先生和汕頭商會會長賴禮園先生合資于1894年興建的一所完全小學,其校舍和教學設備曾為“三陽”(海陽、潮陽、揭陽三縣)之冠,從而解決了當時仙圃寨各村高小學生的入學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4村在仙圃寨的地位,也反映了作為一個祭祀圈在教育文化上的聯系。
2.以三山國王為中心的祭祀圈
除了以龍尾爺為中心的儀象社,三巷也以三山國王為中心組成祭祀圈。三巷的始祖都是先遷居赤石宮,后才遷至現村址的。他們的村落創建史和以三山國王為中心組成祭祀圈是否有因果聯系,現在已不得而知。但三山國王雖然為三村的共祭神,現卻只有香爐供人祭拜,沒有神廟,也沒有塑像。究其原因,是因為三山國王廟原址建于陳厝巷,建國后廟被鏟除,1979年后雖然恢復祭拜,但其他兩村都覺得自己是大村,把廟建在陳厝巷這樣一個小村對自己不公平,因此不愿出錢建廟。這表明神明在村民心目中不僅是乞求發財平安的精神寄托,同時也是反映村落力量的象征。
仙圃寨各村以風雨圣者、龍尾圣爺、三山國王等神明為中心組成祭祀圈。根據某些學者的研究,“祭祀圈與婚姻圈有相互重疊的現象。”[5](P177)但就仙圃寨祭祀圈來看,辜厝和上官路,廠頭吳和田頭黃卻禁止通婚;就龍尾爺祭祀圈來看,廖厝和賴厝也禁止通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祭祀圈的各個村落的利益并不一致。如上官路和辜厝作為寨內兩個較大的村落,互相爭奪寨內事務的主導權;廖厝和上官路是鄰村,常因水利種植發生矛盾;廠頭吳和田頭黃則因男女關系處理不當而發誓不通婚。
3.以村廟為中心的祭祀圈
仙圃寨的信仰活動和祭祀活動,除了上述幾個超村際的祭祀圈外,在這些超村際的大祭祀圈下,又各自形成以村廟為中心的村內祭祀圈,如三山國王作為村落的“地頭父母”,每個村落都有祭祀。關于這些祭祀圈,請參看圖2。
附圖
圖2仙圃寨祭祀圈略圖
三、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
風雨圣者最初是以能呼風喚雨的雨神形象立足于仙圃寨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功能發生了變化,逐漸轉化成為地區保護神,在村民的心目中,它能保佑信徒發財平安、心想事成,成為仙圃寨最具權威的主祭神和勘定仙圃寨與外界之分的象征。
1.廟宇的重建
期間,風雨圣者信仰作為“四舊”的封建迷信活動而被加以取締,不僅風雨圣者巡游會被取消,連廟也被鏟除,神像被砸碎。但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還是有一些膽子比較大的虔誠信徒偷偷拿祭品到舊址去祭祀。1981年當林任炎、辜克昌等人提倡重建圣廟時,立即得到全寨村民和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他們傾資傾力投入圣廟重建工作中。在仙圃圣廟(風雨圣者廟)的墻上勒刻著這樣一段文字:
大寨仙圃圣廟重建新樓,荷蒙上官路鄉僑胞林旺隆先生首倡善舉,興力基業喜題建樓,承賠地面權壹萬捌千元并歷年香火積余及各善男信女樂助捐資,是設斯樓暨贈鐵篷、鐵欄、香爐、燭臺等茲其勒石流芳。
捐贈人共計36人,捐資額合計66888元。石刻只舉了一些代表,至于為建新樓積極捐資的寨內外信徒則是不勝枚舉了。難怪有些干部感慨:要群眾捐資建橋修路,他們總是不樂意,但是一旦要修廟宇祠堂,他們不用號召也十分積極。這些都反映了民間信仰強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在風雨圣者廟重建活動中,華僑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在《仙圃寨修復風雨圣者廟新建敬老院籌建會委員》名單中,就有10名華僑代表。華僑們不僅慷慨解囊援助,同時又積極獻籌謀略。當圣廟重建活動遇到阻撓時,他們以自己的社會名望、財富作為資本,四處活動。華僑們之所以這么熱心投入圣廟重建活動中,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把神當作祈求平安發財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建廟祭祀活動,表達自己的故鄉之戀。華僑們還時常帶動子孫回來訪祖尋根,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祭祀風雨圣者。可見,風雨圣者作為仙圃寨的地方認同,在鄉土——海外關系的重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象征仙圃寨人的總認同的風雨圣者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海外華僑的支持而重建的。
由于眾多信徒的慷慨合力,歷經8年,新的風雨圣者廟終于在1989年建成。新廟宏偉輝煌,坐北朝南,長39米,寬23米。前后有兩殿,前殿是主廟,長14米,寬10米,安置風雨圣者及風、雨兩神童;后殿原是黃林莊謝四姓所祀女神娘娘(神廟原名娘宮),重建后未設女神像,只設案床、娘娘香爐供奉拜、存香火。娘宮原來的主祭神是女神娘娘,風雨圣者只是附祭在那里,然而仙圃寨為增全寨團結、共御外侮的需要,把風雨圣者定為全寨的主祭神,這無疑使風雨圣者一躍成為全寨的最高神,因此也就反客為主,娘宮變為風雨圣者廟,人們逐漸只知有風雨圣者而不知有女神娘娘了。這種情況和翁厝加入仙圃寨后,把風雨圣者視為全村的主祭神,而王公由主祭神降到較次要位置,道理是一樣的,即神明在一個社區中的地位,除了其神格因素外,還必須考慮到社區發展的需要。
2.民間信仰對社會生活及權力分配的影響
在風雨圣者巡游過程中,廢除爭插香的例俗反映了民間信仰對民眾的行為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以前,在巡游過程中,信徒們喜歡手拈線香,擠在風雨圣者必經之路,想最先向香爐插上自己的線香。據說,這樣做風雨圣者會特別保佑其全家。為了能得到風雨圣者的特別垂青,每個人都是不遺余力拼命往前擠,盡管保安人員大聲制止還是無濟于事,常引起大騷動。1995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理事機構經過“擲杯”(即用竹片制成的器具請示于神),規定在風雨圣者未就座之前,不準人們插香。神示如此,人們也就不敢再違背。這表明,在游神活動中,令人們信服、引起畏懼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神(盡管有人的安排成分在其中)。神對人們思想及行為的約束性也就顯而易見了。
風雨圣者打醮活動也體現了民間信仰對群眾思想和行為的影響。打醮活動于農歷十月二十一日舉行,每年一次。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在仙圃圣廟前建一牒棚,棚上請道士頌經誦佛;信徒到負責人那里拿牒文,填上要為之請牒的老婦人的姓名、籍貫、出生年月日及時辰,再交給醮頭,由醮頭拿著牒文帶領10名老人(這些老人都是各村的代表)到牒棚上游行一周,再發給信徒。請牒的對象局限于老婦人,請牒人可以是寨內人,也可以是寨外人。據說在老婦人去世時,把牒文壓在棺材底,可以消除其在世時的罪孽,讓其來世再投胎為人。因此每次打醮寨內人總是熱心為不屬于仙圃寨的親戚請牒文。這無形中也擴大了風雨圣者的信仰范圍。
風雨圣者巡游活動是風雨圣者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風雨圣者創造社區認同、增強村落團結的具體表現,同時,它也反映了仙圃寨各村落之間及村落內部權力的分配情況。仙圃寨組織風雨圣者巡游會的目的是為了創造社區認同感,使社區作為一個合作性的共同體能被不同宗族的村民所認同接受。因此,在風雨圣者信仰及儀式組織上平等是村民的要求與愿望,而這種平等性則體現在巡游會的輪祭制度上。仙圃寨村民都認為風雨圣者祭祀是全寨最重要的節慶,然而,“他們雖然都積極參與祭祀,卻不是每年都主持這一活動。儀式的主持,采用了不同村落分年輪祭的制度,這種輪祭制度把村民分為儀式的主角和配角,但又使每個村民都有機會成為主角,這就造就了一個內部相對‘平權’的社區。”[6](P172)
風雨圣者巡游會活動不僅通過采用輪祭制度體現了各村落在信仰上的平等,而且也體現了村落內部權力的分配情況。在明清時期,族、房長便是村中的政治首腦,他們對村中的社會生活、權力分配起著關鍵性的作用。1949年以后,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對基層政權加以強化,在宗族社會中嵌入比較正規的權力機構,使村中的權力逐漸集中到村主任、村長等人手中。目前,宗族的族、房長制度已不復存在,不過在村落的民間祭祀活動中,作為國家人的村主任、村長卻要聽從村里長老的安排,何時祭祀、怎樣祭祀等種種規定,均由長老們做出,祭祀所需款項由他們向村民募集,祭祀后所余款項也由老人保管,或用于來年的祭祀活動,或用于村里的公益事業。這些都表明,在仙圃寨中,以廟宇為中心的、由民間信任者組成的非正式的首領組織,在村落的內部關系調節和認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仙圃寨風雨圣者廟理事機構的組成也同樣體現著寨中各村的“平等”及長老們在寨里的重要地位。風雨圣者廟理事機構分成四股:黃厝巷、陳厝巷、張厝巷一股;辜厝、南埔黃一股;田頭黃、上官路一股;翁厝、賴厝、廠頭吳和廖厝一股。這四股機構各派出8位老人組成理事機構,他們一般任期終身。再在這32名代表中選出10名代表組成常務理事機構,其中正主任1名,副主任4人,文書、會計、出納、保管、秘書各1名,這10名常務理事每2年改選一次。這些代表負責制定有關風雨圣者事務的規定及主持重大的祭典活動。平時圣廟事務則雇傭2位老人負責,這2位老人必須能寫會算,忠誠老實,沒有家庭后顧之憂。之所以要具備這些品質,是因為他們要24小時在此值日,收納信徒的捐款等。
正因為人們認為風雨圣者能賜福于民,確保社會安定,因此香火旺盛。據理事人員說,圣廟一年能收到20多萬的捐款。這樣便能以風雨圣者的名義為社區辦善事,如新建的大寨中學,圣廟捐資10多萬元;太公橋、寨尾溝橋、黃厝巷橋,均由圣廟出錢建鐵欄桿;還致力于建雨亭、修公路等公益事業。(注:筆者調查材料。報告人:廖鎮漢,男,廖厝村人,71歲,高中文化,風雨圣者廟理事人員。調查時間:2001年12月23日。)
3.民間信仰對村落相互關系的影響
“宗族通常是指以男性血緣聯結起來的實體性社會組織。”[7](P153)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村落可視為一個宗族社區,而仙圃寨就是由11個宗族社區以風雨圣者為紐帶而結成的祭祀圈。那么,當血緣的利益與地緣的原則發生沖突時,村民是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從上面各個有矛盾的村落彼此不通婚的例子及其原因來看,村落在處理這種沖突時,往往是以血緣的利益為優先的,并且,為了達到保護血緣利益的目的,宗族社區甚至聯合祭祀圈以外的同宗族來對付屬同一祭祀圈的村落。上官路村聯合其他林姓村落與儀象社四村械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民國初,以仙都、上官路、古樓林為首的13個林姓村落結成聯盟共同對付儀象社,其中尤以廖厝和上官路兩村的械斗最為激烈,雙方斗到五月初五這一天也沒有停止。現在廖厝有些人家中午祭祖,有些人家下午祭祖,就是因為當時村民輪流和上官路人械斗。但上官路雖然人多勢眾,卻不能打敗廖厝,因為廖厝有公共田產、富人、廖厝人械斗受傷,可以用公費療傷,上官路人只能自費療傷。這樣廖厝人械斗起來不用顧慮,上官路人卻不敢這樣,結果,雙方講和了。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上官路和儀象社進行激烈械斗,但無論誰擔“燈腳”,雙方的游神隊伍還是要到對方村里去。其他村落械斗時也一樣。這就充分體現了風雨圣者信仰在民眾中的權威及其作為社區文化標志在社區整合中的作用。
與上官路聯合同宗攻打異姓村落的性質一樣,南埔黃改村名也體現了血緣原則在廟宇活動中的互動作用。南埔黃本叫“南埔銀”,它原是上九社(注:上九社:潘厝、黃斗隴、埔后翁、庵后、深巷、劉厝、程厝、石門蔡、南埔銀。)的成員,以三山國王為主祭神。后來村民搬到田頭黃、黃厝巷的鄰近地方,遂改名為“南埔黃”,并加入仙圃寨。之所以改成該名,是為了和田頭黃、黃厝巷聯宗,這樣在被別村欺負時才不會沒有外援;同時,由于南埔黃是一個小村,沒有能力獨自組織風雨圣者巡游會,需要田頭黃、黃厝巷的援助。
仙圃寨作為一個祭祀圈,還以風雨圣者信仰為紐帶創造了社區與社區外部的新關系。仙圃寨與仙都、東鳳向有矛盾,但民國初期,仙都、東鳳爆發瘟疫,迎仙圃寨風雨圣者到村里祭祀求平安。因此,仙都村以林大欽狀元府的名義贈三臺神轎給圣廟,每逢風雨圣者節慶日,這兩個地區的一些信徒紛紛詣廟行香,祈財求福。
4.民間信仰對正式權力的影響
在中國鄉村社區中,政府正式權力一般都離民眾比較遠,因此,民眾寧愿選擇神明創造的非正式權威作為他們現實生活的主導,這無疑損害了政府正式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力度。正是從維護政府權威的角度出發,政府歷來都對民間信仰實行排斥政策,有時甚至出面干預鄉村社會廟宇活動。對仙圃寨風雨圣者信仰也不例外。由于金石鎮的20幾個村中就有11個村祭拜風雨圣者,同時信仰它的寨外人也很多,每年風雨圣者巡游,除了寨中11個村共慶佳節外,鄰近的金石市也會停市參加祭祀活動。這種影響是鎮內其他神明信仰所不能及的,如果抑制了風雨圣者信仰活動,在打擊當地民間信仰活動上也就收到殺雞儆猴的效果。1958-1981年,金石鎮歷任公社書記就任前,必須簽“不準仙圃寨游神賽會”的“都頭狀”,如果任期內寨中發生“游神賽會”,則不稱職。因此,當1981年仙圃寨重建圣廟時,鎮政府決定干涉。當圣廟重建了一小部分時,鎮政府便派人把它拆掉。建廟負責人又帶領建筑工人在半夜里偷偷動工。過了幾天,鎮政府派人捉了一些長老。這種行為引起民憤,驚動了當時的潮安縣政府。縣政府經過調查,決定讓鎮政府放人,允許仙圃寨重建圣廟,這件事才順利解決。(當時,圣廟雖然重建,但風雨圣者塑像并沒有重塑。)鎮政府雖然不再干涉風雨圣者廟的重建,但并不意味著就同意舉辦風雨圣者巡游會,自此開始,鎮政府每年都會照會仙圃寨不要游神。直到1984年,輪到賴厝擔“燈腳”,賴厝人大膽地在村內舉行巡游會,但也只是營“老爺像”,沒有在寨內巡游。1985年,輪到廖厝擔“燈腳”,廖厝決定舉行一次熱熱鬧鬧的巡游會。經過和寨內各村負責人商量后,偷偷請人刻神像和造神轎。公社官員得知廖厝要在全寨中舉行巡游會,便派人到廖厝和負責人談判,要求廖厝負責人放棄這一打算。當他們和廖厝負責人談判時,小孩子就在外面扎破他們的汽車輪胎,群眾也站在外面聲援,同時,由于儀象社(除廠頭吳)共有的“大肚堰”山地供鎮武裝部操練演習,和武裝部有交情,再加上寨內其他村的支持和其他一些因素,1985年廖厝終于第一次舉行了自1964年以來的巡游全寨的風雨圣者巡游會。自那以后,鎮政府一般沒有再干涉仙圃寨的巡游會,只是要其寫保證書,保證巡游時不會出亂子,還派保安人員維持秩序。
風雨圣者信仰不僅迫使政府正式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讓步,還對正式權力的更替產生一定的影響。1938年,仙圃寨鄉長辜可卿不準村民舉行游神活動,自己卻在家中宴請親朋好友。這種做法引起村民的極大憤怒,數千名村民沖到他家與他沖突起來。翁照桓將軍派一名宣傳員去解決這件事。結果為平民憤,辜可卿被撤銷鄉長職務。第二年,這名宣傳員被村民選為大寨鄉長(仙圃寨于1939年改名大寨)。宣傳員是翁厝人。按照10村村民不把翁厝視為大寨成員的觀念,他原是不可能被選為鄉長的,但因為他維護了村民的信仰,結果當選了。這反映民間信仰對于政治有一定的影響。
仙圃寨自建立以來,基本在同一行政區域,這說明行政區域的建立及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根據民間信仰所提供的社區認同,這種社區認同遠比政府的社區識別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仙圃寨作為一個行政區域已不再存在,但它作為一個祭祀圈,卻被村民廣泛認同。
四、結語
總之,以風雨圣者信仰為主的民間信仰,與仙圃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都有密切的關系并產生深遠的影響。以風雨圣者為主的祭祀神作為一種象征,通過巡境游神的活動,勘定仙圃寨與外界的界限,在全寨社區認同和鄉村社會整合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民間祭祀圈進行研究,“就可以認識它的社會結構內涵和組織形式,以及人類群體的社會活動,這無疑是了解該地區傳統社會與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8](P268)
【參考文獻】
[1]陳春聲.嘉靖“倭亂”與潮州地方文獻之關系[A].饒宗頤.潮學研究[C].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2]陳景熙.孫雨仙信仰研究[A].饒宗頤.潮學研究[C].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3]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1997.
[4]轉引自莊英章.林圮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莊英章.林圮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王銘銘.視野中的村落文化與權力[M].北京:三聯書店,1997.
[7]陳樹良.祠堂、廟宇與社會整合[A].饒宗頤.潮學研究[C].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
[8]陳運飄等.普寧西隴的祭祀圈研究[A].饒宗頤.潮學研究[C].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