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規約》幫助犯客觀要件認定探討
時間:2022-03-02 11:02:51
導語:《羅馬規約》幫助犯客觀要件認定探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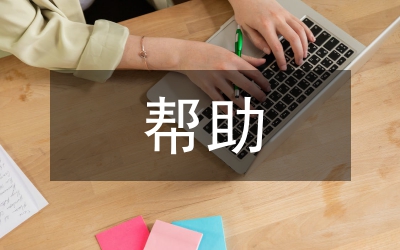
摘要:幫助犯的認定一直是國際刑法中的難點。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一是特殊指向性問題;二是幫助行為的促進程度問題。通過梳理特設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中有關幫助犯的案例,從幫助犯法理結構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指出特殊指向性不應該成為幫助犯的構成要件以及需要設置最低門檻來證明幫助行為的存在。針對我國有關幫助犯的相關規定,建議我國相關法律在對《羅馬規約》進行轉化適用時,應重新考量幫助犯和正犯之間的聯系,合理接納片面幫助犯這一概念,在對“共同犯罪”的認定上無須強調“故意”之條件,并客觀看待幫助犯從屬性問題。
關鍵詞:羅馬規約;國際刑法;幫助犯;客觀要件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是于1998年7月17日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羅馬總部召開,由聯合國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全權代表外交會議通過,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旨在保護國際人權、打擊國際犯罪的刑事法律。《羅馬規約》對幫助犯的規定豐富了國際刑法中的幫助犯理論,但由于國際刑法自身的特殊性,國際刑事法院內部至今也未能就幫助犯客觀要件認定問題的解決達成一致。這既造成法院審判工作缺乏明確的標準和依據,也影響到了部分國際間合作的展開。對我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既推動了我國和沿線國家的法律交流,也對我國的法制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加入《羅馬規約》以及對《羅馬規約》中幫助犯的相關理論和規定進行轉化適用,有利于提升我國刑事立法水平,對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羅馬規約》中幫助犯客觀要件認定的現狀和問題
(一)《羅馬規約》中幫助犯客觀要件的認定現狀。1.《羅馬規約》對幫助犯的規定。《羅馬規約》第25(3)(c)條規定,當自然人“為了便利實施某一受管轄的罪行,幫助(aid)、教唆(abet)或以其他方式協助實施(otherwiseassist)或企圖實施這一犯罪,包括提供犯罪手段”應承擔幫助犯的刑事責任。從客觀方面看,幫助的形式包括現實、物質的幫助(aid)或是精神、道義上的支持(abet),而對規約中的“以其他方式協助實施”,國際刑事法院認為其含義與“幫助”(aid)一樣,不代表某種不同的幫助形式。2.國際刑事法院在認定幫助犯客觀要件時的立場。《羅馬規約》僅對幫助犯的構成要件進行了概括性規定,而國際刑事法院則具體討論了幫助犯客觀要件的認定問題,目前的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如何確定幫助行為須達到的促進程度”,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一,國際刑事法院在Mbarushimana案中沿用了特設法庭的判決內容,認為幫助行為必須對犯罪的實施存在實質性影響(substantialeffect),但在與共同正犯相比較時,這一客觀方面的標準明顯更低①。其二,Mbarushimana案的判決雖支持“實質性影響”觀點,但法院內部對該問題的看法并非一致,該案法官FernándezdeGurmendi就持不同意見,她認為《羅馬規約》第17(1)(d)條并無要求幫助行為須對犯罪實行達到某種促進程度的作用,而僅僅是被用于判斷案件在程序上是否享有歸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資格。因此,她反對在認定客觀要件時給幫助行為設置某種“門檻”。在Bemba等人案中,國際刑事法院認為規約第25(3)(c)條沒有要求被告行為在構成幫助行為時須達到某種最低“門檻”的措辭,因此也拒絕適用“實質性影響”標準,并認為幫助行為可由任何對犯罪實行有促進性的行為構成②。(二)《羅馬規約》中幫助犯客觀要件認定存在的問題。1.特殊指向性作為幫助犯客觀要件是否必要幫助犯是否僅在幫助行為指向特定的犯罪實行行為時才成立,這就是特殊指向性問題。在Tadić案中,上訴法庭提出“不論何種形式的幫助行為都必須指向特定的犯罪”,并最終認為特殊指向性作為幫助犯構成要件具有必要性③。而后的法庭在審理中大多都直接引用了這段判決作為依據。直到Mrkšić和Šljivančanin案的上訴法庭認為這種特殊指向性可以由幫助犯的客觀要件所反映,因此反對將特殊指向性視0882021年02月上半月刊(總第132期)法學作構成幫助犯的必要條件。有學者指出,特設法庭基于習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對幫助犯的客觀要件進行注解,進而分析特殊指向性問題,而國際刑事法院則依賴于對《羅馬規約》文本的解釋,二者的內在機理并不相同[1]。由此可見,特設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在處理該問題的路徑選擇上存在差異。2.幫助行為須達到的促進程度標準不統一正如前文所述,國際刑事法院內部對于幫助行為須達到何種促進程度的標準認定并不統一,除部分判決支持“實質性影響”觀點外,也有判決提出不存在某種衡量被告行為對犯罪實行行為的促進程度的門檻。“實質性影響”標準源于特設法庭,但特設法庭卻并沒有對該標準進行統一的解釋。在Tadić案中,前南法庭認為幫助行為的“實質性影響”就是指:若一般情況下沒有幫助行為,則犯罪很可能不會以相同的方式發生。Furundžija案中,特設法庭則指出幫助行為并非作為犯罪實行行為的必要條件存在,以及邊緣性的犯罪參與者不足以承擔幫助犯的責任④。法庭之后又在多項案件中對“實質性影響”做出解釋,但始終沒有明確的定義。
二、《羅馬規約》中幫助犯客觀要件的認定問題分析
(一)特殊指向性是否應當作為幫助犯客觀要件。1.特殊指向性問題之歷史回溯。前文已述及在Tadić案中,上訴法庭首次提出特殊指向性作為幫助犯構成要件具有必要性,直到Mrkšić和Šljivančanin案的上訴法庭對此持反對態度,并引用了Blagojević和Jokić案針對該問題的論述,認為Tadić案的上訴庭當時只是把幫助犯和其他犯罪責任模式做比較,并沒有完整地論述幫助犯的構成要件;而且既然被告人的幫助行為對犯罪實行行為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那么這一行為本身就具備了特殊指向性⑤。Lukić案的上訴法庭支持Mrkšić和Šljivančanin案針對該問題的觀點,但該案的一些法官有不同意見。Güney法官認為“指向性”這一要素只是隱含在被告的幫助行為中,并且這個問題與本案也無太大關聯,法庭在這種情況下無法確定“指向性”是否是幫助犯必須的構成要件⑥。Perišić案的上訴法庭認為,先前的部分判決雖然沒有直接引用Tadić案關于“特殊指向性”的結論,但那些案件判決沒有背離Tadić案,其本身就已經默示同意了這一觀點。Perišić案的上訴法庭還認為,當被告處在距離犯罪實行行為較近位置時,這種特殊指向性可以隱含在幫助犯的其他構成要件中,但如果被告離實行行為距離較遠,則有必要考慮特殊指向性問題⑦。然而,Perišić案上訴法庭的法官針對該問題的觀點也并非完全一致。Ramaroson法官認為“特殊指向性”并非幫助行為的一個明確要求,反而隱藏在幫助犯的主觀要件中;Meron和Agius法官認為,特殊指向性既是幫助犯客觀要件的一部分,也是其主觀要件的一部分。在Taylor案中,塞拉利昂法庭認為“特殊指向性”和主觀要件中的“故意”相似,并仔細研究了“二戰”以來的國際習慣法,指出這一要件是不必要的。此后的諸多案件中,特設法庭都不再將“特殊指向性”作為幫助犯成立的必要條件。特設法庭的判決揭示出“特殊指向性”與幫助犯的主客觀要件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但其有關“特殊指向性”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對于條約和案例的解釋上。以下分別從特設法庭和國際刑事法院角度基于法理結構來探尋和分析“特殊指向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2.特設法庭角度。《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規約》(以下統稱《前南規約》)和《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規約》(以下統稱《盧旺達規約》)并未區分正犯與共犯,仍采用單一正犯體系。在這一體系下,幫助犯和其他犯罪參與者從本質上來講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也不必考慮從屬性的問題,只是因為刑法的規定而與他者有所區分。單一正犯體系基于擴張正犯概念而構建,在因果關系上立足于因果共犯論,主張幫助犯和正犯都對法益造成了侵害,兩者與侵害結果間的因果關系應該是一致的。而“特殊指向性”要求的提出是為了確定幫助行為與特定犯罪實行行為間的因果關系,這在單一正犯體系下就顯得沒有必要。前文所述的特設法庭的部分法官認為“特殊指向性”可以被包含在幫助犯的主觀要件或客觀要件中的觀點僅僅是基于片面的考量,因為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對犯罪實行行為具有實質影響的幫助行為,但該行為卻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罪行。例如,一個組織犯下了各種罪行,但并不代表這個組織的一切行動都是有罪的。如果某人對該組織給與了一筆捐贈,但由于這筆捐贈有可能被拿來犯罪,也有可能被用來從事一些和犯罪不相干的事,而無法確定捐贈行為的特別指向,那就不能認為這一行為(捐贈)具有特殊指向性。同樣,僅僅在主觀上具有幫助犯罪的態度而無實質性影響,也就不具備幫助行為和結果間的因果聯系,那又何談特殊指向性?此外,由于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特設法庭針對“當被告距離犯罪實行行為較遠時”的情形而提出需要考慮特殊指向性的觀點已經失去了意義。因此,在特設法庭中,“特殊指向性”不應該作為幫助犯的構成要件。3.國際刑事法院角度不同于《前南規約》和《盧旺達規約》這種單一正犯體系的立法模式。國際刑事法院立足于《羅馬規約》采用的正犯、共犯二元區分體系的立法模式,并接納了Roxin的犯罪事實支配理論,因而擁有討論從屬性問題的理論空間。特殊指向性問題提出的意義在于確定幫助行為與特定犯罪實行行為間的關系,其實質就是幫助犯對正犯的實行從屬性問題。《羅馬規約》第25(3)(c)條規定幫助犯只有在正犯未遂或既遂時才成立,確立了幫助犯對于正犯的實行從屬性。Roxin認為,共犯的處罰根據在于其自身就創造出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并借助正犯的實行行為侵犯了法益。這進一步反映了幫助行為“特別指向”實行行為的特點。因此,基于對幫助犯從屬性和處罰根據的考察,國際刑事法院中的“特殊指向性”要素應當是幫助犯所不可或缺的,但這種指向性要素完全可以被幫助犯的構成要件所吸納。而在Bemba等人案中,國際刑事法院認為,任何促進行為都有可能構成幫助行為的判決,實質上是對實行從屬性的概念發起了挑戰,模糊了幫助行為和實行行為的關系,取消了源于共犯處罰根據的幫助行為獨立法益侵害要求。(二)幫助行為的促進程度問題。1.幫助行為促進程度問題之歷史回溯。在Tadić案中,特設法庭認為“為了判斷被告是否需要為參與一項罪行負刑事責任,有必要確定一個針對幫助行為的量的標準”,并提出幫助行為必須對犯罪的實施產生直接和實質性的影響(substantialeffect)。而到了Furundžija案,前南法庭仍采用“實質性影響”這一判定標準,只是取消了使用“直接”一詞來進行限定。但也指出幫助行為并非作為實行行為的必要條件存在,以及邊緣性的犯罪參與者不足以承擔幫助犯的責任,并引用“二戰”時的Teschetal.案以證明其觀點,在該案中,被告所處的職位使得其沒有能力對將毒氣運往奧斯維辛這一行為施加任何影響,但是負責制造、運輸毒氣的相關公司負責人卻被判刑。Taylor案的上訴庭也認為這種“實質性影響”是判定幫助行為時不可或缺的要件。上訴法庭認為,幫助行為具有“實質性影響”的具體表現為“對有組織的犯罪的支持”“提升了犯罪實行者的犯罪能力”“確保了不人道處境的持續存在”等。上訴法庭也指出了一些案件中的參與行為不被認為具備“實質性影響”的原因,包括基于被告所處的位置以及被告的行為不足以將其和犯罪實行行為結合起來等⑧。如前所述,國際刑事法院在Mbarushimana案和Lubanga案中也沿用了特設法庭的判準,即幫助犯必須對犯罪的實施存在實質性影響⑨,但國際刑事法院在Bembaet.al案中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否定了幫助行為須具備“實質性影響”要求的必要性。本文認為,構成《羅馬規約》中幫助行為的最低門檻應為Furundžija案中的“實質性影響”,這一標準滿足《羅馬規約》第25(3)(c)條中幫助行為“便利犯罪的實施”的規定,而Tadić案中法庭提出的“實質性影響”標準由于特設法庭相關理論的轉變不再適用于目前的環境,而國際刑事法院在Bemba案中提出的“構成幫助行為不需要門檻”的觀點是有一定缺陷的。2.“實質性影響”內涵的解釋在不同時期發生轉變。《前南規約》采用的是單一正犯體系的立法模式,幫助犯和正犯都對法益造成了侵害,兩者在因果關系上是一致的,共犯和正犯僅在罪名上有所區分。在Tadić案中,特設法庭認為“實質性影響”指一般情況下若沒有幫助行為,則犯罪很可能不會以相同的方式發生。這表明幫助行為對犯罪結果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幫助行為實質上屬于實行行為,法庭在此時的看法符合單一正犯框架下對于幫助犯的描述。而到了特設法庭后期,法庭借鑒《羅馬規約》的立法成果,開始對正犯和共犯進行區分,指出幫助犯的可罰性在于其幫助行為和犯罪實行行為間的聯系。Furundžija案中,前南法庭仍接受“實質性影響”這一判定標準,Orić案的判決認為“實質性影響”指幫助行為使得犯罪的實行變得更加容易、簡單⑩。Taylor案的上訴判決書提到的符合“實質性影響”的具體情形中的幫助行為也都是通過正犯行為對犯罪結果產生了間接影響。其實質上是用因果促進說來判定幫助行為的構成標準。可見,隨著相關理論的轉變,特設法庭逐漸開始拋棄單一正犯體系,也放棄了深植于前者內核中的同一因果關系說來限定幫助行為須達到的促進程度,轉而采用促進因果關系說來解釋幫助行為的最低門檻問題。這相應地造成了“實質性影響”的內涵在特設法庭不同時期的轉變。目前,由于《羅馬規約》采用正犯、共犯二元區分體系的立法模式,顯然,Tadić案中關于“實質性影響”的解釋已不具備適用性。3.不設置最低門檻無法證明幫助行為的存在。國際刑事法院在部分案件中認為幫助行為不應該設置最低門檻的觀點無疑是令人疑惑的。這是因為《羅馬規約》第17(1)(d)條規定國際刑事法院審理的案件必須具備相應的嚴重程度,這實質上限定了幫助行為的最低門檻。倘若構成幫助行為不需要一定的影響,則向饑餓的犯罪團伙出售食物,為在悶熱的地下室實施酷刑的人為幫助行為不應該具備最低門檻的觀點將會造成法院在程序和審判兩種情況下面對同一對象,卻持不同判準的雙標情形。從操作層面來講,不管是特設法庭還是國際刑事法院,都是先通過考量被告行為和犯罪實行行為間是否達成一定的因果關系來判定該行為是否構成幫助行為。如果取消幫助行為的最低門檻標準,則國際刑事法院實際上無法證明幫助行為的存在。
三、合理接納和轉化《羅馬規約》幫助犯相關理論和規定
“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包含眾多《羅馬規約》締約國,各國法制相異。我國加入規約之后,在懲處相關罪行時應適用統一、明確的定罪標準,但規約的接納和轉化應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現行《刑法》的基本體系,并把握國際刑法發展趨勢,有選擇地借鑒國際刑法的理論。(一)對片面幫助犯相關規定合理轉化。一般來說,幫助犯在幫助正犯實施犯罪時,存在與正犯進行意思溝通的犯罪事實,但也有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況下予以協力,而助其完成犯罪的情況。后者一般被認為構成片面的幫助犯,屬于片面共犯的一種。特設法庭認為精神幫助應是一種直接影響,只有在正犯意識到受到幫助者精神鼓勵時,精神幫助犯才成立。而在Bemba等人案中,國際刑事法院認為精神幫助行為可以是間接的,即使證人并沒有明確意識到自己受Bemba的鼓勵,Bemba通過中間人而對證人施加影響的行為亦可構成精神幫助⑪。國際刑事法院強調,幫助犯之成立在于其行為與正犯所為罪行的關系,而非與正犯的聯系,因此“正犯必須意識到受到幫助犯精神鼓勵”的構成要件是不必要的。就客觀方面看,幫助行為既然最終加工于罪行本身,則幫助犯與正犯之間的主觀聯系則非屬必要。可見,Bemba等人案的判決實際上承認了片面幫助犯的存在。但是,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情形。該規定指出共犯成立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即行為主體為二人以上、客觀上要有共同的行為且主觀上還必須有共同的故意[2]。幫助犯作為共犯的一種,要想獲得和正犯共同的故意,就只能通過雙方相互間的聯絡溝通,但這與片面幫助犯的定義相抵觸。因此,排斥片面幫助犯在某些情況下就會存在犯罪責任分配的困難。例如,乙和丙之間素有怨仇,甲作為乙的朋友一直想幫助乙教訓下丙。一日,甲未通知乙而將不知情的丙引誘至乙的家中,乙見仇人上門分外眼紅,最終殺死了丙。在該案中,盡管依照我國法律,可以認為甲在主觀上具備殺人之故意,且由于甲和丙之死亡具備因果關系,因而也可認定甲具備故意殺人的客觀要件,從而最終可以判處甲故意殺人罪,并由于其“幫助”了乙殺人而承擔從犯責任。但現行《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因此在法律實踐中,法院往往依照主犯之刑責,來對從犯應承擔的刑責進行適度減輕。由于甲、乙之間無法構成共同犯罪的關系,因而實際上無法確定甲須承擔的刑事責任的大小。可見,幫助行為是單向性的。幫助行為只要促進了正犯的實行行為,為實施犯罪提供了便利即可。至于幫助犯和正犯的意思溝通,則實屬不必。國際刑事法院認為,幫助犯的故意并非實現犯罪結果的故意,從側面指出幫助犯和正犯不一定享有共同故意,而我國對“共同犯罪”的規定則忽略了幫助犯的這一特點。因此,建議我國相關法律在對《羅馬規約》進行轉化適用時,應重新考量幫助犯和正犯之間的聯系,合理接納片面幫助犯這一概念,在對“共同犯罪”的認定上無須強調“故意”之條件。(二)客觀看待幫助犯從屬性問題。幫助犯的從屬性屬于共犯從屬性理論的一部分。共犯從屬性指在區分制體系中,正犯居于定罪處罰的核心位置,共犯之可罰性往往從屬于正犯,即共犯從屬性說的核心是實行從屬性。《羅馬規約》第二十五條規定,幫助犯只在正犯罪行既遂或未遂時成立,即要構成幫助犯,前提是正犯須已著手犯罪實行。因此,《羅馬規約》采用共犯從屬性說。實際上,共犯之正犯化現象如今已普遍存在,適用共犯從屬性說已不再具備優勢。日本雖遵從共犯從屬性說,但其刑法典也仍將部分幫助行為獨立成罪,如幫助內亂罪、援助脫逃罪。再者,由于信息時代中網絡的普及,許多依靠網絡進行犯罪的幫助犯在犯罪中的地位經常高于實行犯罪的正犯,如在網絡上大范圍提供病毒種子文件的行為,相比小范圍內傳播網絡病毒的行為更具有危害性。我國現行《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于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表明即使受教唆者沒有著手犯罪,教唆者都可能僅因為單純的教唆行為而獲罪。又如,我國《刑法》將部分幫助行為單獨成罪,如教唆他人吸毒罪、協助組織罪、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因此,我國《刑法》排除共犯對正犯的從屬性聯系,不采共犯從屬性說。也正因如此,我國才可以依法處罰重罪預備犯,有效懲治威脅社會基本利益的不法行為,維護國家社會秩序的穩定運行。由于我國不采共犯從屬性說,針對能導致共犯處罰范圍擴大的問題,本文認為該論點實際上不成立。雖然在理論上不采共犯從屬性說會使得教唆未遂者和幫助未遂者都受到處罰,但實際上這兩者的社會危害性都較小,一般來說沒有被處罰的必要性,只有那些被刑法所明文規定的,且對法益具有較大危險性的共犯才會被單獨處罰。
參考文獻:
[1]冷新宇.國際刑法中的幫助犯:實踐與理論疑問[J].國際法研究,2018(1).
[2]劉明祥.單一正犯視角下的片面共犯問題[J].清華法學,2020(5).
作者:陳通 單位: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
- 上一篇:后勞教時代“微罪”入刑正當性分析
- 下一篇:污染環境罪之“處置”行為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