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現代人心性體驗
時間:2022-11-15 05:37:00
導語:透視現代人心性體驗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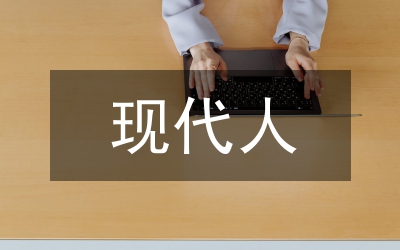
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這樣的敘述并不符合中國文化的實際。歐洲現代化之前的社會是相對一體的基督教社會,神學—形而上學精神可以概括為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形態,無論是社會結構還是個體心性,都具備這樣的神學—形而上學形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面對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以儒文化為核心,儒、道、釋三種不同的文化觀念相互融合的文化。
儒學文化是一個能夠貫通宇宙、社會、人倫的完整思想體系。主要體現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心性儒學、政治儒學和世俗化儒學。心性儒學探求“性與天道”為核心的宇宙觀問題,以追求完美的道德人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為目的;政治儒學探求政治制度的意識形態問題,以綱常觀念規范社會政治行為;世俗化儒學則以忠孝仁義等等道德化的生活理念,潛移默化的制約和規范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3]按照歷代儒學大師的觀念,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是“儒學精英”們關注的領域,對于普通百姓來說,世俗化儒學只是一種“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范疇。
這種世俗化儒學的觀念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中普通百姓的道德化的生活心態(體驗結構),道德觀念在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當中是一種理性的道德,在世俗化儒學體系中卻不再是一種理性的道德了,而是一種具有了宗教意識的道德觀念了。宗教意識的道德雖然可以承擔一些宗教的功能,但畢竟不是宗教。缺乏對生命意義的釋義,對世俗化儒學來說,是一個致命的缺憾。世俗化儒學為中國人提供的生命意義的釋義是什么,簡單的說就是在宗法觀念的人倫秩序中以限定的道德規范為目標,依據習俗生活,完成個人道德化的人生過程。至于何謂“限定的道德規范”不是需要思考的問題。這種生活心態(體驗結構)與舍勒所說的傳統基督教文化的神學—形而上學的精神氣質并不相同,只能理解為一種世俗化儒學的精神氣質。
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撞下崩潰了。“”之后的中國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既用于民族國家建構又用于社會文化發展的精神資源。在經歷了許多波折之后,共產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理論擔當起了這一具有雙重功效的精神資源。提供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建構功能理論的同時也必須成為能夠提供一種與之相應的人的精神氣質的資源。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精神,社會公義、社會公平、社會和諧是社會主義精神的基本理念,平等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核心[4]。在歐洲文化中,社會主義精神是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但是在中國并沒有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現實。中國社會對平等理念的追求主要是對西方強勢文化的一種抗衡,其次才是社會文化發展的一種內在訴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平等還只是文化精英們的理念,并沒有成為一種社會理念。作為社會理想的社會主義精神的形成過程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不得不和政治運動糾纏在一起,因此始終沒有確立一個相對明確的社會主義精神體系。1949年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精神就不再僅僅是一種社會理想,同時也必須是一種能夠提供社會個體生命意義的釋義功能的精神體系,于是出現了雷鋒這個道德化的優秀形象。雷鋒一直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下個人生命意義的釋義注腳。認真分析人們心目中理解的雷鋒形象,不難看出,雷鋒是中國傳統的世俗化儒學理念中忠孝仁義的現代翻版,是世俗化儒學精神和二十世紀理想主義政治潮流的結合體。這種獨特的心性體驗結構成為后來的“”中彌漫的政治激情的群眾基礎。
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結構和文化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者們在接觸了大量西方社會二十世紀的理論研究成果之后發現,其實中國的所有現代化問題都不過是整個人類社會現代化問題的組成部分,強調共性也罷,宣揚個性也罷。問題是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吸收的。
對照舍勒的觀點,以往的學者過多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建設的研究,較少關注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人的研究;即使有限的研究也是因循傳統意識,過多的強調應然,較少的承認實然;往往把研究的目的納入教化和引導的思維模式中,而不是真正探索性的研究。對于“現代人”心性體驗結構的研究看來還有待探索。
現代性不僅是一場社會文化的轉變,環境、制度、藝術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轉變,不僅是所有知識事務的轉變,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轉變,是人的身體、欲動、心靈和精神的內在構造本身的轉變[5]。舍勒指出現代現象中的根本事件是:傳統的人的理念被根本動搖了,以至于“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當前這樣,人對自身如此的困惑不解。”[6]
傳統文化不能自然的被帶進現代社會,這是所有面臨現代化問題的傳統文化不可避免的困境,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能例外。儒學文化重人倫道德、重政治秩序、輕個體生命體驗的缺憾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中顯現出強烈的困境。
困境之一,是現在還沒有一個能夠研究這個問題的領域。習慣的學科劃分體系是一個知識性的學科體系,與西方文化相比沒有神學研究體系,社會學研究也很少關注當代社會作為個體的人的研究,西方文化在上一世紀出現的“現代社會理論”對中國文化界來說還只是一個概念。
困境之二,是缺少可以研究的問題。中國的社會變革在過去十年里有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許多社會問題提出得太倉促,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只有近十年的過程,城市市民階層的形成還處在開始階段。有一些地域文化差異問題研究,鄉村文化研究也基本上轉向了民俗學領域。
困境之三,是社會問題開始大量涌現,擺在學者面前的是沒有途徑應對這些問題。例如大量的青少年癡迷于電子游戲,由此引發的社會思考不少,理論解釋卻沒有。民工問題又以新的方式成為社會問題,理論界卻缺少研究這些問題的環境和依據。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都是社會現實提供給學者們需要研究的問題,卻沒有一個相應的研究方法。
現代人的社會心態(體驗結構)的形成和特征問題,怎樣研究,研究什么,這里提出一個概念,希望可以找到研究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亞傳播現象。
傳播學也是近代西方文化開創的新興學科,研究人類社會的各種傳播行為。傳播學被中國理論界接受的背景是由于新聞媒體機構的迅速擴張,新聞理論界發現以前理解的新聞概念只能算作一種組織傳播行為,還不是真正意義的大眾傳播,迅速擴充的媒體現狀已經具備了實現大眾傳播的條件,所以希望借助傳播學研究完成從組織傳播向大眾傳播的過度。這樣一個功用性的目的導致傳播學在中國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新聞機構展開的,缺少對于處在傳播環境中的人的關注。
由于傳播的技術條件的大大改善,近幾年在傳統的媒體機構內部和新興的媒體當中出現了一種有別于正統的傳播理論的傳播行為,可以稱為“亞傳播現象”。這種現象主要具備這樣幾個特性:
(1)亞傳播現象不是由特定的機構來控制,它具備一種自組織能力;
(2)參與亞傳播活動的人員不再是單向的傳播者和接受者,雙方的界限已經沒有了,甚至不能依據字面意思理解為互動行為;
(3)亞傳播的類型不再是傳播學理解的勸服型概念了,傳播者的目的同樣是希望影響他人,不過不以影響的實際效果來衡量傳播的作用;
(4)亞傳播的具體內容已經不明確了,可能完全沒有實際內容,也可能虛構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內容進行傳播;
(5)亞傳播對參與者來說,對其日常生活的干涉非常明顯;
那些傳播行為可以理解為亞傳播現象,不難列舉。廣播電臺近年來都在晚間開辦了情感熱線類節目,所有參與節目的人共同構成了一種亞傳播現象;網絡游戲是另一個典型的亞傳播現象;各個商業網站開辦了形形色色的聊天活動是又一個亞傳播現象。諸如此類的現象現在已經不算罕見了。亞傳播不是大眾傳播,只針對相應的人群,而非概念化的大眾;亞傳播不是組織傳播,因為沒有一個相應的組織形式;亞傳播也不是人際傳播,因為并不針對具體的人。
亞傳播現象主要指那些由不確定的人群在希望擁有共同的現代性體驗的心態驅使下借助某種傳播技術結合成為一個體驗共同體的行為過程和結果。亞傳播現象的核心是共同體驗,這種體驗無法從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獲得。因此,研究亞傳播現象就可以研究一部分“現代人”的體驗結構。也有一些注意到這種現象的學者嘗試使用“泛傳播”[7]的概念解釋類似的現象。不過論者提出的“泛傳播”更多的是指傳播功能的擴展,與傳統傳播學的研究旨趣沒有本質的區分。提出“亞傳播現象”的概念,正是為了強調與既有的傳播觀念的本質區別。
對于亞傳播現象,可供研究的案例很多,不過上述的網絡游戲,網絡聊天,廣播電臺的晚間情感熱線節目是比較典型的例證。考察這幾個例證,可以注意到一些共同的特征:
(1)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世俗化儒學體系已經解體。前文所述,世俗化儒學的精神氣質是傳統社會中個人生活心態(體驗結構)的基本核心,宗法社會的前提之下,個人的生命意義往往依附于確定的人倫秩序。隨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改變,傳統意義的家族徹底解體了,家庭不再承擔生命意義的釋義功能,而僅僅是一個生活結構方式和情感載體。過去的通過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觀念不再能夠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人提供生命意義的釋義作用。根據最近的統計,經常光顧網絡游戲的在校學生已經超過一千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其中相當多的人都是所謂不愛學習的學生。原因很簡單,通過學習獲得成就的生命意義的釋義方式已經不能說服他們了,他們不再對家庭承擔道德責任(報答養育之恩)。學習本身只是一個知識的獲得過程,不是生命意義的釋義,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喪失了意義,網絡游戲這種通過即時的競技手段賦予生活以虛擬意義的方式自然被接受,網絡游戲成為癡迷者對生命意義的體驗方式。看一看另一個例證,網絡聊天,參與過網絡聊天的人數應該是一個更為龐大的數字,而且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年齡階段和職業階層。人們為什么聊天,因為現實生活喪失了意義。傳統的世俗化儒學觀念對人生意義的理解是一種道德化的理解,既然是道德化的理解,就需要一個道德評價方式,在特定的人倫秩序和日常生活的領域內的公共評論結果就是實現這種評價的基本方式。但是現在這種秩序完全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內容完全改變了,習慣的道德評判方式和結果受到了質疑。人們對意義的理解越來越疏遠了道德觀念。參與網絡聊天的人有一個幾乎共同的特征,交流對象完全脫離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因為需要脫離開傳統的道德評價體系,獲得一種不受道德制約的意義體驗。這種聊天所形成的交流感不管是有實際的意義還是只有虛擬的意義,都是對傳統的釋義方式的否定和叛離。至于各種廣播電臺的晚間情感熱線節目更是確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世俗化儒學精神是一種道德化的人生體驗結構,男女結合是家族延續的神圣行為,傳統家庭結構當中基本上沒有感情生活的內容,無論男女,都沒有理由因為感情問題懷疑和動搖家庭的基礎。現代性社會結構從根本上動搖了這種觀念的道德根基。人們開始尋求對感情生活的需要,開始把感情生活(非道德內容)理解為個人生命意義的組成部分,傳統的世俗化儒學精神在個人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了本質性的質疑。亞傳播現象不僅說明傳統的世俗化儒學的精神氣質喪失了作用,而且說明參與亞傳播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正在形成的現代性體驗方式。
(2)現代性體驗結構有沒有核心內容,現在回答這個問題為時尚早。舍勒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給出了一個關鍵詞“怨恨”[8]。舍勒并不否認贏利欲、工作欲、勤儉、契約意識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征,但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是“怨恨”。怨恨心態是一種生存性倫理的情緒;是一種個體把自身于他者進行對比產生的社會化心理結構。社會個體在生命本質意義上的平等和實際生活境遇中的不平等導致了這種持續性的情緒緊張。為了消除這種生存性的價值比較的緊張情緒(怨恨),怨恨者可能產生兩種價值評價:貶低被比較者的價值或者提出不同的價值比較內容。將舍勒的這種分析和目前出現的大量青少年網絡游戲癡迷者的群體性情緒類型作比較,會發現驚人的恰當。現在的教育制度本質上并不是一種素質教育,而是一種成功教育,通過不斷的甄別和淘汰失敗者來激勵成功者。對于實際上的失敗者和心理感受上的失敗者來說,怨恨就成為一種長期醞釀的緊張情緒,競技類網絡游戲成為宣泄表達怨恨情緒的當然方式,理解了這種強烈的心性體驗的基礎,就不難明白,網絡游戲為什么充斥了大量的暴力和血腥內容,只有暴力和血腥才可以充分地宣泄怨恨情緒。亞傳播現象的社會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傳播活動自身,成為“現代人”心性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達方式。
(3)現代性的生命意義的釋義問題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在傳統社會中世俗化儒學精神氣質為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同一的、即成的目標內容。而在現代性社會中,對生命意義的釋義方式不再擁有同一的目標,不同的人完全可以選擇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和結果。個人的生活心態和道德形象總會經受習俗和傳統的評判與指責,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一般不會主動表現自己獨特的生活觀點,而是選擇習俗可以接受的生活態度,但是在亞傳播環境中,卻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生活心態,不必在意對方如何評判,因為交流者一般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圍內,不會干擾自己的生存狀態。而在亞傳播活動中,人們表達出來的生活心態是具體的和多樣的。只要注意一下廣播電臺的晚間情感熱線節目就會發現,這里完全不存在“意見領袖”這樣的概念,傳播的結果會使所有參與者的心性體驗受到影響或改變,但是究竟是怎樣的影響,已經無從了解了。傳播行為可以形象的理解為一幅畫面,平靜的水面投下了一塊石子,傳播者希望傳播的內容像水波一樣逐漸擴散。但是亞傳播現象則完全不同了,水面已經失去了可把握性特征。在各種各樣的網絡聊天活動中更是如此。
(4)在亞傳播活動中,相互交流情緒性體驗的過程成為傳播的實際目的,用以交流的內容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傳播學研究中依據符號學原理,將傳播的內容分解為“能指”和“所指”兩個不同的層次,將借以實現傳播過程的符號理解為“能指”,將傳播者希望傳播的意義理解為“所指”。傳播的過程就成為“能指”和“所指”相互轉換的過程。在亞傳播現象中,符號學的這種理解方式受到了顛覆。多數參與亞傳播活動的人首先不是考慮表達和接受什么樣的“所指”,而是體驗一種處在傳播過程中的獨特情緒,可以觀察到的所有傳播活動中的“能指”和“所指”其實都是“能指”,傳播過程變成了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情緒體驗過程,這一點在傳統的傳播學中無法解釋。在傳統文化中,一個人可以對自己的未來進行能夠預期的想象和規劃,因為生活是一種可以理解、可以把握的存在方式;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中就完全不同了,生活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面對一些完全陌生的社會現象,會產生一種根本無法消除的疑惑感,會產生一種沒有原由的幻滅感,在生存本質層次上人和社會處在一種極度對峙的狀態,所有來自權威的解釋方式都受到了懷疑,這是現代人獨有的一種無法表達的生存性情緒。參與亞傳播活動只是這種復雜的生存性情緒的體現方式,僅僅是體現。生存性的情緒完全不同于生活中的情緒,這種情緒沒有一個可以由此產生和可以針對的具體對象,所以也就沒有可以表達的具體內容,只能在亞傳播活動中,借助“無所指”的傳播行為來體現。
“現代人”是一個正在形成的概念。現代性問題的研究還處在開始階段;亞傳播現象也只是新近出現的社會現象。
為什么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可以從考察亞傳播現象著手;為什么對亞傳播現象的關注能夠如此直接的引出現代人的體驗結構的這一問題,這兩者擁有怎樣的關聯。解釋這種關聯并不艱難,這與現代性問題的提出方式有關。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貫穿整個近代史,但是現代性問題的提出卻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列強的槍炮挾持下開始的,知識分子最早感受到了中國所面臨的窘境,經過苦苦的思索和探尋,知識分子首先看到的就是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腐敗與衰朽,于是建構一種能夠使中國社會抗衡西方列強的政治制度就成為首要的、也是唯一的強國之路。由前蘇聯的“十月革命”推動的席卷整個世界的政治浪漫主義立即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青睞,共產主義理論和信仰作為西方文化的歷史產物、作為對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批判武器,滿足了中國人的心性欲望,因為它可以戰勝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簡單愿望的驅使下,中國人把對美好生活強烈渴望的熱情全部投入到共產主義制度的建構當中。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狂熱的幻覺中:社會主義是一種遠比資本主義優越的政治制度,所以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當然比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生活的更加幸福。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處境,由于傳統文化的結構性缺憾和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批判性結構還在主宰著學術界的研究旨趣,八十年代的學人們仍然將目標鎖定在制度改革問題上,還在爭執應該建構怎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問題。現代性問題進入研究者的視界應該是在九十年代,現代性問題必然伴隨“現代人”的出現才可能產生,而“現代人”出現的標志應該是九十年代以王朔小說、崔健搖滾、周星池電影的普遍傳播。接受這些文化偶像的年輕人并不是社會主流人群,他們的文化訴求還不能被主流社會寬容地接納。因此相對寬松的亞傳播環境成為這些人聚集并且表達自己的主要環境,由此可以明了,為什么現代性問題如此密切的和亞傳播現象聯結在了一起。
當然,現代性問題對于中國這樣的文化背景來說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這樣的一些“現代人”還只是現代生存方式的早期嘗試者,亞傳播現象能夠體現的也只是紛繁樣式的一個側面。現在在亞傳播環境中體現出來的那些特征還不足以對現代性問題形成整體的把握。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亞傳播”這個概念,還不是梳理現代性問題。亞傳播應該作為一種傳播學概念出現,應該成為傳播學研究的領域之一,其研究價值通過本文已經表明。
亞傳播的概念需要在研究中明確,這里提出的只是一種初步的設想。
- 上一篇:中醫外治法診治皰疹情況研討
- 下一篇:中醫學教育體制中完善生物學教學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