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間藝術象征思維分析
時間:2022-10-23 09:33:04
導語:蒙古族民間藝術象征思維分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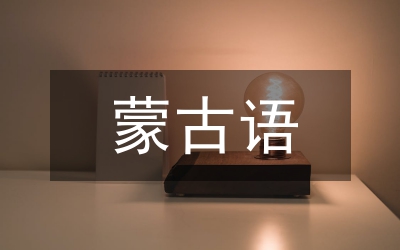
摘要:蒙古族是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其民間藝術象征思維帶有某種神秘性質,它借助原始巫術“互滲”和“靈交”的思維方式,將意義引申到事物內在屬性和深層內涵的比附,使得藝術的象征比喻擺脫了低層次的形態類似的局限,進入到一個更加自由的表現領域,豐富了精神世界的表達。這種由表及里的演進是思想認知的飛躍,從而讓民間藝術的象征性獲得巨大張力,更多地具備文化品質上的獨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遠離原始巫術理念和巫術思維的束縛。
關鍵詞:蒙古族;民間藝術;象征思維
遼闊無垠的草原生活造就了蒙古人粗獷而又豪放的性格,“逐水草而遷徒”的游牧生產方式形成了他們具有濃郁神秘色彩的蒙古草原文化,進而形成了蒙古族獨特的民間藝術文化特征,這種文化特征突出地表現在蒙古民間藝術的象征性思維方式上。盡管造型圖式、制作技法可以構成藝術的象征方式,但象征思維卻深刻地主導與制約著它們。因此,象征思維方式才是研究蒙古族民間藝術最為內在、根本的問題。“象征”這個詞來自于古希臘語symbolum,原意是把一個物件一破兩半,兩人各執其一,作為信物或憑證,以它們是否能夠完整合攏來檢驗真假,表示約定或合同的形成過程。象征思維是憑借意象進行的一種自我喻示的意識活動,通過兩個事物間的某種相近或類似的特征,利用其中一個已知事物的形象或現象的本義加以引伸、聯想、借喻、比附與推導,來解釋和把握另一個未知的、模糊的抽象事物,借此而言彼,它一端指涉物質世界,另一端則指涉精神世界,成為連接物質與精神的紐帶。象征思維具有能動性的特征,它不是邏輯推導而是一種意象推導,帶有鮮明的意象性特點,它決定了思維的走向,構成了象征的軌跡。意象可以觀念性地重構事物,并能克服言傳和意會之間的障礙,變不相似的事物為相似、不合理的現實為合理,從而使原始的思維意識外化為具體可感的形象。然而,象征思維的意象性因其特有的幻想色彩而不具有嚴密的連貫性、邏輯性與概念性,與事物彼此之間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它往往表現出荒誕不經、有悖常理的造象,這種出人意料的跳躍性和發散性的思維活動,讓象征藝術背后的意義也凸顯出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它讓形象和意義天生就有曖昧模糊的一面,而且還使藝術形象和自然形象生來就具有相互背離的一面。它沖破了邏輯和理性的束縛,同時借助原始宗教的詭譎和空靈等神秘手段,為民間藝術打開了一扇通向更加自由、充滿無邊想象界域的大門。民間藝術象征思維必須具有廣泛的認同性,事物之間彼此的類似與相近的特性需要被一個共同的族群認可方才具有普遍的價值和意義。這種認同感一旦形成,就會成為該群體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念而長久地作用于社會中的人們。這種傳統也會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人們的文化意識與藝術創作,成為精神崇拜、道德信仰、思維邏輯和日常生活的思維總綱,進而成為民族精神的內在構架與支撐。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捭闔流變,是象征思維及其藝術創作生生不息的內在驅動力,它使得民間藝術在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不斷發展。正如蒙古族諺語說的那樣:“溪流皆有源,草木必有根。”事物的發展都有其源頭可尋,下面就讓我們依據歷史的線索來考察一下蒙古族民間藝術象征思維活動的緣起。
一從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中我們不難發現,巫術這種原始宗教與象征思維的關系極為密切,通過對象征藝術的廣泛借鑒和利用,使原始宗教意識得到了充分的物化表現,當今民間文化的許多活動中,這一現象的存在依然較為普遍。比如薩滿教施行儀式中的托魂顯靈、驅鬼治病等活動,會大量使用各種法器和面具,它們都有某種神秘的象征意義,以便達到撫慰病人靈魂或提供某種心理補償的目的。原始巫術之所以要選擇象征思維這種表達方式,是因為原始宗教意識所體現的靈魂崇拜觀念看不見摸不著,這種含混的、虛無的觀念要進行彼此的交流與表達,就必然要在物質世界中尋找與之相匹配的物質形態,借用具體的事物、事象來實現。古代先民象征思維持續發展和完善的過程,與這個不斷尋找和篩選的過程是一致的,同時也讓我們發現了它與民間藝術象征性的深層聯系。作為古代蒙古人信奉的薩滿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種晚期形式,而科爾沁地區既是薩滿文化重要的發源地之一,也是重要的傳播區,它成為科爾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薩滿教的施法過程蘊涵了深厚豐富的人類文化藝術積淀,其中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教在實施法術時使用的剪紙,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在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教很多驅鬼治病的儀式中,剪紙藝術造型都是非常重要的輔助工具。例如有一種專治精神錯亂病癥的驅鬼儀式稱為“古碌木”,就是在儀式開始前,由男薩滿(稱“博”)或女薩滿(稱“亦都罕”“巫都干”),根據祖師傳授下來的固定樣式,親自用白色剪紙和高粱稈搭建一個小型的“鬼房子”,坐南朝北置于一個四方形的香灰斗上,左右兩側和背面的紙墻是固定的,名叫“烏日格”。前門臉剪紙可以開合,名叫“耶勒嘎”,其剪紙圖案與后墻相同。四面墻的剪紙圖案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紋樣為短線橫紋,類似于八卦里的乾卦。中層的梵文咒語圖符為箭頭狀,里面的鋸齒形相傳是鎮鬼利器,使鬼魂無法逃遁。下層圖案為連續的拉手人形,稱“阿達”,它們都是鬼魂的替身。為了讓這些紙人具備“真魂法性”,薩滿就在這些拉手紙人頭上點中自己的舌血。覆蓋屋頂的紙張象征天羅地網,上面剪出外輪廓呈八邊形的環狀圖案(紋樣與最上層近似),專門用來壓鬼驅鬼。鬼房子里面還要放置幾個蕎面做成的騎牛馬的鬼魂將軍和鬼兵鬼將(稱“別愣”),以及天神之劍、油燈等,以此象征有力量的神靈,然后再向屋內撒些五谷雜糧。儀式開始后,薩滿掀起前門臉紙剪“耶勒嘎”,點燃蕎面燈,擊鼓唱神調招魂,那些應招飄入“鬼房子”的看不見的鬼魂們,遇到手拉手的“阿達”人形剪紙時會束手就擒。此間,法師一遍又一遍地施念咒語,“阿達”和鬼房子“古碌木”在儀式接近尾聲時會被一同焚燒,這樣驅鬼治病的目的也就實現了。薩滿教的這種巫術活動,其功用是通過薩滿作法,把所有作祟的鬼魂都招進鬼房子中,通過施以法術,使其受困于天羅地網之下不得翻身,無法出來殃民害人。薩滿教是原始自然宗教,其宗教觀念是以萬物有靈思想為根基的,這是人類原始社會時期的普遍思維特征。列維-布留爾(LucienLévy-Bruhl)是研究人類原始思維的著名學者,他認為原始民族思維的基本反映形式是“集體表象”,其規律是“互滲”的不受任何邏輯思維規律支配的神秘方式,兩者是平等互補的關系。他指出:集體表象是原始人類對客觀存在物或現象作出反應時,在他們的頭腦里出現的不只是該事物本身的映像,同時還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粘連著與客體事物相關聯的某種東西,這種被復合的東西與客觀存在物相等同,并能產生可以被外界感覺到的某種不確定的能量、性質和影響[1]70。這樣,由情感和激情的因素復合而成的集體表象,就給客觀存在物或現象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原始人的思維受“互滲律”的支配,在他們的認知中,事物的肖像無論是何種再現形式,它們與原型的性質、生命和屬性都是互為滲透的。也就是說,由于這種互滲的整體性和全面性,原始人在把肖像呈現給自己看時,這里面已經摻入了比肖像更多的東西。他控制了肖像就意味著控制了原型,如果對肖像施加影響的話,那么原型就會相應受到影響。這種不同客體之間的相互比附、滲透和作用的意識形式,就形成了“互滲律”的關聯原則,從而成為民間藝術象征思維的內在依據。由“互滲律”形成的象征思維方式,是在觀念中把形象與原型無差別地一致起來。對原始人來說,客觀化的事實和較實在的客體都是難以存在的,他的思維在掌握了客體的同時又被客體所掌握,因而肖像本身就等同于原型,那里面已經包含了原型的性質和生命。因此,科爾沁蒙古族薩滿教驅鬼儀式“古碌木”使用的紙房子,使得薩滿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那就是鬼魂的牢籠、火之煉獄。蕎面做成的“別愣”就等同于真實的埋伏好的神兵鬼將,被點了舌血的拉手紙人肖像“阿達”就是法力無邊的降魔神吏。在我們看來這一切都是幻念,可在薩滿的思想意識中,這就是無可辯駁的真實存在。在薩滿看來,蕎面人和紙人與鬼神是互為滲透的,反過來,鬼神與這些人偶之間的互滲也是一樣的,因而掌握人偶肖像也就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了原型。于是,在一些考古遺跡中我們看到,在內蒙古陰山山脈、磴口縣默勒赫圖溝、格爾敖包溝、格和尚德溝等地區的巖壁上,蒙古先民們留下的宰殺和狩獵場面的巖畫不計其數。從互滲律思維的文化心理看,人們精心創作出這些畫像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或者占有它們的原型,這些動物形象透射出的是人們希望占有獵物的欲念,這其中反映出肖像等同于原型的互滲律原則和巫術法則與象征思維的雙重思想基礎。正像卡西爾(ErnstCassirer)所說的,“在原始思維中不存在物的再現,再現的形象就是物本身,沒有哪種東西是被另外一種東西再現的。”[2]這就是肖像和原型可以全面互滲的神秘機制。互滲律推動了民間藝術象征思維的發展,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助推力,那就是列維-布留爾提出的“靈交”。“靈交”是互滲的一種延伸,是更深層面的互滲。前文已經說過,某人控制了肖像就相當于控制了原型,進而就可以支配作為原型的人或者物,即“圖畫的神秘意義與圖畫的擁有者對所畫的人或物的權力”[1]240。如果有人盼望那個作為原型的人痛苦、健康、幸福或者不幸時,那么僅需要對他們的畫像作出有益或者有害的處理便大功告成。這種行為的心理基礎雖然類似于交感巫術的“果必同因”,但它的不同之處還在于,由人對肖象的干預作用,進一步延伸到了對原型的支配權利,這種顯然超越了一般的肖象和原型的深層互滲就被稱之為“靈交”。在“古碌木”法術中,就清楚地反映出“靈交”思維原則。薩滿驅鬼儀式的最后環節是把鬼房子付之一炬,就相當于鬼魂被“一網打盡”了。然后再找一個三岔路口挖個三角坑,把壓抑著鬼魂的“別愣”埋掉。這些法事做完時,薩滿繼續念咒,此時病人不能回頭,拿一個沒埋掉的人偶扔向后面,這就等于鬼離他而去,此時鬼房子和“別愣”是通過肖象相類似來實現融通或感應的作用。在這里,將行為主體、人偶與“靈交”受體聯結起來的是同類相生的巫術思想原則。同類相生是精確的互滲思維,進行聯想和比附的事物特征彼此相近或相似。“古碌木”法術中是將肖象與原型、“靈交”受體以及人的心理作用之間的相類似作為聯想比附的契機。古人在施行巫術時,對于事物與現象之間的實在聯系是完全忽略不計的,他們喜歡專注于事物中神秘力量的作用,認為在相類似的東西中還能產生那樣的東西,因此古人通過自己的行為來模擬將來希望得到的結果。同時對于未來不可預知的,被認為可能會招致災禍的不詳之事又要謹慎地加以避免,因為這些被幻想出來的兇險與自己正在從事的行為相類似,即那是與他互滲的存在物。我們不難在民間的文化學現象中看到,心懷不軌的人經常利用巫術加害自己所憎惡的人,具體方法就是用一個人偶代替施害對象,在其頭、胸部或眼睛等部位扎上鋼針,以期達到使該人變瞎或死亡的目的。有的人想如愿以償地獲得子嗣,就做一個布娃娃模擬初生嬰兒,讓有生育障礙的婦女抱著作喂奶狀。科爾沁蒙古族信奉薩滿教的牧民們一旦患病,便會請當地的薩滿扎一個草人,還要剪一個吉祥結樣的招魂剪紙———“索那嘎”,它的兩端分別連著病人和草人,在消災祛病過程中薩滿要擊鼓誦咒使疾病得以轉移,這都是通過真實的模擬來滿足幻念中的欲望。蒙古族民間藝術中對獸角的使用也體現了這種“靈交”思維,鹿角神帽是蒙古族薩滿的法器,那枝杈狀的鹿角,不僅用來表示等級,而且還是生命樹的象征,作溝通天地靈魂之用。喀爾喀和巴爾虎等蒙古部婦女的盤羊角頭飾,代表生育和繁殖能力,模仿這種形狀的婦女頭飾,也表達了相同的愿望和信仰。這些都是依據“靈交”思維和“同類相生”原則進行的極富象征意義的巫術和民間藝術行為。“互滲”與“靈交”的原則就如同修辭中的本體和喻體,它既是象征關系的表征與被表征,又是符號關系的能指和所指。肖像、人偶或者其他替代物都是巫術受體的象征,巫師是借助這種中介或傳媒作為象征藝術的手段施加影響于對象的。由此可見,人類對事物間關系的聯想能力受到了原始宗教意識發展的推動,因而能將一般事物之間的表征,輻射到避兇、祈福等精神層面的象征,這極大地促進了象征思維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流傳于現今的各類民間藝術作品,從表面看似乎不存在明顯的互滲律思維,但從那種“物—物”或者“人—物”的深層表征關系中,還是能覺察出那幽深的“靈交”遺風。蒙古族新娘在婚禮上穿的蒙古袍,常繡有“鴛鴦戲蓮”“鸞鳳和鳴”“蝴蝶翩舞”等圖案,寓意恩愛幸福、子嗣興旺,體現了人們對美滿姻緣的向往。氈毯工藝中的“吉祥孔雀圖”,同樣是以比翼雙飛的孔雀象征夫妻雙宿雙棲,是幸福和諧、生活快樂美滿的祝愿。“搏克”摔跤服“卓德格”上的獅子圖案象征勇猛、強悍和力量,這或許不是單純地出于祝福,從這種以物寓情中透露出的是尚未完全消失的互滲和靈交關系。還有一些有趣的日常現象,如大學生在自習室用課本或書包占座位以代替自己到場,身份證上的照片就等同于它的持有者,追悼會中的遺像就相當于逝者本人,雖然告別儀式現場也放有遺體,但無疑在表現逝者的音容笑貌方面,照片會比僵硬的遺容更優越。在殯儀館存放骨灰處,家屬往往會放幾樣亡者生前喜愛的物品,以確保其來世生活愉悅,等等。當然,不能把這些現象簡單地等同于原始思維的互滲律,因為現代人有清晰的自我意識并能夠明辨主體與客體的區別,也就可以分清一種物品和該物品所代表的象征意義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以這樣說,作為民間象征思維古老思想源泉的互滲與靈交,它與現代人的思維意識產生千絲萬縷的瓜葛,至今仍然潛移默化地左右著我們的行為。二布留爾認為,原始人對事物之間相互關聯的認知是受互滲律支配的,是以“集體表象”作為原始意識反映的基本形式。“表象”之所以是“集體”的,是由于人們對客體表象的認識已經彌漫互滲了種種神秘因素,它們經過原始部族的口頭渲染和集體記憶世代相傳,這種認識深刻地烙印在每個部族成員的心靈深處,成為該集體成員一致認可的表象,因而是集體思維的產物。如對圖騰客體認識的表象,就會在整個集體中每個成員的內心引發崇拜、尊敬或恐懼的共同情感的心像。由于這種神圣的共識,構成圖騰集團中個人和集團之間,個人、集團與圖騰物之間的同一。巫師和部族首領都是一個集團內有權力或有影響力的人,他們擁有在某個神秘客體上附會詭秘的便利條件和機會,一旦他們實施了這種行為,那么這種詭秘深奧的意義就可能在互滲與靈交思維的作用下,迅速被泛化成整個族群的共同意識。現在的我們總是能夠明確區分哪些東西是主觀的、哪些東西是客觀的,而原始意識做不到這一點。主觀和客觀、知覺和情感、顯現和隱匿,這些雙重性分別在集體表象中被抹煞了,它們彼此緊密交織在一起,神秘的互滲關系包圍著客體和對象,并由此實現了對原型本來性質與意義的超越,使得文化意義獲得更為寬廣深遠的拓展,從而在原始思維秩序中為現代意義象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圖騰崇拜起源于母系氏族社會的原始蒙昧時期,那時的人類尚不能從“自然萬物”中分離出“自我”,這個時期是形成原始信仰的重要階段。它以神圣性為基礎,通過神格化、人格化和實體化的方式,使人逐漸脫離自然屬性,讓一個群體或部族的生存方式、道德標準及思想觀念團體化和同一化,從而培育社會屬性和集體認同。圖騰崇拜是某個集體以“向往”“敬畏”及“自我強化”為思想前提產生的,是萬物有靈觀與自然崇拜相結合的產物。作為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顯然繼承了圖騰崇拜的原始文化傳統。“圖騰”這個詞進入蒙古人的視角比較晚,但在古文獻中可以發現,這種文化現象在蒙古社會中似乎很早就已經存在,載入《蒙古秘史》中的“速勒迭爾”這個詞,就可以成為佐證。現今所稱的“蘇魯錠”“蘇力德”“蘇勒德”和“祿馬風旗”,均為這個詞的異音,它既指“纛”(古代軍隊里的戰旗)同時又是指圖騰的涵蓋實物以及精神含義的雙重概念[3]。蒙古族的“祿馬風旗”是英雄崇拜的產物,早在公元前3000至2000年就拉開了英雄崇拜時代的序幕,可以見到英雄勇士紀念碑的形式有石像、石俑、石碑、鹿石等,英雄史詩更是廣為流傳。古代蒙古人是一個以尚武為榮的民族,當年成吉思汗征戰時用的長矛就稱為“蘇勒德”,作為古代蒙古軍隊的軍旗,被蒙古人奉為神物。“蘇勒德”所到之處,蒙古騎兵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宿營時,這面極具象征意義的大旗就矗立在軍中大帳前,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后來民間牧民爭相效仿,在自家的氈包前也樹立祿馬風旗,遂成風俗,世代相傳。祿馬風旗的圖案一般采用對稱式的構圖,中間為駿馬,周圍四角環繞獅、虎、龍、鳳四神圖像,旗子周圍附以狼牙邊飾。古代蒙古族的祿馬風旗只有藍、白兩色,后來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其色彩逐漸演變為紅、黃、藍、白、綠五色,圖像中也增加了不少佛教經文符號。蒙古人對祿馬風旗的尊崇以及相關的祭祀活動,實際上是馬崇拜的結果。有學者認為,蒙古人的動物崇拜、偶像崇拜以及祖先崇拜是混為一體的。雖然目前學界對于究竟何種動物才是蒙古族圖騰的問題還存在爭議,但蒙古人將駿馬作為英雄主義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卻是不爭的事實,它構成了草原文明的永恒主題。北方民族對馬的崇敬,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大量的巖畫以及后來的青銅器和金銀器等,從中都能見到馬的造型。薩滿教是古代蒙古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該教認為“騰格里”是主宰宇宙萬物的最高天神,他同時創造了包括山神、火神、吉雅其神、馬神等99個神。馬就是天神“騰格里”派到人間的神,它是“通天”之神,肩負著人和“天”之間溝通的使命。因此,蒙古族任何形式的大型祭祀活動,馬和馬奶都是必不可少的。馬作為一種信仰的映射與核心價值,體現了草原牧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成為蒙古人生命和自己靈魂的寄托。也就是將靈魂觀念對象化,把它附加到自然事物之上,這種心態和信念必然導致人們對馬的崇拜與祭禮。馬在祿馬風旗中是用圖像來替代實物的,這是人類的思維方式以圖像形式表達的結果,如果我們遮蔽其象征意義,祿馬風旗將無法存在。祿馬風旗中的圖案———馬與客體事物是同一的,它能夠與每一個信奉這一圖騰的人相互感應而構成天神信仰的一部分。人們相信,是天神將馬賜予人間的,對于駿馬的崇拜與對天神的信仰在此被重疊在一起。由于這種神圣的共識,構成了蒙古族群中個人與部族之間,個人、部族與作為圖騰物的祿馬風旗之間的同一。而現實中的馬與作為祿馬風旗圖案中的馬,以及天神“騰格里”在這里也實現了同一。由于以上這些同一,以及蒙古族世世代代的那些關于馬的本性、屬性和對生命意義的認知,經過不同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的流變,在互滲律泛比附、泛作用意識的影響下,沿著人們所期望的心理方向,自然地溢出馬自身原有的意義,進而衍生出令人驚疑、惶惑、恐懼等神秘意義。某些越是能夠體現部族身份的,同時頗具保護意義性質的圖騰物,其神秘意義越是會遠離自然原型的本性。由此我們才得以在蒙古族各類民間藝術和英雄史詩中見到,關于馬的靈性和神性的奇思異想:它能瞬間翻越崇山峻嶺,能馳騁于蒼茫無盡的大海,能神秘地和主人交談對話,常常千鈞一發之際大顯神威,拯救主人于危難險象之中。對馬的崇拜也就是對天神的崇拜,這種動物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有極其神圣的位置,已經成為該族群集體意識中令人仰視的精神創造物。人們通過對圖騰有意識地施以某種行為,就可以實現支配和操縱圖騰原型的目的。真實的馬與作為肖像的馬一起被神話,因而人們對祿馬風旗展開的祭祀活動就表現出既敬畏又有所求的心態,以期用對神崇敬的行為贏得神的歡心,以換取某種功利性愿望的滿足。許多資料都顯示,在蒙古族信仰中,祿馬風旗具有祈福降災的功能。在祭祀活動中,人們都對它表現出由衷的畢恭畢敬,即便到現在,從旗子下面穿行而過也是被禁止的。在中世紀的蒙古,馬被認為是由天神造化而來,那時的蒙古人將馬掌釘在自家周圍的樹上或房屋的門檻上,他們相信這樣兇神惡煞就會敬而遠之。牧民們為了避免毒蛇接近自己,常常用馬鬃制成的繩子把族人駐扎之地圈隔起來。這些都反映出蒙古人希望威力強大的馬神能震懾住妖魔鬼怪和毒蛇猛獸,不讓它們危害自己的生活,這是古人很常見的祈求神靈保佑平安的方式,它由“互滲”導向了“靈交”,其中蘊含了強烈的情感色彩。此處體現為三個層次的互滲關系:第一層是原型(即真實的馬)與圖騰(即馬的肖像)之間的互滲;第二層是圖騰與信奉該圖騰形象的人之間的互滲;第三層是人與原型(即真實的馬)之間的互滲,這種依次遞進不斷延伸的趨向就是“靈交”,它超越了原型只能和肖像互滲的局限,引申到人和原型的互滲,從而通過人對圖騰的某種作用對原型施加一定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取了某種功利性的價值和意義而成為受益對象,從而大大拓展了古代蒙古人的藝術想象力。從以上的事例中我們看到,肖像和原型原本簡單的“互滲”關系,在“靈交”中又多出了一個因素,也就是延及到人。兩個因素的互滲環節(即原型—肖像或人—圖騰)就變成了三個因素的環節(即人—圖騰—原型),這是由自身情緒的影響和自然粗陋狀態的社會生產力導致的原始思維方式。人種學的研究表明:原始人的情緒波動較大,智力活動受感情沖動影響的性質明顯,加上周圍環境危機四伏,生活條件艱苦,他們的神經系統脆弱而易受傷害。正像布留爾所言,“集體表象”真正依賴的是情感的基質而不是思維的基質,它主要依靠的不是邏輯的法則而是情感的統一性。原始人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低下,現實中的乏力和無可奈何必然驅使他們轉而尋求精神上的幻念,所以人就會對圖騰形象背后的原型事物提出要求并渴望發生作用。
人們受到自然和社會的壓抑越深重,精神上主觀的幻想就越強烈,對自然和社會觀念的創造及精神活動就會更豐富[4]。先民們借助這種人生夢想和浪漫情懷,在許多關于自然和社會的對象上,超越它們對人的限制,超越其本來意義,從而把自己的意志、情感和幻想賦予其上,使意義與形象結合,努力把自然事象改造成為承載著自己某種理想的象征物。蒙古族先民既對自然現象蒙昧無知,又受到自然因素的廣泛壓迫,因此原本只局限于圖騰崇拜范圍內的“靈交”關系在社會活動中逐漸擴展開來,形成“泛互滲”和“泛靈交”而彌漫到生活環境的各個方面。古人生活中的這種精神狀態和環境氛圍,在歷史上為民間藝術象征思維的成熟帶來一股巨大的內在驅動力。早期的蒙古民族是神話英雄崇拜思維,他們把無知和恐懼交給創世英雄,通過對英雄的崇拜來完成對世界的認識。將生命賦予無意義的自然界,讓心目中的英雄去完成本該由人來完成的任務,在對英雄的絕對信仰中實現人和世界的統一,這是最初形成的英雄崇拜情結。接著是史詩英雄崇拜思維階段,史詩文學出現意味著民族文化開始由神話階段進入到人文文化時期,人的理性思維開始從上天神界回歸到現實中的部落英雄,此時對英雄的歌頌代替了對神靈的崇拜。然后是汗權英雄崇拜思維階段,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代替了史詩英雄崇拜,人們對他豐功偉業的頌揚和神化,使其脫離世俗原型步上神壇而成為救世主,完成了從人到神的轉變,從此汗權成為民族的精神寄托,這標志著英雄崇拜思維世俗化的開始。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英雄崇拜還是個人迷信,人們往往又會將夢幻思想與浪漫情調結合在一起。這是因為,人在把現實中的異己力量轉換成超現實的力量時,或者把自身纖弱的力量變幻為身外的強大力量時,最便捷也最能明示自己意愿的舉措,就是把它們與自己崇拜的各種偶象結合在一起。偶象雖然也有自然物象,但人形偶象因與自己相類同則會更具吸引力,也更適合在信仰崇拜方面構成人們的寓意寄托,人們必然會以諸多“靈交”的方式,來實現夢想中無法實現的企圖。正如同布留爾指出的那樣,在原始人的思維里,不存在只是圖像的圖像,也不存在完全是形狀的形狀,那種純粹是現象的自然現象同樣不存在[1]201。這就表明,那些神秘的因素總是隱匿在圖像、形狀和現象的背后,人與圖像、形狀和現象之間有某種不可見的契合關系,那些神秘因素就構成了這些可見物或現象的表征,進而成為蒙古人某些精神寄托的載體。蒙古族民間藝術象征思維從早期與巫術理念的分而未斷,發展到超越了事物表象的相類比附,將意義引申到事物內在屬性和深層內涵的比附,豐富了精神世界的表達,這種由表及里的演進是思想認知的飛躍,它使得藝術的象征比喻擺脫了低層次的形態類似的局限,進入到一個更加自由的表現領域,從而讓民間藝術的象征性獲得了巨大張力,更多地具備了文化品質上的獨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遠離了原始巫術理念和巫術思維的束縛。
參考文獻:
[1][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德]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神話[M].北京:三聯書店,2017.
[3]那仁畢力格.蒙古族狼圖騰文化考究[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5):69.
[4]胡瀟.論民間象征藝術的思維張力[J].求索,1994,(5):67.
作者:王同旭 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
- 上一篇:公共藝術與公共話語研究
- 下一篇:象征性藝術觀念在舞教學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