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發展論文:主流文化背景下當代舞蹈創作發展
時間:2022-02-12 09:55:41
導語:舞蹈發展論文:主流文化背景下當代舞蹈創作發展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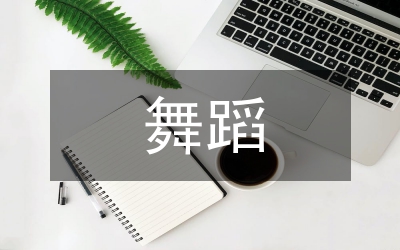
本文作者:肖向榮
一、啟蒙時期——以表現主義為發端的人生之舞
翻開《中國近現代當代舞蹈史》第一編第一章標題醒目,在社會急劇變革中發展的中國舞蹈。[2]在這一章節中,隆重介紹兩位舞蹈先驅:吳曉邦與戴愛蓮,同時把他們歸結為“新舞蹈”的奠基人。與鄧肯喊出的“芭蕾一點也不美”而引發的現代舞的那一場運動不同,新舞蹈藝術并不是為了反對封建舞蹈,或是中國傳統的戲曲舞蹈。新舞蹈誕生于當時30年代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運動之下,她所反對是當時受美國歌舞片影響的,為追求票房價值的“麗珠滿目,媚態萬千,玉趾勾魂,嬌聲攝魄”[3]的資本主義舞蹈,當然這是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與當時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的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時隔一個世紀的今天,兩位先生如果打開電視機,應該看到都是這一類的節目,不知是何感想,這是后話。
(一)從表現主義出發,尋找人生之舞無論是《饑火》《傀儡》《小丑》以及《義勇軍進行曲》,吳曉邦先生的創作意識一直鮮明地體現出巨大愛國熱情,他的視野始終關注當時的社會矛盾,用舞蹈藝術向著全社會吶喊,完成他為人生而舞蹈的精神追求。不能否定的是,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日本舞蹈藝術家石井漠,年輕的吳曉邦正是被《群鬼》這個作品而擊中自己的內心,作品以各種鬼的形象與行為揭示現實矛盾,雖然沒有看過這樣的舞蹈,但是腦海中卻出現蒙克的畫作《吶喊》。作為表現主義的發端人物蒙克在1893年完成他一系列作品《吶喊》《接吻》《思春期》,[4]在創作中觸及生命本質與內涵,人物的不安與焦慮體現表現主義的特征。可以大膽地猜想《饑火》中瘦骨如柴的饑民形象,有可能是石井漠《群鬼》的某個記憶的碎片,而《群鬼》是否是《吶喊》在美學上的殊途同歸,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表現主義的主要特征強調反傳統,不滿于社會現狀,要求改革,要求“革命”。這些都恰恰應和吳先生當時的生存環境以及社會現狀,在創作風格以及審美上也是突出表現事物的實質,例如《饑火》;要求突破對人的行為和人所處的環境直白描繪而是揭示人的靈魂,例如《丑表功》。在整體混亂的時代中,作者厭惡城市的喧鬧與墮落,主題的選擇常常是隱喻的傷感或是對人性的贊揚。尤其是《義勇軍進行曲》可以看出吳先生的充盈的愛國主義激情,來自于他內心的主觀愿望的抽象表達,而不是粗略的形象描繪。因此情感的主觀表達而高于對事物表象的臨摹,成為吳曉邦先生為人生而舞的“精神性”計劃,在那個時代中,這個計劃真正的解決了社會矛盾,滿足社會需求,如果說吳先生的創作激情來源于巨大的愛國主義激情的洪流中,而來自歐美表現主義的創作美學則是創作法則的波濤暗涌。
(二)從情感出發,尋找民族之魂與本土成長的吳曉邦老師不同,戴愛蓮先生出生在西印度群島,亞熱帶氣候使得她更加具有生命的活力和生命的律動。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戴先生比鄧肯的境遇好很多,從啟蒙就是純正的芭蕾舞教育,而且都是名師名校,例如安東•道林的學校,蘭伯特學校。有了堅實的身體能動性與規范性的她,也是在表現主義舞蹈大師瑪麗•魏格曼的一場舞蹈中投向現代舞懷抱。也許是亞熱帶氣候的緣故,戴先生不拘泥于古典芭蕾以及表現主義舞蹈的各自規律,而是大膽的將靈動的芭蕾技術與表現主義的內省式的情感表達融合在一起,成為她日后從事表演和編創的風格基礎,尤其是在大型歌舞《和平鴿》的創作中尤為突出。在劇中和平鴿為芭蕾的身體美學,而在情感表達與矛盾沖突時有介入大量的現代舞元素。戴先生的創作風格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她對于民族元素的敏感,或許與她的出生地不同,中國民族舞蹈整理收集以及運用,戴先生是獨具匠心的。如果說吳先生更多是在精神上題材上原創性整體開創新舞蹈的先河,那么將芭蕾舞與現代舞融合再在加上民族元素的這種創作模式,則整整影響到今天古典舞、民族民間舞的創作,主流藝術家們還在運用戴氏的“三合一”編舞法,只是整合的程度更高,而動作原創性則遠遠不如前輩。因此在建國之后,吳曉邦先生的那些具有鮮明時代表現主義美學特征的“丑惡”形象,逐漸被淡化,而戴先生的這種創作模式不帶有具體精神指向,而受到主流文化的廣泛接受。
二、發展階段——以現實主義為綱的上升之舞
在第一段落中主要是以1949年到1989年期間的中國舞蹈創作為研究對象,從建國前的在野狀態到建國后的執政40年間,按照創作美學的劃分大概可以分成:整合時期(1949-1964),樣板時期(1966-1978),上升時期(1979-1989)。如此劃分是基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個重要轉型期。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整個社會情緒處于一個新鮮、興奮的狀態,一切都是新的,人們從戰爭死亡線上逃離出來,因此舞蹈創作也多是歌頌、贊美新時期的光明。集大成者就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一)《東方紅》主流文化意識的形成在“三化”文藝方向的指導下的中國舞蹈創作中,《東方紅》的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早在1949年9月的那臺《人民勝利萬歲》的大歌舞中,就依稀體現了這種以“階級”劃分的創作意識轉型,在這個大歌舞中集中了建國前的左翼聯盟文化的精品以及新解放區整理積累的民間歌舞,藝術家們懷著對新中國的熱情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類型化大歌舞——即開場鑼鼓,歡天喜地;大型合唱,宏偉高昂;民族歌舞,色彩斑斕;軍隊文化,雄壯威武。這樣節目構成不僅僅影響《東方紅》甚至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舞臺上,電視文藝中也依然存在,春晚就是很好的例子。高歌猛進的方式成為當時整體文藝創作的方向,現實主義的創作美學也逐漸替代原先的表現主義美學,把這個時期歸結為現實主義的創作似乎體征不太明顯,但是我想起杰克•唐納利所指出的那樣,現實主義不僅不能提供一種一般理論,而它基本上也是前后矛盾的。現實是變動不居的,針對不同現實主義給出的解釋也是不一樣的,由此我把這個時期的創作稱為啟蒙現實主義。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出現以前,中國的舞劇雛形已經在《魚美人》《小刀會》《寶蓮燈》的創作中體現,在創作上由于蘇聯專家的介入,創作者從開國的激情中脫離出來,開始進入一個民族化和藝術化的舞劇本體創作。然而好景不長,在1960年的第三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會議在北京召開,開始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以人性論代替階級論”的表達方式,在50年代的許多優秀節目都被批判與影響,這是主流文化對舞蹈創作一次粗暴的干預,就是新舞蹈的先驅、奠基人吳曉邦先生也未能幸免。“為人生而舞蹈”也被冠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指責他的作品,尤其建國之后的作品“遠離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向”。[5]在這樣干預下,出現一些現實主義作品,確切地說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洗衣歌》《豐收歌》這些表現當時社會階層與生活狀態的舞蹈就擔著有明顯主流文化干預現實主義的風格。一切以階級斗爭斗爭為綱的主流文藝方針也深深地烙在中國芭蕾舞劇的經典《紅》與《白》中。作為社會主義文藝方針的主流文化在《東方紅》中匯合,并且形成主體文化意識,在十年登峰造極。
(二)樣板階段主流意識的異化在這十年之中,舞蹈的創作進入一個異化狀態,實際上整體的文化也處于一個高度集權的狀態,領導者的審美取向直接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現實主義在中央集權的統治下被異化成一個政治波普象征。在1966年到1978年期間,中國又一次關起了國門,此時西方社會已經完成從新舞蹈到現代舞,甚至后現代舞的階段,從表現主義舞蹈以及進入全新超現實主義,達達、波普藝術等等創作思潮。舞蹈界已經從鄧肯的自由舞蹈,發展到瑪莎•格萊姆的舞蹈詩句,坎寧漢已經在約翰凱奇的影響下玩起機遇舞蹈,而德國的皮娜已經拒絕了常規舞蹈身體,而轉型成舞蹈劇場。如果說,當年吳曉邦先生《饑火》與日本人石井漠《群鬼》創作美學相類似,而這十年的所謂社會主義樣板文化發展與整個西方世界南轅北轍,現實主義在現代主義的顛覆下已經退出西方社會主流文化視野,追求藝術風格力求美學的多樣性的文化創作取向逐漸成形。當然從創作風格上我們不去判斷孰高孰低,甚至有人覺得八大樣板戲更有特點,富有鮮明的時代精神。但是在整體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形成斷層,行政干預藝術創作,領導人的審美決定社會主流文化審美的習慣種種因素下,藝術風格上探索的停止,至今還無法彌補。
(三)上升階段的鄉土現實主義通常把這段時期看成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在這十年間,文化由于長時間的壓抑而形成井噴,從文學上的一系列傷痕文學、鄉土文學,繪畫中羅中立《父親》以及陳丹青的《西藏組圖》真實客觀再現社會現實。現實主義排斥虛無縹緲的幻像,排斥了神話故事企圖真實的呈現社會生存的本真狀態,對于形象的刻畫,采取多樣化的探索以及向西方現代主義的借鑒。在這期間舞蹈界也出現了驚人的創造力,不同于以往的《東方紅》,也不同于八大樣板戲,在1979年建國30周年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既有《絲路花雨》這樣具有獨特民族審美特征的“戴氏”創作風格,也有《割不斷的琴弦》這樣直面嚴酷現實的“吳氏”人生之舞。80年代以來,好作品更是層出不窮,《金山戰鼓》《再見吧媽媽》《希望》體現出新現實主義的氣象。《金》取材于古代梁紅玉的故事,但是在戲曲與舞蹈的結合上有開創性的建設,以至于90年代風靡一時的《醉鼓》也難逃其影響。《再見吧媽媽》則在雙人舞技法上有所突破,在人物形象與劇情推進中借鑒的大量現代舞與芭蕾的技巧,脫離以往舞蹈加啞劇的表達方式,整體流露的情感與舞蹈更加融洽,似乎又回到戴先生提倡“從情感出發”的創作原點。《希望》是一個《饑民》的穿越,大量表現主義的美學充斥在舞蹈之中,迷茫、恐懼、掙扎、求助、渴望,使得這個作品成為一個中國現代舞登上主流視野的開端之作,之后一系列的現代風格的舞蹈站在舞臺上。但是誰也不曾想到,在2005年全國舞蹈比賽中,具有相同氣質的《守望》成為中國現代舞在主流舞臺上的謝幕之作。80年代主流觀念上的轉變以及創作尺度的寬松,使得中國舞蹈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中,迅速達到高峰。在1985年創作會議上,5臺作品60個節目中,有人統計:古典風格10個,民間風格10個,少數民族17個,而現代風格的舞蹈則占27個。[6]這樣比例在今天的比賽或是匯演中都是一個難以超越的標桿。以往的“三化”慢慢地被“面向生活,面向時代,面向世界”轉換成那個時代主流文化視野下的“精神指標”。
三、轉型階段——以科學主義為準則的虛無之舞
隨著90年代的到來,整個中國社會從開國的興奮,到的壓抑,直到改革大潮的洶涌,到90年的初期達到一個鼎盛期。踏著經濟改革的大潮,創作主體意識覺醒,許多以人為本的人性之舞出現在舞臺上,其中代表作品有《一個扭秧歌的人》,舞蹈回歸到人性刻畫的本身,在一個民族民間舞中第一次將一個農民的形象與秧歌聯系在一起,長達3分鐘的“擠眉弄眼”自得其樂的表演,居然能夠贏得比賽,可見當時舞蹈界的寬容之心。國力日益增強,市場開放,院團轉企,從表面上看,主流文化視野似乎更加寬松與自由,但是實際呈現的舞蹈作品的質量卻遠遠不如以往。曾經在80年代大力贊揚現代意識的舞蹈界,走入技術至上的科學主義,猶如聲樂界的“千人一聲”的現象一樣,大國崛起需要配得上盛世華章的“金屬般”的高音,來彰顯國力。舞蹈也一樣進入一個科學主義的怪圈,創作中注重技法勝過表達,表演中注重技巧勝過內涵,現代舞作為小眾甚至是不和諧的聲音備受排擠。曾經在1995年的廣州小劇場展演中的“方便面與避孕套事件”,引起舞蹈界主流的異議甚至是憤怒。在首都北京,舞蹈學院招收第一屆現代舞本科班,躊躇滿志要打造中國現代舞。而這個使命神圣19人的首屆現代舞班只有2人進入現代舞團,如今只有1人繼續從事現代舞。而在中國主流文化的展演中,現代舞作為比賽舞種在2005年第一次進入荷花杯的范疇,在紅土高原的云南、廣州軍區的《守望》成為現代舞進入主流的絕唱,從此現代舞退出主流文化的視野。這也意味著在當今創作上,更多的作品出現題材撞車,審美單一,在不能直面人生的時候,逃避到古代或是一個虛無的幻境中。在多樣化審美的今天,一方面鼓勵創新,另一方面又強硬地恪守緊縮的文化政策,時代喧嘩,急躁而浮夸,在功利心的驅使之下,文化創作的規律也被視同于機械的復制,大量的文化工程一個個矗立在觀眾的視野之中,“炫”“奇”“新”成為主流文化中精神指標,指導著大多數的創作方向。這是一種賣弄風情的甚至有些欣欣然的虛無主義。[7]尋求感官上的功能滿足,而精神上則走向虛空,既看不到開端時期為人生而舞的新舞蹈精神性,也看不到洋為中用的民族精神性,在物質極大豐富的今天,舞蹈選擇了為舞而舞,為編而編。在此時的舞蹈創作中,當代中國的盛世氣象得到充足的體現,好像又回到建國初期的那種《人民勝利萬歲》的狂喜。2008年的奧運會《擊缶而歌》就代表這個精神特質,2008面缶敲響,震動全場十萬名觀眾,也震動了全世界,代表了大國崛起的最強音。在震撼之余我想起蔡國強先生的話:滿場都看見中國,古代的中國,現代的中國,就是看不見當代中國人。
(一)科學主義不等同藝術創作法則誠然,科學是一個重要的詞匯,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文明的古老國度,幾千年的儒釋道影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直面臨著西方文化的侵入,到了我們自己了斷與傳統的血脈,改革開放又受到西方文化全面進入的致命一擊。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拯救傳統文化,否則將動搖我們的傳統文化根基。然而與文化危機相比較,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而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政治永遠將壓倒文化,這也是現實體制的現狀。在經歷了文化上農業社會的自卑,時期的自大,工業時期的自虐,隨著經濟的騰飛,交流的頻繁,面臨高度信息化社會,我們自省了。人們有一種觀念,認為科學拯救了中華民族,因此科學又成為最大的宗教。就文化藝術而言這是值得考量的問題。正如田青先生所言:面對科學的態度有二,一是崇洋媚外,事事以西方為楷模,凡是與西方不同的,統統在自己身上開刀,墊鼻闊嘴隆胸,以求貌似洋人。二是信奉“科學主義”,將科學凌駕于藝術之上。[8]同樣在舞蹈界也有這樣的問題,從而導致當代題材創作上的真空,以及當代中國人形象建立的缺失。因為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們不知道當代的精神性是什么?大多數人都普遍理解為是精神文明建設的缺失。是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文化建設緩慢的矛盾造成的。于是社會和諧,生態和諧,精神和諧成為整體主流文化,追求真、善、美。和諧,來自于“和諧”,出自管子,原文如下:“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而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9]這是一種生存法則,而不是文藝創作法則。追求創作的和諧恰恰代表最大虛無。虛無的最大表現就是沉默。在禪宗里,叫做“拈花一笑”,就是什么都沒說,但似乎什么都說了。《千手觀音》成為這個時代最著名的舞蹈,她代表似乎表達一切,也似乎什么也沒有表達,這是虛無之舞。這個時代最著名的舞蹈家是成名于80年代的楊麗萍,在最近的春晚中《孔雀》成為舞蹈文化的焦點,舞蹈家也前所未有替代那位紅極一時的農民小品演員,哪怕是接受雌孔雀的開屏行為。孔雀代表一切的美,而這種美不帶有任何意義,既不傳情也不達意,在激越的宏大音樂聲中,舞蹈成為一場幻像。正如蘇珊所言:“當代藝術家一類“喧嚷”一類“溫和”,但這就是沉默的兩種風格。”[10]喧嚷的風格,正是應變“充實”、“虛空”。以感性的、欣狂的、超越語言的方式理解“充實”實在是脆弱不堪,可怕的是在瞬間高潮后所帶來的無盡的虛空。
(二)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引起沉思當我們看到張繼鋼先生的《一個扭秧歌的人》,陷入對一個民族情感的沉思,孫龍奎先生的《殘春》陷入人性生存本身的深思,看到高成明先生的《守望》,陷入了人性欲望的深思。這三個獨舞都是舞蹈作品中的經典范例,對我們的創作和教學都很有指導意義,他們都回答了先前蔡國強先生的問題,即中國人的形象。然而在大多數方面的當代舞蹈卻不是如此,在形形色色的觀念驅使下,變得愈來愈理論,愈來愈抽象,愈來愈“哲學”,如果說我們的前輩們的創作是謙卑地站在生活面前、聚沙成塔式的虔誠之作的話,現在舞蹈創作者們更多的是膚淺傲慢之作,“對生活的挖掘”“對人性的挖掘”等等句子常常出現在當代創作者的嘴邊,我們放棄以往的對生活的崇敬之情,高高在上,猶如煤窯主一般將現實生活肆意開采,將生活的素材胡亂拼貼,體現千瘡百孔的人性底線。熱衷觀念地將舞蹈成為“玄學”,看得觀眾一頭霧水,還埋怨觀眾不懂得欣賞。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熱衷于技巧的則拼命炫耀技術(這里也包括編舞技法),幾乎將舞蹈成為江湖藝人的把式活兒。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舞蹈?就像從未跳過舞的聞一多,卻留下了他對舞蹈最好的見解:“舞是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烈、最尖銳、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他還進一步認為:“生命的機能是動,而舞便是節奏的動;或更準確點,是有節奏的移易地點的動但是只有在原始舞里才看得出舞的真面,因為它是真正全體生命的總動員”。[11]當代的舞蹈不過是一種退步了的審美和社會的遺物罷了。我們越是研究藝術,對自然就越不關心。我們越是關注舞蹈的技術,也就越漠視舞蹈原來的意義。所以張羽軍在十分年輕的時候就創作了《黃河》,之后的幾十年里他鮮有作品,每當我問起他時,他總是回答說:我對這個時代無話可說。沉默,意味著放棄,放棄在“表面的計劃,厭倦了瑣碎的努力和裝腔作勢的能干以及自我逞能的模樣”(貝克特語)。沉默也是一種表達,一種對純凈開闊視野的隱喻。面對當代如此的喧囂繁雜的聲音,面對光怪陸離的燈光,面對激情四溢的身體,沉默可能是一種對抗的法則吧。我相信這個時代中真正的舞蹈一定會在這樣的沉默中誕生的。
結語
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重新梳理中國現當代的舞蹈創作走向,也是為了給自己提個醒。我們既是這個行業里的創作者,也是這個行業外的觀賞者,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鏡子,在我們自己的身體上折射出怎樣的光。站在歷史的面前,吳先生的“為人生而舞”喊出那個時代精神。站在世界的面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堪稱黃金歲月,呈現出美學的多樣性,造就中國舞蹈創作的巔峰。回到文章的開頭,“每個時代必須為自己重新啟動一個“精神性”的計劃”。當代藝術所渴求創新模式是應該按下重啟鍵,還是徹底關機?傳統藝術行為,招來只是觀眾,只是看客。都是觀看的藝術,在英語中“looking”與“staring”是截然不同的態度,前者是看見,后者是凝視。我想這兩個詞匯代表了兩種立場,看見是隨機的,偶然地看見,不確定的;而凝視則是一種主觀的強制地關注,不允許注意力松懈,在凝視中帶來沉默。猶如蘇珊說:凝視也許是當代藝術遠離歷史,切近永恒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12]這句話的啟示是,也許我們還沒有找到這個時代精神,但是我們必須堅持立場,要確認自己的作品是引發“看見”或是“凝視”。有時候想想,身處這個時代到底是幸運還是悲摧,用一首歌詞回答自己吧。“沒有新的語言,也沒有新的方式,沒有新的力量,能夠表達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愛較勁,不過是積壓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應。情況太復雜,現實太殘酷了,誰知道忍受的極限到了會是什么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