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舞蹈藝術創作生命情調
時間:2022-12-29 08:53:12
導語:淺談舞蹈藝術創作生命情調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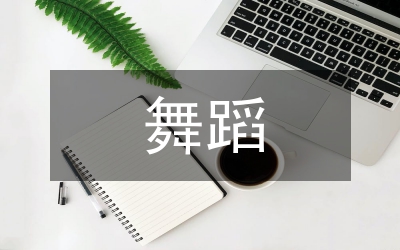
摘要:生命的內涵及表象意義在亙古不斷地被詮釋和闡發,而這種闡發恰被集中地體現于人類反觀自身的藝術活動過程中。在藝術創作與表達中,生命常常“化”之為“情調”,“化”之為個體與宇宙萬物“普遍生命”妙契、冥合于藝術品之上的“生命情調”。舞蹈是最深入“直覺”的靈動,是以最“純粹”的形式體現出“人”之生命“意味”。在舞蹈藝術創作中,藝術家以時間創化生命,以空間承載生命,以身體顯現生命,言說著幽深、致遠的生命情調。
關鍵詞:舞蹈創作;生命情調;時間;空間;身體
生命的內涵及表象意義在亙古不斷地被詮釋和闡發,而這種闡發恰被集中地體現于人類反觀自身的藝術活動過程中。在藝術創作與表達中,生命常常“化”之為“情調”,“化”之為個體與宇宙萬物“普遍生命”妙契、冥合于藝術品之上的“生命情調”。蘇姍•朗格指出了:“藝術結構與生命結構的相似之處。”[1]55在她看來,藝術即為生命的形式。宗白華先生也強調:藝術“深深地表達了生命的情調與意味”[2]373。的確,生命化生出藝術,藝術承載著生命,二者相生共融、無法割裂。藝術的創造便是將“浩蕩奔馳的生命收斂而為韻律”[2]102;藝術的形式與節奏表現著“生命的內核,是生命內部最深的動”[3]98;藝術品即是“藝術家的第二生命或生命自身”[4]59-60。正是藝術與生命在“同構”、“化合”中,最終構建并呈現為一種至“情”、至“性”、至“純”、至“真”,“至動而有條理的生命情調”[3]98。這個“情調”是“美”(藝術)之本體;是情感、志趣、風范與格調……;更是藝術家對生命根由妙契體悟而主客冥合化生的“意味”形式的“生命境界”。舞蹈作為最是“情動于衷”的藝術形式,她是那樣的激烈如火,哀怨多情,她是最深入“直覺”的靈動,是以最“純粹”的形式體現著“人”之生命“意味”。宗白華先生站在“宇宙生命論”的基礎上,曾評價舞蹈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動、力、熱情,是一切藝術表現的究竟狀態,且是宇宙創化過程的象征”[2]366。誠然,若藝術與生命的彌合存在程度之分,那舞蹈無疑是最為純粹的生命形式,是“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烈、最尖銳、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5]195。舞蹈正是以時間創化生命,以空間承載生命,以身體顯現生命,言說著生命之情調,將“深不可測的玄冥境界具象化、肉身化”[2]366。正如張彥遠所言的:“窮元妙于意表,合神變乎天機”。也如方東美先生所說的:“生命的醉意與藝術的夢境深相契合,產生一種博大精深的統一文化結構,在這里面,雄奇壯烈的詩情……與錦絢明媚的畫意……融會貫通,神化入妙。”[6]222這正是道出了舞蹈藝術與“生命詩情”的共鳴。這一共鳴是“人”的存在、欲念、情愫與性靈,是宇宙萬物“普遍生命”的“生生不息”與“大化流行”。
一、舞蹈以時間創化生命
“時間”概念的探討由來已久。中國的《詩經》、《管子》、《禮記》、《易經》等著述,西方的亞里士多德、牛頓、奧古斯丁、康德等先哲都對這個概念進行過論述。出現了“客觀時間、主觀時間、關系論時間、先驗時間、實體論時間、相對時間、心理時間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7]。“時間”的認知對藝術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甚至直接導致了藝術流派的誕生。對于舞蹈而言,時間無疑是其核心要素之一。在時間的過程中,舞蹈運化生成,才有了四維的運動天地,情境和意味流淌鋪陳。舞蹈中,一方面,時間“綿延”直透出生命之永恒;另一方面,時間流淌涵容著生命之創化。首先,舞蹈創作中以“綿延”之時間意味結構作品,并體現生命永恒之主題的,無疑受到了立足于生命哲學的直覺主義者伯格森的“心理時間觀”的影響。伯格森從生命體驗的角度將“‘時間’歸于‘心理狀態強度’……認為‘流動的意識狀態’的‘綿延’是時間的原初和本質”[7],在此“綿延”中,時間長短的意義被消解,過去、現在與未來彌合共存,生命得以超越,得以永恒。當代編舞大師尤里•季利安的《最后的第一次觸動》中,編者的生命體驗運化于時間的過程,主體“流動的意識狀態”之“綿延”結構出整個作品,化為生命永恒之“動”。該作品創作靈感源自一張老照片,照片“這個‘時間片段’,就成了……出發點”(季利安語)①。作品的開頭和結尾處,舞者均為同樣空間結構造型,只是由開場的立體空間壓縮為結束的臺口平面空間(照片),伴隨著結尾天籟般的一聲敲擊,“整個場面就像是一只手表的縮影”(季利安語)②,40分鐘的作品仿佛只是“秒針”的一頓,只是生命流中“重要瞬間”(照片)展開的意識“綿延”而已。在此“綿延”中,舞者在機械化的極盡緩慢的“動”,喝著酒、看著書、搖著椅……外化著主體“意識流動”的視像。舞臺的時間被無限的拉伸,時、分、秒的速率長短完全聽由主體的直覺與生命體驗。這里,“時間是永遠無法絕對測量的”(季利安語)③。時間即為生命,剎那成為生命之永恒。其次,舞蹈創作中時間也融貫著“生命之進程”[8]134,時間化育生命,生命在時間中創生。孫穎先生的作品《謝公屐》依托于山水詩派開創者———南朝詩人謝靈運,在時間的鋪陳中,以謝公之登山游歷的木屐突出“行”之生命意趣。“行萬里路”,“行于山水之間”歷來承載著中華文人的人生志趣。“山”與“水”更是中華文人性情超凡絕俗、生命自由曠達的寄托與歸宿。作品中,舞者緩步于“山水之境”(舞美背景),在清亮悠遠的山澗晨曲(音樂背景)中頓足而行,怡然而舞。正是在“行”之時間運化中,舞者“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人的性靈與生命因絕塵而顯露,心性與天地合一,生命與自然妙合。倘若《謝公屐》在時間的“行”進中,運化出人之主體的生命情愫,那么,林懷民先生的《流浪者之歌》的“行”走則帶上了生命輪回而永生的印記。作品以超乎常態的“緩”、“靜”、“慢”營構了強烈的生命儀式感。舞臺上,一邊是稻米不斷垂落之下的圣者長時間的凝若雕塑,另一邊是遭難者互相攙扶及其緩慢的不斷前行。稻米之“動”與圣者之“靜”,圣者的“定”與遭難者之“行”,皆為時間流淌中之生命樣態,生命永無止境地向前行進,“動”與“行”的生命之流,最終沉淀出生命恒定的超然與永在。尾聲,一名舞者長達15分鐘的極緩慢的推動地上的稻米由圓心向外形成層層“圓”環,時間與生命合一,時間輪轉,生命往復。舞蹈之時間中,人之生命得以展開,舞蹈之時間中,宇宙萬物的生命也得以運化。房進激先生的作品《小溪•江河•大海》在時間中,消弭“人”之主體意義,人融合為物性的存在,化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元素。作品設計了舞者不斷穿插流動的網狀空間調度,以人作為“水”的自然生命象征,在舞臺呈現出粒粒潺潺涓流,融而為江、河、湖、海的意象。時間化育中,人構筑了“景”,人融入了“景”,“人”體味著,并幻化出涓涓細流之真情,“大化自然”之博愛,主客和合于此,舞蹈的時間流動孕育出的是天地萬物即現之“生命場”。在時間的流淌中,作品以人之物象,構建起生命象征的“水”之意象,創化著宇宙萬物的“生生之美”。方東美先生說的好:“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變化,創造不息。我們若要原天地之美,則直透之道,也就在協和宇宙,參贊化育,深體天人合一之道,相與浹而俱化,以顯露同樣的創造,宣曳同樣的生香活意,換句話說,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與璨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創造,在于浩然生氣與酣然創意。”[9]212舞蹈之美正在于節奏感的時間中呈現出“生命”不斷“創造”之“形”,正是通過舞蹈生命之“形”將宇宙萬物的“生生之美”具象化、肉身化。可謂“與天地和諧,與人人感應,與物物均調……隨順普遍生命,與之合作同流”[9]37-38。時間中,舞蹈滌汰而至清凜,深覺而至性情,流淌化合出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化育出生命之氣度與情趣,直透永恒。
二、舞蹈以空間承載生命
空間是舞蹈藝術的另一個核心要素,是舞蹈存在的領域和環境,是舞蹈得以呈現之條件。空間的維度中,舞蹈建構起了意象與意境。現代舞大師瑪麗•魏格曼就認為:“空間是舞蹈家真正活動的王國。”[10]129在舞蹈范疇內談空間,有著身體空間與空間構圖之分。前者主要針對身體自身的運動而言;后者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內容,主要指“舞蹈者在舞臺空間的運動線(不斷變化、流動的舞蹈路線或隊形)和畫面造型”[11]213。隨著眾多舞蹈藝術家創作實踐和藝術探索的展開,空間的價值和意義也不斷被凸顯和強化,空間的“意味”也愈加豐富起來。它是“運動發展和變化中的和諧場面”[12]36,鋪陳敘事、展開氛圍、轉換情節、顯現情感……;更是“‘舞情’和‘舞律’密切結合中而形成的動的畫面”[12]36,這里,“情”化作“景”,“景”充滿“情”,“情”“景”交融為“生命情調”的空靈境界。就像著名電影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言:“任何場面的調度不應僅僅展現一些創意,更重要的是緊扣生命。”[13]22也如方東美先生所說:“所有生命……原都在空間展開”[9]133。誠然,舞蹈空間承載著人的生命欲情,舞蹈空間更是承載著萬物生命的靈性天地。“生命情調”于空間中展現,蕩滌致遠。首先,舞蹈空間構圖包容著人之生命的欲念、情愫與境遇。“人”之生命情狀在舞蹈的空間設計中展開,或和諧、或沖突、或向往、或糾纏……。四人舞《東》(樊興華)的空間成為了生命的方向,成為了群體向“東”追尋、生命前行和性靈升華的方向。作品空間中設定“人”之群像,舞者的散點分布強調了遠近、動靜的視像構建,搭建了空間構圖的層次。誠如編導所言:“情感的訴說融合進布局的變換里……立體的空間感中達到情感的迸發。”[14]這個“情”是追尋,是期盼,更是向往,是作品營造出的向“東”而行的空間意象。結尾處,四位演員攜手邁向舞臺深處與遠方時,構圖化為深深的情愫與眷戀,展示著生命向性的追求,向往著“東”,向往著生命的“詩與遠方”。有時候,人總想沖破束縛,求得心靈的自由,這時的空間寄托著心靈突圍的向往;但有的時候,人卻被周遭環境壓迫、壓榨得奄奄一息,了無生存希望,這時的空間變成了心靈與生命之囚牢。獨舞《阮玲玉》(黃蕾)以限定性的空間布局構建出社會與主體的矛盾性沖突。作品的整體空間構圖僅僅為舞臺中間縱向的垂直線,舞臺兩側廣闊的黑暗空間象征著人的生存環境,暗示了陰暗冷漠的人情與人性。舞者在細窄的空間中,左沖右突,奮力的舞動著,她時而奔跑,時而抽搐,欲抗爭卻無力,想逃離卻無門。人深陷于燈紅酒綠世俗無情的冷寂之中,與空間對抗、沖突著。空間的不斷緊縮和擠壓,人在“環境”面前無助、無力又無奈,個體生命是那樣的孤寂、黯淡與渺小。空間承載著人之向往和壓抑,空間中,更顯現著人與人的糾葛和欲念。現代芭蕾舞大師貝雅的《波萊羅》就是這類中的經典力作。作品將一張碩大的圓桌置于舞臺的中心,一名獨舞演員始終在桌心定點舞動,而數十位群舞演員環桌而舞,構圖始終保持著環狀。這種空間構圖體現出強烈的引力感,一種向內緊縮,同時向往擴張的來回激蕩的“虛幻的力”。在充滿儀式感的空間磁場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凸顯,誘惑與激情,統治與奴役,生命最本真的欲念萌發、噴薄、糾纏錯落著,貝雅呈現出對“人”之本能和人類生命欲情的關照與關懷。誠然,站在“人”的主體性角度,舞蹈空間布局無疑承載著人之存在,及其欲、念、情。當人“心”之舞蹈藝術創作的生命情調向往、人“境”之沖突、人“欲”之糾葛……體現在舞蹈構圖中時,舞蹈空間便擴張為丈量“生命的尺度”。其次,舞蹈空間構圖承載著“普遍生命”之“生生之美”。若前述的空間構圖顯現之“生命情調”帶有強烈的“人”的存在、欲念等主體生命印痕,尚屬“有我之境”的話,而下面談到的空間構圖則成就了主客消弭、情景交融、物我同一,而沁透心靈深處的精神性的靈境天地,體現出“冥齊物我”的“無我之境”。孫穎先生的《玉兔渾脫》的空間構圖浸透著清新而淡雅的情調,輕舞曼妙的空間意象中,“勾深致遠,直透內在的生命精神,發為外在的生命氣象”[9]227。作品中,女子或頓或行,或折腰或旋轉,陰柔舞動而自然化合于空間的流轉,“人”之情韻不斷上升融合生成臨空超拔的“生生”之境,在至“情”而至“真”、至“虛”而至“靜”、至“樸”又至“靈”的氛圍中,“于空寂處見流行,于流行處見空寂”[2]370,人的主體性消弭化合為超拔空靈的“生命氣象”。林懷民先生的《水月》則浸潤著濃重的東方文化氣息,空間構圖營構出主體“生命悠然契合大化生命”[9]227,冥合物我的“空靈”之境。該作品的整體空間構圖,美得不可方物,舞臺上活水涓流,潺潺不息,光、水、鏡相映成趣,人存其間,舞動、忘我、化合。畫面中的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而然、晶瑩剔透而又“生生不息”,舞者、流水、光色、鏡像營造的“鏡花水月,畢竟終成空”之“空靈”境界。這個“空”里“心靈”與“造化”融合,主體與客體消弭,“人”與“物”“合一”,至空、至性的靈性天地承載著宇宙萬物的“生生之美”。《玉兔渾脫》和《水月》是超卓而氣象萬千的,她們營構的空間于“空寂中生氣流行,鳶飛魚躍”[2]372,這里,“空間譬如瑩鏡,其積形雖若甚小,及其流光照燭,則舉天地以總收之,攬括無余矣。空間宛如心源,其積氣雖若甚微,及其靈境顯現,則賅萬象以統攝之,障覆盡斷矣”[8]130。構筑化合出生命之“靈境”。“靈境”中,沒有隔絕與痕跡的物我冥合,無我無物,主客融合而浸潤著生命靈性的“敞亮”,人之生命與宇宙萬物的生命親昵貫通,舞蹈創作即在“空靈”的空間境界中超越為自然與生命之和諧,撼人心魄,歷久彌新。
三、舞蹈以身體顯現生命
梅洛•龐蒂曾言:“身體是我們能擁有的世界的總的媒介……身體通過……行動呈現出了一種新的意義的核心:這真切體現在像舞蹈這樣的習慣性行為運動中。”[15]199-200“身體”對于人是重要的。通過“身體”,人通達“世界”,知曉“生命”。舞蹈以身體為本體和媒介,“是人體造型上‘動的藝術’”(吳曉邦語)[12],是“依靠身體、同時挖掘身體潛能、并且超越身體極限的藝術”(袁禾語)[16]329。身體無疑是舞蹈之根本和本質,正是通過“以人體本身為物質材料,以經過提煉、組織、美化了的人體動作”(王克芬語)[17]546,舞蹈“體現”著“我們能擁有的世界”之“意義的核心”,“體現”著“生命”。首先,舞蹈創作中藝術家以身體禮贊生命,身體語言的構建帶有強烈的生命意識。貝雅的經典之作《生命之舞》以對生命逝去的緬懷,顯現了對愛與生死的禮贊。作品中,舞者疊加扭動,交織游走,激情跳躍,熱情相擁,貝雅式的肢體情調呈現出超潔的張力。舞臺逆光普照的身體光影中,身體內力蓬張為光潔的生命個體,生命終有歸宿,終得升華。當演員全體平趟于舞臺,將白布掩沒自己的身體時,舞作完成了生命祭奠的儀式,升華為對于生命的禮贊之歌,生命終將逝去,而生命之美長流。若《生命之舞》的禮贊如詩如歌,帶有一絲浪漫的情愫,是順應生命的感發,那尼金斯基的《牧神的午后》則是以身體的抗爭顯現出強烈的“生命意志”,表達著對生命自由的頌揚。尼金斯基是那個時代古典芭蕾的“舞蹈之神”,而他的創作卻對古典芭蕾帶來了顛覆性的影響。在《牧神的午后》中,他刻意運用了古埃及具有生命再生意義的“正面律”來進行身體語言形態的結構,設計了粗糙的、直線的、棱角性的舞蹈身體語言,顛覆了古典芭蕾的身體美學。作品中的身體成為了編者思想的活的化生,身體的反叛,是對于古典芭蕾遮蓋人性的揭露與反叛,是對于人本真的性與“愛”的生命主題的頌揚。的確,身體是“人”之生命的承載,然而,身體也是宇宙萬物生命流轉之表征。編舞家林麗珍的《花神祭》就以飽含東方美學的身體構型,呈現出對天地之生命的誠敬。在《春芽》、《夏影》、《秋折》、《冬枯》四個篇章中,舞者的身體運動要么寂靜與緩慢,綿長而撼人的身體運轉達至骨節;要么又舞動得張狂頓挫,充斥著生命的躁動。極致的身體運轉引發著生命內力的張揚,肢體似花、若芽,枯榮自在。這里的身體徹底與萬物化合,誠贊著天地之生,物我兩忘于生命的虔敬與祭禮,“齊萬物、一死生”。其次,舞蹈創作中藝術家探尋著純粹身體的絕對意義,從而映射著生命的今在與自在。正如舞蹈史家袁禾教授在《中國舞蹈美學》中所言:“舞蹈演繹生命之‘生’與‘在’”,當“用心靈舞動身體,感知生命,體驗生命,表現生命”時,“動作語言就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語言”[16]333。“歆舞界•藝術實驗室”一直致力于身體的探尋,想建構起可資多重解讀的舞蹈“身體文本”。在《水墨游》和《活著就好》等作品中,進行著“舞蹈化的身體”、“戲劇化的身體”、“生活化的身體”、“幾何的身體”這“四種身體語匯的找尋”,探尋著舞蹈身體的本真性。[18]而“陶身體劇場”的身體探尋就顯得更為極致。其借助《2》、《4》等數字系列作品,以身體極簡的劃圓、滾地、疊合等“重復”運動,使身體褪去世俗生活與事件成為純粹動作,并以之探尋著舞蹈身體在環境中的內在張力和本真存在。正如主創陶冶強調的“‘身體’就是一個獨特的劇場”[19]。舞蹈中,當所有的因素都被剝離,只剩下純粹的身體時,身體的視覺隱喻性和內在的生命張力被無限加強,“肉體純粹變成了貯藏精神中存在的超人力量的容器”[20]。身體成為了生命內在情調本真的見證。作品《生》(樊興華)便凸顯出了“生”之哲學意義。在單純的身體運化中,舞者的蹲、走、行、臥都是“生”之狀態和生命最本質的表現,這個身體是“身與心”的融通與共在,結構了意象,進而升華出舞蹈的生命意境感。純粹的身體舞動中,承載著生命意義最終的表達,生命無止無休的向前行進,自由而美好。純粹的“身體變得猶如液體一樣清徹透明,從中分明能看到靈魂的波動”[21]48。而當代編舞大師莎夏•瓦茲的作品《肉身》則是身體探尋的扛鼎之作。在柏林的猶太博物館中,舞者們赤裸身體。他們顛倒的描述著身體的構造;將身體作為標尺,在墻上測量標注身體的長度;將舞者超長頭發(假發)作為琴弦拉動;赤裸的堆疊滾動,構筑起各種身體的流動線條……作品極盡探索著身體的各種可能性。身體的內與外,美與丑,生與死都在這身體的極致象征中,藝術的、社會的、心理的、生理的、柔情的、暴力的……身體意象交融在一起,身體被極盡所能的“解剖”,引發出“身體—生命”存在的思考。主席曾談到:“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22]。因此,藝術創作一定要以“人”之“靈魂”鑄造為本,要體現人味、富有情味、托舉出人之生命本身的價值。通過發自心靈深處的感知和再現人的“事業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存在和死亡,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顯現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22]的人之生命情調。誠然,有社會責任和良知的藝術家以時間、空間與身體交融一體,通過舞蹈的藝術形式鑄造著鮮活的生命與靈魂。他們鋪陳時間、筑建空間、結構身體,探索、生發而凸顯出時間、空間與身體的不同意趣,以此感悟生命、體味生命、呈現生命、頌揚生命……正是在以本真之身體融入時間與空間的言說中,舞蹈創作化合出生命之流,幽深、曠遠而飽含情調;也正是在身體與時空的激蕩中,舞蹈創作以身體的靈動彰顯生命本身,“借助時空力的感性彰顯生命本身,演繹生命的生意、生機、生氣、生趣,演繹生命的所在、自在、今在、此在”[16]333,鑄造了靈魂,抒發了情調,提升了格調,呈現出舞蹈藝術本真的生命力與永恒的藝術價值。
作者:陳捷 周亮 單位:1.深圳大學 2.南通大學
- 上一篇:淺談藝術創作動機
- 下一篇:分形美學藝術創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