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為貴的美學文學思想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1 10:38:00
導語:以和為貴的美學文學思想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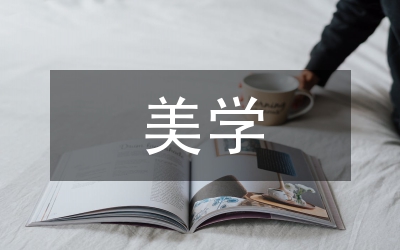
論文摘要:稽康“和”的美學思想及其“和”三種具體表現形式“太和”、“中和”與“保和”與其詩文創作關系十分密切。通過論證進而得出“和”美學思想是貫穿其詩文創作的主旋律之一。
論文關鍵詞:稽康;“和”;文學創作
在中國文化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和”為美的審美觀念,作為中華民族的智慧寶典的《《周易》就有“保合大和”之說。而后來董仲舒所謂“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天地陰陽》)。強調的更是“和”的美麗與偉大。而作為魏晉名士,著名的麼學家、音樂家、文學家的嵇康,歷來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在人們對其哲學思想、詩文風格津津樂道時,對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和”美學意蘊卻關注很少。在嵇康現存的詩歌五十余首和文十四篇中“和”大量出現,共達82處,除一處無實意外,其余均為實指。應該說“和”是不僅成為貫穿其詩文創作的主旋律之一同時也貫穿于嵇康的一生。作為“竹林七賢”領袖,三國魏晉時期著名的麼學代表人物的嵇康,其詩文中“和”含義十分豐富,既與道家所崇尚的“知和日常,知常日明。”(《老子?五十五章》)意義相近又與儒家所倡導的“中道”和“中庸之道”含義相通。在嵇康詩文中的“和”表現最突出的應首推“太和”。后清王夫之也指出“太和,和之至也。
“太和”一詞,蓋源出《易?乾?彖辭》:“保合太和,乃利貞。”對這一概念的含義,北宋張載解釋:“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氳相蕩、勝負、屈伸之始。”(《正蒙?太和》)在他看來,太和就是“道”,其中包含著浮沉、升降、動靜等既矛盾又統一的陰陽二氣,它們不斷變化、互相激蕩,同時應始終處于一種和合狀態。而在天地萬物之本原的“道”面前,人們應尊重它并與之和諧相處,使它始終處于平衡狀態。所以說“太和”指的就是最高境界的、無遠弗及、無所不包的整個宇宙的和諧其中當然也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
關于“太和”,嵇康在其創作中屢次提及。如《秋胡行》中“思與王喬,乘云游八極,思與王喬,乘云游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極。”再如《答二郭》“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文如嵇康的代表作品《聲無哀樂論》中也有。
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反復在嵇康藝術世界中,直至其生命的終結。如其早期作品《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中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在這首詩里,闡發人生真諦:淡泊名利,不為物累,遠離世俗,返歸自然,才能“萬物為一,四海同宅。”再如:“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皤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麼。”(《第十四首》)詩中的抒情主人公一邊若有所思地目送北歸的鴻雁,一邊又信手撫撥著五弦鳴琴,心游于天地自然的玄妙之中……
在其逝世兩年前,他更將與自然融為一體作為自我理想生活樣式去追求“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與山巨源絕交書》),在《幽憤詩》中(被誅前在獄中作),再次抒陳了回歸自然與自然相融和的強烈愿望。“采薇山阿,散發巖蚰。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嵇康曾在《聲無哀樂論》中提出:“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音,得于管弦也。”認為世界上最美的聲音無外乎是自然之音,最美麗的畫面無外乎是自然之畫面。人屬于自然之物,理應包含在內。
嵇康詩文中所表現出的人與自然的親和與無間,正如羅宗強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嵇康)或琴詩自樂,或在淡淡流水中鼓楫容裔,或流諾平皋,或垂綸長川,或泛蘭池,都是處身于大自然中,人與自然相親相近,在返歸自然中與自然融為一體。是整個生活與自然的和諧,然后才有心靈與自然的和諧,于自然的生命與美的領略中,領悟自然之道。”
嵇康在詩文中表現出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畫面有很深的生活基礎。以他為首的“竹林名士”結伴而行、縱情于山水,沉醉于山水竟而忘記了路途與時間。據《太平御覽》引《向秀別傳》載:嵇康與其友人的瀟灑行動“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嵇康得山水自然之神韻至而忘我的情境,時人以為神。“(嵇)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晉書?嵇康傳》)這里的“得意”,即是說自然景物與人某種情思相切合。晉人李充曾在《吊嵇中散文》中也同樣述說了嵇康沉入自然而感慨的情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至人之麼旨,味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托歸流而永吟,乃自足于丘壑,孰有慍乎陸沉。”此中的“寄欣”“取樂”云云,即是說醉心于自然景物并由此觸發了詩人的情思,所以才會凌風而長嘯,托流而永吟。
漢末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士子報國無門,家的意識比國的意識更濃厚。余嘉錫云:“蓋魏晉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r5]文學家族內部篤厚親情,在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中體現親情也是其家族意識的集中體現。這種親情有父子、叔侄的長幼倫理之情,也有同族兄弟的手足之情……這種與親人的和諧共處,也是我們先人最重視、討論最多的問題即“中和”。
在拒絕朋友山濤的推薦后,嵇康表明與親人朝夕共處才是畢生的愿望,“今但愿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而不愿出仕做官的借口之一也是“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崴,未及成人”,(《與山巨源絕交書》)由此可見親人在其心中分量。
嵇康給其兄嵇喜的贈詩,是在其兄入軍,離別時而作,有《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十八章前四章以鴛鴦的“邕邕和鳴,顧眄儔侶”起興,反襯兄長獨征的寂寞與孤獨,“獨行踽踽”、“靡瞻靡恃”。“朝游高原,夕宿蘭渚。”“朝游高原,夕宿中洲。”寫兄長的從軍的艱辛與旅途勞頓;“仰彼凱風,涕泣如雨!‘仰彼凱風,載坐載起。”母親的辛勞和悲傷來勸阻兄長。《凱風》是《詩經?國風?邶風》中的篇章,是一首歌頌母親的詩。詩歌稱贊母親的辛勞善良,“母氏劬勞”,“母氏圣善”,而“我無令人”,兄弟們不成材,以致“莫慰母心”。嵇康用此典,意在表明母親育兒的辛勞,兄弟應在母親身邊,以樂天倫。五至十五章言人生短暫,兄弟分離,隔山乘水,因而無限傷感,抒發兄長入軍后自己的思念和孤獨之情。詩歌反復抒寫“雖有好言,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郢人逝矣,誰與盡言”,“旨酒盈樽,莫與交歡”,“佳人不存,能不永嘆”!以期用兄弟之情打動對方,使勿離家入軍。
親人去世后,嵇康十分痛苦,屢次在詩文中表達思念之情。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良好的家庭的人際關系,怎能寫出如此感人至深的作品來。有《思親詩》為證。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都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嘆。感機杖兮涕沈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規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流襟。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嘆成云。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對于兄長、母親牽掛、思念如此,對于幼子嵇康更是割舍不下。《家誡》一篇體現出一位父親對于兒子的關心與愛護,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文中雖沒有說讓兒子做個忠臣孝子,但舉的例子都是符合儒家正統觀念的,特別“謹慎言語”一點,嵇康再三盯嚀,這似與其本人所作所為相去甚遠。因此“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愿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但我們知道在“庸碌”背后隱藏的是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作為父親的嵇康不愿意看見嵇紹象自己一樣艱辛,為了保全兒子的性命嵇康寧愿他象普通人一樣平安而健康地活著。但這并不表明嵇康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否定。
我們在大量的資料中可以看出嵇康性烈、率直。“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游。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世說新語?榱逸》,又《晉書-嵇康傳》:“登日;‘君性烈才雋,其能免乎?”);嵇康也說自己是“不識人情,暗于機宜,無萬石之慎,有好盡之累。”(《與山巨源絕交書》)……正是因為這種個性得罪了鐘會,遭致了殺身之禍。但即便如此性格暴躁之人,在世說雅量第六在敘他臨死前:“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很難想象一個從不注意維護親情的人,會有如此的人緣。
對于如何保持心志和順,身體安適,做到個體“小宇宙”的和諧,嵇康有著自己獨有的看法與認識。在其著名的《養生論》中,嵇康提出“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強調對個體生命精神方面的維護。這與前人所提的“保和”意思相當。《魏書?崔浩傳》:“遣諸憂虞,恬神保和。”唐韓愈《順宗實錄三》:“居惟保和,動必循道。”也就是說人要清心寡欲,心胸坦蕩。不要追逐名利,不為外物所累,不為情欲所惑,才能使精神處于一種平靜、醇和的健康狀態。
在這篇文章他多次強調養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為名位利祿去傷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貪美味佳饌;四是不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靈世界,達到生存的“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虛”的“至樂”境界。“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哀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后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唏以朝陽,綏以五弦,無為自得,體妙心麼。忘歡而后樂足,遺生而后身存。”
《答難養生論》的一文中,嵇康又從反面論證了如果“名利不滅”、“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轉發”就很難達到養生的目的。
在重視精神養生之外,嵇康認為還可通過服用一定藥物來達到“保和”的目的。“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這是加強對身體的練養。只有這樣,才能“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也”。通過服食養生,飲甘泉,沐朝陽,撥五弦,人的生命就達到了自然無為的麼妙境界。
這種觀念在其詩歌創作中同樣有所表現,如“飄遙戲麼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采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殤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游仙詩》)再如:“輕舉翔區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戲靈岳,彈琴詠泰真。滄水澡五藏,變化忽若神。恒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一縱發開陽,俯視當路人。哀哉世間人,何足久托身。”(《五言詩》對于嵇康的養生史書也有記載:王戎日:“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世說新語?德行》)“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言……”(《世說新語》注引《嵇康別傳》)“(嵇康)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道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晉書?嵇康傳》)這里的嵇康嚴謹持身,澹淡處世,和光同塵,心如止水,這是其數年來追求的個體生命“保和”的結果。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嵇康“和”思想,而這種思想歸根到底源于他儒道雙修的文化底蘊。早在先秦時期,道家強調自然的和諧,比如老子曾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儒家強調社會的和諧,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孔子的學生有子就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在以上的“三和”之中,“太和”為最高的和諧,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中和”是講人與人的和諧,“保和”是講人體自身的和諧。而嵇康所追求正是這種以“保和”為基礎,“中和”為依托,“太和”為最高目標的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他的思維模式是一個儒道互補的新型的世界觀,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體現了中國思想的共同特征。
- 上一篇:清代女性作家文化背景研究論文
- 下一篇:剖析難事件新聞報道圖片應用策略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