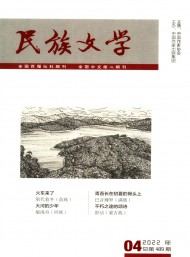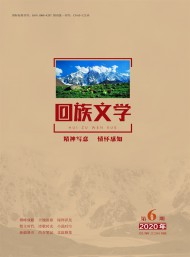文學(xué)敘事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5 14:02:49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文學(xué)敘事論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英雄敘事文學(xué)意識形態(tài)論文
【內(nèi)容提要】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英雄敘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學(xué)敘事形態(tài)之一。“十七年”文學(xué)的英雄敘事基本上可以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條發(fā)展脈絡(luò):其一是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制導(dǎo)下,在顯形層面上展開英雄敘事的文本,這承繼了《講話》以來獲得認(rèn)可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在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的對峙中凸現(xiàn)外在的交鋒;其二是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下,糅進(jìn)了具有個人化的審美情調(diào),使英雄敘事在大體上滿足主流意識形態(tài)規(guī)范的同時,傳達(dá)出了屬于個人的審美情趣。“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的這兩大脈絡(luò),從不同的向度上彌補(bǔ)了各自的英雄敘事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學(xué)史價值和意義。
【關(guān)鍵詞】英雄敘事;“十七年”文學(xué);意識形態(tài)
在“十七年”文學(xué)中,英雄敘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學(xué)敘事形態(tài)之一,甚至可以說,英雄敘事是“十七年”文學(xué)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征。在20世紀(jì)的中國文學(xué)史上,還沒有那一個時期能夠產(chǎn)生如此之多的文本。面對如此之多的英雄敘事文本,通過梳理其發(fā)展的脈絡(luò),進(jìn)而對其發(fā)生、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獲得進(jìn)一步的認(rèn)知,這不但能夠有助于我們加深對“十七年”文學(xué)的認(rèn)識,而且也有助于我們對當(dāng)下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存在的某些缺失有所匡正。“十七年”文學(xué)的英雄敘事發(fā)展脈絡(luò)基本上可以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條發(fā)展脈絡(luò)。正是這兩大發(fā)展脈絡(luò),從不同的向度上彌補(bǔ)了各自的英雄敘事的不足,對各自的發(fā)展脈絡(luò)起到了潛在的規(guī)范制約作用。
一
根據(jù)“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所顯示出來的美學(xué)風(fēng)格的不同,最為清晰并占據(jù)著主流的發(fā)展脈絡(luò),是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制導(dǎo)下,在顯形層面上展開英雄敘事的文本,這承繼了《講話》以來獲得認(rèn)可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在階級斗爭或民族斗爭的對峙中凸現(xiàn)外在的交鋒。所以,這些文本基本上保持了《新兒女英雄傳》的敘事風(fēng)格。“十七年”文學(xué)的英雄敘事,從時間上來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要早些,在共產(chǎn)黨基本獲得全國性勝利的情形下,“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就進(jìn)入了蛻變定型的階段,具體來說,《新兒女英雄傳》是其起始的標(biāo)志,這在根本上確立了“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的基本模式;第一次文代會所確立的文藝政策在理論上標(biāo)志著英雄敘事范式的定型;《保衛(wèi)延安》的出版標(biāo)志著英雄敘事的定型;《紅巖》的誕生則標(biāo)志著這一階段的英雄敘事的高潮已經(jīng)基本過去。《新兒女英雄傳》標(biāo)志著“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在完成了自我的蛻變之后的定型之作。嚴(yán)格講來,《新兒女英雄傳》在時間上要稍早于“十七年”,但它卻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特別主要的是,其英雄敘事的模式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獲得了已經(jīng)占據(jù)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認(rèn)同。《新兒女英雄傳》被當(dāng)作實(shí)踐《講話》的精神的成功之作,其所規(guī)范和確定的方向就對嗣后的英雄敘事具有了規(guī)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英雄敘事的文化品格:其一是農(nóng)民和革命具有天然性的聯(lián)系,主流意識形態(tài)視閾下的農(nóng)民個體行為被充分政治化,凸顯了農(nóng)民在和革命融合的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英雄業(yè)績;其二是大團(tuán)圓的英雄敘事模式。這就使得“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盡管也會出現(xiàn)一些悲劇,但從總的結(jié)局來看,基本上都遵循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樣的一個大團(tuán)圓敘事路徑,而英雄則是這一先驗(yàn)性存在的一個明證。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郭沫若才會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指示,給予了文藝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創(chuàng)作的前途。在這一照明之下,解放區(qū)的作家們已經(jīng)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顯然,這成功的重要標(biāo)志在于“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jìn)自己。”在這里,論者凸顯的是《新兒女英雄傳》的教化功能,把文學(xué)作為鼓舞人民革命的重要武器。這樣的闡釋,實(shí)際上也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的基本規(guī)范和要求,即歷史中客觀存在的英雄怎樣是一回事,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是怎樣又是另一回事,那么,裁定其是否符合規(guī)范和要求的標(biāo)準(zhǔn)則是能否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起到強(qiáng)化作用,能否對“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jìn)自己。”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新兒女英雄傳》標(biāo)志著“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模式的基本確立,從而客觀上規(guī)范了“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沿著《新兒女英雄傳》的敘事模式展開。正是在這一模式的規(guī)范導(dǎo)引下,作家們在文學(xué)中所進(jìn)行的英雄敘事就特別凸現(xiàn)了英雄之作為“英雄”的那一面,而相對來說,那些無助于凸現(xiàn)“英雄”的方面則被遮蔽了。如劉白羽作為戰(zhàn)地記者對戰(zhàn)爭有親身感受,這就使他的英雄敘事最大限度地切近了真實(shí)生活。作者通過解放軍渡江作戰(zhàn)中表現(xiàn)出來的英雄氣概,塑造了一群只要“火光在前”就“永遠(yuǎn)前進(jìn)”的指揮員英雄形象(《火光在前》),但它同時遮蔽了戰(zhàn)爭中人的其他屬性。這奠定了后來的英雄敘事昂揚(yáng)向上的革命基調(diào),即便是死亡這樣的沉重的話語,也通過“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氣概完成了向革命的精神家園“回歸”并存在的形式。《銅墻鐵壁》是柳青的一部有關(guān)革命歷史敘事的重要文本,其講述的是陜北農(nóng)民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的支前故事。柳青在此塑造了石得富這一英雄形象,突出表現(xiàn)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戰(zhàn)爭中巨大的歷史主動性。知俠的《鐵道游擊隊(duì)》則用粗獷的筆法,其所講述的是一批活躍在鐵道上的游擊隊(duì)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傳奇故事,其所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有劉洪、李正、王強(qiáng)、林忠等,知俠在英雄敘事中,注意把民間傳奇和革命歷史有機(jī)融合起來,這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下的其他英雄敘事相比,具有獨(dú)特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如果說在這些長篇小說中,其英雄敘事還顯得粗獷豪放的話,那么,還有與此相對應(yīng)的一支英雄敘事脈絡(luò),這就是峻青和王愿堅(jiān)的英雄敘事,他們似乎更喜歡在短小而嚴(yán)謹(jǐn)?shù)慕Y(jié)構(gòu)中,以寫意的筆法來塑造英雄。峻青所塑造的英雄主要是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的英雄,他把刻在自己記憶里的英雄,通過文學(xué)想象的方式,為我們營造了一個英雄敘事的文本世界。峻青的代表作是《黎明的河邊》,峻青在此把革命和親情設(shè)置于同一場景中,凸現(xiàn)了革命和親情的緊張關(guān)系。英雄小陳在和敵人對峙的過程中,敵人為了迫使小陳交出革命者,挾持了小陳的母親和弟弟作為“人質(zhì)”,這就使小陳處于二難抉擇的窘境中,要救出母親和弟弟,就要交出自己的同志;要保護(hù)自己的同志,就要失去母親和弟弟。作家在展開英雄敘事的過程中,沒有詳盡地觀照英雄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而是讓小陳選擇了與還鄉(xiāng)團(tuán)頭子同歸于盡,由此把小陳從政治與道德的緊張對峙中解脫了出來,緩解了革命和親情的緊張關(guān)系,塑造了一個道德和革命和諧完美的英雄。其實(shí),在這樣的英雄敘事中,包含著峻青這樣的一種英雄理念:革命和親情是緊張對立的關(guān)系,二者在不可能兼顧時,犧牲親情既然把革命者置于道德的對立面,犧牲同志既然把自己置于政治的對立面,那么,唯一的選擇就是犧牲自己以舒緩革命和親情的緊張關(guān)系。王愿堅(jiān)是對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中的英雄情有獨(dú)鐘。王愿堅(jiān)最有影響的是《黨費(fèi)》,這是較早涉及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蘇區(qū)軍民在敵后堅(jiān)持斗爭生活的英雄敘事文本,這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有關(guān)這一題材的英雄敘事偏弱的局限。杜鵬程則善于從宏大的歷史中把握中國革命歷史,其《保衛(wèi)延安》的英雄敘事從對局部和細(xì)微的革命戰(zhàn)爭敘事轉(zhuǎn)向了對宏大的革命戰(zhàn)爭的敘事,這標(biāo)志著英雄敘事獲得了巨大的突破。作者以高昂的激情、宏大的規(guī)模、磅礴的氣勢,從正面描繪了解放戰(zhàn)爭中著名的延安保衛(wèi)戰(zhàn)。司令員的運(yùn)籌帷幄,指揮員周大勇、衛(wèi)毅等的身先士卒,戰(zhàn)士王老虎、寧金山們的英勇頑強(qiáng),都集中展示了英雄們的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具有一定史詩性。但遺憾的是,這樣的文本,在“”中卻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對此,杜鵬程在《保衛(wèi)延安》重印之后說過:“你明明是在歌頌,他卻硬說你‘惡毒攻擊’。”)其實(shí),我們暫且撇開其所涉及的問題,而是從另一面來看問題的話,也許就會發(fā)現(xiàn),其英雄敘事先驗(yàn)地存在著一個至高無上的主題,這就使其英雄敘事當(dāng)作了“歌頌”的具體注腳。這也就說明了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制導(dǎo)下,在顯形層面上展開英雄敘事的文本,都存在著一個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人的其他某些屬性擠壓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這自然也就限制了其英雄敘事所可能獲得的歷史的深度和廣度。能夠代表“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所達(dá)到的高度和水準(zhǔn)的是吳強(qiáng)的《紅日》。吳強(qiáng)的《紅日》出版于1958年,它采用紀(jì)實(shí)文學(xué)和小說虛構(gòu)相結(jié)合的手法,為我們塑造了軍長沈振新、副軍長梁波、團(tuán)長劉勝、連長石東根等英雄形象。《紅日》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現(xiàn)在作者并沒有把英雄寫成簡單的戰(zhàn)爭英雄,而是把戰(zhàn)爭英雄置于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中,特別是情愛關(guān)系中加以表現(xiàn),使戰(zhàn)爭和情愛在對峙中獲得了深層展現(xiàn),這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英雄所具有的本色。對此,吳強(qiáng)曾經(jīng)說過:“有些人說過緊張、艱苦的斗爭里,哪有人談愛情之類的話,想證明一下事實(shí)不是那樣,把戰(zhàn)爭時期的生活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來。”實(shí)際上,戰(zhàn)爭中的愛情以及愛情的毀滅,都更清晰地傳達(dá)出了這樣的意蘊(yùn):戰(zhàn)爭的最終目的恰恰是為了讓人世間包括愛情在內(nèi)的所有美好情感獲得健康的發(fā)展,而不是人為地扼殺這一美好情感,否則,這戰(zhàn)爭和政治就是反人性的。如此說來,十七年文學(xué)英雄敘事中的愛情主題,盡管在政治的夾縫中沒有獲得充分發(fā)展的機(jī)緣,但作家在嚴(yán)格恪守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的同時,沖決了當(dāng)時的文化語境的羈絆,依然為我們奉獻(xiàn)出了諸多的“戰(zhàn)地黃花”。這標(biāo)志著這一階段的英雄敘事模式出現(xiàn)了新的突破,即把戰(zhàn)爭和人性結(jié)合起來。但這樣的一種模式,并沒有獲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認(rèn)可。“十七年”文學(xué)中具有廣泛影響的另一重要英雄敘事文本是曲波出版于1957年的《林海雪原》。這一文本塑造的英雄楊子榮帶有傳奇色彩,其突破主要在于它把民間所喜聞樂見的傳奇和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有機(jī)地結(jié)合了起來,在民間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夾縫中,尋找到了一條融合的發(fā)展路徑。歐陽山出版于1959年的《三家巷》是本階段少有的反映20年代革命策源地斗爭風(fēng)云的文本,它拓展了本階段英雄敘事的范圍,把過去較為薄弱的都市生活納入到了英雄敘事中。但相對來說,這一范式的英雄敘事并沒有取得應(yīng)有的地位,居于邊緣化的位置。楊沫出版于1958年的《青春之歌》標(biāo)示了本階段革命歷史敘事的另一發(fā)展緯度。它以林道靜在共產(chǎn)黨的影響和領(lǐng)導(dǎo)下,最終成長為具有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英雄。其作為具有較大影響的英雄敘事文本,在兩個方面有重大突破,一是女性兼知識分子的英雄形象,這隱含了知識分子人生道路和女性個性解放的雙重命題,二是這雙重命題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命題的皈依。這樣三個命題糾纏在一起,使《青春之歌》獲得了解讀上的多種可能性。梁斌出版于1957年的小說《紅旗譜》,則以大革命失敗前后十年為歷史背景,寫出了農(nóng)民英雄朱老忠成長歷程。朱老忠在階級斗爭的歷史背景下,獲得了豐富的社會內(nèi)涵,同時也帶有詮釋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局限。“十七年”文學(xué)中具有較大影響的革命歷史敘事還有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紅巖》由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這標(biāo)志著有關(guān)革命的歷史已經(jīng)被這是一個有關(guān)煉獄中的英雄故事。作家塑造的江姐、許云峰等許多堅(jiān)貞不屈的殉道英雄,具有極其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魅力。《紅巖》的誕生則標(biāo)志著這一階段的英雄敘事的高潮已經(jīng)基本過去。這一方面是因?yàn)橛嘘P(guān)革命的歷史故事已經(jīng)基本講完;另一方面是因?yàn)楝F(xiàn)實(shí)問題更為緊迫的提到了人們的思考視閾中,這也意味著“十七年”文學(xué)中的英雄敘事主潮將出現(xiàn)轉(zhuǎn)向。在大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特定文化語境下,有關(guān)革命歷史的英雄敘事的“準(zhǔn)星”已經(jīng)使作家們很難琢磨或追隨。在此情景下,作家在英雄敘事中涉及革命歷史中的“大題材”,就難免會和具體高級指揮員有所瓜葛,如果這指揮員將來有一天因?yàn)槁肪€斗爭而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循此展開的英雄敘事文本就會面臨滅頂之災(zāi)。所以,衰退階段的英雄敘事出現(xiàn)了一個很大的轉(zhuǎn)向,這就是作家從革命大題材轉(zhuǎn)向了革命小題材或歷史題材。如徐光耀的《小兵張嘎》、黎汝清的《萬山紅遍》等。
二
文學(xué)形象敘事翻譯和語用翻譯論文
摘要:翻譯的首要標(biāo)準(zhǔn)是“忠實(shí)”,即對原來文本意義的準(zhǔn)確理解和用新文本作準(zhǔn)確再現(xiàn)。然而,文本的意義受作者、文化系統(tǒng)、讀者等多方面的制約,具有自身的語義不確定性和理解上的多重含義性。本文以人物形象,包括動作、對話和人物心理活動描寫幾方面的具體實(shí)例探討了在文學(xué)作品翻譯中敘事學(xué)理論和語用學(xué)理論如何使譯文與原文達(dá)到語用等效。作者認(rèn)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必須對特定語境中的意義進(jìn)行分析,確定有關(guān)成分的意義。并以不同的視角對意義的特征進(jìn)行分析,然后準(zhǔn)確恰當(dāng)?shù)刈g成目標(biāo)語,達(dá)到與原文的動態(tài)等效。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形象;翻譯;敘事學(xué);語用學(xué)
一、引言
文學(xué)形象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包括外貌(肖像)描寫,心理描寫,行為(動作)描寫,對話描寫,細(xì)節(jié)描寫,環(huán)境與人物、人物與事件的關(guān)系的描寫,等等。在翻譯文學(xué)作品時,既要忠實(shí)于原作的靈魂,又要便于讀者的理解與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確傳遞,又注意原作者美學(xué)意圖的充分體現(xiàn)。文學(xué)翻譯作為一個獨(dú)立的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西方譯論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譯領(lǐng)域,由于對文學(xué)翻譯的本質(zhì)特征認(rèn)識模糊而陷入重藝術(shù)、輕語言或重語言、輕藝術(shù)的傾向,翻譯實(shí)踐的隨意性和翻譯批評的極端化等現(xiàn)象不時出現(xiàn)。本文嘗試將敘事學(xué)理論和語用學(xué)理論運(yùn)用于文學(xué)作品的翻譯實(shí)踐。基于對人物刻畫的多視角、多方位的考察,著重從微觀層次,即人物的動作語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動,探討這兩種理論對文學(xué)作品翻譯的指導(dǎo)作用,以求拓寬翻譯的研究領(lǐng)域。
二、人物動作語言翻譯
人物描寫方式屬于正面描寫,人物描寫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和心理描寫,采用人物描寫方式,能以形傳神,增強(qiáng)人物形象的鮮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質(zhì)。人物的動作描寫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國古典文學(xué)傳統(tǒng)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方法。武松、林沖、李逵、魯智深、張飛、諸葛亮等典型藝術(shù)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動描寫。一提起武松,婦幼皆知他景陽岡的打虎行動;一說到關(guān)羽,人們總忘不了他過五關(guān)斬六將的一系列行動。因?yàn)榇蚧⑦@一行動成了武松勇氣和力量的標(biāo)志;而過五關(guān)斬六將的一系列行動,則充分揭示了關(guān)羽勇猛善戰(zhàn)的英雄豪氣。也就是說,行動是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表露。文學(xué)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來揭示的。人的行動是受思想支配的,通過一個人的行動,可以窺見其思想和心理活動。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常常通過人物的行動來表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
文學(xué)演變視域下本科畢業(yè)論文選題策略
摘要:中國古代敘事文學(xué)重要成書方式之一是對前文本進(jìn)行改編,我們同樣可將這一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引入漢語言文學(xué)本科畢業(yè)論文教學(xué)。這種以小見大、小題大做的研究方法既易于激發(fā)學(xué)生的探索興趣,也與現(xiàn)代科研的思維規(guī)律相契合。僅以小說、戲曲兩種文體的改編現(xiàn)象而論,學(xué)生的選題方向可厘為五種:戲曲改編小說;小說改編戲曲;戲曲改編戲曲;小說改編小說;小說與戲曲互相改編。教師可以開設(shè)文學(xué)演變選修課;啟迪學(xué)生在比較視域下選擇論題;師生充分溝通以保證自主選題的可行性。
關(guān)鍵詞:本科畢業(yè)論文;選題指導(dǎo);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
一、選題契合本科生專業(yè)基礎(chǔ)及思維水平
中國古代敘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一個突出特征:即許多作品非由一人獨(dú)立創(chuàng)作完成,而是在前代相關(guān)作品基礎(chǔ)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西方互文性理論認(rèn)為,一切作品都是互文本,每個經(jīng)典文本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前文本可以尋覓,新作品與前文本構(gòu)成一種對話關(guān)系。換言之,改編行為常常是作品經(jīng)典化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如小說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馮夢龍“三言”,戲曲中的《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等等,莫不如此。這種特征與互文性理論高度契合。對于這一文學(xué)現(xiàn)象,明清以來至現(xiàn)代學(xué)界給予了持續(xù)的、充分的關(guān)注,尤其是二十世紀(jì)20年代至80年代,曾產(chǎn)生眾多學(xué)術(shù)分量厚重的成果,諸如趙景深《宋元戲文本事》(北新書局1934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我們同樣可將這一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引入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本科畢業(yè)論文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主要理據(jù)一是文學(xué)故事具體可感,對象明確,容易引起學(xué)生興趣。學(xué)生便于搜集資料,易于打開思路,可使論文內(nèi)容言之有物。許多文學(xué)故事源遠(yuǎn)流長,隨時代演進(jìn)而不斷嬗變,其版本紛紜復(fù)雜,因此即使對這些故事的演變情況進(jìn)行搜集、梳理,也會帶動學(xué)生查閱大量文獻(xiàn)資料,在對諸文本比對分析時,定會有一些獨(dú)特發(fā)現(xiàn),會進(jìn)一步調(diào)動、提升學(xué)生的思維能力、研究能力。二是切入點(diǎn)小,容易上手,易于以小見大,洞察幽微。這種研究路徑也契合現(xiàn)代科研的普遍思維規(guī)律。一個文學(xué)故事的嬗變往往跨越多個朝代,其不同文本因受時代背景、社會思潮、改編者主體意識等多元因素的影響,這些同一本源故事的不同文本在故事情節(jié)、人物關(guān)系、人物形象、思想主旨等方面,往往表現(xiàn)出很大的差異。對其歷史演變情況進(jìn)行個案研究,可以以小見大,洞察時代、作家、受眾等多種因素對一個文學(xué)文本的共同建構(gòu),進(jìn)而探討文學(xué)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對于本科生畢業(yè)論文選題教學(xué)而言,這種以點(diǎn)帶面、小題大做的選題及研究路徑,也比較切合本科生專業(yè)基礎(chǔ)與研究能力的實(shí)際;自指導(dǎo)教師角度而言,選擇容易激活學(xué)生知識資源、激發(fā)其專業(yè)興趣的題目,可以使指導(dǎo)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從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實(shí)質(zhì)提高本科畢業(yè)論文寫作的質(zhì)量。
二、敘事文學(xué)改編方式與學(xué)生選題方向
馬原小說敘事與先鋒文學(xué)批評困難
1980年代中期,馬原小說以其迷宮式的敘事探索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批評家們以“小說的操作”、“敘事的圈套”為名掀起了一股研究馬原小說敘事的熱潮,期望馬原小說敘事能夠?yàn)橄蠕h文學(xué)實(shí)驗(yàn)開辟一條新路。然而,馬原小說與批評并沒有依照人們的意愿走向深入:一方面是馬原本人的寫作不久即陷入了“操作”困境;一方面是馬原小說批評在迷宮式的“敘事圈套”中漸入誤區(qū)。作為新時期小說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馬原小說研究與新時期小說批評之間的這一吊詭值得回味和反思。
一、馬原小說敘事及其意義的生產(chǎn)
馬原小說的敘事實(shí)驗(yàn)最初體現(xiàn)在《拉薩河女神》、《疊紙鷂的三種方法》兩篇小說中。文學(xué)史家洪子誠認(rèn)為:“馬原發(fā)表于1984年的《拉薩河女神》,是大陸當(dāng)代第一部將敘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說。”[1](P337)然而,當(dāng)時的批評家并不看重馬原小說敘述方法的探索。辛力認(rèn)為:不管馬原小說在藝術(shù)形式上如何“搞得撲朔迷離”,讀者最終尋求的是作品的“內(nèi)涵”,馬原小說的“內(nèi)涵”在于他向讀者展示的“西部世界”[2]。張志忠肯定了馬原小說的敘事方法,但他認(rèn)為這種方法是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服務(wù)的:“多線條并進(jìn)與多框架結(jié)構(gòu),真切感與假定性,形成了馬原故事的特殊功能———它主要地不是為故事而故事,而是借故事演人生。”[3]1985年,馬原的中篇小說《岡底斯的誘惑》在《上海文學(xué)》第2期上發(fā)表,洪子誠在其《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年表”里面記錄了這件事情,把它看作是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的一個重要細(xì)節(jié)。然而據(jù)馬原回憶:當(dāng)時的情況并非如此,“我把我特別看重的小說,寄給了我特別尊重的刊物。當(dāng)時,《上海文學(xué)》回一封信,說馬原你的小說我看了也很激動但是好像沒有把握,還是過一段時間吧,眼前暫時沒法發(fā)表,退了回來。”
作為《上海文學(xué)》的編輯,蔡翔回憶證實(shí)當(dāng)時編輯部對于這篇小說也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馬原的稿子是1984年到這里,七八月份,秋天吧。也討論,文章我也看過,大家意見完全不一樣。很難有個說法,討論很激烈。發(fā)表《棋王》之后有一點(diǎn)尋根文學(xué)的趨向,突然有馬原的現(xiàn)代主義色彩很濃的作品,后來一直討論到杭州會議,請李陀,韓少功看,李陀,韓少功都很肯定。”[4]雖然人們都感覺這個文本“不錯,有意思,發(fā)表了,其實(shí)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說不清。”[4]由此來看,即使是當(dāng)時頗具前衛(wèi)意識的《上海文學(xué)》也對馬原小說的敘事實(shí)驗(yàn)不置可否。這一狀況到1986年發(fā)生了變化,從這一年開始,關(guān)于馬原小說敘事方法的評論一度成為文學(xué)批評的焦點(diǎn)。王斌、趙小鳴認(rèn)為:馬原小說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常常象搓洗撲克牌似的,把情節(jié)的嚴(yán)整有序的結(jié)構(gòu)模式徹底打亂,然后又微笑俏皮地向你亮出他手中零亂不堪的底牌來”,從而讓“時序和運(yùn)動的空間位置變得模糊不清,真?zhèn)坞y辨。”[5]曉華、汪政從“小說操作”的角度入手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前中國文壇,還沒有能像馬原這樣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敘述意識及對操作活動的一往情深的專注和享受”;馬原只是一味地編故事,他注重的是“編”而不是“故事。”[6]賀紹俊、潘凱雄以“柔軟的情節(jié)”命名馬原的《錯誤》、《虛構(gòu)》、《游神》、《大元和他的寓言》的“敘述結(jié)構(gòu)”,指出這是作者“創(chuàng)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的獨(dú)特方式”[7]。吳亮是馬原小說敘事的有力支持者,他指出:馬原小說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將追尋故事的戲劇性、內(nèi)容的潛在性放在首位,而是把文學(xué)的文體要素———敘事的技巧、敘事人與主人公之間的錯綜復(fù)雜的聯(lián)系等看成重點(diǎn)。他說:“在我的印象里,寫小說的馬原似乎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尋找他的敘述方式,或者說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尋找他的講故事方式。他實(shí)在是一個玩弄敘述圈套的老手,一個小說中偏執(zhí)的方法論者。”[8]吳亮從敘事理論出發(fā),認(rèn)為:“馬原的重點(diǎn)始終是放在他的敘述上的,敘述是馬原故事中的主要行動者、推動者和策演者。”
吳亮的批評實(shí)踐以馬原小說的整體為研究對象,深入打撈馬原的寫作動機(jī)或?qū)懽饔^念是否有反抗傳統(tǒng)的自覺等問題。他從文本樣態(tài)入手,發(fā)現(xiàn)馬原小說雖然都刻畫了讓人難以忘懷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但它們只是片片斷斷,根本無法使用一種邏輯將它們串聯(lián)起來:“馬原的經(jīng)驗(yàn)方式是片斷性的、拼合的與互不相關(guān)的。他的許多小說都缺乏經(jīng)驗(yàn)在時間上的連貫性和在空間上的完整性。馬原的經(jīng)驗(yàn)非常忠實(shí)于它的日常原狀,馬原看起來并不刻意追究經(jīng)驗(yàn)背后的因果,而只是執(zhí)意顯示并組裝這些經(jīng)驗(yàn)。”[8]他非常形象地使用了“組裝”一詞,意在表明這些經(jīng)驗(yàn)的真實(shí)性只在局部,和傳統(tǒng)文本所追尋的“意義深度”、“本質(zhì)聯(lián)系”等理念基本無緣。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所有這些與馬原的認(rèn)識論有直接的聯(lián)系:“在經(jīng)驗(yàn)背后尋找因果是馬原所不愿意的,那么在故事背后尋找意義和象征也是馬原所懷疑的。馬原確實(shí)更關(guān)心他故事的形式,更關(guān)心他如何處理這個故事,而不是想通過這個故事讓人們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種抽象觀念。馬原的故事形態(tài)是含有自我炫耀特征的,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開場里非常灑脫無拘地大談自己的動機(jī)和在開始敘述時碰到的困難以及對付的辦法。
有時他還會中途停下小說中的時間,臨時插入一些題外話,以提醒人們不要在他的故事里陷得太深,別忘了是馬原在講故事”。[8]正是源于這種對文本形式的自覺,馬原才真正做到了對傳統(tǒng)敘事模式的間離。吳亮敏銳地感覺到馬原不僅僅在講故事,更主要的是在講故事:“它不僅要敘述故事的情節(jié),而且還要敘述此刻正在進(jìn)行的敘述,讓人意識到你現(xiàn)在讀的不單是一只故事,而是一只正在被敘述的故事,而且敘述過程本身也不斷地被另一種敘述議論著、反省著、評價著,這兩種敘述又融合為一體。”[8]沿著這一脈絡(luò),吳亮從“馬原”這個名字在他小說敘述中的地位、馬原的朋友們和角色們在其小說中的不同表現(xiàn)、以及馬原的經(jīng)驗(yàn)方式與文學(xué)觀念等方面入手,完成了對馬原小說“敘述圈套”的理論建構(gòu),稱他是“一個玩弄敘述圈套的老手,一個小說中的偏執(zhí)的方法論者”,一個“玩熟了智力魔方的小說家”[8]。吳亮等人關(guān)于馬原小說的批評模式對后來的研究者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譬如,吳義勤認(rèn)為:“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們重新審視小說這個概念,他試圖泯滅小說形式和內(nèi)容間的區(qū)別,并正告我們小說的關(guān)鍵之處不在于它是寫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寫的,他第一次把如何敘述提到了一個小說本體的高度,敘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確的確認(rèn)。”[9]洪子誠這樣概括:“雖然殘雪和馬原幾乎同時出現(xiàn)和同樣引人注目,但只有馬原(而不包括殘雪)被批評家看作是‘先鋒小說’的起點(diǎn)。這種區(qū)分,立足于對‘文體’的純粹性的信仰。”[1](P337)陳思和這樣寫道:“馬原對傳統(tǒng)敘事的似真幻覺的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經(jīng)驗(yàn)的主觀性、片斷性與不可確定性,打破了任何一種宏大敘事重新整合個體經(jīng)驗(yàn)的可能性,這使得充滿個性與主觀性的現(xiàn)實(shí)凸顯了出來。先鋒小說正是這樣一種打破統(tǒng)一的世界圖像與文學(xué)圖像的努力。”[10](P295)其實(shí),無論是吳義勤話語中的“第一次”、“第一性”,還是洪子誠所說的“對‘文體’的純粹性的信仰”,抑或是陳思和所使用的“打破了任何一種宏大敘事”、“打破統(tǒng)一”等等,都可以在吳亮的批評話語中找到源頭。由此可見,馬原小說意義的生成與吳亮等人的文學(xué)批評密切相關(guān),可以說,正是在后者的積極參與下,前者才以先鋒的姿態(tài)進(jìn)入了文學(xué)史。
馬原小說敘事與先鋒文學(xué)批評困境
1980年代中期,馬原小說以其迷宮式的敘事探索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批評家們以“小說的操作”、“敘事的圈套”為名掀起了一股研究馬原小說敘事的熱潮,期望馬原小說敘事能夠?yàn)橄蠕h文學(xué)實(shí)驗(yàn)開辟一條新路。然而,馬原小說與批評并沒有依照人們的意愿走向深入:一方面是馬原本人的寫作不久即陷入了“操作”困境;一方面是馬原小說批評在迷宮式的“敘事圈套”中漸入誤區(qū)。作為新時期小說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馬原小說研究與新時期小說批評之間的這一吊詭值得回味和反思。
一、馬原小說敘事及其意義的生產(chǎn)
馬原小說的敘事實(shí)驗(yàn)最初體現(xiàn)在《拉薩河女神》、《疊紙鷂的三種方法》兩篇小說中。文學(xué)史家洪子誠認(rèn)為:“馬原發(fā)表于1984年的《拉薩河女神》,是大陸當(dāng)代第一部將敘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說。”[1](P337)然而,當(dāng)時的批評家并不看重馬原小說敘述方法的探索。辛力認(rèn)為:不管馬原小說在藝術(shù)形式上如何“搞得撲朔迷離”,讀者最終尋求的是作品的“內(nèi)涵”,馬原小說的“內(nèi)涵”在于他向讀者展示的“西部世界”[2]。張志忠肯定了馬原小說的敘事方法,但他認(rèn)為這種方法是為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服務(wù)的:“多線條并進(jìn)與多框架結(jié)構(gòu),真切感與假定性,形成了馬原故事的特殊功能———它主要地不是為故事而故事,而是借故事演人生。”[3]1985年,馬原的中篇小說《岡底斯的誘惑》在《上海文學(xué)》第2期上發(fā)表,洪子誠在其《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年表”里面記錄了這件事情,把它看作是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的一個重要細(xì)節(jié)。然而據(jù)馬原回憶:當(dāng)時的情況并非如此,“我把我特別看重的小說,寄給了我特別尊重的刊物。當(dāng)時,《上海文學(xué)》回一封信,說馬原你的小說我看了也很激動但是好像沒有把握,還是過一段時間吧,眼前暫時沒法發(fā)表,退了回來。”[4]作為《上海文學(xué)》的編輯,蔡翔回憶證實(shí)當(dāng)時編輯部對于這篇小說也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馬原的稿子是1984年到這里,七八月份,秋天吧。也討論,文章我也看過,大家意見完全不一樣。很難有個說法,討論很激烈。發(fā)表《棋王》之后有一點(diǎn)尋根文學(xué)的趨向,突然有馬原的現(xiàn)代主義色彩很濃的作品,后來一直討論到杭州會議,請李陀,韓少功看,李陀,韓少功都很肯定。”[4]雖然人們都感覺這個文本“不錯,有意思,發(fā)表了,其實(shí)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說不清。”[4]由此來看,即使是當(dāng)時頗具前衛(wèi)意識的《上海文學(xué)》也對馬原小說的敘事實(shí)驗(yàn)不置可否。這一狀況到1986年發(fā)生了變化,從這一年開始,關(guān)于馬原小說敘事方法的評論一度成為文學(xué)批評的焦點(diǎn)。王斌、趙小鳴認(rèn)為:馬原小說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常常象搓洗撲克牌似的,把情節(jié)的嚴(yán)整有序的結(jié)構(gòu)模式徹底打亂,然后又微笑俏皮地向你亮出他手中零亂不堪的底牌來”,從而讓“時序和運(yùn)動的空間位置變得模糊不清,真?zhèn)坞y辨。”[5]曉華、汪政從“小說操作”的角度入手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前中國文壇,還沒有能像馬原這樣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敘述意識及對操作活動的一往情深的專注和享受”;馬原只是一味地編故事,他注重的是“編”而不是“故事。”[6]賀紹俊、潘凱雄以“柔軟的情節(jié)”命名馬原的《錯誤》、《虛構(gòu)》、《游神》、《大元和他的寓言》的“敘述結(jié)構(gòu)”,指出這是作者“創(chuàng)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的獨(dú)特方式”[7]。
吳亮是馬原小說敘事的有力支持者,他指出:馬原小說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沒有將追尋故事的戲劇性、內(nèi)容的潛在性放在首位,而是把文學(xué)的文體要素———敘事的技巧、敘事人與主人公之間的錯綜復(fù)雜的聯(lián)系等看成重點(diǎn)。他說:“在我的印象里,寫小說的馬原似乎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尋找他的敘述方式,或者說一直在樂此不疲地尋找他的講故事方式。他實(shí)在是一個玩弄敘述圈套的老手,一個小說中偏執(zhí)的方法論者。”[8]吳亮從敘事理論出發(fā),認(rèn)為:“馬原的重點(diǎn)始終是放在他的敘述上的,敘述是馬原故事中的主要行動者、推動者和策演者。”[8]吳亮的批評實(shí)踐以馬原小說的整體為研究對象,深入打撈馬原的寫作動機(jī)或?qū)懽饔^念是否有反抗傳統(tǒng)的自覺等問題。他從文本樣態(tài)入手,發(fā)現(xiàn)馬原小說雖然都刻畫了讓人難以忘懷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但它們只是片片斷斷,根本無法使用一種邏輯將它們串聯(lián)起來:“馬原的經(jīng)驗(yàn)方式是片斷性的、拼合的與互不相關(guān)的。他的許多小說都缺乏經(jīng)驗(yàn)在時間上的連貫性和在空間上的完整性。馬原的經(jīng)驗(yàn)非常忠實(shí)于它的日常原狀,馬原看起來并不刻意追究經(jīng)驗(yàn)背后的因果,而只是執(zhí)意顯示并組裝這些經(jīng)驗(yàn)。”[8]他非常形象地使用了“組裝”一詞,意在表明這些經(jīng)驗(yàn)的真實(shí)性只在局部,和傳統(tǒng)文本所追尋的“意義深度”、“本質(zhì)聯(lián)系”等理念基本無緣。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所有這些與馬原的認(rèn)識論有直接的聯(lián)系:“在經(jīng)驗(yàn)背后尋找因果是馬原所不愿意的,那么在故事背后尋找意義和象征也是馬原所懷疑的。馬原確實(shí)更關(guān)心他故事的形式,更關(guān)心他如何處理這個故事,而不是想通過這個故事讓人們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種抽象觀念。馬原的故事形態(tài)是含有自我炫耀特征的,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在開場里非常灑脫無拘地大談自己的動機(jī)和在開始敘述時碰到的困難以及對付的辦法。有時他還會中途停下小說中的時間,臨時插入一些題外話,以提醒人們不要在他的故事里陷得太深,別忘了是馬原在講故事”。[8]正是源于這種對文本形式的自覺,馬原才真正做到了對傳統(tǒng)敘事模式的間離。吳亮敏銳地感覺到馬原不僅僅在講故事,更主要的是在講故事:“它不僅要敘述故事的情節(jié),而且還要敘述此刻正在進(jìn)行的敘述,讓人意識到你現(xiàn)在讀的不單是一只故事,而是一只正在被敘述的故事,而且敘述過程本身也不斷地被另一種敘述議論著、反省著、評價著,這兩種敘述又融合為一體。”[8]沿著這一脈絡(luò),吳亮從“馬原”這個名字在他小說敘述中的地位、馬原的朋友們和角色們在其小說中的不同表現(xiàn)、以及馬原的經(jīng)驗(yàn)方式與文學(xué)觀念等方面入手,完成了對馬原小說“敘述圈套”的理論建構(gòu),稱他是“一個玩弄敘述圈套的老手,一個小說中的偏執(zhí)的方法論者”,一個“玩熟了智力魔方的小說家”[8]。
吳亮等人關(guān)于馬原小說的批評模式對后來的研究者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譬如,吳義勤認(rèn)為:“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們重新審視小說這個概念,他試圖泯滅小說形式和內(nèi)容間的區(qū)別,并正告我們小說的關(guān)鍵之處不在于它是寫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寫的,他第一次把如何敘述提到了一個小說本體的高度,敘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確的確認(rèn)。”[9]洪子誠這樣概括:“雖然殘雪和馬原幾乎同時出現(xiàn)和同樣引人注目,但只有馬原(而不包括殘雪)被批評家看作是‘先鋒小說’的起點(diǎn)。這種區(qū)分,立足于對‘文體’的純粹性的信仰。”[1](P337)陳思和這樣寫道:“馬原對傳統(tǒng)敘事的似真幻覺的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經(jīng)驗(yàn)的主觀性、片斷性與不可確定性,打破了任何一種宏大敘事重新整合個體經(jīng)驗(yàn)的可能性,這使得充滿個性與主觀性的現(xiàn)實(shí)凸顯了出來。先鋒小說正是這樣一種打破統(tǒng)一的世界圖像與文學(xué)圖像的努力。”[10](P295)其實(shí),無論是吳義勤話語中的“第一次”、“第一性”,還是洪子誠所說的“對‘文體’的純粹性的信仰”,抑或是陳思和所使用的“打破了任何一種宏大敘事”、“打破統(tǒng)一”等等,都可以在吳亮的批評話語中找到源頭。由此可見,馬原小說意義的生成與吳亮等人的文學(xué)批評密切相關(guān),可以說,正是在后者的積極參與下,前者才以先鋒的姿態(tài)進(jìn)入了文學(xué)史。
二、馬原小說敘事與作為內(nèi)在動力的文學(xué)期待
敘事學(xué)與電視媒介分析論文
一
廣播電視這種新媒介在19世紀(jì)末期就已有雛形,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jì)初葉。1895年俄國的科學(xué)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學(xué)家馬可尼兩位科學(xué)家經(jīng)過各自獨(dú)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無線電收發(fā)報機(jī),并先后成功地進(jìn)行了長距離通信試驗(yàn)。1906年加拿大人費(fèi)森登教授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無線電廣播實(shí)驗(yàn)室,并在圣誕節(jié)前夕通過無線電波首次進(jìn)行了聲音傳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廣播電臺誕生,這是由美國匹茲堡西屋電氣公司開辦的商業(yè)廣播電臺,呼號為KDKA。
電視的誕生被認(rèn)為是20世紀(jì)最偉大的發(fā)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發(fā)明的一臺叫作“電視望遠(yuǎn)鏡”的儀器申報給柏林皇家專利局,一年后專利獲得了批準(zhǔn)。1924年貝爾德采用兩個尼普可夫圓盤制作了一臺電視機(jī),首次在相距4英尺遠(yuǎn)的地方傳送了一個十字剪影畫,貝爾德本人則被人尊稱為電視之父。1924年俄裔美國科學(xué)家茲沃雷金的電子電視模型出現(xiàn)。1931年茲沃雷金又制造出攝像機(jī)顯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在倫敦郊外的亞歷山大宮,完全采用電子電視系統(tǒng)播出了一場頗具規(guī)模的歌舞節(jié)目,這一天被公認(rèn)為是世界電視的誕生日。1954年彩色電視在美國試播成功。1957年10月,蘇聯(lián)發(fā)射了“斯普特尼克1號”衛(wèi)星,這是人類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1962年6月19日,美國發(fā)射了“電星1號”,衛(wèi)星首次成功地轉(zhuǎn)播了電視信號。
無可否認(rèn),電視這種新媒介的出現(xiàn),對整個的社會思潮、文化研究、文學(xué)理論等都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傳播學(xué)者麥克盧漢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chǎn)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shù)),都要在我們的事務(wù)中引進(jìn)一種新的尺度。”(2)
二
敘事學(xué)誕生在“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的20世紀(jì),而20世紀(jì)對西方文學(xué)理論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了。“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thelinguisticturn)一詞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邏輯與實(shí)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認(rèn)為,“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發(fā)生的標(biāo)志是哲學(xué)家們共同采納了語言分析的方法。隨后,這一用語主要由理查德•羅蒂編輯的一部題為《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關(guān)于哲學(xué)方法的論文集》的書而被廣泛傳布。什么是“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呢?這是個非常復(fù)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很難說透。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有兩大特征,這兩大特征又是相互聯(lián)系的。之一,由歷時語言學(xué)研究轉(zhuǎn)向共時語言學(xué)研究。這是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索緒爾創(chuàng)立的,他認(rèn)為語言研究的著眼點(diǎn)應(yīng)為當(dāng)今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應(yīng)該研究語言成分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而不是去追蹤這些成分之間的歷史演變過程。之二,由語言學(xué)研究轉(zhuǎn)向話語學(xué)研究。什么是“語言”和“話語”呢?“語言”一般被看作是一個由一整套固定的語法規(guī)則構(gòu)成的完整體系,確定性、清晰性、規(guī)律性是語言的重要特征。“話語”則是能夠表達(dá)一個完整意義的言語,話語意義的確定不僅要取決于話語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語境所決定的。語境的構(gòu)成包括對話者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心理狀態(tài)、文化修養(yǎng)等因素。因此相對于語言來說,不確定性、模糊性和非規(guī)律性成為話語的一些主要特征。這種轉(zhuǎn)向分為兩個階段,前者可以說是語言學(xué)階段,后者是轉(zhuǎn)向話語學(xué)階段。如果說在本世紀(jì)前半期,西方文學(xué)批評得益于“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使得文學(xué)研究更加科學(xué)化,對文學(xué)對象的把握更加確定,那么到了本世紀(jì)的后半期,這種轉(zhuǎn)向由于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使得以結(jié)構(gòu)主義為代表的文學(xué)語言學(xué)批評所確立的研究對象的確定性,變得不確定起來,甚至連語言的表征都產(chǎn)生了危機(jī)。人類文明賴以依存的載體變得不可靠起來。當(dāng)代西方的文學(xué)批評,特別是以解構(gòu)主義為代表的批評陷入了自我解構(gòu)的困境。這便是文學(xué)話語學(xué)批評產(chǎn)生的開始。
初中語文散文教學(xué)與讀寫方法
【提要】散文是初中語文學(xué)習(xí)過程中最常見的一種文體,高效的散文教學(xué)能夠提高學(xué)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文化素養(yǎng)。然而在散文課堂上常常是教師在自說自演,這樣的散文教學(xué)是低效的,因此,在散文教學(xué)中,教師要學(xué)會創(chuàng)新,充分利用已有的教學(xué)設(shè)備來創(chuàng)造適宜的教學(xué)情境,將當(dāng)下流行的教學(xué)模式和散文教學(xué)的特點(diǎn)有機(jī)融合,運(yùn)用讀寫結(jié)合的方法,鼓勵學(xué)生進(jìn)行課外閱讀,學(xué)習(xí)其中的寫作方法,做到讀寫結(jié)合,以讀促寫,發(fā)展學(xué)生閱讀理解和創(chuàng)新寫作的能力,引導(dǎo)學(xué)生通過散文來表達(dá)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學(xué)生將由衷地?zé)釔壅Z文學(xué)習(xí)。
【關(guān)鍵詞】初中語文;散文教學(xué);讀寫結(jié)合
一、初中語文讀寫結(jié)合的散文教學(xué)方法
(一)讀寫結(jié)合在敘事散文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敘事散文注重對事物的敘述表達(dá),敘事情節(jié)不一定完整但一定要集中,它是按照人物和事情的發(fā)展順序,根據(jù)情節(jié)脈絡(luò)來進(jìn)行敘述的。在初中語文的學(xué)習(xí)過程中,敘事散文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敘事散文時應(yīng)將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和文章的內(nèi)容聯(lián)系起來,這樣有利于學(xué)生掌握文章的主旨,體會文中的思想情感。為了教會學(xué)生掌握敘事散文的寫作方法,一方面,教師在課堂上首先要引導(dǎo)學(xué)生對課文進(jìn)行深入精讀,領(lǐng)會文章的深層內(nèi)涵,對課文的框架結(jié)構(gòu)、行文脈絡(luò)、前因后果等進(jìn)行總結(jié)歸納,通過系統(tǒng)地梳理,學(xué)生便能深切體會作者的思想情感。另一方面,教師要將生活化的真實(shí)情景引入課堂中,讓學(xué)生在真實(shí)情景中進(jìn)行學(xué)習(xí),從中獲取靈感以便掌握多種多樣的表達(dá)方式,在寫作訓(xùn)練中,嘗試用自己擅長的方法從各種角度來表達(dá)作者想表達(dá)的情感,對自己喜歡的文章句子進(jìn)行仿寫。通常來說,敘事散文的前半部分是普通平常的敘述,為后文做鋪墊,通過某個特定的情節(jié)點(diǎn)的瞬間爆發(fā)來表達(dá)作者的思想情感,學(xué)生便能通過文章對作者情感的升華進(jìn)一步領(lǐng)悟,從而對自己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進(jìn)行反思,在反思中獲得成長。
(二)讀寫結(jié)合在抒情散文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
敘事理論與文化戰(zhàn)略研究論文
理論之道有兩條,一條簡捷,一條艱難。近年來許多人擁擠在簡捷的路上,把西方的特殊情境中式樣翻新的思潮術(shù)語饑不擇食地搬來,未經(jīng)選擇、消化、質(zhì)疑,更舍不得潛心去融匯貫通,便急急忙忙地以為這就是“觀念更新”,中國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在他們的手下,就像借得純陽祖師呂洞賓的“金指頭”一般似乎點(diǎn)石為金了。敘事理論方面的情形也如此。一批學(xué)者認(rèn)真地翻譯了英、法、美諸國的一些重要的敘事學(xué)著作,令人視野大開;但也出現(xiàn)一些對我國漫長的敘事文學(xué)傳統(tǒng)不加深究的學(xué)人,大寫理論批評或文學(xué)史論著作,進(jìn)行了半是探索性的,半是削足就履的工程。開通風(fēng)氣是非常必要的,除非對民族生存和發(fā)展不負(fù)責(zé)任的妄人,才會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把自己封閉起來。但是為了使開通的風(fēng)氣不致成為過眼煙云,有必要采取實(shí)事求是的態(tài)度,深入地研究中國敘事文學(xué)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研究其本質(zhì)特征,并以西方理論作為參照,進(jìn)行切切實(shí)實(shí)而又生機(jī)勃勃的中國與世界的對話。作為中國數(shù)千年非常輝煌而獨(dú)特的敘事遺產(chǎn)的繼承者,我們似乎不應(yīng)該滿足于給西方的敘事理論提供一點(diǎn)例證,而應(yīng)該走著一條哪怕是艱難的道路,也要境界獨(dú)辟,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理論體系,去豐富人類在此領(lǐng)域的智慧。
對于理論思維,我自知是一個非常笨拙的人,雖然想用艱苦來彌補(bǔ)笨拙,也不敢自信在艱難的理論探索的路上會有甚么漂亮的姿態(tài)。誰知道呢,也許我避免了壽陵余子學(xué)步于邯鄲的窘態(tài),逃過莊周先生“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的嘲笑,卻陷入了古希臘神話中西緒福斯在冥府服苦役,徒勞無功地推巨石上山,總是從山頂滾回原處的尷尬。八十年代初期,我在開始《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三卷的研究和撰述的時候,就曾經(jīng)向一位前輩學(xué)者表達(dá)了將來寫一部“中國小說學(xué)”的愿望。十年歲月于苦讀中過去了,我把生命消蝕在數(shù)以千計的現(xiàn)代文學(xué),主要是小說的閱讀和思考之中,當(dāng)這個項(xiàng)目完成之時,我果然向所在的研究院申請了小說學(xué)的重點(diǎn)項(xiàng)目。但是我總覺得心中無數(shù),要談中國的小說學(xué)如果只是把西方的小說觀念加上一些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實(shí)例感受,就編排章節(jié),湊合成書,到底于心不安。這就需要由現(xiàn)代文學(xué)進(jìn)入古典文學(xué)的領(lǐng)域,探索中國小說的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過程,探索中國小說的本來面目、本然意義以及它的深層結(jié)構(gòu)、形式特征。于是我又啟動了《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的項(xiàng)目,大量地閱讀從先秦到清代的小說,以及神話、歷史和戲曲一類文獻(xiàn),至今大概也讀有數(shù)百種了。然而從占至今紛紜復(fù)雜的敘事形態(tài)和形式,簡直把我的頭腦攪成一鍋粥,感性體驗(yàn)不可謂不多。卻到底難以理出一條差強(qiáng)人意的思路。我需要讓自己的頭腦沉靜下來,需要使自己的理論思維得到更廣闊的啟發(fā)和參照,于是1992年我開始了英國牛津訪學(xué)的旅程。
英國是近代文明的發(fā)源地,牛津的學(xué)院空氣也是博雅淵深的,脫離一些煩惱的雜務(wù),在此地思考著東方與西方,整理著自己的體驗(yàn)和思路,也許是再合適不過了。感謝牛津的劉陶陶博士和英國科學(xué)院給我這么一個機(jī)會。大英博物館的東方文化館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但這一次無暇顧及,因?yàn)槲倚枰獜娜齻€角度拓展學(xué)術(shù)視野和思路。一是在牛津、劍橋、倫敦大學(xué)亞非學(xué)院和愛丁堡大學(xué)進(jìn)行旅行講學(xué),講述中國神話的闡釋體系,講述中國文學(xué)與歷史,講述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英國文學(xué)的關(guān)系,通過這些講學(xué)和課堂討論,從若干宏觀的角度清理了對中國文學(xué),尤其是它的敘事體系的把握.并且摸索與西方學(xué)術(shù)界進(jìn)行對話的方式。二是在牛津和劍橋的幾家圖書館,披閱了一些西方敘事學(xué)的著作,從法國的羅蘭·巴爾特、杰拉,爾·日奈特、茲維坦·托多羅夫,到美國的維恩·布思、華萊士·馬丁,還讀了些英法人論述喬伊斯、勞倫斯和普魯斯特的文字,甚至包括一本英國人研究《易經(jīng)》的著作。這些閱讀無疑對我的中國敘事學(xué)的思考,提供了另一種眼光,另一片視野,相互參照、質(zhì)疑、駁難、汲取,激活了我的思緒,豐富了我的思維層面。三是作為一種補(bǔ)充,我也讀了王國維關(guān)于甲骨文、陳寅格關(guān)于唐史以及聞一多關(guān)于神話的一些著作,看一看前輩學(xué)術(shù)大師面對浩瀚典籍和西方思潮沖擊時的學(xué)術(shù)選擇,尤其是他們的治學(xué)境界。心有三弦兮,這三種從不同角度牽引出來的思維線索,使我長久沉浸在中國古今敘事文學(xué)典籍海洋中的腦袋,似乎在其合力的作用下浮出了水面。
我是帶著中國數(shù)以千計的古今敘事典籍的閱讀感受,去領(lǐng)略西方的敘事理論體系的。在這場東西方的對話之中,我感受到歡欣,也感受到迷惘。西方自六十年代以來,受結(jié)構(gòu)主義,尤其是索緒爾變歷時性為共時性的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的影響,以及受俄國形式主義,尤其是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tài)分析的啟迪,開始了敘事文本的內(nèi)在的、抽象的研究,建立了術(shù)語錯綜、見解互殊的敘事學(xué)體系。以至有人宣稱,近二十年西方文藝學(xué)的值得引人注目的進(jìn)展,均與敘事學(xué)有關(guān)。他們打破了神話、民間故事、史詩、羅曼司、小說、新聞記事、電影等具體的文體界限,把敘事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現(xiàn)象,卻又摒除制約著具體敘事行為的社會、歷史、心理因素,把敘事作品的文本視為獨(dú)立自足的封閉體系,探究著它的敘事者、所敘故事和敘事行為方式,力圖抽象出能夠籠罩各種敘事文體的模式。這種強(qiáng)調(diào)文本內(nèi)在分析,以及溝通文體界限的研究角度,都是頗具創(chuàng)造性的。它對敘事層次、視角、時間諸方面的研究,確實(shí)有不少令人佩服的建樹。但以完全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為代價去研究一種人類精神現(xiàn)象,又使這種學(xué)說陷入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尷尬處境,難以經(jīng)受來自社會歷史和文化哲學(xué)的置疑。西方某些理論思維追求競爭效果和片面深刻性,具有展示新的研究視野的沖擊力,卻缺乏使對立物在辯證思維中統(tǒng)一起來的學(xué)術(shù)性格,在這一學(xué)說的探討中也表現(xiàn)得相當(dāng)淋漓盡致了。
學(xué)術(shù)思維要獲得創(chuàng)造性的建樹,不是把現(xiàn)成的理論模式搬來注解一番就可完事,它往往需要以獨(dú)特的知識儲備和文化視野,對某種理論體系于似乎不可懷疑中產(chǎn)生懷疑。當(dāng)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學(xué)府的名教授對中國人引為驕傲的曹雪芹、魯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多少有資格對西方敘事學(xué)的“世界性”產(chǎn)生懷疑。在西方學(xué)者較少涉足的領(lǐng)域,中國學(xué)者有必要作出發(fā)現(xiàn),這應(yīng)該是人類發(fā)展的共同主題。我不敢說自己具有這樣的能力,但是中西文化明顯存在的反差,使我時時以中國自古及今的敘事經(jīng)驗(yàn),對西方敘事學(xué)進(jìn)行比較性的閱讀。發(fā)現(xiàn)東西方相通之處,自然會心一笑;發(fā)現(xiàn)東西方異質(zhì)之處,豈不也是智慧的愉快?比如西方某些敘事學(xué)學(xué)者是從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的角度進(jìn)入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的,他們在進(jìn)行敘事作品分析的時候常常套用語言學(xué)術(shù)語,諸如敘事語法、時態(tài)、語態(tài)、語式之類。但是所有這些,對于中國人都是“洋腔洋調(diào)”,完全是建立在西方語言的認(rèn)識基礎(chǔ)上的.中國語言的時態(tài)是非原生性的,它使用的是某種意義上的“永遠(yuǎn)現(xiàn)在時”,孔夫子如何說,以及今人如何說,這個“說”字沒有什么區(qū)別,區(qū)別是在附加詞上。即便讀《紅樓夢》吧,這種沒有時態(tài)間隔的語言形式,使讀者不必時時想到賈寶玉、林黛玉是古人,而在一種臨場的境界中和書中人物哀樂與共。進(jìn)而言之,中國語言表達(dá)時間采取“年-月-日、”的順序,有別于西方大語種所采取的“日-月-年”的順序,這一點(diǎn)習(xí)以為常,西方敘事學(xué)學(xué)者也沒有使用比較的方法揭示其中的奧秘。實(shí)際上時間表達(dá)順序反映著兩種不同的時間觀,一者是整體性的,一者是分析性的,而且它們以集體潛意識的形態(tài)深刻地影響了東西方敘事作品結(jié)構(gòu)方式。
如果不嫌牽強(qiáng)附會的話,在明清之際,也就是公元十七世紀(jì),我國以金圣嘆為代表的一批小說評點(diǎn)家即進(jìn)行過溝通敘事文體之界限,細(xì)讀敘事文本的工作,取得了影響二、三百年的小說版本和閱讀風(fēng)尚的成績。比金圣嘆早一百年,明嘉靖年間的李開先在《詞謔》中說:“《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有一事而二十冊者。倘以奸盜詐偽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學(xué)之妙者也。”把《史記》這樣的史書和《水滸傳》這樣的小說溝通起來,在金圣嘆的“六才子書系統(tǒng)”中體現(xiàn)得更為自覺和充分,他甚至評點(diǎn)了《西廂記》,把形式分析的細(xì)讀法應(yīng)用到戲劇作品之中。這種溝通文體的“擬史批評”影響巨大,連毛宗崗評點(diǎn)《三國志演義》也說:“《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張竹坡也說:“《金瓶梅》是一部《史記》。”中國文史相通的傳統(tǒng),在明清之際的評點(diǎn)家手中得到了另一形式的回歸。并不是說,這些評點(diǎn)家已經(jīng)具有現(xiàn)代的敘事學(xué)意識,他們的感覺還處于三百年前那個時代雖然富有才華,卻到底尚屬直觀的狀態(tài)。然而他們溝通文史和細(xì)讀文本所表現(xiàn)出來的才華與智慧,是值得重視的,某些論述甚至包含現(xiàn)代敘事理論思維的萌芽。比如金圣嘆對《水滸傳》的某些修改,體現(xiàn)了他對敘事視角的朦朧猜測和敏感。該書第十二回寫楊志北京比武,略寫比武二雄,轉(zhuǎn)而描寫將臺、看臺和陣面上觀戰(zhàn)的軍士的反應(yīng)。金圣嘆有眉批道:“一段寫滿教場眼睛都在兩人身上,卻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滿教場人身上。作者眼睛在滿教場人身上,遂使讀者眼睛不覺在兩人身上。真是自有筆墨未有此文也。此段須知在史公《項(xiàng)羽紀(jì)》諸侯皆從壁上觀一句化出來。”其間對作品的視角和聚焦謀略的評點(diǎn),是相當(dāng)有靈氣的。引發(fā)我更深一層的聯(lián)想的,是三百年前的評點(diǎn)家從史學(xué)文化的角度切入敘事分析,迥異于西方敘事從他們最敏感的語言學(xué)的角度切入敘事研究,這種差異是否隱含著兩種文化思維模式的差異呢?史學(xué)是中國傳統(tǒng)的優(yōu)勢文體,語言學(xué)是西方結(jié)構(gòu)主義思潮中的優(yōu)勢領(lǐng)域,從優(yōu)勢文體向其余文體滲透、這是理所必然。但是形成這種優(yōu)勢局面的,難道和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jīng)]有關(guān)系嗎?
語圖關(guān)系視域中的文學(xué)論文
一、以“語-圖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優(yōu)化文論教學(xué)內(nèi)容
文學(xué)理論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不斷發(fā)展。在傳統(tǒng)的文學(xué)理論教學(xué)中,我們一直堅(jiān)持“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文學(xué)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xué)本質(zhì)、作家創(chuàng)作、文本構(gòu)成等內(nèi)容的講解,都是建立在對語言理解的基礎(chǔ)上,以此來理解文學(xué)所反映和表達(dá)的世界,而對圖像觀念基本上不涉及。當(dāng)文學(xué)遭遇到“讀圖時代”,文學(xué)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語言寫什么以及如何寫,而是關(guān)于語言和圖像之間關(guān)系的問題,這是一個緊迫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面對影像的沖擊和圍困,如果我們還固守象牙塔式的文學(xué)理論教學(xué)理念,那么就無法面對和回答文學(xué)所面臨的鮮活的現(xiàn)實(shí)問題,致使教學(xué)內(nèi)容顯得陳舊和空洞,無法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基于此,在文論教學(xué)中,應(yīng)該把文學(xué)理論所面對的現(xiàn)實(shí)問題作為一個核心理念介紹給學(xué)生,引導(dǎo)學(xué)生掌握文學(xué)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規(guī)律,開拓學(xué)生的視野,不斷激發(fā)學(xué)生的審美興趣。筆者以為,這一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文學(xué)與圖像之間關(guān)系”基礎(chǔ)之上的文論觀,也就是通過探究和闡發(fā)文學(xué)與圖像之間的分分合合、同源共存、對立統(tǒng)一的復(fù)雜關(guān)系,著重培養(yǎng)中文系學(xué)生著眼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傳承文論傳統(tǒng)、面向文學(xué)未來所具有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實(shí)踐創(chuàng)新能力。要實(shí)現(xiàn)這一教學(xué)理念,就要幫助學(xué)生在文學(xué)領(lǐng)域里自覺運(yùn)用語—圖關(guān)系及其相關(guān)理論去把握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基本范疇,了解文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歷史和研究現(xiàn)狀,培養(yǎng)科學(xué)的文藝觀念。在教學(xué)過程中,教師應(yīng)該充分發(fā)揮主動性,充當(dāng)引導(dǎo)者、設(shè)計者和組織者,對課程教學(xué)內(nèi)容進(jìn)行有創(chuàng)意的優(yōu)化和探索。教師應(yīng)該引導(dǎo)學(xué)生多了解中國古代詩畫關(guān)系理論及其豐富的藝術(shù)實(shí)踐,比如了解題畫詩和小說、戲曲等敘事文的插圖。
多閱讀西方現(xiàn)代文論經(jīng)典中涉及語-圖關(guān)系的文獻(xiàn),如萊辛的《拉奧孔》和阿恩海姆的《視覺思維》等。利用多媒體教學(xué)手段向?qū)W生介紹一些當(dāng)代“語-圖”互文的實(shí)踐作品,使學(xué)生從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維度多層次了解文學(xué)與圖像之間的動態(tài)關(guān)系。在此基礎(chǔ)上,再回到“文學(xué)是什么”和“文學(xué)與語言的關(guān)系”等問題本身時,學(xué)生將更加深入地體會“文學(xué)是語言的藝術(shù)”,在更高的意義上理解“文學(xué)與圖像的關(guān)系”。教師需要設(shè)計語言與圖像之間關(guān)系的具體問題來組織課堂教學(xué)。比如,語言和圖像各自的特點(diǎn)是什么?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互相模仿?在傳播上有什么不同效果?各自給我們帶來何種不同的審美效果?可通過截取一些代表性的藝術(shù)作品回答這些問題,如金庸作品的影視改編,莫言作品的電影改編等,還有像可口可樂、優(yōu)樂美等經(jīng)典廣告案例。這些都是學(xué)生耳熟能詳?shù)淖髌罚菀踪N近學(xué)生的知識經(jīng)驗(yàn),帶給學(xué)生新鮮活潑的學(xué)習(xí)樂趣。教師應(yīng)該組織學(xué)生對“文學(xué)與圖像”關(guān)系進(jìn)行討論。比如在講授“意境”時,提供給學(xué)生一些詩畫一體方面的材料,組織學(xué)生開展一場課堂討論,學(xué)生可以各抒己見,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談?wù)撛姰嬛刑N(yùn)含的抒情和表意成分,形成自己對意境的理解。課后再組織學(xué)生進(jìn)行更深入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最終根據(jù)自己的選題形成一篇小論文,這樣可以比較系統(tǒng)地掌握這一問題的來龍去脈。一方面,避免單純地講解中國古典詩歌來解釋意境概念的教學(xué)方法,教師有充分發(fā)揮自身才能的空間;另一方面,讓學(xué)生跳出教材所限定的知識內(nèi)容,在更加寬泛和自由的知識視野中學(xué)會思考問題,進(jìn)而達(dá)到課堂教學(xué)的目標(biāo)。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種建立在文學(xué)與圖像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文論觀具有強(qiáng)烈的包容性和涵蓋性,能夠整合傳統(tǒng)文學(xué)理論教學(xué)內(nèi)容之優(yōu)點(diǎn),著眼當(dāng)下文學(xué)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讓學(xué)生真正理解和發(fā)現(xiàn)文學(xué)需要理論做些什么。
二、以語-圖關(guān)系問題為主線開展研究型教學(xué)
研究型教學(xué)是創(chuàng)新教育理論指導(dǎo)下的教學(xué)范式,它在充分利用以往教學(xué)模式優(yōu)點(diǎn)的前提下,通過對重大現(xiàn)實(shí)問題的研究,使學(xué)生掌握相關(guān)知識,提升學(xué)生利用理論解決實(shí)際問題的能力。以語-圖關(guān)系問題為主線展開研究型教學(xué),在于通過課堂教學(xué)過程引導(dǎo)學(xué)生創(chuàng)造性地運(yùn)用知識和能力,在對問題的研討中,不斷積累知識、培養(yǎng)能力和鍛煉思維,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目標(biāo)的創(chuàng)意設(shè)計。以問題為導(dǎo)向,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目標(biāo)的多元性。問題是一切研究活動的出發(fā)點(diǎn)。以往的課堂教學(xué)經(jīng)常把問題或提問當(dāng)做檢查學(xué)生是否掌握了所講的知識的手段,起到傳授知識的作用。即使引導(dǎo)學(xué)生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也是以理論預(yù)設(shè)為前提。比如以往講授的“反映論”、“審美反映論”、“文學(xué)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系等內(nèi)容,以本質(zhì)先行的授課思路,圍繞原典或一些抽象概念來勾畫文學(xué)圖景,而忽視鮮活的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及其發(fā)展面臨的困境。研究型教學(xué)則是立足于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問題,教師指導(dǎo)學(xué)生按照興趣愛好進(jìn)行選題。比如,在講解文學(xué)形象時,可以選取《紅樓夢》的電視劇改編為專題展開討論。在閱讀和觀看經(jīng)典片段,輔助閱讀一些代表性學(xué)術(shù)論文的基礎(chǔ)上,教師進(jìn)行專題背景的知識性輔導(dǎo),圍繞寶玉、黛玉、寶釵形象在小說文本和電視文本中表現(xiàn)的異同,以及語-圖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啟發(fā)學(xué)生對兩種不同媒介進(jìn)行思考,進(jìn)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形象的塑造。這樣一來,學(xué)生在研討的過程中掌握了文學(xué)形象的相關(guān)重要知識;在開展專題研究的實(shí)踐過程中,思維、口頭表達(dá)、分析、綜合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綜合素質(zhì)得到進(jìn)一步提高。以雙向互動為機(jī)制,確立師生對話關(guān)系。在研究型教學(xué)中,教師是引路人,是介紹知識的向?qū)В瑢W(xué)生是學(xué)習(xí)者和研究者。由于當(dāng)代大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和知識經(jīng)驗(yàn)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和信息傳播平臺的基礎(chǔ)上,他們對視覺文化和時尚文化比較敏感和好奇,可以通過網(wǎng)絡(luò)途徑獲取大量的信息和資源,來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因此,學(xué)生在一些教學(xué)內(nèi)容上擁有充分的話語權(quán)和表達(dá)權(quán)。比如在敘事的專題討論上,針對文本敘事和圖像敘事等教學(xué)內(nèi)容,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研究能力便得到激發(fā)。
在選題上,以小說《羅生門》與電影《羅生門》的敘事比較為案例,教師和學(xué)生進(jìn)行平等的對話,深入理解兩種不同形式敘事的內(nèi)涵、策略和特征。與單純講解加上例子來解釋和佐證的教學(xué)方式相比,這種互動式的教學(xué),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知識的獲得和能力的提升,只有通過師生的共同研討才能實(shí)現(xiàn)。在此基礎(chǔ)上,以學(xué)生的學(xué)為中心,教師圍繞文學(xué)理論的教學(xué)目標(biāo),貼近學(xué)生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結(jié)合學(xué)生的現(xiàn)實(shí)需要,運(yùn)用多媒體教學(xué)技術(shù)手段,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問題意識。同時,引導(dǎo)和鼓勵學(xué)生從文學(xué)和文化的現(xiàn)實(shí)問題出發(fā),在質(zhì)疑和研討中,幫助學(xué)生進(jìn)入科學(xué)的思維狀態(tài),進(jìn)而掌握文學(xué)理論的知識結(jié)構(gòu),以應(yīng)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不同需要。在研究型教學(xué)過程中,實(shí)現(xiàn)以教為中心到以學(xué)為中心的轉(zhuǎn)變,著力培養(yǎng)學(xué)生思維能力和綜合素質(zhì),絕不意味著可以削弱教師在教學(xué)中的作用,相反,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需要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把握選題,一方面力求研討有明確的指向,能和一定的教學(xué)內(nèi)容結(jié)合在一起,為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目的服務(wù);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相對獨(dú)立性,讓學(xué)生貼近有學(xué)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問題,從中獲得具體的體驗(yàn),實(shí)現(xiàn)對問題的完整把握。在研討的過程中,教師對學(xué)生研究的結(jié)果進(jìn)行點(diǎn)評,從知識到能力,從方法到思維,進(jìn)行綜合指導(dǎo)和評價。介紹和補(bǔ)充相關(guān)的信息,指導(dǎo)學(xué)生對專題進(jìn)行延伸閱讀和深入研究,幫助實(shí)現(xiàn)知識的遷移,從而保證研討活動的順利進(jìn)行和取得實(shí)效,多元而完整地實(shí)現(xiàn)教學(xué)課堂目標(biāo)。
老舍與茅盾文學(xué)觀比較研究論文
論文關(guān)鍵詞:文學(xué)觀;命運(yùn);敘事;指導(dǎo)人生;國民性
論文摘要:老舍和茅盾同為現(xiàn)代“為人生派”作家,而其作品的表現(xiàn)內(nèi)容有相當(dāng)?shù)牟町悾疚恼J(rèn)為是文學(xué)觀的差異造成了作品內(nèi)容的不同,并于表現(xiàn)時代命運(yùn)與個人命運(yùn)、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指導(dǎo)人生和改造國民性三方面比較了兩者的文學(xué)觀,以此來明確二者在文學(xué)史中的參照。
茅盾與老舍俱為現(xiàn)代文壇上的杰出作家,二者又都把目光投注向當(dāng)時的國民啟蒙,表現(xiàn)二十世紀(jì)的城市社會、人物和歷史。他們同樣高舉著文學(xué)“為人生”的大旗,都曾經(jīng)歷過五四思想的洗禮,并具有扎實(shí)的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底子,又在中西思潮交會和激蕩中對西方文化有著各自獨(dú)特而深刻的了解,然而,因?yàn)槲膶W(xué)觀的差異,二者的作品煥發(fā)出迥然不同的光采。
本文試圖從二者作品的文本出發(fā),由表現(xiàn)時代命運(yùn)與個人命運(yùn)、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指導(dǎo)人生和改造國民性三方面來比較兩者文學(xué)觀的不同。
一、時代命運(yùn)與個人命運(yùn)
茅盾對個體命運(yùn)的表現(xiàn)常常投射出在當(dāng)時時代背景下的激化的社會矛盾,這種矛盾的發(fā)展往往關(guān)系著時代國家的命運(yùn)。比如《子夜》中民族工業(yè)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表現(xiàn)出民族資本主義的獨(dú)立性以及他們與帝國主義的——買辦金融資本家的矛盾,吳蓀甫一次次的抗?fàn)幎际敲褡遒Y本主義的掙扎,一次次的失敗也就說明了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決定了在當(dāng)時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時代的命運(yùn)把握在更具有先進(jìn)性的階級手中。
熱門標(biāo)簽
文學(xué)評論 文學(xué)鑒賞 文學(xué)批評 文學(xué)性 文學(xué)賞析 文學(xué)論文 文學(xué)評論論文 文學(xué)論文論文 文學(xué)創(chuàng)作 文學(xué)賞析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