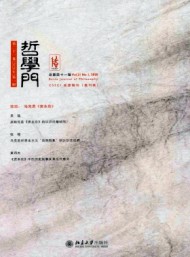哲學史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4 19:15:46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哲學史論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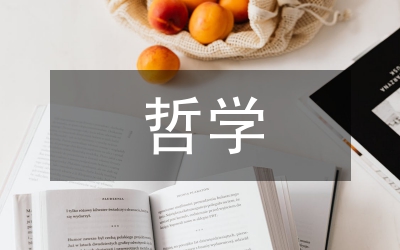
研究范例哲學論文
關鍵字:中國哲學史研究范例論析論文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哲學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哲學史研究范例管理論文
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哲學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我國哲學史研究范例分析論文
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哲學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中國哲學史研究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中國哲學史的撰寫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有導向性作用,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是與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現有中國哲學史論述的種種不足直接導致了目前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因此,必須重寫中國哲學史。重寫中國哲學史必須從哲學的一般意義和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積極開發中國哲學特有的問題域,闡明它與時代的互動關系,特別要突出中國哲學的根本特征——實踐哲學的意義。就中國傳統哲學特征而言,實踐哲學遠比心性之學更具解釋力和現實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觸使得原教旨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利用西方哲學的某些資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在使用西方哲學觀念解釋中國哲學時仍要謹慎,概念不是純粹的形式。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哲學自己的概念體系是未來中國哲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內在批判和釋義學闡發則是新的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方法論原則。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內在批判自主性
一
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不滿的加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成了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話題,甚至被某些刊物評為2003年十大熱門學術話題。對研究現狀的不滿導致對其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哲學學科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于,與文學、史學等學科不同,中國人是在接觸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學”的。
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本沒有“哲學”一詞。漢語“哲學”一詞是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發明,他在他的《百一新論》(1874)中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一詞,但同時特別聲明:他用它來與東方的儒學相區別。直到1902年中國人才在《新民叢報》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將“哲學”用于中國傳統思想。用是用了,卻并未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可稱為“哲學”的東西嗎?
在有些西方人看來,答案是否定的。胡塞爾在他的維也納演講中就否認中國有哲學。伽達默爾也認為遠東文化中那謎一樣的沉思與智慧與西方哲學不是一回事。理由是哲學是希臘人創造的一種非常特殊的東西,有其特殊的形態、內容、概念和問題。中國人自己一開始也這么看。王國維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之一,也是那個時代西方哲學造詣最深的中國人之一。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中,根據自己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檢討中國傳統,發現在中國“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之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1]雖然王國維在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國傳統有哲學,但從整篇文章的上下文來細細玩味,不難發現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國并無嚴格意義(即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我國哲學史研究論文
[提要]史的撰寫從1開始就對中國哲學的有導向性作用,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是與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問題聯系在1起的。現有中國哲學史論述的種種不足直接導致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因此,必須重寫中國哲學史。重寫中國哲學史必須從哲學的1般意義和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出發,積極開發中國哲學特有的問題域,闡明它與的互動關系,特別要突出中國哲學的根本特征——實踐哲學的意義。就中國傳統哲學特征而言,實踐哲學遠比心性之學更具解釋力和現實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觸使得原教旨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利用西方哲學的某些資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在使用西方哲學觀念解釋中國哲學時仍要謹慎,概念不是純粹的形式。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哲學自己的概念體系是未來中國哲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內在批判和釋義學闡發則是新的中國哲學史的基本論原則。
[關鍵詞]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內在批判自主性
1
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哲學研究現狀不滿的加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成了研究者持續關注的話題,甚至被某些刊物評為2003年10大熱門學術話題。對研究現狀的不滿導致對其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本身就說明了中國哲學學科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于,與文學、史學等學科不同,中國人是在接觸了西方文化后,才知道有“哲學”的。
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本沒有“哲學”1詞。漢語“哲學”1詞是日本哲學家西周的發明,他在他的《百1新論》(1874)中首先用“哲學”來翻譯philosophy1詞,但同時特別聲明:他用它來與東方的儒學相區別。直到1902年中國人才在《新民叢報》的1篇文章中第1次將“哲學”用于中國傳統思想。用是用了,卻并未解決1個真正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可稱為“哲學”的東西嗎?
在有些西方人看來,答案是否定的。胡塞爾在他的維也納演講中就否認中國有哲學。伽達默爾也認為遠東文化中那謎1樣的沉思與智慧與西方哲學不是1回事。理由是哲學是希臘人創造的1種非常特殊的東西,有其特殊的形態、內容、概念和問題。中國人自己1開始也這么看。王國維是中國最早研究西方哲學的人之1,也是那個時代西方哲學造詣最深的中國人之1。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文中,根據自己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檢討中國傳統,發現在中國“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之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1]雖然王國維在這里并未直接否定中國傳統有哲學,但從整篇文章的上下文來細細玩味,不難發現他至少是在暗示中國并無嚴格意義(即西方意義上)的哲學。
我國史學研究論文
20世紀的中國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界乃至政治界,胡適對其均有重要影響。他既是一位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同時也是一位史學家,而且是在20世紀中國史學轉型中不應被忽視的、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史學大家。
胡適(1891—1962年),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祖輩經商,父親是清朝官吏。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新式學堂求學。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后轉入文科。畢業后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的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1917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同年啟程回國,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后又曾擔任過中國公學校長、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并于1938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國大使。1949年4月起寓居美國。1958年到臺灣中央研究院任院長。1962年2月在臺灣去世。
一、開史學新風氣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文化領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學術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階段,胡適正式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以首倡文學革命而名聲大振,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專制,活躍和發展學術文化,在五四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科學精神和理性觀念成為人們所遵奉的信條。推翻偶像,拒絕迷信,摒棄成說,凡事都要問一聲“為什么”,用科學方法重新估價中國的史學遺產,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重新看待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在新思潮影響下的五四時期中國史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胡適開風氣之先,出版了根據他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擴充而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內容,真偽難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為信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的中國古史的內容采取了拒絕的態度。《中國哲學史大綱》于1919年2月出版。這部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框架。胡適此舉產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顧頡剛談到他的感受是:“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胡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⑴馮友蘭說:“這對于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⑵
哲學與政治之辯證:賀麟的經驗
關于學術與政治,韋伯在1919年的講演中斷定:“這是兩個完全異質的問題”,“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有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韋伯:《學術與政治》,三聯書店,1998年,第38頁)學術獨立于政治不但是韋伯的結論也是普世性的現代訴求,五四以來的中國學術之具有現代性,正基于其內在的自由品格。但千方百計爭取獨立的中國學術,遭遇的卻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政治的纏繞和權力拘束為所有學者難以擺脫,其關系之復雜、過程之曲折,即使細讀韋伯也無法透徹理解。
1986年,著名哲學史家賀麟先生將1947年完成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修改后以《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為名重新出版。新序有言:“全書在不影響原書的體系及主要論點的前提下,作了適當的修改和補充。”(《新版序》)揭呈此一修改所關涉的諸多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學術與政治在現代中國所表現出來的關系形式。
一哲學的政治化
經過50年代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和學術思想批判等“洗腦”、“交心”的運動之后,賀麟一代的學者紛紛修改舊作以適應新的環境。馮友蘭修改《中國哲學史》,劉大杰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等都是著例。賀的《中國當代哲學》之所以要等到80年代才修改再版,原因正如他1988年為《文化與人生》的新版寫序時說的:“我記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對于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意義,駁斥傅銅、胡適、馮友蘭等人反對此說的論點,及發揮知行合一說的理論,也還有其新穎之處。不過嚴重的錯誤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所謂‘力行哲學’。”(《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新版序言)除了吹捧,此書還包含對辯證唯物論的根本性批判,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在此前的30多年中連修改的基礎也不具備。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種新的政治標準代替舊的政治標準,新舊兩版實際上都具有政治化寫作的性質。
賀在新版序中交代說:“只有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剖析,因為涉及政治問題,且系基于學生的筆記寫成,由于我當時對于辯證唯物主義毫無所知,所以這次作了較大的修改。”就“物質在于意識之先”而言,舊版認為這是科學常識而非哲學,“哲學要問在理論上邏輯上什么東西最根本最重要:什么東西是核心,是命脈?”新版在“物質在于意識之先”之前加上“有人誤以為”數語以為限制;在指出哲學與科學的不同之后,加上“這并不能說是辯證唯物論”一句,表明所批評的并非真正的辯證唯物論,但辯證唯物論究竟是什么,新版卻沒有交代。
就辯證法來說,舊版首先強調,辯證法產生于哲學家研究人類情感生活后發現的通理,“只有應用到精神生活內心生活上去,才見其生動活潑”。賀本以此批評唯物辯證法,新版卻加上“各國新黑格爾派大都認為”一句,表明這不是自己的觀點。其次,辯證法不能顛倒:“馬克思并沒有把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過來。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讀黑格爾柏拉圖的著作。讀馬克思的著作對于辯證法的學習,并無多大幫助。”新版刪去了最后一句,減輕批評的力度。第三,關于辯證法的三大規律,舊版認為對“對立統一”的原則,“辯證唯物論者從不曾好好發揮”,新版式改為“辯證唯物論者不見得有更多更好的發揮”,語氣稍緩;有關“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新版沒有改動;關于質量互轉規律,舊版認為質量關系“既無所謂互轉,其本身和辯證法也不相干”,新版改為“它們的對立,不是僵死的,也有互相轉化,自身辯證發展的過程。”有改有不改,新版對辯證法的評論前后矛盾。
馮友蘭釋古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論文系統考察了馮友蘭“釋古”的理論和實踐以及與王國維“證古”的關系,認為馮友蘭的“釋古”與“信古”、“疑古”并非同類的問題,不能與“信古”、“疑古”相提并論;馮友蘭的“釋古”較胡適的“疑古”疑得有過之而無不及,現行的中國哲學史排隊的錯誤,主要是由馮友蘭系統完成的;馮友蘭的“釋古”與王國維的“證古”對待“歷史舊說”的態度基本不同,王國維是在基本肯定“歷史舊說”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對“歷史舊說”進行補充和修正,而馮友蘭“釋古”的基本傾向還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馮友蘭“釋古”說的意義。
【關鍵詞】馮友蘭釋古疑古證古
引言
針對二三十年代學界流行的疑古思潮,馮友蘭先生從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闡述了他的“釋古”觀[1]。其要點是:一、將中國當時研究古史的觀點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釋古為研究中國古史“態度”“進步”的“三個階段”。三、認為釋古“介于信古與疑古之間”,“釋古便是”信古與疑古“這兩種態度的折衷”[2],具體說,“‘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傳說”,“須知歷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3]。四、認為“‘信古’、‘疑古’、‘釋古’三種趨勢,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辯證法,即‘信古’為‘正’,‘疑古’為‘反’,‘釋古’為‘合’”[4]。
馮氏之說,在當時學界影響頗大。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概述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中國史學研究的新進展,就引證了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的三分說,并對其釋古的理論和實踐發表了自己的評論[5]。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基本接受了“釋古”說,認為“歷史家之任務,本在研究具體之歷史,既得真實之史料,自當據科學史觀或整個歷史過程學說以為概括之解釋,此釋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終之以‘釋古’,然后史家之能事盡矣”[6]。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史學界和哲學界在反思疑古學說和評價馮友蘭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時,都注意到并較高地評價了馮友蘭的釋古說[7]。這些評價,第一,認同了馮友蘭的“釋古”理論,認為馮友蘭提出的“釋古”說是對“信古”說和“疑古”說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時代”的濫觴;第二,肯定了馮友蘭的“釋古”實踐,認為馮友蘭對中國哲學史史料的處理,是其“釋古”方法運用的典范,代表了“合的階段”;第三,將馮友蘭的“釋古”說上溯至王國維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其他導師,甚至認定“釋古”是清華學派治學的特色和傳統。
我國哲學分析研究論文
牟宗三提出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具有雙重的背景和意義。一方面是相對于中國二千多年的哲學傳統來說的,另一方面則是與近現代西方哲學相比較,以近現代西方哲學為參照而說的。相對于中國哲學的傳統來說,中國哲學必須哲學地反省自身和哲學地重建,才會有進一步地發展;相對于近現代西方哲學來說,中國哲學必須哲學地建立起來,才能走向世界,與西方哲學進行對話,有未來的拓展。因此,哲學地重建中國哲學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偉大變革。牟宗三明確地認識到哲學地重建中國哲學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重大課題及其重大意義,他哲學地反省了中國哲學,以及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界,自覺地擔負起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的時代使命──牟視之為哲學家的“天職”。(1)
一、哲學地反省中國哲學
牟宗三在他八十歲生日的宴慶上說:“從大學讀書以來,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國之文化生命,以重開中國哲學之途徑。’”(2)對牟宗三來說,反省中國的文化生命主要就是反省中國哲學。反省中國哲學,必須以承認中國有哲學為前提。在這一前提下,必須回答“什么是中國哲學”,必須弄清中國哲學的問題,必須分清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特質、重心及缺陷的區別,為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奠定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哲學在未來的拓展尋找合理的根據與豐富的資源,因此必須重寫中國哲學史。牟宗三對中國哲學的哲學反省,正是建立在他對中國哲學的深入透辟地研究的基礎上,也就是他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基礎上的。從1953年開始,牟宗三先后出版《荀學大略》(民國42/1953年,后編入《名家與荀子》),《王陽明致良知教》(民國43/1954年),《魏晉玄學》(民國51/1962年),《中國哲學的特質》(民國52/1963年),《心體與性體》(三冊,民國57-58/1968-69年)和《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心體與性體》第4冊,民國68/1979年),《佛性與般若》(上下冊,民國66/1977年)、《名家與荀子》(民國68/1979年),《中國哲學十九講》(民國72/1983年),以及發表相關的論文和講演錄多篇。其中,尤以《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上下冊)、《心體與性體》(共四冊)、《中國哲學的特質》、《中國哲學十九講》五書為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3)在五書中,學界對前三大部著作有極高的評價,(4)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但是即使對牟宗三的觀點持嚴歷批判態度以及不喜歡他的人,如像羅光、林毓生、方東美等人(5)也肯定了它們的學術價值。在三大著作中,又尤以《心體與性體》的影響為最大,被認為是“前無古人的”“劃時代的偉構”(6),“里程碑”式的巨著。(7)方克立先生指出,這部著作(包括《從陸象到劉蕺山》)“對宋明理學諸大家的分析研究確實是比較細密深邃,相對而言,唐君毅專門論述宋明儒學思想之發展的《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在觀念之清晰和理論之深度上都顯然要遜色一些。”(8)在這些著作中,牟先生本人最得意的卻是《佛性與般若》,也是一部“令人為之嘆為觀止”的偉構(9)。殊為特別的是,在五書中,唯一只有《中國哲學十九講》是一部以哲學問題為對象的通論性著作,雖然是“講錄”,但卻在牟氏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顯得十分重要。至于《中國哲學的特質》,則主要是從儒家思想與西方哲學的比較中,來闡示中國哲學的特質,揭示了中國儒學“即內在即超越”與“即宗教即哲學”的兩個基本特征,奠定了牟氏的“道德的形上學”──“無執的存有論”的內在的兩大基本原則,在牟氏的哲學中仍然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這本書已譯成兩種外文(韓文、法文)出版,也說明了它的重要價值。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哲學史是胡適、馮友蘭獨領風騷的時代,那么從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后三十年開始,在中國哲學史這個領域中,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家以外來看,能夠扮演主角,獨領風騷的人物當首推牟宗三和唐君毅二先生。劉述先先生說:牟宗三先生“把傳統里講得糊里糊涂的東西賦予概念上的確定性與清晰性”,“他是把中國哲學由主觀體驗轉變成為客觀學問的關鍵性人物”。(10)郭齊勇先生也指出:牟先生“創造性地提揚、體認、檢討、轉換了中國哲學傳統的基本精神、核心價值和主要問題”,“他深化并豐富了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的內涵,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牌。”(11)這是從兩個角度對牟宗三的中國哲學史的學術貢獻所作出的高度評價,當不是溢美之辭。
牟宗三在哲學地反省中國哲學,與在進行中西哲學的比較與會通的歷程中,樹立了他富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觀,他分別為哲學下過不同的定義。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中,他明確地為哲學下的定義為:
什么是哲學?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12)
在《中西哲學會通十四講》(民國79/1990年)中,他為哲學所立的定義是:
牟宗三論中國現代哲學界
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進行哲學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學地反思中國哲學的繼續,這步工作的完成,對中國哲學的哲學地反思才臻完善,這也是哲學地建立中國哲學的一步必要的工作。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發展到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已隨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國近代以來的哲學只能從民國開始講起。牟宗三把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的演變脈絡分為三個階段[1]: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1911~1937)為第一階段,從抗日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控制大陸(1937~1949)為第二階段,從“國民政府”遷臺后逐步走向現代化(1949~1985左右)為第三階段。他分別從中國大學哲學系與哲學家來省察這三階段的哲學。
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顧與評論了中國大學的哲學系。依他看來,自民國以來,中國的大學已設有哲學系,但比較完整的僅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的哲學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的哲學系,在南方則有武漢大學與中山大學的哲學系,但并不完整[2]。從前三者來看,北大哲學系的歷史最長。在第一階段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北大哲學系最熱門,大家都念哲學,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卻很少,多的是空話,不能入哲學之堂奧。新文化運動僅是一般性的思想啟蒙運動,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學家,譬如胡適就是一個典型,所以“五.四”運動在哲學方面沒有成就,沒有一個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腳[3]。清華哲學系在邏輯方面有金岳霖領導,有所表現。哲學上以實在論、經驗主義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憲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張申府先生講數理邏輯,后來去了清華;雖然出了個胡世華(與王浩同輩),但是與哲學脫了節;有張季真(名頤)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邏輯,而是比較重視古典哲學,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實在論。張季真先生留學英國,研究黑格爾,在北大講康德哲學,但他是否有黑格爾的頭腦,很有問題。康德哲學講是可以講,學是可以學,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張申府先生最崇拜羅素,對羅素生活的情調與思考問題的格調很熟悉,但是羅素本人的學問,張先生卻講不出來。所以,羅素那一套哲學沒有傳到中國來。(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羅素訪華,有“五大講演”的事。)胡適之先生宣傳杜威,可是對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還達不到那個程度。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來的著作他大概都無興趣,或甚至根本沒有讀過[5]。杜氏的學問相當扎實,自成一家之言,美國將來能不能出像杜威這樣的哲學家都有問題。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當年所宣傳的杜威,根本就沒有傳到中國來。實用主義成了望文生意的實用主義。(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訪華講演的事。)當代的羅素、杜威無法講,十八世紀的康德,就更難了,要講清楚都辦不到。所以北大對西方哲學無所成就,進不了西方哲學之門。以后變成專門講中國哲學。講中國哲學以熊十力先生為中心,加之湯用彤先生講佛教史。抗戰期間,北大遷到昆明,完全以湯用彤為中心。湯先生后來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湯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據,代表的是純粹學院的學術作風,對佛教的教義、理論沒有多大興趣,造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學,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學,不是哲學系的本分。因此,北大辦哲學系,歷史最久,師資最多,結果無所成。至于中央大學哲學系,更是亂糟糟,尚不及北大與清華的哲學系。總的來說,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6]此外,除了燕京哲學系出了個張東蓀先生,算是當時幾個念哲學念得不錯的人之一[7],其他大學的哲學系就更談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臺大的哲學系有方東美、陳康諸先生。陳康是亞里士多得專家,幾年后就去了美國,在臺大沒有影響。方先生年資最高,讀書最博,但在使臺大哲學系走上軌道的問題上,他盡了多少責任(──這與他個人性格有關,牟認為不便多說),則不無可疑。而臺大哲學系還是清華、北大的那一套老傳統,以西方哲學為主,但并沒有成就。[8]二戰以后,真正能把哲學當哲學讀而進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國外去,讀西方哲學不能入,對中國哲學(由于平素心存鄙視)無基礎,甚至連熏習也說不上。“對西方哲學無所得,對中國哲學無所知,這是二次大戰以后念哲學的風氣。”[9]
總之,民國以來的哲學界是以西方哲學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識中心”的邏輯思辯,接觸到了一些邏輯問題、科學問題、以及外在的思辯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并沒有注意生命的問題。特別是經過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文化生命所結晶成的那套實踐的學問,便真斬絕了,成了一無所有。”[10]所以,“中國的思想界大體是混亂浮淺而喪其本”。[11]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對民國以來中國的大學哲學系進行了初步的估價,──以清華、北大、中央、臺大為中心,而尤以對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學系的評述為詳,并由此而對中國哲學界發表了評論,他的評價甚低,這與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對北大、清華哲學系的評價適成鮮明對比。無疑,牟宗三對中國大學的哲學系不重視中國哲學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的評價,給人一種印象,他好象不贊成中國大學的哲學系以講西方哲學為主,甚至還會讓人造成他輕視西方哲學的錯覺。其實,他十分重視西方的哲學和邏輯,他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確地說過:“以西方哲學為主不算壞,要真能訓練出來,那很好”。[12]他認為西方哲學的訓練是必要的,非經過不可,對西方哲學的認識越深入,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就會越透辟,但是對西方哲學的訓練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讀讀邏輯學、哲學概論和哲學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對中國哲學界的反省、檢討、是與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估價聯系在一起的。應該說,他對中國大學的哲學系與哲學界的哲學反省是真誠的,嚴肅的,所站的位置極高,不乏深刻與獨到,常常切中問題的要害,發人深思,他講話一任天機,但他這項工作尚不夠深入、系統和嚴謹。然而,牟氏沒有否定民國以來,中國也出了幾個稱得上哲學家的人物。
相關期刊
精品范文
10哲學與科學的關系